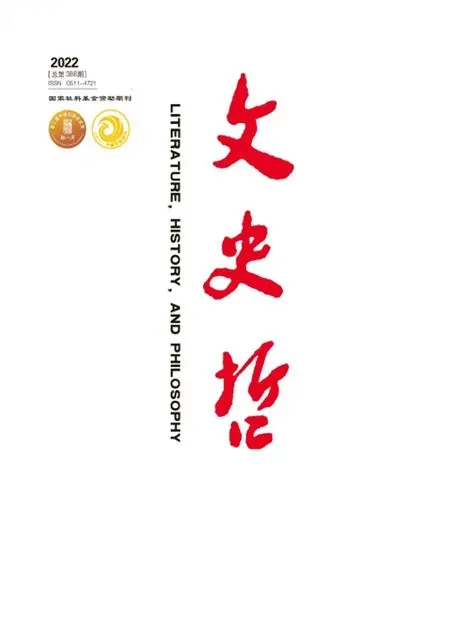一本逊清朝廷的政治斗争实录
——论《王忠悫公哀挽录》及相关问题
2022-11-08彭玉平
彭玉平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在男性辫发已经少见的年代,一个在外表上带着比较鲜明清朝形象的知名学者突然自沉,所引起的轰动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加上王国维曾任职晚清学部,民国后又出任逊清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其与清廷之间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定了其自沉不但是一个著名学者生命的简单消逝,而且带有更强烈的政治意味。
王国维去世后,追忆追思的文章,一时几乎遍及中日各大报刊。其情形如王国维之子王高明所云:“先忠悫公既完大节,海内外人士,识与不识,同深哀悼,并为文字以表彰之。”罗振玉也说:“海内外人士知与不知,莫不悼惜,公至是可谓不负所学矣。”“海内外人士亦莫不惜其学术,竞为文字以志哀挽。”“识与不识”“知与不知”之人的共同关注使此自沉事件迅速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除了国内京、津两地以及日本京都的公祭之外,一时名流如郑孝胥、杨钟羲、章钰、林葆恒、张尔田、罗振玉、金梁、梁启超、黄节等,王国维的部分亲友以及日本汉学家如内藤虎次郎、神田喜一郎、长尾甲、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木村得善等,也创作了众多祭文、挽联、挽诗、挽词等,以此构成了当时中日诸多报刊的刊载重点。而在五月十七日罗振玉假全浙会馆主持的公祭现场,“共收得哀挽诗联数百副”。但这些诗文散布各处,未免聚读为难。赵万里曾致信陈乃乾云:“此次开吊所收入之哀挽诗文,均在金息侯先生处,即当印成《哀挽录》。”则编纂《哀挽录》之念,或最初出自赵万里。后在罗振玉等人的统筹下,由王国维之子高明、贞明、纪明、慈明、登明同具名编次《哀挽录》,将一时能搜集到的哀挽文字汇为一书,在王国维去世两个月后,由天津罗氏贻安堂刊行。《哀挽录》主体分国内、海外与华侨三个部分,另有补遗、续补。国内部分为其中大端,计有文7篇、挽诗36人62首、挽联166副;《海外追悼录》次之,计有文3篇、挽诗5人9首;《华侨哀挽录》复次之,计有诔文2篇、挽诗2人4首、挽联2副。若干后续搜集到的挽诗、挽词、挽联、悼文,因无法再入正编,故分系于补遗、续补。一书既成,则一时追悼之情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一本名家群体悼一名家的著作,不仅对于研究王国维其人十分重要,也客观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其思想、情感和时代价值值得充分重视。但或许是由于当时印数偏少,流传不广,故检诸学术史,此书确实备受冷遇。即便其中一文一诗一联偶被拈出以论,但对其整体情况,却一直未见有全面考量者。重读斯书,这本看似单纯的纪念文集其实内蕴着当时种种政治势力的较量,在哀情涌动之余,也有激愤之意存焉。这与一般的哀挽录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就有关此书的若干重要问题,略述己见。
一、何以有溥仪诏书而无托名王国维之遗折
《哀挽录》封二完整地影印了王国维去世后溥仪下发的“诏书”,录文如下:
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着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醊,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
这篇诏书在诸多纪念文章中被引述时,多是片段的转引,难见整体之意,今特备录于此。检读这篇诏书,其大意无非如下几点:第一,高度评价了王国维的道德文章。所谓“学问博通,躬行廉谨”,前者言学,后者述德,说明溥仪对王国维的才德是充分肯定的。王国维入直南书房时,金梁也在宫中。他曾追忆说:“曩尝侍,闻上论曰:‘新旧论学,不免多偏,能会其通者,国维一人而已。’”溥仪对王国维才学有如此之评价,也可见其眼光之精准了。第二,强调了自己对王国维的提携之事。所谓“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说明了自己慧眼识才,故不拘定规,把王国维从一个诸生破格擢拔为南书房行走。关于这一点,王国维也感受得到,故自称“南斋之命,惶悚无地……此次之命,出于不次”。因为在清室遗民看来,有清三百年,由诸生身份而晋此位置的,也仅有朱彝尊与王国维二人。溥仪的擢拔虽然先有升允等人的荐举之力,但认同同样需要眼光。第三,突出了王国维的“贞臣”品格。谥忠悫之号,称其为“孤忠耿耿”的“贞臣”,这部分来自读“遗章”所感,更多的是溥仪对王国维生前的印象。所谓“依恋出于至诚”,即溥仪对王国维的基本印象。溥仪被冯玉祥部下逐出紫禁城,王国维即说自己“忧惶忙迫,殆无可语”,又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幸车驾已于前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待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王国维对溥仪的安危至为关切,这种关切,溥仪当然感受得到。王国维对清朝的感情与对溥仪的感情虽然不可简单等同,但毕竟两者是有关系的。而对王国维这种感情感受最强烈的人确实要算溥仪了。
大概基于对王国维学问人品的高度评价,也为了说明自己擢拔王国维是英明之举,溥仪在诏书中说王国维之至诚与孤忠“深恻朕怀”,故要以此诏来表达自己“悯惜贞臣之至意”。既然是“遽览遗章”后所下的诏书,则从一个侧面说明罗振玉代撰的这封遗章契合了溥仪平时对王国维的认知,所以当时不致生疑。对此,罗继祖解释道:“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这份遗折虽未留稿,内容可以估计到,一定是希望溥仪毋忘在莒,近贤远佞。在祖父认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又说:“静安无遗折,殆不欲为身后乞恩计,乡人乃为代作,窃比古人尸谏,冀幸一悟。”关于代撰这封遗折的目的,从罗振玉自身的角度来说,因为家事矛盾令他深感愧对王国维,长期无法释然,故希望以此弥补愧疚之情;从王国维的角度来说,罗振玉希望能藉此为其争取到更多哀荣。事实上,“其哀荣为二百余年所未有”,“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至公既受殊遇,世人莫不羡其哀荣”,所达到的效果也完全在罗振玉的预期之内。从溥仪的角度来说,罗振玉希望他能将王国维之死理解为“尸谏”,并因此认清形势,重新振作。罗振玉一生虽没有以公开的文字承认代作遗折之事,但私底下曾对其外孙刘蕙孙说过,因为王国维已死,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这封遗折的全文似乎一直未公开,而公开的文字如下:
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洲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此遗折藏于故宫,秦国经曾亲见溥仪当日留存之档案,因录于其《逊清皇室轶事》一书中。上面所引中间省略的部分是秦国经原文就省略的,一时尚未能补上。这省略的内容,据罗振玉之孙罗继祖的猜测,或主要是劝说溥仪离开天津,另觅安全之地。他说:“遗折中间省略一段当是劝溥仪速离津他去以避危就安,孤臣孽子之用心,愚忠可悯,史鱼、灵均,一身兼之。溥仪倘地下相逢,不知何言以对!”罗继祖的猜测可能有偶闻罗振玉之言的依据,应该还是合乎当时罗振玉的心态的。虽然罗振玉是护送溥仪从北京日使馆去天津寓居的功臣,但在张园初定后,溥仪的周围便很快为郑孝胥等一帮人所包围,几成铁桶阵,罗振玉、王国维则同属于被排挤的人。这种政治的较量,王国维生前就已经深刻感受到。1925年3月25日,在溥仪悄然到天津并安定后,王国维致信蒋汝藻即说:“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可见在逊清朝廷内部,这种政治排挤一直存在,令王国维深感失望。他决心离开这个充满争斗的小朝廷而就清华国学院导师之职,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而在1927年,王国维也深感溥仪处境之危险。金梁说:“近以世变日亟,公请行在预谋迁避,阻不为达。每语及,忧愤几于泣下。”
通过王国维的这些言论及其关系亲近之人的追忆,也可证明罗继祖的猜测大致不误。不仅罗振玉,王国维也是当时溥仪近臣所“阻”的对象。王国维请求溥仪“预谋迁避”,与罗继祖推测的罗振玉当时“避危就安”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其时罗振玉与王国维因子女家庭问题闹得很僵,彼此数月不通音问,即便偶然在张园相逢,也无一语相接,但以近三十年相交之经历,罗振玉多少还是知道王国维之心衷的。其借王国维之口劝说溥仪,表达的也是自己的意思,从表述政见的角度来说,可谓一举两得。罗继祖猜测的“避危就安”,并非凿空而想,而应当与遗折中“请奋乾断,去危即安”数语有关,而处理安危的潜台词就是“近贤远佞”,着眼点不仅在溥仪个人之安危,还在君臣关系之调整上。遗折中祈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之历史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云云,即希望诸臣之间勿为个人利益彼此挤压,因为无限制的内斗只能消磨激情与力量,而“一德同心,以拱宸极”才是当下最紧迫、最关键的事情。就公开部分的遗折内容而言,罗振玉将王国维“报国有心,回天无力”作为一篇之主旨:一出于因自身无能而带来的愧疚,一出于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愧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甲子之变,王国维虽侍左右,然“不能建一谋,画一策”,对突变之局束手无策,深感自己“可耻可丑”;其二是认为民国“赤化将成,神洲荒翳”,而一旦日后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他也觉得自己无力匡佐。既然过去不能谋一略,未来不能有所为,则唯有以己之一死,唤醒有力者的意志。这就是罗振玉虚拟的王国维自沉的价值所在。《哀挽录》中诸多诗文都以“尸谏”来定位王国维之自沉,其中未尝没有因罗振玉代撰的这篇遗折而引发溥仪下诏书的暗示作用在内。
以上的分析虽大体由遗折而来,但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王国维的思想。虽然罗振玉也曾说过“封奏予固不得见,然公之心事,予固可忆逆而知之也”,——“不得见”云云当然是假话,但罗继祖认为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心事“是明白的”,也应是事实。这封遗折毕竟是罗振玉的手笔,其中除了多少带有罗振玉一己之心思,还存在是否能更大程度契合王国维本心的问题。但溥仪因此称王国维为“贞臣”,并因其“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而谥“忠悫”之号,至少说明这篇遗折与溥仪此前对王国维的印象是合拍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罗振玉的代笔确实是成功的,因为它建立在罗振玉对溥仪和王国维双方深度了解的基础上,故至少加深了溥仪此前对王国维的印象。从为王国维赢得更多哀荣这一点上,罗振玉用尽了心力,而且用得相当到位。但疑问还是有的:罗振玉既然自认为了解王国维的“心事”,代拟代奏遗折,也很“心安理得”,何以在这本《哀挽录》中居然只附溥仪的诏书而不附这封遗折?此未尝不是其心有不安的一种表现。毕竟溥仪的诏书乃由“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一句而来,罗振玉自己也说过:“初六日疏入,天子览奏陨涕,诏曰……。”溥仪后来曾回忆诏书与遗折的关系说:“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明确说是看到遗折才知道王国维自沉之事。但《哀挽录》不附这篇遗折,相关的语境也就不完整了。
罗振玉一直以“殉清”“尸谏”定位王国维之死,这封托名王国维的遗折原本是最有力的证据。有此遗折——前提是遗折的真实性得到认同,则王国维自沉的原因自然可以合纷纭之说而为一,勿劳诸家再繁复论证或出以旁逸斜出之论,罗振玉本人也可以一篇“证据确凿”的遗折而趁势安然抽身。但事实是:罗振玉只想让溥仪一人看到这封遗折并因此给王国维以更大的哀荣,而无意于更大范围之传播。毕竟字体不是王国维的,措辞风格也当略别于王国维,若公之于众,作伪的痕迹便很容易被识出。所以在代拟代奏遗折时,罗振玉虽然心安理得,但在编辑《哀挽录》时,心思就未免有点复杂了。这大概是这本《哀挽录》全文收录诏书而无一字涉及遗折文本的原因所在了。
二、沈继贤与罗振玉:《哀挽录》序作者考辨
罗振玉主持此《哀挽录》的编撰,并以罗、王相交近三十年的经历,以常理言之,这篇《哀挽录》序的作者也非罗振玉莫属。但此序作者却署名“沈继贤”。序中说:“予与忠悫同乡贯,初不相知。甲子都门之变,始相见于京师,久乃知其平生于罗叔言参事……参事交公久,其言宜可信,乃纳交焉。及今年五月,公果以舍身徇义闻天下,参事畴昔之言,于是乎为有征矣。”按此所述,沈继贤是王国维的同乡,1924年冯玉祥派兵逼迫溥仪撤离紫禁城后方得以与王国维相识,继而通过罗振玉对王国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此序对王国维之死的理解也正应和了罗振玉此前数文对王国维的评价。从这一节文字来看,序言作者虽然署名沈继贤,但所持的基本立场则来自罗振玉。
其实,此文的作者正是罗振玉,只是托名沈继贤而已。《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0集之《贞松老人外集》卷一即收录《王忠悫公哀挽录序》,并注一“代”字,其页边注云:“此序代沈端臣太宁作。”“沈端臣”即沈继贤。《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主编乃罗振玉文孙罗继祖。罗继祖自幼随侍乃祖左右,深得宠爱,对乃祖相关论著的熟悉程度非他人可及。他不仅代罗福成等撰写过《先府君行述》,也辑述过《永丰乡人行年录》,对罗振玉生平也应是罗氏家族中最为稔熟者,故将《哀挽录》序收录集中并加注说明的做法当证据确凿,或为平时祖孙言谈而及,也不无可能。今检罗振玉晚年所著《集蓼编》,其与王国维的交往经历大率陈之其中。其中有云:“予伤忠悫虽致命,仍不能遂志,既醵金恤其孤嫠,复以一岁之力,订其遗著之未刊及属草未竟者,编为《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由公同学为集资印行。”这节文字写于王国维自沉五年之后,并未言及为编《哀挽录》之事,亦未提及序言代撰之情况。而《集蓼编》撰成之后,付长孙继祖书之,可见关于自己生平能书入此编者,已悉入此编,未便书入者,或言谈及之,也是很自然的。后来罗继祖编纂《永丰乡人行年录》,于罗振玉丁卯年(1927)相关行迹中与王国维相关者,记载如次:“五月三日,静安忧愤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本月及六月,乡人两次入都赴吊,并经纪其丧。作静安传二千余言,叙两人遇合及静安一生治学经历……七月十七日,静安既安窆清华园侧,乡人即着手为整理遗著……乡人与其弟子海宁赵斐云万里复就其家搜讨而整比之,订为四集,付博爱工厂陆续印行……仲冬,工垂竣,作《遗书》序,述静安遗事数则,又作《别传》,录静安《论中西政学异同疏》全文,以见其政论之一斑。”罗继祖的这一节文字,对1927年罗振玉在王国维去世之后的相关活动及活动时间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经纪丧事、撰静安之传、整比遗著、撰遗书序及别传皆一一罗列,为编纂《哀挽录》、撰序之事,未有一字涉及。而若《观堂集林》前所冠罗振玉之序,罗继祖也在年谱中直言:“其文实静安自撰而适如乡人所欲言者,乡人见为易数字。”盖此序在当时确有不便言说者。
撰文纪念与整理遗著是公开的事情,而此《哀挽录》涉及编纂主体问题,就当时情形而言,罗振玉其实并不是最佳人选。因为他年来与静安关系“疏阔”,是当时许多人知晓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自己凸显于《哀挽录》的最前列,确实有些不大合适。而《哀挽录》跋也是以王国维之子王高明等的名义来写的。录跋文如下:
先忠悫公既完大节,海内外人士,识与不识,同深哀悼,并为文字以表彰之。不孝等愚昧无状,不能显扬先德,幸藉椽笔以传不朽,此王氏子孙世世衔感,不仅不孝等感激已也。兹将诸家文字编为《哀挽录》,以志盛德。惟苫块余生,瞀乱失常,文字讹舛,刊落未尽,幸鉴恕之。丁卯七月晦,不孝高明、贞明、纪明、慈明、登明谨识。
再,南北阻兵,邮筒迟滞,异日远方有以文字见寄者,当为续录,以志嘉惠。高明等又记。
从跋文的语气来看,此《哀挽录》当由以王高明为代表的王国维之子编纂完成。但何以在王、罗两家尚在“疏阔”之时,让罗振玉来写这篇序言,确实其中还有一些令人难解之处。可以推测的情况是:王家及王门弟子当时尚无能力完成遗著、《哀挽录》等的出版,只能由罗振玉出面。毕竟此前两家多年的密切交往情况是王家熟知的,加上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积极经纪其丧,并在京津两地主持公祭,谅王家对其真情也感受得到。
再来回看《哀挽录》序的署名作者沈继贤。他似非当时知名人士,《哀挽录》曾收录其挽联云:“志士继三闾,还应披发叫阍,效睢阳誓为厉鬼;忠魂归故里,将见素车白马,随灵胥怒拥银潮。”上联用了张巡在睢阳(今河南商丘)之战中大战叛军,在城破之际,表达了生不能效劳陛下,死后也当化为厉鬼杀敌的决心。下联用了伍子胥死后化为涛神,随潮来往,涛激崩岸的传说。无论是张巡,还是伍子胥,他们都是以死效忠的典型。藉由他们,对联表达了激越的殉清主题,这也多少呼应了《哀挽录》序中的情感,但同时这种激越之情也直接面对着另外一个群体。
虽然沈继贤与王国维同乡是事实,沈继贤从罗振玉那里获悉更多关于王国维精神品格的介绍也应该是事实,而且在王国维死因上,沈继贤对罗振玉大力提倡的殉清说无条件地赞成,但这都改变不了序言乃罗振玉代作这个事实。而且另外一个基本事实是:按照序言所述,沈继贤结识王国维不足三年,关于王国维的行事,多听闻于罗振玉,其与王国维的实际交往并不多,则为一本名家云集而悼念王国维的《哀挽录》撰序,无疑是不够资格的。罗振玉之所以能托名于沈继贤,大概是由于两人关系的密切程度非他人可比。
三、回击“晚近士夫”与《哀挽录》序的“檄文”色彩
王国维去世后,面对种种关于其死因的猜测,尤其是其中有关于自己者,罗振玉虽然无法挺身自白,但以编纂《哀挽录》之机,借托他人之口,一吐郁闷之气却是可行的。这篇序原本应该是一篇深情涌动、哀感顽艳的文字,但现在读来却是情感激越,甚至带有义愤填膺的檄文色彩。这显然不是常规的哀挽录序言的写法。这种非常规的写法当然与不寻常的背景有关。
序言的开头便有来者不善的意味。试读以下文字:
天下有正义而后有是非,是非者,根于正义,公论之不容泯者也。晚近士夫,平日高谈忠义,其文章表襮,则杜陵之许身稷契也,屈子之芳菲恋君也。乃一旦临大节,则委蛇俯仰,巧说以自解于己所不能,而他人能之,虽内怍于中,而必竭力以肆其挤排。见有向义者,必为之说曰:“夫夫也,殆有他故,非徇义也。”甚则为匪语诬蔑之。士夫之行如此,乌在其为士夫也。
“肆其挤排”与“匪语诬蔑”八字,乃这一节文字的情绪基础和现实背景,而其矛头指向则在“晚近士夫”这个群体。打击面有点大,但也足见罗振玉当时孑立之情形。其实,他也是典型的晚近士夫,不过在这一语境中,他把自己与其他的士夫作了泾渭分明的区分,而区分的标准便是是否坚持根于正义的是非观。他把士大夫群体中的主流视为言行不一甚至语言张皇而流于猥琐者。类似的意思其实已先见于他的《海宁王忠悫公传》。此文末“论”部分特别提及升允对王国维的赏识、荐举及听闻王国维死讯后的悲痛之情,并专门引用了升允的一节话:“士夫不可不读书,然要在守经训耳,非词章记诵之谓也。尝见世号博雅者,每贵文贱行,临难巧辞以自免。今静安学博而守约,执德不回,此予所以重之也。”在引用这一节话后,罗振玉便以“呜呼!相国知人哉”煞尾,可见升允之说也即罗振玉之说。而升允对“贵文贱行,临难巧辞以自免”的讽刺与批评,与《哀挽录》序中“乃一旦临大节,则委蛇俯仰,巧说以自解于己所不能”,简直如出一辙。这也是此序乃罗振玉所作的一个间接证据。事实上,升允的“忠肝古谊”也曾得到王国维的高度评价。
序言中“殆有他故,非徇义也”一句,略见当时关于王国维死因论说的两大派别。罗振玉当然是坚持“徇义”的一派,而“殆有他故”的一派则包括了诸如罗振玉逼债、梁启超阴加排挤甚至中媾等说的提出者。居于“他故”最前列、影响范围最广的就是逼债说。此说的策划者为郑孝胥。郑、罗两人堪称宿敌,在溥仪移居天津张园后,为争夺溥仪宠臣的地位,两人各出其招。此乃溥仪周围的政治群体心知肚明的事情。王国维之死给了郑孝胥一个难得的机会。据说,他通过收买罗家的佣人而获悉了王国维的死因。之后,他不仅将此“机密”告知了溥仪,也告知了京津两地的士夫群体。而当时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罗振玉当然听闻了这一说法,当然也知道这背后主使的是郑孝胥。但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如何能光明正大地发声呢?所以他只有隐忍不言。而当《哀挽录》编竟,他把内心压抑数月的苦衷向沈继贤作了倾诉,赢得了沈继贤的同情与支持,但要把所受的委屈以罗振玉之名在序言里直接说出,时机也还是不够成熟的。为此,罗振玉借托对自己深度了解的沈继贤来署名,也就很自然了。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沈继贤的位置还相当边缘,但一个边缘人也正契合表达激愤之情的身份。正是在这一种周密的忖度中,一个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沈继贤出现在了一部名家云集的《哀挽录》之序作者的位置。
罗振玉敢于以如此锐利的语气回击“晚近士夫”,当然是有底气的。譬如现在已经考明,他完全没有逼债之事;江湖上传其《殷墟书契考释》乃用钱购买王国维之署名权,现在也已经被证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他在当时还不能直接发表意见,但换一个角度表达情绪还是可以的。所以在《哀挽录》序的最后,罗振玉既激愤又嘲讽地说:“公既完大节,海内外人士群相悼惜,竞为文字以志哀,虽间有口褒扬而中不尔者,然亦不得废公论而著其私也。昔太史公有言:‘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忠悫死矣,是非定矣。彼口忠义而恕己所不能,而嫉人之能或且肆毁者,不知其异日盖棺时,视忠悫何如也。”“公既完大节”五字也见于罗振玉《祭王忠悫公文》中,可略见其语言习惯。《哀挽录》以“文”著首,而冠以金梁的《王忠悫公殉节记》,这一安排应该有罗振玉的用心在内。而金梁在《哀挽录》一书编辑印行后,意犹未尽,另撰《〈王忠悫公哀挽录〉书后》一文,以两人“往还既密,知之尤深”的身份,继续褒扬王国维之节义,并建议在颐和园鱼藻轩前勒石曰“王忠悫公殉节处”,终因典守者不许而作罢。此在在可见王国维的节义在当时被认同的程度。在罗振玉看来,关于王国维的“是非”已经有了“公论”,也就是殉忠义而死。在这种公论面前,一些猥琐龌龊的言论其实也就失去了空间。其中“彼口忠义而恕己所不能,而嫉人之能或且肆毁者”二句,若孤立来看,或许只是泛泛地批评,但检《哀挽录》,此二句显然针对郑孝胥之论而起。挽诗部分序列其二者即郑孝胥之诗,其一曰:“河清难俟浊难止,留得昆明一湖水。能令湖水共千秋,节义何曾穷此士。”其二曰“泰山之重鸿毛轻,天下孰敢轻儒生。云中袒背受戈者,谁信由于有不能。”二诗都赞赏了王国维作为“儒生”的节义,在河清无望、浊流难止的现实背景中,称誉王国维之死有泰山之重。这里的“河清”指复辟清朝,而“浊”当是指民国的现状。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首末二句“云中袒背受戈者,谁信由于有不能”,“不能”二字是否能与罗振玉序中所言“彼口忠义而恕己所不能,而嫉人之能或且肆毁者”对应起来呢?此二句典出《左传·定公五年》:“王之在随也,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泄。闻王所在,而后从王。王使由于城麇,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辞。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对曰:‘固辞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盗于云中,余受其戈,其所犹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弗能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是郑孝胥化用这则典故的核心之句。在楚昭王的时代,子西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忠心耿耿,为世所称。在楚昭王入随国之后,子西为了凝聚楚人,沿路设立路标,并在脾泄(今湖北江陵附近)这个地方建立了临时国都。由于也是楚王重用的大臣,曾被派往麇地筑城,后来子西问由于所筑之城的高度与厚度,有多大的规模,由于居然无法回答。子西就不高兴了,并出言不逊,而由于也同样很生气,并由此引发出什么是自己能做到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到的,并特别强调被强求的事情做不好,也是很正常的。诗歌的语境往往隐约迷离,更何况还掺杂了典故在里面,所以要精准地解析郑孝胥此二句诗的意思,还是不容易的。但大致而言,郑孝胥从用典中透示出来的言外之意可能是王国维能以一死来报溥仪、殉清室,但你罗振玉却说自己尚不能身殉这样的托词,谁会相信呢?这一解释似乎离《左传》的意思有点远,但建立在“能与不能”基础上的两种态度,总还是清晰的。罗振玉回击郑孝胥,其实是回击郑孝胥及其身后的政治群体。罗振玉虽言辞激烈但指向隐约,也因为他当时尚身处溥仪政治集团的边缘。
四、关于罗振玉“犯三死而未死”的事实考量
如此来解读郑孝胥诗中的隐喻,确实也有罗振玉的相关言说作为背景。罗振玉曾在数篇文章中言及自己自民国以来的赴死之心,有的是与王国维同有此心,有的则是一己之念。他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即说:“十月值宫门之变,公援主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者再,皆不果。”这里字面上虽然讲的是王国维,但其实自沉神武门御河乃当时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三人的共同约定。此意对勘他文便自了然。罗振玉在《祭王忠悫公文》中更有一节“无法赴死”的陈述:
忆予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当乘舆仓卒出宫,予奉命充善后委员,忍耻就议席。议散,中怀愤激,欲自沉神武门御沟,已而念君在,不可死,归寓抚膺大恸,灵明骤失。公惊骇,亟延医士沈王桢诊视,言心气暴伤,或且绝,姑与强心及安神剂,若得睡,尚可治。乃服药得睡,因屏药不复御,而卒不死。后数日危益甚,乃中夜起,草遗嘱,封授叔炳兵部际彪,告以中为要件,俟异日得予书以授家人。寻乘舆家幸日本使馆,又得不死。两年以来,世变益亟,中怀纡结益甚,乃清理未了各事,拟将中怀所欲言者尽言而死。乃公竟先我死矣。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自是以后,但有谢绝人事,饰巾待尽而已。虽然,予所未死者,七尺之躯耳;若予心,则已先公死矣。……呜呼!予今与公生死殊矣,公能以须臾之倾维纲常于一线,至仁大勇,令我心折。而予自今春以来,衰病日加,医者谓右肺大衰,九泉相见,殆已匪遥。挥涕举觞,灵其来格。呜呼哀哉,尚飨!
罗振玉说自己三次要自杀,第一次考虑君王尚在,不能死;第二次考虑君王转危为安,不能死;第三次则由于王国维之死恩遇隆盛,为免被人误会“希冀恩泽”,所以还是不能死。虽三度欲死而未能,但此前既已心死,当下身体衰病,离死亡其实愈近了,不如顺其自然。不了解罗振玉的人可能会认为罗振玉未免为没有自杀寻找借口,但实际上罗振玉确有赴死之心。前两次未死因溥仪尚在且形势转安,很符合罗振玉通过溥仪复兴清朝的期待;而不愿随静安而去,以免有希冀恩遇之嫌,此在罗振玉的个性,也是很自然的。其中若第二次中夜起草遗书,今遗书俱在,涉及债务及遗产分配等,确实是在作赴死的准备。兹略引《甲子岁谕儿辈》如下:
自遭奇变,忍辱奔走,智穷力尽,有死无二。然圣躬一日无恙,臣子有一日之责,万一不幸,家事应部署。兹以夜深书此数纸,汝等一一当遵办。我年垂耳顺,自问平生不愧不怍,得正而毙,岂不贤于老死牖下,惟圣恩高厚,未酬百一耳。届时再示汝等以死所,此刻不能预言也。汝母处我尚有遗嘱,临时书之。甲子十月二十三日夜五鼓,松翁示成、葆、颐等知之。
溥仪被冯玉祥部下鹿钟麟逐出紫禁城之事发生在1924年农历十月九日,即所谓“甲子之变”。当日溥仪匆匆迁往北府,罗振玉在天津闻讯后,翌日即匆匆赶往北京,先见金梁,然后到位于后门织染局胡同的王国维家,“既见,忠悫乃为详言逼宫状,为之发指眦裂”。当日因鹿钟麟派兵把守北府,罗振玉未能见到溥仪,直到十月十一日晨,才与溥仪相见。罗振玉描述当日情形说:
是日初与鹿钟麟辈相见,先议定诸臣出入不得禁止,及御用衣物须携出两事。会议散,鹿等乃封坤宁宫后藏御宝室。愤甚,欲投御河自沉,寻念不可徒死,乃忍耻归寓,抚膺长恸,神明顿失。时已中夜,忠悫急延医士沈玉桢君诊视。言心气暴伤,为投安眠药,谓若得睡乃可治。及服药得稍睡,翌朝神明始复。盖不眠者逾旬矣。自是遂却药不复御,盖以速死为幸也。
以却药而待死,在罗振玉的记载中,也并非就此一次。其《集蓼编》述及迎溥仪至辽东后云:“冬春间遂病呃逆,先后兼旬,欲谢绝医药以待命尽,乃腊月廿八夕圣驾临视,勉慰周挚。予感激非常知遇,乃不敢复萌死志。”可见自辛亥之后罗振玉的生趣确实愈见其薄。罗振玉在撰毕《集蓼编》之后,联系自己一生因事因病,虽屡有赴死之心,但居然都安然无恙,也不禁赋诗云:“自分此身甘九死,天心特许保余年。”罗振玉只能将自己生命力的强盛归诸“天心”。前引罗振玉此三日间行程及身体变化大率如上,他对自己欲自沉御河而终忍耻以归之心态也描写得很细致。此后即是多日的失眠。十多日后,也就是十月二十三日夜,大概真是生趣殆尽,无意勉持余生,罗振玉遂起书遗嘱告儿辈。罗继祖描述如次:“廿三夜,乡人起作遗嘱谕诸儿,寄津升吉甫长嗣际叔炳(彪),语以俟闻变授家人。”罗振玉中夜起书遗嘱,不将遗嘱留给家人而寄给升允长子,盖当时虽有死志,但时间、地点一时未能定耳。同时也在寄送这一段时间中,可以从容考虑赴死事。若遗嘱在家,则或死事未竟而已为家人所知了。而寄送遗嘱与升允之子,亦是因为升允在复清之志上与罗振玉特契,与罗振玉、王国维私下交谊也特深,但若处理身后之事,还是不宜惊动老辈,故转寄升允之子际彪。这也是托付身后事的常例。
何以说罗振玉确有死志呢?细读这篇《甲子岁谕儿辈》,凡11则,类多了此一生、作别人世之语。先说家蓄之物若善本书、金石拓本、古器物、书画等估价约八九十万元,然后列出各项欠款等,接着分别就余款列出大致分配方案,告诫兄弟和睦、财产共存、同居一处等。而关于自己身后殡殓之事,则更是详加说明:“我身后殡殓,以五百圆为限,不得过先人,不出讣文,不邀人作谀墓之文并传状,即印我遗书赠至亲至友,出殡时,棺车前一铭旌足矣,不许妄费。”读上述文字,再质疑罗振玉之死志,余不知其可也。如果再将他为王国维伪撰奏折视为出于一己利益之考虑的行为,似乎就更过分了。而其中不请人撰墓志、传状这一想法也直接催生了其辛未年(1931)起撰《集蓼编》之念。他在《集蓼编》小序中即说:“且自叙语皆质实,较异日求他人作表状,以虚辞谀我,不差胜乎?”身后表状,无非勾勒生平、赞誉学行,但又有谁能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呢?看来罗振玉对此的理念是一贯的、执着的。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这篇《甲子岁谕儿辈》一文中,在安排身后各事时,所拜托诸人如章式之、王君九、万公雨、方药雨、陈贻重、金梁等之外,居然也有“王姻伯”(即王国维),可见罗振玉自杀之念原只是个人决定。虽然祭王国维文中提及溥仪被逼出宫后,曾与王国维、柯劭忞相约自杀,但真的欲了结尘缘的时候,还是不愿惊动他人。从这一点来说,当时的罗振玉确乎有自杀之念了。
不过,虽然罗振玉在祭文中说得很真诚,甚至悲情满纸,但在如郑孝胥等政敌看来,这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言而已。王国维既然可以袒背受戈,不惜一死,而罗振玉何以制造种种借口,苟全性命呢?故而郑孝胥悼念王国维之诗要特地加上“云中袒背受戈者,谁信由于有不能”这两句,借机表达对罗振玉“虚伪”的鄙视。罗振玉当然也读懂了郑孝胥这两句诗的隐义,所以在托名的《哀挽录》序中要从言行不一的角度来反击他。
五、王国维之“殉清”与“五十余年三杰士”
由于王国维的决然一跃而引发对士大夫群体批评与指责的,也不是只有罗振玉一人。杨钟羲与王国维同时赴南斋,彼此情义深厚,除了为王国维撰墓志铭之外,也有长篇挽诗略述其由王国维之死而引发的感慨。试引述若干诗句如下:“时平惟我贤,事至责人死。君不得之臣,父宁得之子。世乱非我召,屋社自谁使。肯以不訾身,殉彼混浊理。……一警同朝人,国破不知耻。障天凭一手,闻义充两耳。……茫茫天地间,戡乱定谁是。一举清君侧,再举立人纪。狐兔尽城社,夔龙奉祓玺。此时随大化,为乐岂倍蓰。”原诗甚长,但上面节录的文字体现的应该是此诗在哀挽之外的主题之一。而“一举清君侧,再举立人纪”云云,则比罗振玉在托名的《哀挽录》序中所说更为直接而强烈。因为这被“清”的君侧之人正是诸如“时平惟我贤,事至责人死”之类,在关键时候退缩一旁而把国家动乱的责任推给别人,不知羞耻、忘却礼义的猥琐士人。“狐兔尽城社”便是杨钟羲描述当时逊清政坛的一句形象之言。杨钟羲与罗振玉、王国维同为溥仪近臣,而其对郑孝胥的反感也与罗、王二人相似。所以杨钟羲的这首挽诗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感上堪称与罗振玉代序彼此呼应。可以说,这一本薄薄的《哀挽录》,固然呜咽满纸,而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其实也隐藏在其中。
与罗振玉在祭文、传记及托名的《哀挽录》序中一再强调的殉清之意相呼应,《哀挽录》中也有大量持同类观点者。如周善培挽诗“十六年望明湖水,终托清流恨有余”,曾学孔挽诗“家亡国破寻常事,十六年来恨未休”,陈寅恪挽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余累臣供一死”,等等。这些“十六年”“十七年”之说都将王国维之死与清朝灭亡直接联系起来,意思十分显豁。章梫的挽联则更为直接,他说:“辛亥一辱至于今,惟君求仁得仁,允合屈灵均祠祀;丁巳五月如昨日,痛我应死不死,愧为方正学乡人。”若无辛亥之事,王国维也许尚无赴死之心。相对来说,周学渊挽诗所述更为细致,堪称典型,其诗云:“深仁养士到辛亥,殉国大臣仅可指。君以秀才值南斋,扶危岂得振纲纪。今逢汉家阳九厄,死而得所君所喜。行朝相顾气亦壮,遗老为诗诔其美。侧闻天语痛微臣,曲予佳名见深旨。非恤一命葬蛟龙,正愧三公伴蛇豕。”周学渊不但在王国维殉国而死这一点上的态度十分坚定,而且对当时逊清朝廷的邪恶之气进行了讽刺与批评。“深仁养士到辛亥,殉国大臣仅可指”,“非恤一命葬蛟龙,正愧三公伴蛇豕”,其语言之犀利,应该也深契罗振玉之怀。
既然大体有这一集体认同,朱汝珍在挽诗中一方面说“遗书心事具,应勿费猜疑”,不必枉费心思,另作他想,另一方面又说王国维之死为“史鱼宁自恕,屈子有余悲”,“优恤彰奇节”,直接点出其殉节之意。孙雄挽诗小序亦云:“静安之死,但云‘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其词浑涵隐约,而其意弥可悲矣。世人不察,或谓其别有原因,实为处境所厄,如新名词所云‘经济压迫’者。又有援西人之说,诋自杀为无能力者,固属蚍蜉撼树之谭。”在孙雄看来,诸如“经济压迫”、无能力而自杀云云,皆是“世人不察”的耳食之言,不足与辩。而王国维自杀之“真际”则是身殉亡清而见其大节。其挽诗有“怀石灵均葬鱼腹,文山揽揆追芳躅”之句,孙雄在两句后分别自加注释云:“君于端午前数日始自沉,盖有追踪屈子之意。今年湖广同乡于五月五日公祭屈子。文文山生日为五月二日,君逝之前一日也。”把王国维之死与屈原、文天祥联系起来,揭示其追踪志节之意,则所谓“真际”的意思原本就是极为明确的。
胡嗣瑗在沪上与王国维初识于沈曾植之海日楼。他后来虽对罗振玉也有讥讽之言,但在当初写的挽诗中,也认为王国维之死乃“一心安止水,遑附所忠书”。虽然是结合他不知为罗振玉代撰的奏折而论,但其确认王国维乃殉清之意,也是昭昭在焉。其他若钱骏祥之“从此昆明湖畔水,年年重五吊灵均”,王树柟之“伤心一片昆明水,照见孤臣万古情”,邓之诚之“小臣忧再辱,一死报先皇”,等等,把王国维举身昆明湖比为屈原之自沉汨罗江,皆是中心忧悃而不能已,故以一死报国。
而章钰更以“赴水传忠壮,贤孙远嗣之”,“在昔争惟梦,而今谏以尸”等句表明观点;金梁挽联也有“读颐和园词,干净今唯此水;补忠壮公传,从容更过前贤”之句。从屈原、史鱼到王国维先祖忠壮公再到王国维,他们为之梳理出了一条忠诚殉国的历史和家族传统,这是一条历史的线索。
在历史线索之外,在《哀挽录》中,其实还存在着一条现实线索。对此,言之最为分明的是孙雄的挽诗小序。其序云:
吾因海宁王君静安之死而忆及皋兰吴柳堂前辈(可读)与桂林梁君巨川(济),是皆能不求生以害仁,而知所恶有甚于死之义者。夫吴、梁、王三君所处之时与地不同,而皆可以无死,然竟视死如归。彼与人家国、谋人军师、分宜握节死绥、致命遂志者反腼颜而偷生,甚或作桀犬之吠,卖主媚敌以求荣者,何可胜道!宜乎如郑人之以不狂为狂!多方吹毛以求死者之疵,昌黎所谓“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固如是也”。
文中提及的吴可读(1812-1879),字柳堂。因反对慈禧让光绪继同治之位,认为这种兄传弟的皇位继承方式不合父传子的祖制,吴柳堂便一再建言为同治过继一子以继位,但一直不被采纳。光绪五年(1879),在随同治奉安遵化后,吴柳堂居途中一庙,草就遗书而自杀身亡。慈禧无奈,遂以孤忠耿耿而褒奖其死谏。孙雄在挽诗“皋兰心逐虞渊皎,末命王言悲眇眇”二句后特加自注云:“穆宗宾天时,不以兄终弟及为然,持顾命大臣高阳相国之手而泣谓:‘必为朕立嗣!’高阳因两慈圣宗旨已定,不敢言也。柳堂前辈之以死谏,实为此而发。”显然是把吴柳堂的死谏作为忠臣的典范。梁济(1858-1918),字巨川,在清亡后,一度对民国持观望态度,终因失望渐至绝望,遂撰多篇遗书,并决然以身殉清,以唤起国人对“国性”的思考,在民国七年(1918)投北京积水潭而死。孙雄在挽诗“桂林类稿语苍凉,天理民彝一线亡”二句后自注云:“梁巨川自书《辛壬类稿》后云:‘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其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乃不惟无幸福可言,而且祸害日酷。观今日之形势,更虐于壬子年十倍,直将举历史上公正醇良仁义诚敬一切美德,悉付摧锄,使全国人心尽易为阴险狠戾,永永争欺残害,无有宁日,而民彝天理将无复存焉。是乌可默而无言耶?’”这是典型的以引代注,可以见出他对梁巨川之于民国社会根本判断的极度认同,而梁巨川自沉的价值也因此变得不言而喻了。吴柳堂自杀时,王国维才2岁;后39年,梁巨川殉清,时王国维41岁;梁巨川去世后9年,王国维自沉。如果说吴柳堂只是“尸谏”一种皇位传承方式的话,那么,将梁巨川与王国维在民国后的自沉视为对清朝的身殉,自然是当时很多人不期然而然思考的基本角度。梁巨川有长篇遗书在,可略见心衷;王国维遗书虽然言辞隐约,但借助罗振玉代撰的奏折,也自然合成殉清的主题。故孙雄在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得其所光青史。无生久已慨苕华,延秋门侧乌难止。怀忠追步梁与吴,马伸桥与净业湖。五十余年三杰士,始知报国有真儒。”“延秋门”原名章城门,又名雁雀门或燕雀门,原为西汉长安城建章宫与未央宫之间的一座城门,因城楼均用玉石垒成,又称璧门。东汉王莽篡汉,一度改为万秋门。唐代利用汉城北、西、南三面城墙作为禁苑城,禁苑西门改名延秋门。这首诗慨叹苕华之无生与乌鸦之难止,实际上隐喻着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马伸桥”即吴柳堂自缢处,“净业湖”即积水潭,乃梁巨川自沉之地。孙雄把吴柳堂、梁巨川与王国维看作“五十余年三杰士”,是报国真儒。可见,殉清说在很多人心目中确实是“应勿费猜疑”了。
几乎可以说,在《哀挽录》中,呼应罗振玉之说最为强烈和透彻的就是孙雄,这与孙雄同罗振玉、王国维的特殊交谊有关。孙雄说:“宣统初年,余与罗君叔言同任京师大学堂分科监督,屡往象来街叔言寓斋谭艺,与静安接晤,时共唱和。静安默默寡言,余与叔言、伯斧辨(辩)论时,静安微笑而已。”“文科大学弟一班学生毕业后,余因学风渐嚣,决意不入教育界,遂与静安久别。”自然,彼此的同官与交往经历容易令他们往往有用心特契之处。
编纂《哀挽录》,原本主要是通过汇集诸家哀挽文字,以一种群体的方式纪念一个生命的离去,所以合理定位、深情追忆、哀情满纸应该是主要的书写维度。1923年,张勋去世后,溥仪下诏谥号“忠武”,逊清遗老也编了一本《哀挽录》,略述心衷。罗振玉曾谈及他的读后感云:
连日读忠武哀挽集,不成文理者甚多,然有唐蟒八字联,推许甚至。又有章士钊一联,其上联云:“民国竟何如,世论渐移公已逝”云云,则可觇人心之向背也。至某傅联果不成话,上联云“矫俗矢孤行,为国忘身,一节愚忠堪不朽。”此犹可言也(然公则并此一节愚忠而无之),下联云:“堙洪翻横决,连兵穷岁,九原遗恨讵能瞑”,则以连年兵祸,全归狱于堙洪,则虽革命党亦无此言,不知此老果何心也。
虽然罗振玉从张勋《哀挽录》中读出了诸多不成文理或用意突兀处,但该哀挽录的基调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诸种《哀挽录》中,像《王忠悫公哀挽录》这样比较特殊、相当另类的现象还是不多见的。打开这本《哀挽录》,开卷可见的除了悲音悲情,居然还夹杂着不少隐喻的机锋与激愤的情绪。如此将当时政治生态以及由此生发的哀怨之情深度带入书中,应该是非常罕见的。这当然与王国维身处易代之际,是深具国际知名度的一代学者的仪型有关,也与他和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因为是行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学者,故因敬仰而惋惜其学术者有之;因为曾是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又得溥仪下诏并谥“忠悫”一号,在逊清朝廷和遗民圈中引发的政治议论也空前增加,而这种议论背后实际上也带有借此机会调整溥仪身边政治氛围的目的在内,即强势者要巩固强势,弱势者希望扭转弱势。这种明争暗斗体现在这本《哀挽录》中,也就构成了此书错综复杂的情感特征。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当然是不可替代的,王国维的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色彩恐怕也同样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