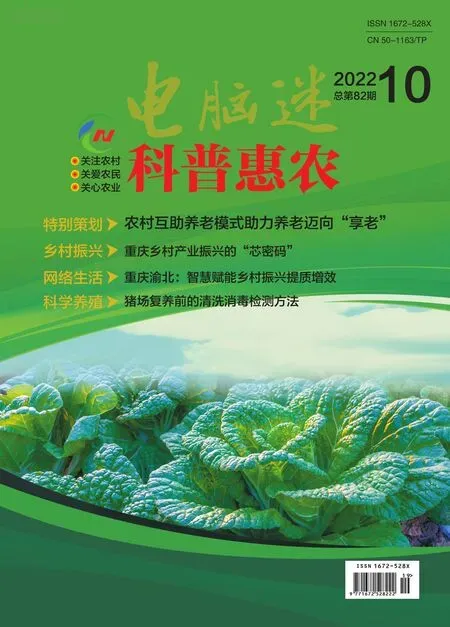垂钓
2022-11-08本刊通讯员卢伟
本刊通讯员 卢伟
老家有条小溪流名曰“天河”,村子也因它而得名“天河村”。它不仅是滋养我们的“母亲河”,更是我们不离不弃的好玩伴。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依然是暑假到来,在夏日午后,来到她身旁,和小伙伴们一起钓鱼的日子。
我读小学的时候,所有的钓具都是就地取材,钓竿是精选直挺的斑竹,鱼线是普通的缝纫线,浮漂是鹅毛剪成的一段一段的小颗粒,坠石是剪成细条裹成花生米大小的牙膏皮。而鱼钩,则是用绣花针烧红用钳子卷成的,这样的鱼钩没有倒钩,不易伤鱼,但也对钓者的技术要求很高,鱼一旦上钩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到了高中,河边才陆续出现了专业的钓具。
钓鱼的最佳时刻,是夏日傍晚的雷雨后。雷雨前,艳阳高照,虽有竹林庇护,但终归炎热,且由于下雨前气压高,鱼儿都浮出水面吸氧,不来吃食。而雷雨过后,天气变得凉爽,气压降低,鱼儿重回河底,凉风轻抚着竹林和水面,伙伴们便陆陆续续来到河边,或坐或站,举竿抛线,开始为晚餐准备食材。
天河里大多是成人中指长短的鲫鱼和“参子鱼”,若遇下大雨,就有可能将山上水库及河两边鱼塘、水田的鱼冲入河中,这时就有可能钓到两三斤的草鱼、鲤鱼。那些年,谁能在天河里钓到大鱼,谁就会成为全村伙伴们心中的英雄,且在他钓到大鱼的地方,全村的小伙伴第二天都会蜂拥而至。我哥就曾钓到一条三斤左右的草鱼,讲起钓起大鱼的经过,俨然是在开报告会。
如果技术不好,钓到的鱼很少,加之鱼又小,我们便将鱼倒进一个桶里,一起到某个小伙伴家里煎来吃。那时,我们家家都杀年猪,并将猪油切成一坨一坨的放进瓦罐里,炒菜时便从瓦罐中舀一坨出来,放在热锅里熔化,将油渣扔进潲水桶喂猪。估计这也是如今我一看到油渣莲白就想到猪食的原因吧。
那时,我们对鱼的烹饪方法很简单。大家先一起杀鱼,由于鱼小,只需在颈部划一条口挤出内脏即可,所以通常都将杀鱼称作“挤鱼”。然后,我们便在一边玩游戏坐享其成。小伙伴的父母则将几坨猪油熔化,再把鱼下锅加入盐巴煎至金黄,起锅即可食用,他们也总会赠送凉拌黄瓜、炝炒空心菜等菜品。当然,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宽裕,油一般吃到下半年就捉襟见肘了,煎鱼得轮流坐庄才行,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夏季,似乎每天下午都有雷雨,我们也总在雨前抢收晒在地坝的粮食,雨后到河边钓鱼。如今,天河发源地的樵坪山上没了水库,儿时的小伙伴也大多进了城,几乎没人继承父母的耕种之业,导致村里几乎没了“冬水田”,天河就少了鱼苗的来源。如今,我已是多年不在天河钓鱼,一来工作忙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想多留点时间陪陪父母,二来现在的天河鱼很少,可能蹲守半天也毫无收获。但回到老家一看到天河,就会想起那些年那些个垂钓天河的宁静的夏天。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