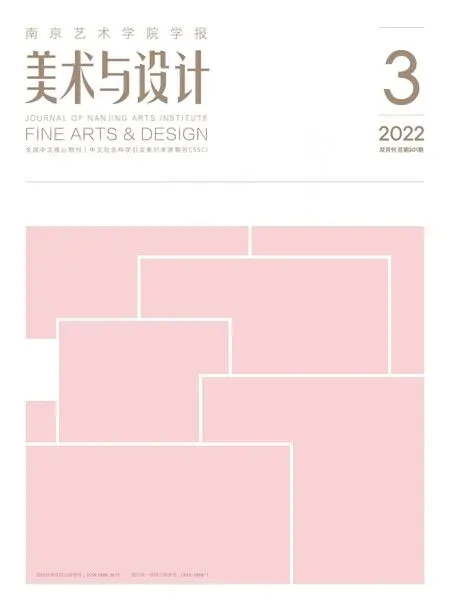“孔颜之乐”与北宋书法美学刍议①
2022-11-07李嘉文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李嘉文(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世人皆知“颜柳”正书为二绝,却常常忽视二公除书艺俱佳外,亦是后世推崇的儒家士大夫典范。颜鲁公平乱安史,重振朝纪,晚年为叛军所挟,不屈遇害,得后世“忠烈”美誉。其字“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后学尊其字其人“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柳诚悬曾“笔谏”唐穆宗:“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以书喻政被后人尊为书教典范。二公都将儒家伦理渗透入书法创作与学习中,且身体力行,终被后世士人奉为修身楷模。明人项穆受益于其父项元汴家藏丰盛,对书法感悟颇深,其所撰《书法雅言》是将书学与儒学审美艺术观相融合,并以此构建出较前人更为深刻的书法美学体系。虽然后学认为其中过分护卫“心学”道统之论略有不妥,但是项氏在程颐“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的论点之上将书学与儒家“诚意”“致知”“中和”的道德践履工夫关联,提出“正心”说, 确是道明自北宋儒学复兴,书学亦能复兴之根源。儒家文化与书风演变自古便是密不可分的,汉之儒学与八分,晋之玄学与行草,唐之经学与楷法,宋之理学与尚意,无不证实儒家的变化与书风的更迭是并行不悖的。“孔颜之乐”作为儒家理想人格自孔子提出,一直被后世传承,虽历经唐末五代破坏,但宋儒为维护和发展儒家道统,再次将儒家这一最高道德标准延续并重构,书法受之浸染亦在唐法基础之上得以发展。
一、溯源与推崇
《吕氏春秋·慎人篇》中有言:“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古之通晓事理的君子,皆能从生活中汲取快乐,无论顺境抑或逆境,如同四季的更替,风雨的交替一般。这种超越世俗的心理感受,一般后儒都会把它归为“孔颜之乐”,即“安贫乐道”的理想道德境界。这种审美人格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一直秉持的理想与典范,但是历经中唐、五代之乱,这种理想人格的信仰逐渐动摇,面对信仰危机以及国家重拾以儒立国的优渥条件下,宋代士人对这一乐观精神进行重建,并将“孔、颜乐处”上升为哲学命题,逐步完善和推广。
宋初柳开、王禹偁等先贤虽已维护儒家道统,但其主要成就尚停留在对西昆诗派“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的批判,并提出“词丽而不冶,气直而不讦,意远而不泥”的主张。虽有“慨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力追古格,一变偶俪之习”的雄心壮志,奈何在实践领域仅停留于文论之中,并未涉及过多理想人格的构建。最早真正将“孔颜之乐”人格意义与社会价值相关联,并提供新的解释的是欧阳修。欧阳修在其晚年所编《居士集》中开篇即是《颜跖》一文中谈道:
欧阳修用其犀利的笔锋直指世人皆感叹颜回困滞的一生,甚至如愚夫一般怨天尤人,却未能看见其身后万世的光辉。欧阳修只是以后世之荣辱去劝慰世人、震慑世人,并未提出真正有效的现实意义,显然多有牵强。作为早期重建“孔颜之乐”审美人格信仰的士人之一,司马光也曾作《颜乐亭颂》极力推崇这一儒家士大夫应当遵从的基本价值取向,批评韩愈“其汲汲于富贵”“如市贾然”,并歌颂颜回“贫而无怨难”,指出其“在陋巷,饮一瓢,食一箪,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的理想人格当为后世之典范。但是欧阳修、司马光二公只是推重“颜乐”,并未在此基础之上将这种精神与现实相融合,所以还只是停留于泛泛的理论层面。这与宋初书法的取法以及形式的表现十分相似。
宋初受制于五代战乱,士人尚处水深火热,无暇顾及书艺,宋高宗在《翰墨志》中曾言:“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加之国祸兵灾,作为最大且最为安全的收藏机构——王公内府,亦不能将历代名迹善存。宋初书学之步履维艰可探一二,也无怪乎五代尚有杨凝式这样鹤立鸡群的书家,宋人皆觉诧异。据蔡絛、朱长文、米芾等书论所述,太祖、太宗略善书艺,也诸体皆能。降臣之中,亦有南唐徐铉,后蜀王著、李建中等善书,但由于他们或取法狭隘,或格调病韵,终归只是延续书学脉络,而未启一代之宗。正如宋初儒家“孔颜之乐”理想人格的构建,书学虽有复兴之势,却无复兴之实。
欧阳修作为儒家复兴的代表人物,也是北宋最早呼吁复兴日益式微的书学领域的士人,他曾感慨:“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欧阳修之前,宋人在书艺领域多是置若罔闻,诸多儒生虽文章学问甚佳,但书迹潦草,稚拙难堪,显然是有悖儒学传统六艺。欧阳修《集古录》中也多次提及书学之衰,并倡议士人不可忽视。在儒家理想人格上,欧阳修推重“孔颜之乐”,书学的复兴则树立起以颜真卿为核心的取法格调,其不仅在《集古录》中发掘和整理了大量颜真卿的书法遗迹,并题写跋语大力推崇,更是在修撰《新唐书》时,刻意塑造出颜鲁公“忠义”之态:“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后皆有功。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与此同时,欧阳修更是将书法运用于伦理的教化之中,在《跋颜鲁公二十二字帖》时称:“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在《跋颜真卿麻姑坛记》又云:“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画。”以颜真卿忠义气节的儒家典范来推崇具有儒家韵味、端庄雄厚的书学体系,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与此同时,欧阳修还提出“学书为乐”的观点,这在《试笔》一书中多有体现,但是他在书法的实践领域却如其构建“孔颜之乐”理想人格一致,未能跳出藩篱,其也毫不掩饰其所欠缺,自嘲“余以集录古文,阅书既多,故虽不能书,而稍识字法”。其“喜论古今书”而不善书的自评基本也为后世认同。
北宋时期,儒家理想人格的重构和书学的复兴几乎是相伴相生的,即如同早期“孔颜之乐”的理想人格,诸公推崇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中,书学虽有起色,却尚不具备成为儒家美学意蕴典范的条件。蔡襄虽已初具风范,甚至曾得宋徽宗赞曰:“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但细品其书,多为颜、虞二体杂糅,只是“方入格律”而已。苏舜元、苏舜钦所善多为狂草,文彦博书似晋人,多散漫风棱,与儒家深厚、宏阔书法美学意蕴相悖。韩琦之书,尽得鲁公之法,后世多以“端庄谨重”“雍容和豫”誉之;司马光则多以篆隶笔意入楷,“端严古茂”如其学术思想一般一丝不苟。但二公之书,掺杂古意多于实践创造,略有食古不化之疑。北宋立国至中期,儒家士人虽不断努力以“孔颜之乐”理想人格的构建作为核心,以期重建儒家和谐秩序,书学受益于此,亦有精进,但受限于多将焦点集中于理论层面,未能真实有效融入现实生活中。
二、中兴与矛盾
作为欧阳修的门生,二苏也曾就孔、颜这一审美人格提出其独到见解。苏轼在《三槐堂铭》中,根据欧阳修《颜跖》对于颜回和盗跖的善与恶、荣与辱、寿与夭的反差归咎于“此皆天之未定者”。苏辙在《寄题孔氏颜乐亭》一文中则进一步以天命之说来推崇“孔颜之乐”:
在二苏看来,“孔颜之乐”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当精神修养达到一定程度,不必刻意去追求理想的人格,也无需刻意去冲淡生活的不幸。“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在“乌台诗案”后,面对命运的转折,苏轼依旧能够乐观处世,或许正是“孔颜之乐”感染下的结果。贬谪之路上,无论是开荒播种,取号“东坡”;抑或是徜徉山水,而悟出的“君子如水,因物赋形”的人格理想。其实都是苏轼将“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人格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苏辙在《答黄庭坚书》中对黄庭坚的赞许正是引用了“孔颜之乐”的理性人格。曾巩在《南轩记》中所提出的儒家士大夫应具备的理想人格,虽未直接提及“孔颜之乐”,但其本质是异曲同工的。“所要挟道德,不愧丘与回”,曾巩对欧阳修身处逆境而悠闲自若的称赞,其实也是对自身人格理想构建的要求。
苏轼论书与其论文“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类同,世人也皆以其“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是为宋人尚“意”书风的开端。苏轼论及其文、其书常将之与自然相关联,这与其所论“孔颜之乐”理想人格的构建相辅相成:“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黄庭坚评其书亦与其文相关联:“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葱葱,散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他对书法的理解与欧阳修、司马光迥然不同:“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焉能过此?从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会作字也。”对于他们刻板机械的学古而无创新显然更有清晰地认识。苏轼早年学魏晋钟王书风,晚年则多用功于颜真卿,但是面对宋初诸儒学颜书终究“难复措手”和“极书之变”的窘境,他提出了“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的观点,用辩证的角度去学书,不必刻意“举体皆似”,即“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论断,这与其对于“孔颜之乐”理想人格的构建理念如出一辙。
在实践领域,苏轼虽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但其所书却不见“快也”的自然之态。李之仪曾描写苏轼的书写状态,述其“喜浓墨、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谛思乃在其间也”,可见苏轼所书并不如其书论所述一般信笔而为,自然而成,这与其对“孔颜之乐”人格构建的理想状态与其实际所处环境下的窘迫略为相似。虽处处标榜无羁无绊,快意无畏,但心中似有丘壑未能跨越,或是政治领域的缺憾,抑或是跌宕起伏的人生,终归未完全了然于胸。苏辙、曾巩书法,名气稍逊苏轼,书风特征基本也受欧、韩二公影响,多以颜书为宗,虽不乏创新,却也未能打破桎梏。黄庭坚、米芾确有突破,奈何二公不可以传统儒家士人评判,且二公于“孔颜之乐”理想人格构建层面也鲜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议。
王安石因“熙宁变法”而名声大噪,但也因此承受诸多曲解。虽有好事者冠其“外儒内法”的称号,但他在完善士大夫理想人格方面确是儒家绝对的代言人,其引经据典,从多方面阐述并证实了“孔颜之乐”是儒家士大夫不可背离的最佳理想人格。他在《命解》中指出:
在王安石看来,孔孟之所以可以历经千年,而依旧为后世所称颂,正是因为他们“不以弱而离道,不以贱而失礼”的审美人格价值所致。在《对难》一文中,他更是将以“孔颜之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上升为“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的终极高度。在《推命对》《夫子贤于尧舜》 《礼乐论》 《大人论》 等诸文中,他又对“孔颜之乐”进行分析和阐释,并大力倡导士大夫须以此完善理想人格,从而实现矫时救世。王安石较之二苏、曾巩,则更进一步认识到了重建“孔颜之乐”理想人格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重建途径,为后来理论解释的完成和审美的人格的最终建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王安石书法墨迹存世较为稀缺,后世评议也多呈两极分化,赞者多以其书“飘逸纵横、略无凝滞”称颂,且以“不着绳尺,而有魏、晋间风气”的高古神韵而啧啧称奇。贬者多掺杂政治因素,指其所书如其学为“无法之法”“不甚端遒”,并责其书写习惯如其变法一般“躁率任意”“躁扰急迫”。仅从王安石存世墨迹来看,论者所述皆不无道理,只是角度不同而产生了偏颇而已。王安石书法确实有超脱时人的创新,这种创新也不是完全脱离前人法度下的创造,而是一种返璞归真下的自然流露,与其所释“孔颜之乐”实现途径几无差别。党争时势和学派争鸣下,书论诸多评议不可全信,加之存世之作已不多见,在论及北宋书风多不提及王安石,但从取法王安石而受益的书家成就来看,有如其建立“孔颜之乐”理想人格的信念未被重视一般,是为缺憾。
三、重构与完善
“孔颜之乐”这一理想人格真正被后学所重视,源起于自周敦颐起,后经二程发扬,并被理学家纳入理学体系,奉为圭臬。周敦颐尝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他将伊尹只是作为一种理想,一种志向,但是付诸行动的“学”这一阶段当以颜回为宗。二程受学于他时,也曾反复强调“孔颜之乐”是周敦颐理想人格的追求。在理学家的探索中,“孔颜之乐”的理想人格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后经朱熹、张栻、真德秀等诸家的推崇,使得“孔颜之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的理想和哲学的命题,它更多地融入士人具体的生活方式中,并且是符合情理的审美方式,即便是与程朱在学术领域存在异同的叶适、陈亮、陆九渊等,也未尝否定这一理想人格的塑造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从欧阳修、司马光对其推崇,到二苏、王安石将之上升为“道”的高度,二程等理学家则更多得将“孔颜之乐”具象,使之有了现实意义。“箪瓢陋巷”涵咏的是“贫贱不能移”,但是士人如果都以此为理想,仅仅独善其身,是不符合重建儒家审美人格的现实意义的。“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算瓢陋巷何足乐?盖别有所乐以胜之耳。”“颜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二程在论及颜子之乐,一直强调其所乐并非是“箪瓢陋巷”下以“贫”为乐,而应当是“浑然与物同体”下,实现“万物皆备于我”,并完善以“仁”为核心的审美人格,实现“理与己一”的大乐境界,才是真正的“大乐”。朱熹在释孔子“贤哉,回也”时便引用了程颐所论“孔颜之乐”,并批注“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朱熹在此虽然“不敢妄为之说”,但是在其后他还是阐释“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此与贫窭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乐”。显然朱熹是认同二程对“孔颜之乐”更深层次的理解,即构建儒家士大夫审美人格并非仅仅适用于贫寒逆境,也非仅仅对待个人命运态度本身,并局限于社会伦理范围之中,而是将之上升到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的“天人之际”,这样才能得到“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的真乐。
“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正是这种与“万物为一”下的“自优游”,方能去除“李白愁”而得“颜回乐”。正如南宋真德秀所释:“所乐者道之言岂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盖道只是当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娱悦也。若云所乐者道,则吾身与道各为一物,未到混融无间之地,岂足以语圣贤之乐哉?”只有将“此身此心皆与理为一,从容游泳于天理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孔颜之乐”的审美境界。至此后学论“乐”都将之融入完整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之中,自觉地要求士人当在审美愉悦中去实现理想人格的构建和对宇宙观、审美观、价值观的把握,终而理解“惟颜子知自备天地万物之道,其陋巷饮水,如寄泊焉”才是“乐”之真谛。
理学家的精力多用于为往生继绝学,相较于阐发圣贤之学,书法领域的关注则鲜有深究。周敦颐、邵雍、二程诸公书法今之存世罕见,且多有疑议,仅从后人书论可窥探一二,多数与所论苏轼书法认知与实践的二重性一般,如朱熹论邵雍“自言大笔快意,而其书迹谨严如此,岂所谓从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大抵北宋书风后世谓之尚意,实则是在唐法基础之上的变革,但真正做到如理学家所述“孔颜之乐”复归自然,与万物消融为一体的理想精神状态,似乎尚有距离。即便是被誉为南宋“中兴四家”的朱熹,虽在书法理论与实践皆有建树,并尝试复归自然,但从其存世墨迹的多面性来看,多数亦未脱去束缚,多是崇古因循状态下的刻意为之。
理学家构建的“孔颜之乐”理想人格体系,真正达到“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的“以自然为宗”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明代中后期,也正是由于这一儒家理想信念完整体系的构建,儒家在历经磨难下依旧能烈火重生,并使士人不再受限于庙堂之争,在现实生活中将纯粹的“乐”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自然融合,“从心所欲”又“不踰矩”,终而领悟“孔颜之乐”的真正内涵。纵观“孔颜之乐”的发展过程,宋代、明初更侧重于道德理性,明中后期着重于生活感性,前者更注重道德和理性,给人的往往是崇高感;后者更注重自然和自适,让人感觉到生活的轻松和愉悦。自宋廷南渡,高宗将“国事失图”追溯至“熙宁变法”之祸,北宋理学家所倡议的“孔颜之乐”复归自然又因高宗保守复古的思想而停滞,书法领域也因其力主归宗魏晋二王,未得充分发展。至元代初期,赵孟 书风得元廷赏识,风靡朝野,其“当则古,无徒取法于今人也”的崇古书法观直接将理学家极力构建的“孔颜之乐”复归个性情趣的价值观直接否定,虽不乏后人评其“矫宋之弊”,但对比之下,应是与两宋诸家一般未能挣脱古人束缚,这从明初被后人诟病的台阁体书风的风靡足见端倪。元人郑枃以程朱理学论书,著有《衍极》一书,但书中表现的却是理学化的复古主义书法美学,甚至否定了欧阳修、苏轼等“学书为乐”美学精神,受此影响,直至明代中期,书坛皆笼罩于崇古拟议之风下。
明代中期,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儒家士人进入“天崩地解”的时代,在“程、朱之学几于不振”之时,王阳明“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心学实则是理学的传承和发展,在论及“孔颜之乐”,王阳明指出:“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乐”其实是“心”的本体,只有进入自然状态,才能真正领会“乐”的内涵。泰州学派的王艮也同样认同这种观点:“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并指出“无边快乐”是“不费些子气力”的。这一阶段的儒家士人不仅在理论上完成对“孔颜之乐”的理想人格的构建,在实际生活中亦一以贯之,书学领域亦一改自宋以降过分崇古的陈规陋习,以徐渭、张瑞图、倪元璐、王铎、傅山等诸家领衔的书坛,呈现出各种个性强烈的面貌,这种面貌并非杂乱而无法度地随意挥洒,是兼具古典美学和现代精神的自然流露,是儒家“孔颜之乐”理想人格下的完美演绎。书法只有在自由的心灵中发展,才能将优美演绎至极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性情为本。”这种性情是沉着痛快的“乐”跃然纸上,兼之“理”与“乐”,便可“临大节而不夺也”。人生本体即是一乐,即如孔门之游于艺,得人性一大自由,亦即人生一大快乐,乃为人生一大道义,所以“孔颜之乐”是中国艺术人生的最高境界。书法只有将这种“从心所欲不踰矩”下的“乐”作为书法文化的本位继承和发展,才能将书法的美学精神成为现实。
结语
阿恩海姆曾将其对西方书法的理解阐述为:“书法一般被看作是心理力的活的图解”。虽然此论是由笔迹学引申,但不置可否的是书写艺术是由“心”而发的。字里行间只有臻至偃仰顾盼,阴阳起伏,如树木之枝叶扶疏,而彼此相让。如流水之沦漪杂见,而先后相承的随性奔放,才能谓之为书法艺术,这点与“孔颜之乐”的真实精神内涵实则是殊途同归的。北宋自儒学复兴,士人皆追求外在事功,至“三冗”积弊,改革失败以及军事落败,士人立场转向更为温和的现实主义,这种结果最终导致社会基本价值判断的转向。“孔颜之乐”作为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由守道之乐的精神体验转向学道之乐的现实认知,并最终实现体道之乐的自我解放。这种过程也直接影响北宋书风的演进,书风的演进其实是士人心态的直观反映,李春青根据文化价值取向的异同将宋代士人阶层分为三派:力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经术派、弘扬儒家心性之学的道学派,积极入世和追求心灵自由兼顾的文章派。三派所追求的侧重点不同,自然造成士人心态的诸多差异,在搦笔濡墨间皆化为线条流于笔端。自宋初经术派的代表柳开、王禹偁弘扬儒学精神首开政事教化之道,至文章派欧阳修“寓意乐心”的书法美学观和苏轼鼓吹“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踰此者”的尚“意”美学观,最终受道学派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影响下,明代中期崇尚天性与自然的书法美学观,可以看到书法在儒学的浸染下,逐渐摆脱束缚,不为外物所左右。“孔颜之乐”的深沉内涵实则就是艺术精神的最终展现,并以此区分艺术与劳动的差别:前者只是游戏,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书法显然是不同于普通的工艺劳动,而是具有能够展示天性,体现高尚的娱乐功能,并能获得自我享受和自我愉悦的艺术,才能真正书写出具有艺术精神的传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