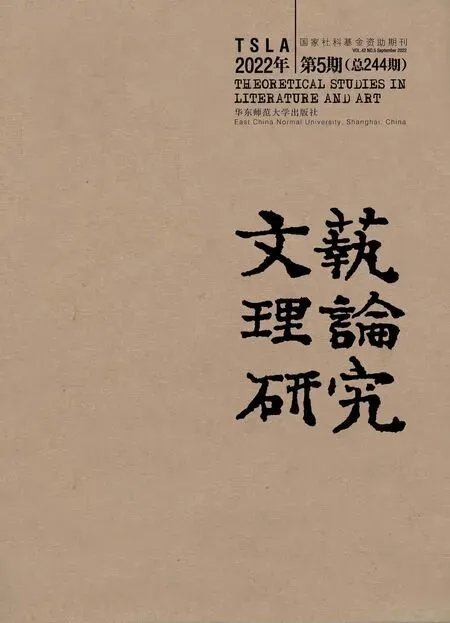文学伦理的两张面孔:玛莎·努斯鲍姆的文学观及其内在紧张
2022-11-05范昀
范 昀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影响力广泛而深远。其研究兴趣广泛,成果丰厚,其思考与写作穿梭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是当代难得一见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学者。尽管如此,在努斯鲍姆庞杂而多元的写作主题之间依然存在着共性,那就是她对文学叙事/想象的倚重。在她的任何一篇论文中,人们都不难发现文学的案例;在她任何一段文字表达中,也不乏充满温情的诗性叙事。“通过文学的技术来描述活着的经验的每个细致之处,玛莎改变了哲学的面貌。”(Aviv 36)哲学家南希·谢尔曼(Nancy Sherman)的这句评价可谓切中肯綮。努斯鲍姆在哲学上的卓越建树及其社会影响力,跟她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文学实践智慧的尊重与吸收有着密切的关联。
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理当对这样一位富于诗性的哲学家给予重视。尽管努斯鲍姆并非专业的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尽管文学只是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手段之一,但正如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言,作为“行外人”的努斯鲍姆有其独特的优势,她为当代文论与美学研究所作的贡献得到行内人士的认可: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充分肯定努斯鲍姆为当代美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认为在其努力下,“美学在伦理学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韦尔施 79);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则认为“很少有什么批评家,甚至是像卢卡奇和奥尔巴赫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大家”,能像努斯鲍姆那样,“对小说的社会效益做出辩护”(迪克斯坦 290);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夫雷斯(Julian Wolfreys)在其编著的《21世纪批评述介》中,专辟一章“伦理批评”介绍努斯鲍姆与列维纳斯的伦理批评。随着努斯鲍姆相关作品被陆续译介到国内,汉语学界对她的关注也达到了一定的热度。但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对努斯鲍姆文学观尚无整体性的介绍梳理,对其贡献与局限也未作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在此背景下作出推进,力图在全面阅读努斯鲍姆作品的基础上,对其文学观进行梳理介绍,并作批判性的分析与解读,进而发掘其文学观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启示价值。
一、 伦理的缺席:从哲学到文学理论
在所有哲学问题中,伦理问题是努斯鲍姆的首要关切。她发现,当代哲学领域存在严重的“伦理缺席”。这首先体现在英美主流哲学对伦理问题的回避或漠视。绝大多数哲学家热衷于对哲学问题采取形式意义上的语言分析,对内容意义的伦理问题缺乏兴趣,即便涉及伦理,也仅限于“道德语言”的讨论(如黑尔)。其次,尽管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在当代伦理学领域影响卓著,但其问题视野较之古代伦理思想却狭隘许多,日益脱离现实而沦为抽象的思辨游戏。再者,当代道德哲学抽象枯燥的写作风格也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感性而丰富的人生并未得到哲学家的应有对待。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所言,现代道德哲学受制于一种理性共同体的梦想,这种梦想远远脱离“社会与历史现实”,远远脱离“某种特定伦理生活的具体意识”(Williams 197)。深受威廉斯的影响,努斯鲍姆同样认为当代伦理学亟须革新,这种革新依托于回归古代思想,重新思考伦理学的原初问题——“人应当如何生活(How should one live?)”。
于是,当伦理学研究用“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来取代“我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之时,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伦理思想资源浮出水面。伯纳德·威廉斯、艾丽丝·默多克、理查德·罗蒂、阿兰·布鲁姆等当代哲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都充分意识到文学叙事对于伦理学的重要价值。努斯鲍姆亦不例外,文学是让她对哲学产生兴趣,并最终迈入哲学门槛的重要源泉。从年轻时期开始,她对文学的兴趣就与对人生问题的关切联系在一起,她的哲学启蒙并非源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这类“正统哲学家”,而是源自阅读欧里庇得斯、狄更斯、简·奥斯丁、阿里斯多芬、本·琼森、莎士比亚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故事所引起的人生困惑:“在经常性地反思一个特殊人物形象与特定小说的过程中,这些伦理问题就像根一样植入了我的心底。”(Nussbaum,’11)
当努斯鲍姆认为文学能为伦理学提供启迪之际,却惊讶地发现文学界同样对伦理问题不屑一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学界有一套自我信奉的游戏规则:文学研究只讨论纯粹的语言、结构、叙事等“文学性”问题,绝不涉及历史、现实、社会等外部问题。“伦理”自然也成为一个只有行外人特别关心,行内人刻意回避的议题。如果一位文学学者试图通过文学作品去追问生活的问题,以现实实践的态度来对待他所研究的作品,那么他会被认为是“无药可救的幼稚与反动,并且缺乏对文学形式复杂性与文本间指涉的敏感”(’21)。努斯鲍姆指出,文学研究者虽经常从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但他们对伦理学家的作品从来就缺乏足够兴趣。尤其是近几十年开始涌现的一些卓越的伦理学作品(如伯纳德·威廉斯、艾丽丝·默多克、希拉里·普特南等人的作品),几乎就没得到过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与青睐,那些“激发当代伦理学也常常激发伟大文学的那种重要的实践感,更是甚少出现在这些领衔的文学理论家的作品中”(170—171)。当代文学理论面对社会现实的那种漠然,令努斯鲍姆感到遗憾:
我们身边的所有其他学科都在形塑我们文化中的私人与公共生活,告诉我们如何来想象与反思自身。经济理论通过运用理性来为公共政策提供依据,法学理论通过对基本权利的思考来寻求社会正义,心理学与人类学在描述我们的情感生活、性别经验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道德哲学试图对一些棘手的公共伦理困境作出仲裁,文学理论却在这些争论中保持了太长时间的沉默。[……]在这件事上,沉默是一种投降。(192)
正基于此,努斯鲍姆试图以伦理问题为导向挖掘文学作品的实践智慧,通过重新架起一座文学与哲学互通的桥梁来实现当代伦理学的革新与完善。她的这一做法并非她的一己创见,而是源自她深厚的西方古典文化功底,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以及希腊化时代伦理思想的敏锐意识与深刻理解。
二、 诗与伦理学的结盟:来自古典的启示
在追求专业化的当代学科体制中,文学与哲学这两个领域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学专业的学生不需要读跟伦理学、政治学有关的作品,而哲学专业学生则轻视文学作品的价值。即便涉及对伟大思想家的阅读,专业化也要求将思想家的作品进行分类。比如文学系只需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无需关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努斯鲍姆意识到,这种学科上的隔离是有问题的。
通过对古希腊思想的考察,努斯鲍姆指出在古代思想中并不存在对“哲学”与“文学”的区分,柏拉图与索福克勒斯并不存在今天人们所理解的这种差别,现代意义上的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对于希腊人而言是全然不可理解的。现代人对古希腊“诗与哲学之争”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二者在应对“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上的结盟。若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结盟,二者之间的争执也会失去意义。在通往“诗与哲学结盟”的道路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希腊化哲学共同为努斯鲍姆提供了重要启示。透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努斯鲍姆看到一种与文学完全兼容的伦理学,文学可为伦理学提供独特的道德洞见;通过对希腊化时代思想的审视,她还注意到可从治疗的角度理解哲学,这种哲学的治疗与文学的文体与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为努斯鲍姆建立哲学与文学的联盟提供了启发,努斯鲍姆看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有四个与文学相互兼容的特质。首先,亚里士多德强调感知(perception)与特殊性在伦理判断中的首要地位。在亚氏看来,伦理问题上的判断或辨别源于“感知”,即“一种关系到把握特殊事物而非普遍事物的辨别能力”(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 465)。普遍原则在此受到批评,因为其既缺乏具体性又缺乏灵活性。反过来,感知则能回应细微差别,好的感知是“一种对实践处境本质的完全认识或理解”(’79)。其次,从广义的角度看,这种感知包含着对情感与想象的重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情感不仅是形成良好感知的重要辅助,而且自身就包含了重要的认知,情感是成就实践智慧的重要条件。再者,这种感知能够引导人们看到人类价值的多元及彼此间的不兼容性。亚里士多德挑战了柏拉图所认为的关于世界上所有不同的价值应当彼此兼容,并可化约为一种更高价值的观点,认为各种价值彼此之间并不兼容也不可比较。最后,借此可推论出善与人生的脆弱性。价值之间的冲突与不兼容性使完美无缺的生活缺乏现实可能,人类必须正视与面对生活的复杂与冲突。这种感知最终能够抵达一种叫作“道德慎思(moral deliberation)”的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与当时的悲剧艺术存在高度的契合。努斯鲍姆指出,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观看悲剧相当于某种严肃的人生与社会介入,而亚里士多德的道路就是一条文学的道路,古代悲剧通过对感知与特殊性的强调、对情感的重视、对价值不兼容性以及人生脆弱性的正视来显现其独特伦理内涵:“不像哲学只是利用一个相似的故事作为示意性例子那样,一整部悲剧能够追溯一段复杂思维模式的历史,展示它在一种生存方式中的根源,并预期它在这种人类生活中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使我们体会到了真正思想的困难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善的脆弱性》 19)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呈现了主人公阿伽门农在敬神与家庭伦理之间的两难处境:神向他传达旨意,如果他不献祭他的女儿伊菲革涅亚,那么他的整支远征军都将遭受重创,难逃一死。在努斯鲍姆看来,埃斯库罗斯向其观众表现的不是对这种“实践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反倒是这个问题自身的复杂与深度:“冲突的危险”本身就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事实,我们似乎应该接受并且考察这一现实”(69)。对于《安提戈涅》这部悲剧,努斯鲍姆认为“这部悲剧考察了消除紧张和冲突状态的两种不同努力,它们都试图简化行动者的承诺和爱的结构”(74)。由于两位主人公对各自价值体系的深信不疑,导致了他们在是否要为波吕尼刻斯收尸的问题上爆发激烈冲突。努斯鲍姆承认,尽管安提戈涅在道义上要比克瑞翁高尚,但两人对于生活的看法同样存在着“片面”与“狭隘”,他们拒绝以开放的态度面对生活的复杂性。这部悲剧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冲突的形式来提醒人们要对自身的“固执己见”有所警惕,而应开放地面对生活中价值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冲突性。悲剧向我们显示了“凡人在自然发生的世界中的实践智慧,和伦理上应当肩负的责任”(67)。
努斯鲍姆还从希腊化时代的伦理学中获得启发。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更多被视为一种认识世界与真理的方法,那么在希腊化思想中,哲学则被赋予浓重的医学内涵,哲学被理解为一种治疗灵魂的手段。在当时以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为代表的希腊化哲学看来,人类的诸多不幸在于其情感和欲望受到不良社会环境的腐化,亟待治疗。在这一治疗理念的影响下,人们对文学的思考产生两个重要结果:其一,由于人类的欲望情感被视为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其就存在被腐蚀与扭曲的可能性,承载这一情感的文学未必能提供关于世界的真实图景,反倒会助长与强化某种情感偏见;其二,作为治疗的手段,抽象的理性论证难以取得真正的效果,相较之下,哲学“更需要考虑如何运用想象力、叙事、共同体、友谊以及可以有效地把一个论证包装出来的修辞形式与文学形式”(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 34)。某种能够超越传统道德与情感的文学叙事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基于这种治疗理念,文学与哲学存在着另一种协作的可能性。
于是,无论在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还是在塞内卡的悲剧《美狄亚》中,努斯鲍姆都看到了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哲学治疗的可能性。卢克莱修的作品体现了伊壁鸠鲁主义者利用诗歌形式去治疗人类爱欲的尝试,尽管在此诗歌仅被视为“一件外套或一层外表”(《欲望的治疗》 158)。在斯多亚学派的作品中,文学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悲剧被认为是“最适宜于驳斥激情的文学形式”(454),因为它可以让人充分在情感而非理智层面来体会激情带来的危险。塞内卡的《美狄亚》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叙事以及运用文学意象展示了爱的“凶残”,它“并不是一种温柔可爱的激情[……],它是自然界中最强烈的那种暴力,是燃烧的火焰,令我们忽而惊奇忽而恐惧”(469)。在此,努斯鲍姆找到了另一条将文学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的路径,这也同时使她的文学观显得斑驳与复杂。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式的文学伦理观将文学视为感知与认识生活的一面镜子,致力于探寻生活的复杂困难面目的话;那么希腊化哲学式的文学观念则更强调文学作为哲学手段所具有的治疗与教育功能。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两种观念截然对立起来,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式的感知理念中隐含着何为好生活的理念,在斯多亚式的治疗理念中也不乏对伦理知识的探求。但相较而言,前一种观念更注重探寻“好生活究竟是什么”,强调文学在其自身的独立性中所形成的有关人生的伦理知识,后一种观念则更偏重“如何实现好生活”,强调文学在治疗情感和欲望中的功用价值。前一种观念致力于对好生活的探寻,而后一种观念则致力于推动好生活的落实。这两种文学观念共同影响和塑造了努斯鲍姆对文学伦理的理解,其中暗含的矛盾与紧张也在其文学的思考与批评实践中得到了显著的呈现。
三、 感知的智慧:探询伦理的文学叙事
从努斯鲍姆的大多数作品可见,她更多是从亚里士多德式的感知角度去诠释文学的伦理贡献。在她看来,如果在古典时代悲剧是通往伦理生活的重要道路的话,那么文学(尤其是小说)则是当今时代的“悲剧”。文学与人生之间的紧密联系并非表层意义上的联系(如下棋那样的娱乐或者游戏),而是深层意义上的联系,就在于文学能够提供一种深刻的实践智慧。
文学能提供怎样的实践智慧呢?努斯鲍姆理解的文学伦理,是一种具有现实感的文学观念。文学的伦理落实于对现实人类生活的认识理解中,而非对现实社会生活的逃逸。因此,即便文学具有某种超越性,也绝非神性或乌托邦意义上的“外在超越”,而是一种基于现实感的“内在超越”。文学的这一超越体现在其对习俗道德以及抽象原则的挑战和质疑,相较于后者所呈现出来的简单性与精确性,前者体现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文学提供的伦理知识不单单是对命题的智力掌握,也不是对特殊事实的智力掌握,而是基于感知与情感的角度去回应人类具体生活的伦理问题。因此文学的伦理不仅不同于那些抽象的道德原则与道德主义,而且还会对其形成挑战与反叛:文学不是作为“说教的道德主义者,而是作为迂回的同盟与反叛的批评者”参与到伦理问题的探寻之中(’169)。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努斯鲍姆视小说为最具优势的体裁。从修辞伦理的角度看,小说的特定形式有助于把握道德智慧。在那里“生活不仅仅通过一个文本呈现出来(present),而且还总是被再现(represent)为某种事物”(’5)。从接受的伦理效果看,小说“建构了一位与小说人物分析特定希望、恐惧以及普遍人类关怀的隐含读者,并与之对话。”(Nussbaum,7)。努斯鲍姆援引普鲁斯特的观点,将文学视为一种“光学仪器”,认为小说“通过展示‘我们真实冒险’中的神秘与不确定性,它们对生活的描绘比一个缺乏这些特征的案例更为丰饶与真实(甚至更准确),它们也会让读者获得一种对于生活更为合适的伦理作品”(’47)。需要指出的是,努斯鲍姆对“文学”的理解是有所限定的。这不仅体现为她对小说体裁的青睐,而且还体现为她对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视。在阐发文学观的过程中,她并不满足于笼统抽象的讨论,而更愿诉诸个案批评来探讨文学的伦理贡献。在诸多案例中,亨利·詹姆斯无疑是她最为倚重的作家。无论是这位小说家的创作本身,还是其有关小说的见解,都为努斯鲍姆的文学观提供了例证。在詹姆斯看来,小说家承担了一种使命,即通过表达一种“投射的道德(projected morality)”来协助我们追寻如何生活的使命(James,45)。对詹姆斯几部后期小说的解读,集中展示了努斯鲍姆文学伦理观:文学能以感知的方式抵达对一个更为复杂且充满冲突的世界的真实认识。
首先,文学透过小说人物的感知意识以及读者对人物的认同来获得一种关于生活复杂性的认知。在评析詹姆斯的《金钵记》时,努斯鲍姆指出小说讲述了一位少女的成长故事,尤其是通过玫姬心灵成长过程的叙述展示其在伦理上的日益成熟。她起初是一位单纯天真、追求完美的美国少女,不愿意因自己即将开启的婚姻生活而影响她与父亲之间的亲密关系,为此她试图在妻子与女儿这两种角色之间寻求完美的平衡。但事与愿违,就如小说中的隐喻——“有瑕疵的金钵”所暗示的那样,玫姬所期待的完美世界并不存在。但正是玫姬后来对生活不完美的正视,体现了其在伦理上的成熟。努斯鲍姆指出,玫姬最终以詹姆斯意义上“细微的体察与完全的承担(finely aware and richly responsible)”懂得了生活的本质(James,62)。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中,她对世界的道德感受并不依托于简单的教条或原则,而是一种依托于具体情境之下的“即席发挥(improvising)”(’155)。在这种道德感知得以重塑的前提下,一个更为复杂、脆弱且充满运气与冲突的世界才会展现在眼前,玫姬在此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道德慎思。詹姆斯的另一部小说《专使》也被认为展示了同样的实践智慧。小说讲述主人公斯特雷瑟肩负了一项使命,从美国前往巴黎去寻找名叫查德的年轻男子,因为查德的母亲纽瑟姆夫人认为这个年轻人已在巴黎的不道德生活中迷失方向。然而来到巴黎之后的种种见闻使得这位使节不仅未能完成劝说查德回家的使命,自己反倒被这里的一切所深深吸引,甚至还背弃使命,劝说年轻人留在巴黎,因为在巴黎他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在努斯鲍姆看来,这一切源自斯特雷瑟所具有的那种发现生活丰富性的道德能力、其感知的开放性与对生活的好奇心。除了詹姆斯的小说之外,还有一些作品则提供了反面的案例。《艰难时世》中格雷戈林的悲剧在于他缺乏对情感与想象的认可,丧失了对特殊性与生活丰富性的理解。《追忆逝水年华》主人公马塞尔的自恋恰恰体现为他缺乏面向外界的开放性。即便对于爱,他也缺乏真正的感知,只有在“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的那一刻,他才有所意识(普鲁斯特1)。在努斯鲍姆看来,正是在对主人公的认同或质疑中,读者可以逐渐习得道德慎思的能力。
其次,文学的伦理知识不仅体现在作品主人公的实践智慧中,而且更体现在作为整体的作品文本中。努斯鲍姆不仅透过文本分析指出,“以一位想象中人物的努力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整个文本”(’141)。玫姬、斯特雷瑟、海厄森斯等人物形象是通过整部作品的叙事来得到刻画的,对人物本身的认同包含着一种对文本的整体性理解;而且她还借用了韦恩·布斯的“隐含作者”概念,从整体上确认了像《艰难时世》等多人物作品的伦理价值;此外她还通过文本分析指出,这些人物之所以拥有这种实践智慧,本身就得益于对文学阅读的热爱。比如《专使》中的斯特雷瑟从小就对文学(尤其是小说)有一种由衷的热爱(詹姆斯 66);《卡萨马西玛王妃》中的海厄森斯在革命风潮中的清醒同样得益于文学想象的馈赠(’211)。

总而言之,复杂(complexities)、丰富(richness)、充分(fullness)、具体性(concreteness)、多样(diversity)、艰难(difficulty)、困惑(perplexity)、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努斯鲍姆在论述中最常用的词汇。她在论证文学在伦理学意义上独具智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文学的自主存在,强调其绝非伦理学的工具或注解。在此意义上,努斯鲍姆与莱昂内尔·特里林、艾丽丝·默多克等人对于文学伦理的知性定位基本一致。在特里林看来,文学的伦理价值就体现在一种“知性(intelligent)”中,它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永恒的、艰难的、粗俗的、让人不悦的”现实(特里林 114)。在“教会我们认识人类多样化的程度,以及这种多样化的价值”的过程中,小说取得了“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取得的效果”(119)。在默多克看来,美德是一种知识,并以如此的方式把我们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而某种非诗歌的散文文学(prose literature)提供了这样的道德知识(Murdoch 284)。努斯鲍姆在此走得更远:通过更为哲学的论述,她对特里林点到即止、语焉不详之处,作了更为细致与有条理的分析阐释;通过更为细腻的文本分析,她也弥补了默多克文学思想中抽象思辨压倒审美批评的缺憾。
不过,努斯鲍姆对于文学感知的强调,有时依然有所保留。她在强调感知的首要地位,突出文学挑战道德原则,贡献独特伦理知识的同时,有时也强调“感知与原则之间的平衡(或对话)”,即感知可以修缮道德原则,但道德原则也可以用来纠正感知,因为失去责任的感知将处于“危险的自由浮动中(dangerous free-floating)”(’155)。尤其是当文学感知触及更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时,努斯鲍姆就倾向于维护感知与理性原则之间的平衡,甚至还会为了捍卫某种原则而放弃文学感知的优先地位。在此背景下,努斯鲍姆的另一种文学伦理观——治疗的观念——浮出水面。
四、 情感的治疗:追寻正义的文学想象
文学所提供的丰富性,不仅可为个体的生活增光添彩,而且还为社会正义的推进作出贡献。“社会如果想要鼓励对所有成员公平对待,就有足够的理由鼓励富有同情心的想象,这种想象跨越了,或试图跨越社会界限。而这意味着要关注文学。”(《培养人性》 76)努斯鲍姆自然希望将文学的伦理价值延伸到公共生活领域,她对如何有效实现亨利·詹姆斯的“想象力的公共使用(civic use)”(James,223)抱有极大的热忱,这种热忱也令她对文学的治疗观念情有独钟。

但不可否认,在更多情况下,文学的认知理念似乎让位于文学的治疗理念。关于文学作为一种治疗的观念,在努斯鲍姆的思考中存在着这样一些预设:首先,治疗的目标是“健康”,我们需要对“什么是健康”有基本的共识,文学需要为社会意义上的健康即“正义”服务。其次,文学是情感的载体,人类的诸多情感往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文学作品以两种方式向他们的读者歪曲这个世界。它们能错误地呈现历史与科学事实。”(75)因此对文学所承载的情感与欲望,需要以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进行鉴别。最后,我们需要用好的文学促进社会正义,也应警惕坏文学可能对社会正义形成的潜在威胁与挑战。关于社会意义上的“健康”-“好生活”,尽管努斯鲍姆不认可某种柏拉图式的先验知识,认为对于“好生活”的认识源于人类现实中情感和欲望,但从约翰·密尔到约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观念还是在原则性的意义上确立了她有关好生活的基本信念,并将这些基本原则(尤其是平等)理解为必须捍卫而非质疑的目标。在2015年出版的《政治情感》中,她援引诗人惠特曼的比喻,认为“公共诗”能够赋予自由与平等的“骨架”以“血肉”(12)。这种“血肉”与“骨骼”的比方暗示:文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应被确立为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如果说在勃朗特与贝克特那里,文学的治疗更多体现在一种针对不健康的情感所进行的“消极治疗”的话,那么在其更多的作品中,努斯鲍姆致力于一种对健康情感进行培育与塑造的“积极治疗”。在《培养人性》,中她将文学的伦理价值定位于“同情想象”与“跨越边界”,尤其是“通过描绘所有被遗弃和受压迫的人所作的奋斗,促使我们对他们予以同情和理解”(《培养人性》 81)。在《诗性正义》中,她进一步指出,“思考叙事文学有可能在特殊意义上对法律,以及一般意义上对公共推理有所贡献”(xvi)。文学能够实现的是让“人们有能力以想象的方式进入遥远他者的生活,并产生参与其中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进入现实的人类之中”(xvi)。她通过对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以及E.M.福斯特的《莫瑞斯》等作品的分析,指出文学想象的价值即在于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对边缘群体(非洲裔美国人、同性恋)产生更深的同情。借此证明,“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其基本的结构与追求中,是平等与所有人类生命尊严这一启蒙理想的捍卫者,而非缺乏批判性的传统主义的捍卫者”(46)。



五、 努斯鲍姆与自由主义文论的困境
在1950年为《自由的想象》所写的序言中,莱昂内尔·特里林曾就文学如何为自由主义作出贡献表达看法。在他看来,“那种以自由主义利益作为核心批评应该发现,它最有用的工作并非在于肯定自由主义的普遍正确性,而是在于对当下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观点施加一定的压力”,在施加压力方面,文学具有独特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其能“最充分、最精确地讨论与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以及困难性相关的问题”(特里林 541,544)。特里林这番表述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纷争的年代背景下作出的,受约翰·密尔的启发,他试图提醒他的左翼同行们不要因为抽象的原则与教义而丧失现实感,文学的重要价值恰恰体现在其对抽象原则与教条的质疑中,哪怕该原则看似“正确无疑”。
在很多情况下,努斯鲍姆与特里林持有一致立场,也深受后者的启发(如她充分肯定特里林对亨利·詹姆斯小说尤其是《卡萨玛西玛王妃》的解读)。她不仅认为较之于哲学,文学批评“需要少一些抽象与概要,多一些对情感与想象的尊重,多一些假定性与即席性”,总而言之,它需要“为自己选择一种形式来显示文学的洞见,而不是去否定它”(’239),而且还能写出“为了找到一种政治上有价值的体验,一个人并不需要认为一部小说在所有方面都政治正确”如此富于洞见的句子(77)。尽管对希腊化时期伦理学的治疗理念倍感兴趣,但她显然更看重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尽管强调理论与原则对于良好感知的重要性,但她依然捍卫感知的首要地位;尽管她认为道德哲学的背景有利于深化对詹姆斯小说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完全赞同用理论介入文化,放弃全身心投入文学的可能性。在读《金钵记》的感受中,我们就明显地体会到这一点:
我读完《金钵记》的那天是1975年的圣诞节,在伦敦林肯小酒馆的一间小寓所中,独自一人。自那时起,最后那几行难忘的句子中的怜悯与畏惧,与我对悲剧及其效应,对个人生活中运气、冲突以及损失所做的反思交织在一起,并且还表达了这些反思。(’18)

一个下午,坐在雅茅斯岸边,六月初的阳光下,我背对着那些难看的赌场、廉价的旅店、粉色与蓝色的小别墅,我的眼神从小说的纸页转向面前召唤着我的黑蓝色大海的宽广地貌,我感到脸上吹过一阵轻风,内心一阵激动,在每个事物的崭新面貌前感到的那种感官上的愉悦,不知怎地与小说篇章中栩栩如生的描写,尤其是与斯蒂福斯存在的力量联系在了一起。(335)
但在有些时候(尤其是在探讨文学如何有助于公共生活的问题时),努斯鲍姆较之于之前的立场有所退缩,未能一以贯之地遵循自己确立的感知优先性原则,不再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来自文学复杂伦理的挑战,而是试图去控制文学的伦理走向,将其限制在为平等主义政治服务的层面上,从而限缩文学的伦理潜能。这时,她在理性原则上捍卫自由主义的意志压倒了在诗性层面上修缮与发展自由主义的灵感,伦理认知的目标被道德疗愈的诉求取代。当文学的复杂性挑战了那些她所不支持的教条与原则时,努斯鲍姆会欣然接受这种复杂性;一旦文学的模糊性挑战了她所认同的价值原则时,她也未能做到从容与开放。努斯鲍姆对个体伦理生活的思考常常能超越道德主义的束缚,但在公共生活层面依然受到了一种新的道德主义的束缚。这最终使她在个体人生与公共生活的不同层面上,传达出两种虽不能说完全无法通约,但的确有所紧张与矛盾的文学观念。
特里林对此早有预见。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在捍卫自身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封闭:“只要自由主义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就是说,只要它能朝着有组织的状态进发,那么它就会倾向于选择最易受到组织影响的情感和品质。在它实现其主动性和积极性目的的过程中,它会无意识地限制自己的世界观,使其缩小到可以应付的范围,而且它会无意识地倾向于形成一些理论和原则,尤其是与人类的思想本质有关的理论与原则,并以此来为自己的局限性提供辩解。”(特里林 543)尤其在当代思想环境极化、自由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质疑的背景下,这种强烈的自我戒备与警惕更是格外显著。“(浪漫主义)虽然在私人生活中很有魅力,但给公共生活提供了自由主义社会必须抵制的种种诱惑。”(沃尔夫 125)艾伦·沃尔夫的这一态度道出包括努斯鲍姆在内很多自由派学者的心声,他们对于文学在伦理与政治上的暧昧与不正确,持有强烈的疑虑与警惕。

结 语
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曾指出:尽管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宽容,但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两张不同的面孔。一张面孔致力于寻求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性共识,因为这一共识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宽容的形式前提;另一张面孔则并不执着于寻找理性共识,而是认为人类可以探索多种方式的和平共处,理想生活的形式并不是唯一的(格雷 1—2)。尽管格雷有意识地区分出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及其代表人物,但与其说这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两条支流,不如说是很多自由主义者思想内部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在努斯鲍姆的文学观中得到显著呈现。
努斯鲍姆对文学的认识呈现出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第一张面孔主要体现在感知伦理的层面。她通过对詹姆斯等作品的阐释,揭示了文学在引导人们以开放性、被动性的态度对生活进行敏锐感知,从而揭示生活复杂性与价值冲突性方面的重要性,这种文学的伦理甚至有时还有效抵达社会政治领域。在其呈现的第二张面孔中,努斯鲍姆更强调文学的治疗价值,强调其在捍卫与推进民主价值上所体现的价值,尤其体现在对同情与平等理念的培育中。要实现文学的这一伦理价值,需要的不是开放性与被动性,而是批判性与主动性。这两张面孔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区分。如果说在个人生活中,努斯鲍姆更看重来自文学本身的伦理教导的话,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她更倾向于对文学伦理进行批判性意义上的吸纳与使用。如果说在个体生活层面,努斯鲍姆认为文学致力于认识生活的复杂与困难,那么在公共生活层面,她更强调文学在捍卫民主政治基本原则方面的价值。如果说前一张面孔是多元主义的,那么后一张面孔则是普遍主义(或平等主义)的。当然在具体的文学思考与批评实践中,努斯鲍姆的文学观并非如文中分析的那般泾渭分明,而是呈现为更为复杂的面貌。
通过分析可见,这两种文学伦理观念在努斯鲍姆思想中并非和谐共处,而是充满矛盾与紧张。文学治疗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伦理感知观念的忽视与否定,该观念暗示:我们不需要继续为何为好生活殚精竭虑,只需文学为促成好生活的普遍共识添砖加瓦;相反,伦理感知观念则会消解文学治疗观念的前提,即对好生活的探寻永无止境,我们没有理由与必要就“何为好生活”形成僵化和教条的论断。在笔者看来,相较于其对文学治疗的强调,努斯鲍姆对文学感知价值的肯定显得更为重要,也更具现实意义。略感遗憾的是,越到后期,治疗理念越是在努斯鲍姆的思考中占据重要的分量。她逐渐放弃文学在探寻人生伦理智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文学来上一门关于道德或社会正义的课程,尽管较之于那些要对各种文艺作品进行意识形态审查的激进同行们,努斯鲍姆已展现出难得的开放性。她的文学观与批评实践也在一个更为普遍的层面上折射出当代自由主义在处理文艺及文化问题时所遭遇的困境。
努斯鲍姆对文学所作的思考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无论有关这些文学作品的主张是否被接受,她已成功地将那些关于文学文本的讨论引入了道德哲学。”(Diamond 40)正如克拉·戴蒙德所言,努斯鲍姆对文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她发掘了文学在思考伦理学问题上的潜力,而且她对伦理思想的重视亦有助于让文学研究走出“躲入小楼成一统”的狭隘视野,她的积极贡献更体现在其对文学与好生活之间密切联系的不断重申中。她时时提醒我们,面对当今时代面临的重重社会问题与人生困惑,文学研究不该成为一块脱离现实的“飞地”,理应参与到对“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历久弥新的古老问题的回应中去。尽管在将文学推向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努斯鲍姆的文学观呈现出一定的矛盾与紧张,但这也在客观上为我们思考当代文学研究所遇到的共同困境提供了契机。为此,我们绝不能轻视玛莎·努斯鲍姆所作出的思想贡献,也应在直面她所面对的困境与挑战时,为思考文学理论事业的未来找到一个更为坚实的起点。
① 参见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著:《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目前国内关于玛莎·努斯鲍姆的硕博论文已近40篇,单篇论文将近80余篇,已有专著1部——《玛莎·努斯鲍姆“好生活”伦理思想研究》。
③ 对努斯鲍姆文学观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围绕着《善的脆弱性》与《诗性正义》展开,对她的其他作品如《爱的知识》《欲望的治疗》《政治情感》以及与文学相关的研究关注不足。
④ 参见伯纳德·威廉斯的《羞耻与必然性》、爱丽丝·默多克的《存在主义者与神秘主义者:论哲学与文学》(:)、理查德·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阿兰·布鲁姆的《爱与友谊》()等。
⑤ 努斯鲍姆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是一种有意识的思想建构,并将她的方法称为“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在此,她有意识地忽略了亚里士多德思想中与柏拉图一致的成分,而有意放大了其在强调价值多元性以及运气在生命中的重要性。
⑥ 努斯鲍姆也指出亚里士多德思想本身具有医疗的内涵,但同时也指出他也批评过这个类比,论证说有一些很重要的方式使得伦理哲学不应该与医学相仿。参见《欲望的治疗》,第40页。
⑦ 参见拙文《追寻美学的现实感:评玛莎·努斯鲍姆〈善的脆弱性〉》,《文艺研究》12(2018):150—160。
⑧ 努斯鲍姆的文学观念具体地渗透在其批评实践之中,通过对其批评实践的考察,不难提炼与总结她的文学观念。她对文学的“使用”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其一,借助相关文学文本的片段为其探讨社会与政治议题中的论证提供分析材料,如对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阿兰·佩顿《哭泣的大地》、特奥多尔·冯塔纳小说《艾菲·布里斯特》、莎士比亚《裘利斯·凯撒》、安东尼·特罗洛普《索恩医生》()、劳伦斯《虹》以及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分析。其二,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来对道德哲学中的教条与原则进行批判性反思。如对《金钵记》《艰难时世》《专使》等作品的分析。其三,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来思考被道德哲学所忽略或回避的问题,如爱与及交流的问题。如对塞内加《美狄亚》、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安·贝蒂(Ann Beattie)《学会投入》()、《呼啸山庄》、爱丽丝·默多克《黑王子》、《大卫·科波菲尔》的分析。其四,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来发掘文学对推进社会与政治正义的实践价值,比如对《土生子》《莫瑞斯》《看不见的人》《卡萨马西玛王妃》等作品的分析。由于第一类分析大多只是对文学文本部分情节的引述,并不构成对文学整体的理解,因此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后三类分析中所涉及的文本。
⑨ 亨利·詹姆斯几乎为他的每部小说都写过序言,后收录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该书的国内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出版,朱雯等译,但较之于英文本,存在不少差异。不少篇目(如《卡萨马西玛王妃》的序言)都没有被收录并得到译介。
⑩ Martha C. Nussbaum. “Literature and Ethical Theory: Allies or Adversaries?”9(2000):5-16.













Aristotle.. Trans. David Ro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Aviv, Rachel. “Captain of Her Soul.”25 July (2016):34-43.
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Bloom, Harold.. Trans. Huang Canr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李媛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Carrol, No⊇l.. Trans. Li Yuany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Diamond, Cora. “Martha Nussbaum and the Need for Novels.”,,. Eds. Jane Adamson,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39-64.
布莱迪·科马克等编:《莎士比亚与法》,王光林等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
[Cormack, Bradin, et al. eds.:. Trans. Wang Guanglin, et al. Harbin: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2015.]
莫里斯·迪克斯坦:《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刘玉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Dickstein, Morris.:Trans. Liu Yuyu.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Eagleton, Terry.. Trans. Yin Zhike.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Gray, John.Trans. Gu Aibin,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James, Hen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2.
- -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亨利·詹姆斯:《专使》,王理行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年。
[James, Henry.. Trans. Wang Lixing.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8.]
莎伦·R.克劳斯:《公民的激情:道德情感与民主商议》,谭安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Krause, Sharon R.:Trans. Tan Anku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5.]
Murdoch, Iri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99.
Nussbaum, Martha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
- - -.:.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玛莎·努斯鲍姆:《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李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Nussbaum, Martha C.:. Trans. Li Yan.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玛莎·C.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修订版),徐向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 - -.:. Trans. Xu Xiangdong,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18.]
——:《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徐向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 - -.:. Trans. Xu Xiangdong,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Posner, Richard A. “Against Ethical Criticism.”21.1(1997):1-27.
理查德·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Posner, Richard.:Trans. Xu Xin.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2.]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第六卷),刘方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Proust, Marcel.Vol.6. Trans. Liu Fang, et al. Nanjing: Yi Lin Press, 2012.]
莱昂内尔·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职责》,严志军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Trilling, Lionel.. Trans. Yan Zhijun,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Welsh, Wolfgang.. Trans. Lu Ya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Williams, Bernar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艾伦·沃尔夫:《自由主义的未来》,甘会斌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
[Wolfe, Alan.. Trans. Gan Huibin,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