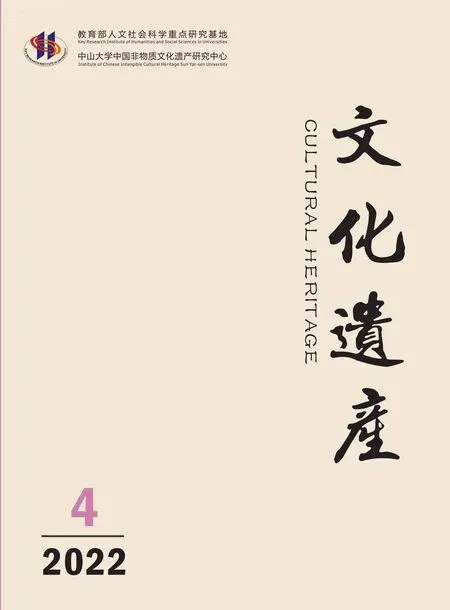英国人对中国戏剧的认知与接受(1400-1799)*
2022-11-05徐巧越
徐巧越
“中国戏剧在英国的传播”是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此前,海内外学者集中研讨了《赵氏孤儿》《老生儿》与《汉宫秋》等剧作的翻译与改编,从中国文学外译与欧洲汉学史等角度,对这些作品在英国社会的接受展开深入的探讨。他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戏剧文本在19世纪以后的传播。相较之下,由于15至18世纪末的相关资料散见在游记、报刊与时评,年代久远,信息零散,如今已不易见得。是以,学界对19世纪前英国人的接受情况则谈论得较少。
中英两国的交流,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的蒙古西征。1287年,大都人列班·扫马(Rabban Sauma)出使罗马,在法国南部的加斯肯尼城(Gascony)谒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这是已知文献记载中,中国人与英国的首次接触。以此为起点,英国人对中国戏剧的认识与态度,也随两国关系的深化与国家实力的扭转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在文本翻译之外,尚有赴华英士的观剧记录、外销戏画,以及西方作家所创作的中国主题戏剧等。这些资料记录下早期英国人认知中国戏剧的情况,动态地呈现出英国社会建构“中国形象”的历程,也有助于丰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叙事层。
本文在蒐集15至18世纪各类西文文献的基础上,梳理英国人在不同阶段对中国戏剧的认知与评论,尝试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中国戏剧艺术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
一、大航海时代的财富象征 (15世纪-17世纪初)
英国对中国的兴趣,始于对财富的追逐。大约在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东方见闻录》出版,他在游记中对“财富”的夸张描述,引发西人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半个世纪以后,英国作家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的游记()问世。该书依据马克·波罗游记、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东游录》、文森特(Vincent of Beauvais)《世界镜鉴》、海敦亲王(Haiton the younger)《东方史鉴》与伪托“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信件,结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讲述了曼德维尔游历东方诸国的经历。在他的笔下,蒙古大汗是英勇贤明的君主,他的花园养殖了各类奇珍野兽,宫殿镶满了金银珠宝,就连管道流出的液体也是香醇的美酒。这部作品虽是一部虚构的游记,可《曼德维尔游记》对中国的物质化建构,为英国读者编织了一个充满异域情调的美梦。这部游记对英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成了指代“财富”的符码。譬如,乔叟(Geoffrey Chaucer)《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侍从的故事》(’)便提及一名英勇贤明的蒙古大汗(Cambuscan),故事中还出现“青铜马”“宝镜”等充满东方色彩的物件。
15世纪以后,欧洲的冒险家纷纷扬帆远航,试图开辟通往东方市场的海上航线。在这个扩张的时代,英国旅行家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在1497年便试图寻找去往印度与中国的航线,可惜无功而返。此后,英国忙于政体改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开展此类探寻。至16世纪下叶,英国对东方市场的开拓已滞后于毗邻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与法国。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登基后,她鼓励拓展海外市场,并把远东视为开展外贸的重要目标。在政策的鼓励下,各类介绍中国的著述纷纷问世。1573年,威廉·布尔(William Bourne)在《论海上霸权》便探讨了五条通往中国的航线。十年后,伊丽莎白女王派遣约翰·纽伯雷(John Newberry)携带公文赴华建交,她在公文中称中国皇帝为“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主陛下”,更单刀直入地声明,出使是为了“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虽然,纽伯雷一行因遭到葡萄牙的阻挠而未能完成使命,但英女王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探索。1596年,她再次派遣罗伯特·都德雷(Robert Duddley)使华,并在公文中盛赞中国“治理坚固而贤明,其声誉遍布天下”。然而,都德雷的航船因遭遇海难,无果而终。
直到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大举进军远东市场。13年后,英国在日本平户设立商馆,远航的商人可从东瀛购买中国货物。17世纪30年代起,英国愈加关注对华贸易的开拓。1635年,英葡签订《果阿协议》,葡萄牙主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开放葡方在远东的港口。同年,新组建的“科腾商团”(Courteen’s Association)派遣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率领船队前赴中国开展贸易。1637年夏季,威德尔的船队先抵达澳门,后驶入珠江口岸,试图进入广州城区。因为葡萄牙人的挑拨离间,船队与当地官兵发生冲突,威德尔一行在中国逗留了六个月,却没能顺利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这一次使华虽阻力重重,但威德尔的远航却标志着中英关系揭开了新篇章。
在威德尔的随行队伍中,英国旅行家彼得·芒迪(Peter Mundy)肩负着调查广州商贸情况的职责。尽管船队成员只能在澳门与沿江口岸活动,不能进入广州城,芒迪依然以日记的形式,详细地记录了这次远征的所见所闻。其中,即包括1637年11月12日澳门街头的一场戏剧表演:
在商舰船长下榻的住所(这是属于耶稣会信徒的漂亮房子)前,搭起了一个可供男童表演的戏台。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外部动作都非常不错,这群孩子也十分讨人喜欢。他们的演唱和印度的歌咏有异曲同工之妙,与面鼓的击打、铜质器皿的节拍保持着一致的节奏。班主站在一旁的空地,并未对前来围观的看客索取任何费用。这似乎是上层人士为庆贺婚礼、添丁得子或节庆之类的喜事所请来的助兴表演。他们自掏腰包,请老百姓免费观看这些戏剧表演。除了童伶,表演者也包括成年男子。
芒迪的这段文字,是英国人描述中国戏剧表演的已知最早记录。他把这场街头献艺与印度的歌咏作了相互比照,并对童伶整齐划一的表演表示了肯定。13天后,威德尔一行受邀在圣保罗教堂欣赏戏剧表演。这出戏记述了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的生平事迹,表演者依然是中国童伶。芒迪在游记中表示,观众都十分喜欢这群训练有术的孩子,一些年幼的童伶已经可以展现高难度的表演,这让在场的英国人感到惊异。芒迪从一名西方人视角,记录了17世纪初澳门的演剧生态,他对中国人表演西洋戏的记述,更是探讨早期中西戏剧互动的珍贵史料。
在这个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著述开始介绍函夏,英国戏剧也出现 “中国”的身影。大学才子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在剑桥求学期间,创作了十幕剧《帖木儿大帝》()。这部剧的上半部曾在1587年的伦敦上演,剧本在3年后出版。该剧记述了蒙古贵族帖木儿征战与建立政权之事。马洛借帖木儿之口宣称,他所统治的领土“由东到西,正如太阳每天所照亮的地域”,剧中所推崇的“武力征服世界”,反映了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对外扩张的野心与壮志。此后,英国剧作家频频在戏剧中加入“中国”元素。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在《第十二夜》()与《温莎的风流娘们》()都提及了“契丹人” (Cataian),而《一报还一报》()第二幕第一场中,庞贝还有这么一句台词:“虽然它们不是瓷器盘子,但也算得上很好的盘子”(They are not China dishes, but very good dishes)。托马斯·德克(Thomas Dekker)的喜剧《从良妓女》()与戴夫纳特的闹剧《爱情和荣誉》()都分别出现了“完美的契丹人”(perfect Cathayane)与“勇敢的契丹人”(bold Cataian)。受游记文学的影响,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会将“中国”与富庶、文明、英勇等褒义词汇相联系,这反映了英吉利民族对东方的总体想象,并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对天朝的憧憬。
二、中英文化交流的发展期 (17世纪中叶-18世纪初)
东方与西方接触的直接契机是贸易,中英关系亦是如此。英国对中国的考察,起步虽晚于欧洲诸国。但随着“日不落帝国”海上霸权的确立,以及中英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英国传教士、外交官与商人来到中国,他们的撰述对英国的社会思潮、艺术风尚与演剧传统皆有所浸染。
1670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小型帆船“万丹号”(Pink Bantam)与单桅帆船“珍珠号”(Sloop Pearl)抵达台湾,与郑经(郑成功之子)协议通商。郑氏家族本是海商起家,再加上清政府的海禁与迁界政策,从内陆补给等同钻火得冰,他们亟需通过对外贸易来缓解困局。在此之前,英国试图从台湾打通与中国的贸易渠道,无奈一直受到荷兰人的阻挠。彼时,海贸劲敌已被郑成功驱逐,英商再次看到建立中英贸易的契机。两年后,英方与郑氏政权缔结通商条约,英国东印度公司陆续在台湾、厦门、福州与泉州建立商管。商路的亨通让中国的货物远销英伦,其中包括一批汉籍。剑桥大学藏明刊《满天春》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的明刊《万锦徽音》是英国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文献,这两本闽南曲集极有可能是在“郑英通商”时期通过航运传入英国,成为上层人士的东方藏品,继而辗转入藏公家图书馆。
“郑英通商”维系了十三年,直至1683年,延平王郑克塽削发降清,台湾诸岛复归清朝。在此期间,多位英国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谈及鞑靼民族征服中国的事件,舞台也出现反映明朝灭亡的戏剧。1676年,英国剧作家塞吐尔(Elkanah Settle)的五幕剧《鞑靼的征服》()被搬上伦敦公爵剧院(the Duke's Theatre)的舞台。这部剧主要参考了卫匡国(Martino Martini)《鞑靼战纪》,讲述清兵入关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的故事。除此而外,罗伯特·霍华德爵士(Sir Robert Howard)也创作了一部同名戏剧,可惜全稿未能传世。据钱钟书《17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可知,“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曾考虑改编霍华德的戏剧,但他最终把精力集中在翻译维吉尔的作品上,故没有完成对霍氏剧作的改编。康保成教授指出,“热衷于写中国与鞑靼之间的纠纷”是欧式“中国戏”的特征之一,直到20世纪初,依然有英国人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在戏剧创作中加入此类情节或背景。
1684年,康熙下令解除海禁,设立了粤、闽、浙、江四个海关,开放贸易。《海防总论》记载的“德泽汪沫,耄倪欢悦,喜见太平,可谓机一时之盛矣”,正是对当时繁荣海运贸易的描述。中英贸易的欣荣,不仅给英国民众带来香料、茶叶、瓷器与各式工艺品,这些东方奇珍品所引发的中式风尚,也影响了英国的园林、装饰艺术。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爵士的《论园艺》(,,1685 )称赞了中国园艺的“无序美”,他将这种“萨拉瓦日”( sharawadgi)式风格视为艺术的极致。无独有偶,塞吐尔在1692年排演歌剧《仙后》(-,)时,就以中国花园作为第五幕的背景。中式风尚对英伦舞台的渗透,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旬。
在18世纪初,一些赴华英人也在游记或档案中留下了观看中国戏剧表演的记录。17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在广州街头观看了一场中国戏,他将观后感与剧情简介记录了下来。1720至1721年,苏格兰人约翰·贝尔(John Bell)随俄国使团赴北京觐见康熙皇帝。他在《从俄国圣彼得堡环游亚洲记》(,)中,对宫廷承应、会馆演剧与街头戏班的表演都作了详细的描述。贝尔虽不了解中国戏曲的内涵,但他非常欣赏这门独特的东方表演艺术。在观看了康熙安排的宴席承应后,这名见多识广的苏格兰人惊叹道:“我坚定地相信,在表演的花样和灵巧的特技方面,很少有国家能与中国相匹敌,更没有一个国家(的伶人)可以超越中国(的伶人)。”对于会馆晚宴演出,贝尔仔细地观察了表演场所与演出情境,在他看来,舞台上的男伶与女伶“身着华袍,举止得体”,来宾对他们的表演都十分满意。在欧洲的知识传统中,戏剧是最高级的文艺形式,贝尔站在西方的视角,记述了康熙年间各阶层繁荣的演剧状况,多方位展现了该时期北京城的戏剧表演生态。
在这一阶段,贸易的繁荣促进了中英文化的深化互动,英国演剧亦受到了中国素材与艺术风尚的渗透。英伦舞台上所呈现的异文化戏剧景象,给英国观众带来感官与思想层面的冲击,成为他们认知“中国”的初印象。此外,该时期赴华英人的观剧记录是反映清初演剧生态的纪实资料。他们的直观感受与详实记述,对探讨该时期宫廷承应与民间表演具有重要价值。
三、“中国热”潮流下的东方幻想 (18世纪30年代60年代)
自17世纪末起,在法兰西“中国热”(Chinoiserie)与“启蒙运动”的双重作用下,西方文艺圈十分推崇中国的思想文化。1735年,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赵氏孤儿》法译本发表,为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主编的《中华帝国通志》(é,,,')所收录,中国戏剧作品正式进入西方社会的视野。《赵氏孤儿》为启蒙思想家所构建的“哲学东方”提供了具象化文本。随着这部作品在欧洲传播范围的扩大,一批欧洲剧作家将“赵氏孤儿大报冤”的故事改编成地道的西方戏剧,以此阐释各自的政治目的或思想主张。对这部中国戏剧的频繁转译、改编,迎合了欧洲观众对东方帝国的想象需求,激发西方社会对中国戏剧的浓厚兴趣。
在法译本问世后的30年中,英国出现了三种译本,另有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与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的两种改编剧本,英国批评家纷纷就这部中国戏剧发表评论(学界已有充分的研究,故不再赘述)。这股对中国的崇尚风潮,自然地波及至各类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针对英国文艺圈的这类现象,作了如下评论:
当今主持娱乐活动的人们既然有了这样的癖好,并且开创了一时的风气,那么诗歌也跟着走了,戏剧也以中国习俗为内容而与观众见面了,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探讨中国习俗,作者即使略有差错,也不用着急,因为能辨别真伪的读者毕竟只占少数。
无论是经过“文化移植”的《赵氏孤儿》改编剧,还是各类以“中国”作为噱头的闹剧、舞剧、默剧与歌剧,这些表演只是“异域东方”在欧洲人想象层面的延伸,即英国学者休·昂纳(Hugn Honour)所谓 “契丹幻象”(Vision of Cathay)的舞台景观。
自1760年起,哥尔斯密在《大公纪事报》()上连载“中国人的信札”()。这部作品以旅居英国的河南人李安济(Lien Chi Altangi)的口吻,向北京的官员朋友分享伦敦的风俗人情与他的生活体验。格尔斯密的创作初衷,是想借用“中国”来启迪英国社会。在第二十一封信函中,作者通过李安济与黑衣人的交谈,比较了中英演剧传统的异同。
(李安济:)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喜爱看戏,但(两国的戏剧)在表演风格上截然不同。我们在户外表演,而英国人要在屋檐下演出;我们在白天开演,而他们要在火光的照明下献艺。我们的一部连台大戏可以持续演八至十天,一部英国剧作的演出甚少会超过四个小时。
除此以外,当李安济为舞台上的童伶从事了一项不入流的职业而感到遗憾时,黑衣人则回复,表演在英国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演员还能凭高超的技艺获得丰厚的回报。整体而言,哥尔斯密对中国戏剧描述,主要源于早期传教士与旅行家游记的相关信息,认识有片面之嫌,对戏曲的表演程式也存在误解(李安济声称中国戏剧没有“自报家门”的程式,这是哥尔斯密对传统戏曲表演的认知偏差)。《中国人信札》是“中国热”顶峰时期的产物,展示了英伦文艺圈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值得注意的是,格尔斯密曾在1759年观看墨菲的《中国孤儿》,他在信札中有意涉及对中国戏剧的介绍,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英国社会对中国风尚的误解与盲目模仿。而这些评述也侧面反映了英伦舞台的“中国热”潮流。
关于该时期英国的“中国热”,钱钟书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在18世纪,英国文学所反映的对中国的态度,恰恰与当时的生活现实相反。非常具有悖论意义的是,英国文学中对中国的仰慕情感已经开始退潮,但在英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却方兴未艾。”英伦舞台上各类充满中式情调的演出,正反映了这种“悖论”。英国观众对此类表演的追捧,依然停留在仰慕中式风尚的层面,光陆怪离的异文化景观则是“东方幻想”的舞台式呈现。
四、“他者神话”的裂痕(18世纪末)
在18世纪中叶之前,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尚未意识形态化,整体而言,他们秉持相对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中国文化。即使偶有英国人对中国的风俗陋习与官僚体制作出批判,也没有在英国社会形成风气。至18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发起工业革命,国家实力已跃居欧洲前列,对中国的扩张欲望也日益增强。随着清朝政府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摩擦与冲突的增加,英国的对华态度开始扭转。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缩紧开放政策,仅开放广州口岸对外通商贸易,加剧了两国的矛盾。有如休·昂纳在《中国热:契丹幻象》所言:“怀疑的种子一旦播下,质疑者们便催促着它生根发芽,不久以后,作为启蒙思想家理想天堂的契丹幻想轰然倒塌。”
随着“东方神话”出现裂痕,英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解读也由带有仰慕情感的“美化”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大航海时期,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大多是高尚、英勇的王公贵族。1773年,乔治·史提芬斯(George Steevens)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评注本,他将“契丹人”阐释为“小偷”(a thief),这与莎翁的初衷背道而驰。史提芬斯对莎翁时代“中国形象”的丑化解读,明显是受到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偏见、歧视的浸染,他的注解更直接影响了19世纪的英国学者。罗伯特·纳尔斯(Robert Nares)在编撰1822年英国文学词汇表时,就把“中国人”解读为“善于偷窃的恶棍”。
在此之前,旅华英人在介绍中国的演剧艺术时,他们的关注重点虽各不相同,但记录都是据直接观察而来,部分旅行家会对伶人的高超技艺表示赞许。1769年,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受邀参加广州十三行商总潘启官的家宴,他对宴席上的表演表示了赞许:“我们还观赏了一部战争题材的中国戏,(伶人)展示了许多精彩的打斗场面,当中的舞蹈与音乐比我预期的要更好”;对于变戏法、杂技与哑剧等表演,这位英国人在回忆录中表示:“这是我见过最巧妙的节目之一。”至18世纪末,随着英国人眼中“中国形象”的转变,英国人对中国戏剧与表演艺术的的评价已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演剧艺术的负面评价。
在1793年访华期间,马戛尔尼使团曾与清朝政府发生数次冲突,未能与乾隆皇帝达成通商协议,因此,使团成员在评价老大帝国时,不可避免的会带有消极情绪。而且,他们在观察社会风俗与文化礼仪时,常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标准,故对中国呈现出较为强烈的批评态度。关于中国戏剧的评价亦是褒贬相间,甚至毁多于誉。
为接待来访的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专门命张照与周祥钰等人“着重编写了一批与年节、时令、喜庆活动内容有关的剧目”,当中便包括备受学界关注的《四海昇平》。该戏以英使访华作为引子,在舞台上营造了“万国朝圣”的盛况,以此在外宾面前宣扬国威。然而,马戛尔尼却将这出承应大戏的内涵误解为“海洋与大地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the ocean and the earth)。在观看了一系列的宫廷演剧后,马戛尔尼认为:“虽然我们一定会认为中国宫廷的品味与风尚甚差,其中最高雅的表演即上述的几种形式,以及上午表演的几出蹩脚戏剧,但必须承认的是,整个演出还是营造出一种气势磅礴的效果。”约翰·巴罗对这些表演的批评则更激烈,他认为“京城的宫廷演出让人难以恭维”,更指出,“自从满族征服中国以来,宫廷的戏剧演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退化。”
相较于代表中国戏剧最高水准的宫廷承应,使团成员对民间表演的批判则更为激烈。巴罗对中国戏剧在表演时加入锣鼓的敲击声表示十分的不满,他认为舞台演出不更换场景的现场非常可笑。在巴罗看来,这些表演低级、粗俗,连英国小镇集市上的杂耍与木偶戏都比不上。马戛尔尼的男仆安德森(Aeneas Anderson)对中国表演艺术的态度则相对温和,他觉得中国的音乐缺乏和谐的旋律音,对英国人来说非常刺耳,但舞台戏还是存在一些可取之处。
巴罗在《中国行纪》中写道:“当英国使团离开英国时,我们对即将前往访问的这个民族抱着良好的印象。”然而,使团成员经观察发现,曾被视作启蒙模范的文明古国,实则是停滞的专制帝国,其国民是被奴役的民族,而且个性卑鄙、懦弱和爱撒谎。总而言之,东方帝国的文明程度与国家实力,根本无法与刚经历工业革命,实现生产力革新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英国相匹比。随着他们的游记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陆续出版,给英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转变历程中,英国舞台上的“中国形象”也由公主、贵族与汗王,降格为寡妇、仆人、小丑与魔法师等角色。“中国热”在欧罗巴彻底退潮。钱钟书指出,“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汉学在英国发展为一门专门性的学科,随着专业学者对相关课题所积累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时,普通大众对中国的关注却越来越少,这也是汉学专业化的损失。”
英国人对中国戏剧认识与态度的转变,与两国的实力转换、贸易往来与外交互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影。伴随国家实力的崛起,英国社会经历了从“仰望中国”至“俯视世界”的思潮变化,而由此反映的英吉利民族的“中国观”,主导了19世纪中英两国关系的走势。
结 语
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冒险家的航行轨迹编织出一张遍布寰宇的网络。世界各国逐渐建立起联系,东西文明开始对接。纵观世界文化交流史,英国虽不是最早与天朝建立联系的西方国家,但在“冒险”与“重商”民族精神的驱使下,英吉利却是最积极开拓中国市场的欧洲民族。
鸦片战争以前,明清政权长期实行“朝贡贸易”与“一口通商”的对外政策,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互动十分有限。中国戏剧因其“表演性”“文学性”与“社会性”等特质,吸引了赴华西人的注意,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欧洲的文人墨客从中汲取文化因子,用以阐释不同的政见与思想。不同于意大利对异域东方的猎奇想象、法国对儒教哲学的文化移植,英国对中国戏剧的认知主要源于外交官、商人与传教士的实地观察与记实。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化,贸易摩擦与外交冲突增多,英国率先在18世纪下半叶褪去“中国热”,旅华英人关于中国百戏杂剧的评述渐渐趋于贬斥与批判。这一变化由英伦辐射至欧洲诸国,改变了西人对中国戏剧的看法,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19世纪以后西方的“中国观”。
回顾19世纪以前英国人对中国演剧艺术的认知,他们的记载与评论是英国社会建构“中国形象”的素材,即时地记录下英国在近代化进程中,借“他者”之镜自鉴的历程。这些资料不仅有助于了解“中戏西传”的纵向历程,也为我们回看中英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