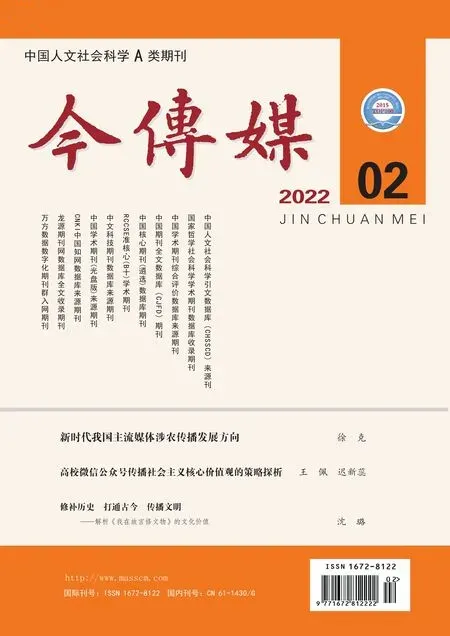“滇西小哥”短视频中乡土记忆的建构
2022-11-05杜积西
杜积西 孙 丹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
一、前言
近些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媒介在回顾历史、书写当下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媒介记忆作为记忆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也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媒介是一个不停述说的体系,是记忆在这一体系中从活跃到凝固、再从凝固到活跃的反复不断地激活和唤醒的过程。媒介记忆的书写是一个动态、系统的过程,相较于个人的认知记忆和仪式的身体操演,媒介对乡土记忆的传递具有更高的可回溯性、能动性和更大的储存容量。新媒体时代,人不仅仅是麦克风,还是行走的摄像头。无论是微博、微信,还是抖音、b站,人们在这些媒体上发布和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的短视频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是潮流。可以说,短视频逐渐成为了某些社会记忆书写和传递的重要载体。
相比于精美的电影和电视剧,短视频的“短时长”特点为用户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制作成本,同时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容易拉近短视频制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这对于乡土类短视频博主来说尤为重要。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逐渐被社会淡忘。在此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乡土主题类短视频开始出现,成为探究不同地域乡村人文风貌的一个窗口。这些短视频如何构建和传递一个地方的乡土记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
二、媒介记忆与乡土记忆
记忆是人类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不同群体也有所属群体的集体记忆,而社会也有自己的记忆,也就是社会记忆。保罗·康纳顿在 《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到,“我们一般认为记忆属于个体官能,不过,有些思想家一致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它叫做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社会记忆对于社会群体及其成员而言具有认同功能,而维持和传递社会记忆,则需要通过举行仪式或身体操演来完成。法国大革命后对国王路易十六的处死就体现了康纳顿的观点,即新政权的上台会用力打破和消除原有政权所孕育的社会记忆,并通过纪念仪式、活动、习惯等来塑造新的社会记忆,着力使这种社会记忆及其价值观神圣化与集体化。“这不是普通的处决,也不同于以往的保留帝国体系的国君的死亡,是一种公开的仪式,通过否定国王地位,让他的公共身份死亡”。然而,遗忘作为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和过程,使记忆的保存与传递受到极大的阻碍。但是,我们对记忆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对抗遗忘,还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并正确地对待过去与将来。人们对媒介的关注,不仅仅出于对媒介传播功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媒介对历史的记载,是我们回溯过去的关键。
媒介记忆是指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理解、编辑、存贮、提取和传播,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人类一切记忆的平台和核心,并以此影响人类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从古至今,不同形态的媒介在历史的书写和传递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加拿大传播史学家英尼斯认为,任何媒介若不具有长久保持的特性来克服时间,便会有便于运送的特点来克服空间,二者必居其一。媒介的本质是传递和保存信息的物质载体,回溯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媒介及其内容,为我们回顾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和便利。麦克卢汉甚至提出了大胆的论断——媒介即讯息。从莎草纸到互联网,媒体的形态不断地更新迭代,但是功能和性质却从未改变,即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汤姆·斯丹迪奇在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中写道,“乱七八糟的涂鸦与使用高级的莎草纸卷举行文学晚会的精英媒体系统相去万里。但是,涂鸦提供了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共用媒体环境”。正是通过研究这些残存的遗留资料,也就是底层市民房屋墙壁上留下的不知名涂鸦所传递的信息,才为我们今天研究那个时代下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留下了一个探险的洞口。
乡土记忆是乡村地域社会民众生活记忆和身体记忆的总和。一个村落、一座小镇都有属于自己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乡土记忆,对于家乡的记忆,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浓浓的乡土情怀。乡土记忆传递和维持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个体或族群认知记忆的维持和传递;二是地域文化活动或者纪念仪式的重复和强化;三是媒介记忆的重塑和书写。个人的认知记忆可以通过学习和观察来完成;纪念仪式和文化活动则通过在场的身体实践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操演,从而完成对乡土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重现、回顾和强化;媒介记忆的书写则表现为各种形态的媒介对乡土相关内容的记录和传递。
目前,学界关于媒介记忆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部分学者关注媒介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记录作用,这类事件主要包括“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汶川地震”等话题,此类研究的视角偏向宏大叙事,且多为历史研究,重点考察媒介对于国民记忆的塑造;另外,也有部分学者从社会记忆的总体视角出发,研究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媒介记忆、社会记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介记忆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书写载体。从已有研究情况来看,学界针对当前传媒环境下的媒介记忆研究相对单一,尽管存在一些对新媒体媒介记忆或数字记忆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多停留于理论探讨的层面,缺乏对媒介实践的具体考察。因此,本文以“滇西小哥”b站短视频的媒介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短视频媒介如何构建起地方乡土记忆这个问题。
三、“滇西小哥”短视频中乡土记忆的书写
“滇西小哥”是Bilibili视频平台 (以下简称b站)上一位知名美食up主,在b站共有87.9万粉丝,短视频作品获赞已达492.9万,到2020年5月为止已经拍摄了230个短视频;此外,“滇西小哥”在YouTube上共有728万订阅者。他的短视频总是不遗余力地挑选那些最能体现云南乡村生活和民风习俗的素材,为观众最大程度地还原和呈现真实的乡土记忆,不论是自然风光,还是风土人情,这些记忆文本总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童年和家乡的回忆。
(一)自然风光的刻画
云南简称滇,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历来就享有“彩云之南”的美誉。云南旅游业十分发达,这与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有着密切联系。大理的洱海、丽江的古城和雪山、泸沽湖的神秘仙境、香格里拉——最接近天堂的地方等等,这些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是我们对云南的习惯印象。而与之稍有差异的是,“滇西小哥”的短视频特色虽然也是使用自然风光作为转场,但却更多地体现了乡村的“声音”和“面貌”。无论是山间田野,还是羊肠小径;无论是荷塘蛙声,还是鸡犬相鸣;抑或是烈日骄阳、晨雾漫起、星河璀璨、云卷云舒。这些云南边陲的乡村自然风景,远离了城市喧嚣,静谧祥和中又带有一丝热闹生气,这种引人入胜、真实“贴地气”的乡土美景,在小哥的视频中不胜枚举。伴随着熟练的拍摄技术、运镜手法和剪辑技巧,小哥视频中的乡土风光便十分引人入胜,让观众在观看视频的时候仿佛跟随着镜头踏入了这现实图景,观众沉浸于这样的体验,对自己家乡的回忆和共鸣便油然而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两百多条短视频构成了一张乡土风光的画卷,短视频选取的只是部分乡村风景,但是网友透过屏幕里的浮光掠影,也能将这样的风景无限延伸、想象。老屋、小河、深山、果树、池塘、麦田等等,它们一起构成了云南传统村落的一部分。这些记忆文本唤起的是网友心头的乡土情怀,透过屏幕和镜头,我们记住了云南乡村的风光,同时也忆起了自己的“乡愁”。
(二)田间地里的劳作
对于城市人口来说,他们对于乡村劳作日常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书本、文字、照片和新闻稿当中。当李子柒带着影像视频,让乡村劳作进入广大网友的视线时,这种类型的视频内容文本便如雨后春笋般陆陆续续地出现在众多乡村生活类短视频当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类型,同时也是文字、照片的补偿性媒介,克服了传统媒介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图像、声音的综合,给受众带来更为沉浸式的体验。相比于文字和图片,视频对于乡村劳作生活的刻画更加直观、立体和真实。“滇西小哥”的视频当中,从来不乏田间地里的劳作,收豆苗、拔花生、挖土豆、打稻谷、捡蘑菇、摘水果、找野菜、采鲜花、晒玉米、放牛、捞鱼、捡田螺等农活画面,向观众们展示了乡村生活的辛苦忙碌以及乡民的怡然自得,深深地吸引着、感染着每一位观众。正如学者陈瑜提到的那样,乡土档案中的影像记录以图像和视听方式呈现了乡土中国的历史图景和人文风貌,对乡村记忆起着重构作用。“滇西小哥”的短视频通过对乡间劳作的“原生态”刻画,也成为建构乡土记忆的一个重要文本。
(三)熟悉的家乡味道
民以食为天。人类对于美食的追求从来都是无止境的,当然,美食对人类的吸引也从未消失过。《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陈晓卿提到,一些关于食物的记忆深深埋下了种子,历经数十年都难以改变。味觉记忆十分持久,可能人们脑海中对某个地方的印象已经模糊不清,但是那个地方的“味道”却总是绕上心头。2021年春节,许多人响应政策就地过年,虽然不能回到家乡与亲朋好友团聚,但是许多网友都收到了满载着“家乡的味道”的美食,并纷纷在朋友圈晒出了“妈妈的味道”。“滇西小哥”的短视频主打云南乡村的特色美食,比如爆炒田螺、蘸水辣、木姜子炖旱鸭、傣味牛丸、竹筒烧烤、杨梅醋拌米线、松花糕、鲜花饼等,几乎包含了大部分云南乡村的特色美食。从市场来看,许多美食博主将自己的节目定位于家庭日常美食、街头探秘美食、四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淮扬菜)美食等主要的几个美食板块,而乡村美食也是近两年才开始火爆起来。从地域上来看,这些乡村美食多集中于一些小城市或小乡镇,在细分市场上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地方,这给“滇西小哥”形成自己独特定位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前景,也恰恰是这一点为“滇西小哥”的短视频增加了独特的吸引力。
(四)和睦的邻里往来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用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特点。在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比石头丢入水中泛起的一层又一层涟漪,社会也通过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纽带构建起一张张关系网,这样的社会关系格局便被称为“差序格局”。在农村社会,这种依赖于血缘和地缘而构建起来的人情关系网更为明显,往往一个村落便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向外扩散形成的人情圈子。随着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但是也有许多传统村落更新的步伐转为缓慢,仍保留了原始乡村的魅力,那便是人情往来。在用大量钢筋和水泥浇筑起来的城市森林里,同一小区甚至隔墙而住的两个家庭之间,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永远不会有任何交流,这也是许多人认为城市是十分冰冷的陌生人社会的直接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讲,乡村社会更加像熟人社会,完成一次生产劳作、完成一道美食制作、完成一项重要仪式,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帮助与配合,这恰巧也是许多人向往乡村生活的重要原因。
在“滇西小哥”的200多条短视频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美食正是在亲邻友客的帮助下共同完成的。比如一家人一起做的团圆年夜饭,小哥和弟弟阿豪一起上山摘的板栗、下田抓的田螺;小哥和藏族阿奶一起完成的酥油;小哥和阿婆一起采的春天美味牛涩子尖;和邻居亲朋一起做的冬月年猪饭等等。除了制作美食,还有分享美食,小哥的乡村美食视频中人间烟火气的由来正是与一大家人围桌而坐,传递出的丰收、团圆的幸福和喜悦。在“滇西小哥”的视频中,通过对充满“人情味”的场景搭建 :家人的支持陪伴、亲邻的打趣寒暄,使得别样的人情互动成为了“滇西小哥”内容创作的一种独特风格,这种特色也构成了观众对云南传统村落的别样记忆。
四、“滇西小哥”短视频中乡土记忆的传播
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主要通过纪念仪式得以传递,而纪念仪式又主要是通过身体操演也就是“身体实践”来完成的。“滇西小哥”通过短视频刻画和展现出来的种种美食制作的“身体实践”和风土人情的“媒介再现”,正是对云南传统村落乡土记忆的传承与书写。短视频通过拼接与合成,将云南传统村落中的“风”“土”“人”“情”等记忆文本以影像的形式上传到媒介平台。在此基础上,用户对记忆文本进行阅读、理解和再生产、再传播,记忆文本得以借助互联网的巨大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样一来,以记忆文本的书写为前提,媒介记忆传播实践的完成,才在真正意义上使得乡土记忆的建构得以实现。
(一)弹幕、评论与用户再生产
除了建构记忆,媒介往往会囿于其他因素对记忆进行加工与重构。这里的其他因素,既包括媒介生产者的生产实践,也包括媒介消费者的消费实践。短视频博主往往会根据自身立场、目的、兴趣和能力的差异对记忆素材进行选择,观众也会根据自身的知识储备、见闻阅历和个人兴趣对媒介内容进行适当的补充、更正和评价。可以说,在本文的案例当中,短视频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起,在乡土记忆文本的传播实践中共同塑造了更为完整的乡土记忆。在b站这个以实时弹幕和评论为特色的媒介平台上,用户的生产力不容小觑。视频未能完整表达出来的意义和内涵,往往能在弹幕中看到补充答案。其中,那些点赞排名较高的弹幕及其二级回复评论,对人们理解乡土记忆的影响也越大。
在“滇西小哥”的短视频当中,弹幕和评论十分丰富。抒发感情感想类:比如“第一个镜头就美呆了”,“真好哇!我在大理洱海边上看小哥的视频,感觉小哥视频里的景色我抬头就看到了”;表达共同记忆类弹幕:比如“想起小时候家里也有”“看到大王喝牛奶我就想起以前村里的”;澄清刻板印象类弹幕:比如“不是所有云南人都重口味”“我惊呆了,云南人也这么能吃辣吗”;事实科普类评论:比如“‘撒’是傣语,是 ‘拌生’的意思;猪撒、牛撒、鱼撒、水果撒,每一款都独具特色,而最经典的还是 ‘牛苦撒撇’”“乳扇是主产于大理州洱源县的奶制品,又是特产,在大理市的喜洲镇、下关镇亦有出产,尤以洱源邓川出产为佳”。弹幕和评论在视频播放的同时在屏幕上滚动呈现,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特殊的阅读语境。短视频生产者发布的视频、弹幕和评论背后的其他观众表达的内容和观众对视频内容的自我理解,形成了一个意义交织和共现的文本。b站用户观看一个视频,不仅仅接收了视频博主所表达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接收了精彩纷呈的用户意见。正是视频、弹幕的相互配合和依存,才形成了完整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也完成了媒介内容的重塑。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媒介及其自身属性的不同对媒介所塑造的社会记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媒介接触的用户准入门槛降低,使得用户群体的影响无限扩大,媒介和群体之间的记忆相互交织和作用,重新构成了社会关于某些方面的记忆。
(二)媒介内容的跨时空流动
媒介对于云南乡土记忆的书写与传播,使得屏幕前的观众实现了“异地同愁”的情感体验。尽管“滇西小哥”的短视频主要涉及云南地方村落的乡土人情,但接收和观看其视频的用户却不仅仅局限于云南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子通过媒介记忆这个中介、平台和载体,唤醒了自己的“乡愁”。此外,“异地”不仅限于不同的省份,更意味着跨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国外学者Astrid Erll提出了“旅行记忆”(travelingmemory)的概念。他认为,“在当代社会,记忆的范围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记忆通过各种媒体以各种形式不停地传播和 ‘旅行’,并且不停地在时间和空间中被转换、重构”。“旅行记忆”的提出基于当今社会的全球化浪潮,记忆不再是单一维度的东西,它在旅行的过程中逐渐添加了新的元素。
“滇西小哥”在YouTube平台上有728万订阅者,共发布了220余条短视频,每期视频约有1000万播放量,也引来众多国外网友的围观,其视频下方不乏外国人对于云南乡村生活的评价和感受,这也印证了社会记忆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载体实现跨时空流动。例如,网友Lincy L的一条评论,“云南有最好的天气!我以前认为乡村生活方式都很相似,因为它很糟糕,现在我可以分辨出不同省份之间乡村生活的许多不同,它们都很棒”;Jiwon Hwang评论道:“我可以看到中国人有多么明智的烹饪技术和他们悠久的历史”。这些评论来自不同的文化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媒介所塑造的云南传统村落的乡土记忆。社会记忆借助媒介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在此过程中进行不同的建构,同时也构成了全球集体记忆的一个部分。
五、结 语
乡土记忆是一切关于乡村地域、生活、风俗习惯的记忆的总和,本质上来源于人们对于某一地域文化的记忆。有学者认为,保护乡土记忆和地方文脉,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留住乡愁”的当务之急。在惯性思维看来,城市化是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和潮流,通过观察现实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和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发展的难题之时,传统的地方村落跟不上现代化都市的发展节奏,乡土文化逐渐被社会忽略,而新媒介的出现以及国家实施的乡村发展战略,让古老的村庄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之中,甚至伴随着“直播+电商”模式的出现,给传统村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乡土记忆通过媒介的建构与书写,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更持久的传承。城市不断地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远离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但埋藏于每个人内心的乡土记忆和乡土文化的种子,伴随着新媒体这道曙光的出现,开始重新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