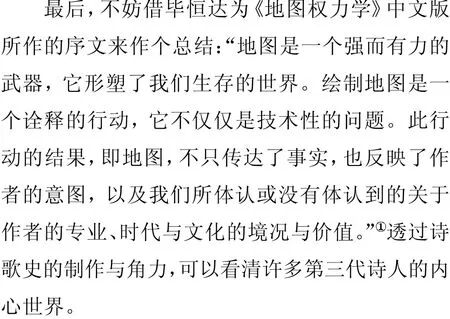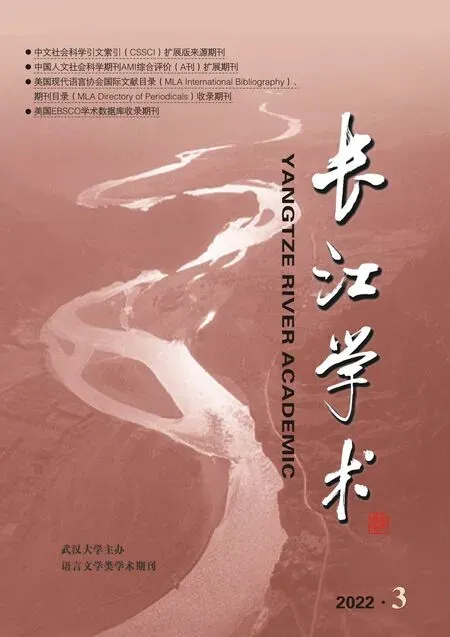论第三代诗人的诗史版图绘制
2022-11-04马来西亚陈大为
〔马来西亚〕陈大为
(台北大学 中文系,台湾 新北 23741)


诗歌史的撰写也是如此。每一部文学史或诗歌史的出版,都是一次诗史地图的重制与维护。这里说的“撰写”不限于诗史专书的撰写,而是一种更具有源头性的行动,包括“原始资料”的生产、将前者形塑成“诗史素材”的论述、诗史素材的强势编辑与营销,像充满战术目的的海量文字,不断向正史逼近、施压,好让正史绕不开这些能见度极高的“地景”,甚至亲自下笔将它正名成正史的一部分。
诗歌史的地图制成,即是这么一个饱含权力欲望和焦虑的过程,诗史撰述原非诗人分内的工作,他们是被评论者,撰史是史家的职责。第三代诗人在1980 年代后期彻底逼退了朦胧诗之后,却产生一股强大的“被篡位的忧虑”,1980 年代的两次后浪推前浪的裂变,让第三代诗人为自己在1990 年代的结局感到极大的忧虑。这股失势的危机感时时警示着他们随时为护位作战。他们一方面得适度压制后浪兴起,持续掌控诗界的发言权,守住主流诗人的王座;另一方面必须阻挡学院的评论力量介入诗史的版图绘制。
第三代诗人群使出前所未见的大战略:(一)以大量目的鲜明的自剖式诗论、诗学叙述、诗坛现象评述,主动进入有关1990 年代诗史的讨论;(二)制造大量“重要征引资料”,努力引导当代文学史(家)的评价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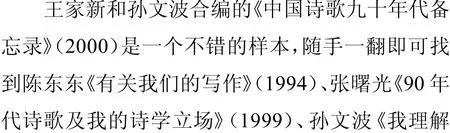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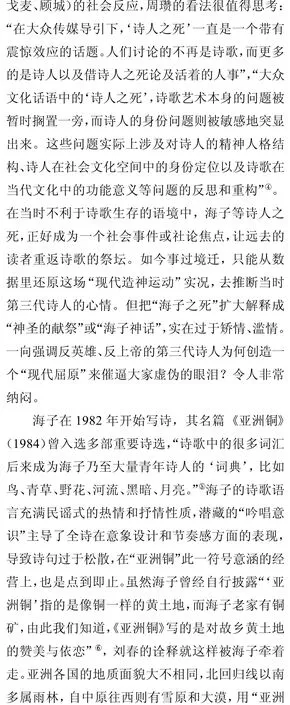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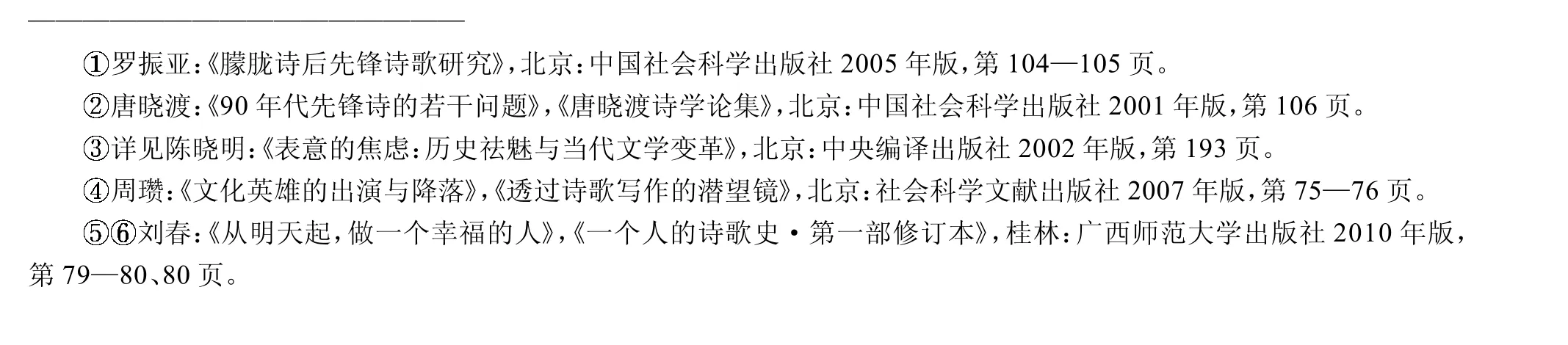


海子在卧轨前不久所写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春天,十个海子》,后来也名满天下,同样胜在旋律感,音色开阔,让人感受到面朝大海时的饱满阳光,也暴露了春天藏不住的黑暗,虽然这两首诗远胜《亚洲铜》,但还不能说是天才诗人的手笔,反倒是另一首《写给脖子上的菩萨》(1985)写出质朴、高妙的意境,是一首信手拈来的佳篇。
撇开无限量的缅怀、神格化的言论,单从最纯粹的诗歌艺术层面来看,海子的部分诗作达到第三代诗人的前端水平,却还算不上一个质量均衡的重量级诗人。即使在万夏和潇潇编的《后朦胧诗全集》(1994)中,海子被收入的篇幅也没有特别突出,从《亚洲铜》到《春天,十个海子》共24 首,排名第23;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2007)一书中,海子仅被定位为“新诗潮主要诗人”,完全没有提及断代意义;在金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2)中,海子的诗被定义为“乌托邦写作”,也没有论及他的断代意义。从诸多客观的选集篇幅和文学史论述角度来看,海子都算不上重量级诗人。他只有被用来断代时,才被赋予天才早逝的感慨和时代的象征性内涵。
其实,海子只是第三代诗人手中的一件道具。
海子的分量,在诗史地图上被有心人刻意放大,好比把一座映照着忧伤夕辉的土丘,放大成悲壮的山峦,进而成为具有神话意味的地理符号。在这里可以读到众多诗人的声音,形同绵密的等高线,强行撑高了海子诗歌的虚胖海拔。
不管实际/ 真实的情绪反应为何,以“海子之死”来断代绝对失之草率。而且极大部分诗人在创作表现上并没有因这一时间节点而产生风格或思想上的大变化。连大声喊话的欧阳江河也没有,一切转变就是渐进式的,“深刻的中断”只是被“某些文学史意图”归纳出来的假象。
二
其实,80 年代末成为诗歌发展的分水岭,“消费时代的来临”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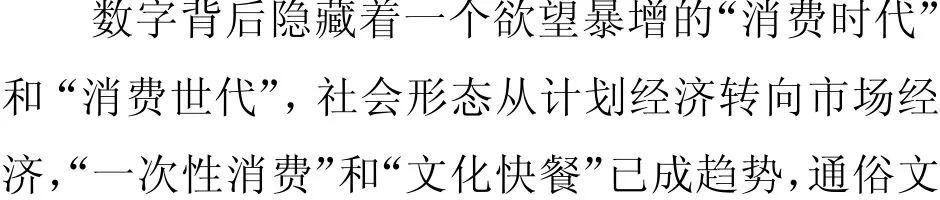


旧的时代拥立了诗歌,新的时代废黜了诗歌。
第三代诗人的无力感来自新时代大环境对诗歌的冷漠态度,这种冷漠态度迫使原本众声喧哗的诗坛冷却下来。不仅是诗歌,整个中国文学界进入1990 年代之后,作家地位和严肃文学的急速边缘化,创作者和学者们对这个高度消费化、物质化的世界感到茫然失措,遂产生一种“沮丧”的情绪,足以支配众多文化人的创作意识。欧阳江河的感受实为时间累积(1989—1993)的结果,以“海子之死”为断代,真正目的是为了将1980 年代“完整终结”,让1990 年代“从头开始”,像是表达倾家荡产后誓言再起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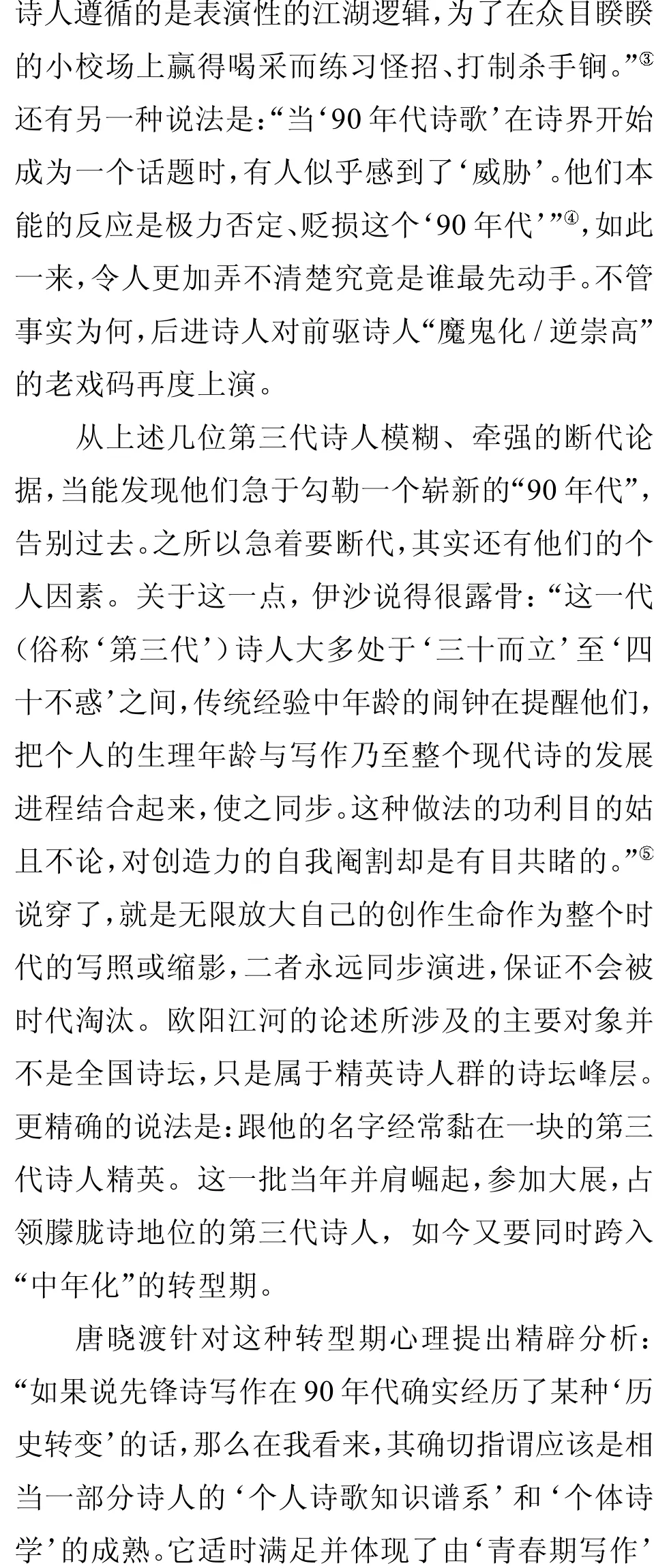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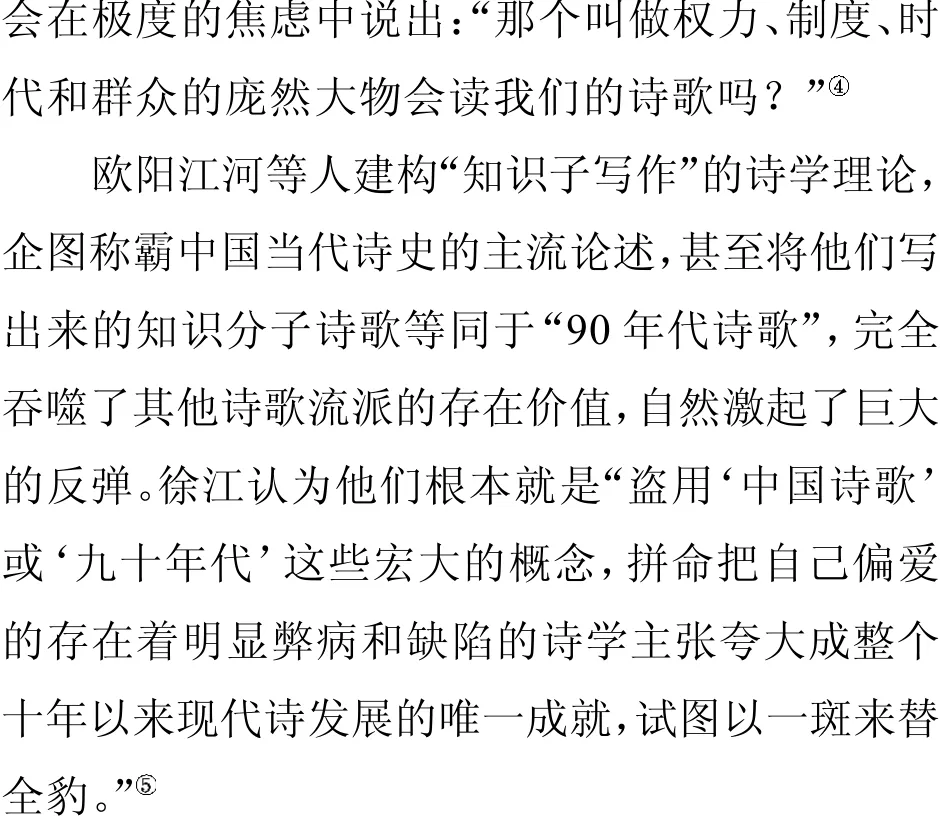
斗性很高的第三代诗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另一批以于坚为首,张扬“民间立场”的诗人,遂展开他们的“反知识分子作战”。
于坚在1996—1998 年间提出“民间立场”,结合对普通话的反思,他认为:“随着知识的开放和丰富,僵硬的知识也到了强弩之末。一个生活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市民的中国重新获得恢复,自然也有柔软的东西开始在诗歌中滋生。在中国,柔软的东西总是位于南方,女人、丝绸、植物、阳光和水、软绵绵的诗歌。例如在南方诗歌于八十年代出现的日常口语的写作,就是对坚硬单一的普通话写作造成的当代诗歌史的某种软化。”在他看来,作为当代中国诗歌发展重心的北京,象征着知识化和阳刚化的诗歌写作向度,唯有南方民间诗人那种柔软的方言写作能够突破前者的僵局与霸权。不过他(们)对“民间vs. 知识分子”议题的讨论太过情绪化,两大阵营的战火终于在1999 年4 月16—18 日的“盘峰诗会”全面引爆,双方正式决裂,诗友之间因理念差异而不断相互攻伐,以致翻脸绝交互相攻击,乃至官司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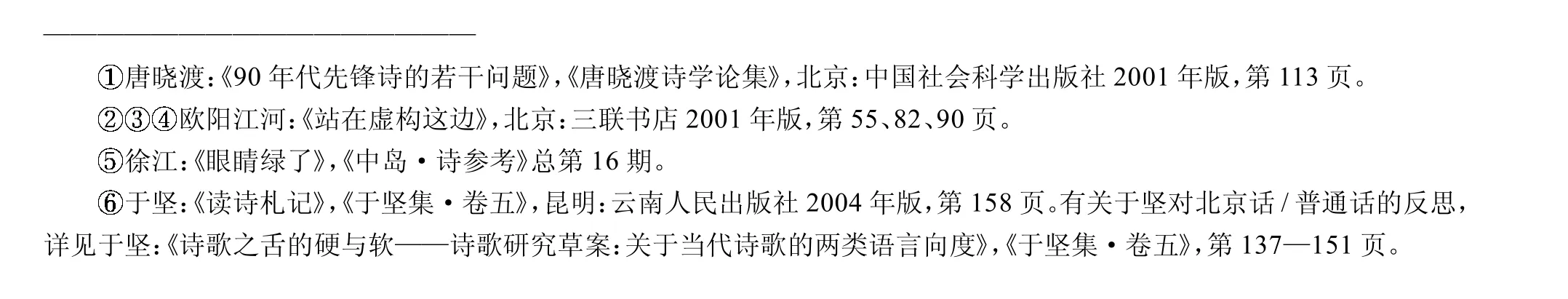

三
“90 年代”的话语权争夺战之外,还有另一个战场:诗选。
撰写诗史是一种制图,编辑诗选也是一种制图。



这几部重要选集面世之后,程光炜编《岁月的遗照》(1998),臧棣主编《1998 中国最佳诗歌》(1999),杨克主编《1998 中国新诗年鉴》(1999),孙文波、臧棣、萧开愚编《中国诗歌评论——语言:形式的命名》(1999),萧开愚、臧棣、孙文波编《中国诗歌评论——从最小的可能开始》(2000)等多部诗选又陆续出版,权力争霸的狼烟四起,令人眼花缭乱。
2004 年5 月,长期被“诗歌群体运动”(以此为论据的当代诗史)冷落的一批1960 年代出生的中间代诗人,如安琪和远村,为了争取本身的历史版图以及历史的发言权,与70 后黄礼孩合作编选了一部厚达2560 页(分上下册)的《中间代诗全集》(2004),收入了82 位诗人的2200 多首诗作。这部以“数大为美”的超级诗选,对那些长期被第三代和70 后上下夹击的中间代诗人而言,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发声机会。在页数上,它确实超越了对中间代诗人产生长期压迫的《后朦胧诗全集》,令人无法忽视。
这些非主流诗人的聚集,或许能够填补诗史的史料缺口,却无法达到诗史版图的洗牌作用。没有理论锐角和颠覆成分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在当代中国诗坛只能沦为无声无色的“中庸之道”,这并不是群体作战或孤军作战的导因,而是诗歌本身的特殊性使然。翻开两位《中间代诗全集》主编安琪和远村的诗作,就可以印证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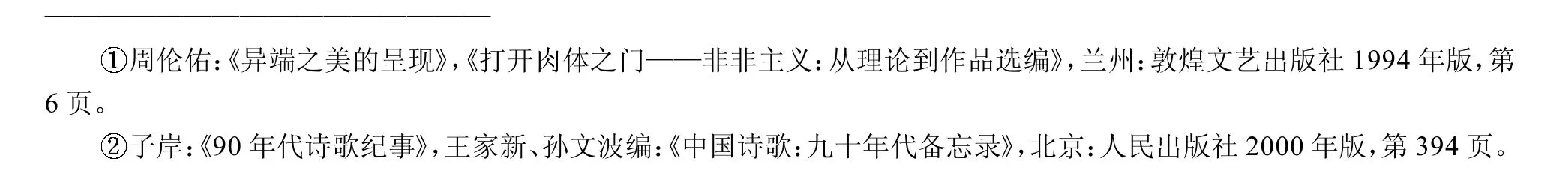

这种透过编辑重要诗歌或诗论选集,“私画”文学史地图/地盘的手段,蔚为风潮,2000 年以后各种诗选如春笋丛出,选文范围也扩大到第三代诗人以外,无形中抵消了某些(另有所图的)选集的聚光效果,这个策略就不管用了。第三代诗人对文学史的焦虑,原本只是圈子里的谋略,他们打从心里瞧不起的学者并非同路人。朦胧诗人虽然老早被排挤出诗歌圣殿的圆桌席次之外,但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尤其在国外掌握出版资源的北岛,结合留美学者的学术力量,卷土重来,直接介入文学史的写作,从1991 年开始展开重写文学史的行动。诗歌史地图会在不同目的的绘图者手中,不断重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