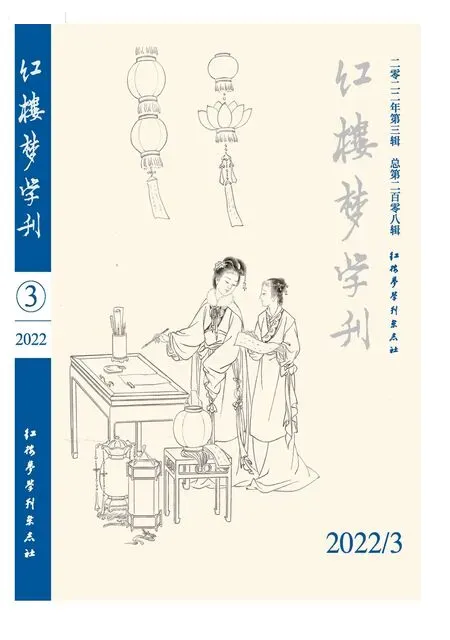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小议
2022-11-04王丽华
王丽华
内容提要:受鲁迅红学观点影响,张天翼在研究红学时将鲁迅的观点进行了延伸与细化。他抓住贾宝玉出家这一主线,对《红楼梦》的悲剧性进行阐释,并将这种阐释与他的文学主张如写实、典型化等密切联系起来。张天翼研究《红楼梦》的目的在于“解释这痛苦的来源”。但是,张天翼过于关注《红楼梦》的写实,不自觉地忽视了《红楼梦》的哲学品质。
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一文于1942年11月15日发表在《文学创作》月刊,1945年,与王昆仑(太愚)的部分人物论文章、金果《杂谈红楼梦》以及东郭迪吉《袭人的身份》诸文组成合集,以《贾宝玉的出家》为名,在东南出版社出版,由史任远(李品珍)作长序。
张天翼是我国著名作家,在文学的漫漫长河中,作家研究《红楼梦》举不胜数,如鲁迅、老舍、张爱玲、张天翼、王蒙、李国文、二月河等,他们或有专文论述,或有研究专著,成果卓著。作家研究《红楼梦》,其本身即是创作者,又是研究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他们的观点也备受关注。近年来,对于他们的研究之研究也在学术界盛行起来。
有部分著红学史的学者对《贾宝玉的出家》一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如郭豫适认为这篇文章“正确地提出了‘说明总不如表现有力’的观点,并且依据这个基本观点着重分析了小说实际描写上的现实主义成就”;陈维昭认为该文“继续着王国维关于《红楼梦》的伦理价值的话题”,但“避免了王国维那种简单化处理方法”,“采用了具体分析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具有“开创意义”,这种方式是“现象描述与分析方法”;白盾认为该文的特色在于“用轻松、诙谐的语言,由浅而深地探讨了一些重大问题,做到了‘深入浅出’”。陈维昭与白盾均涉及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的方法问题,只是一为研究方法,一为写作方法。
笔者认为,在诸多作家研究《红楼梦》者中,张天翼关于《红楼梦》的著述虽不多,但有其独特之处。本文拟以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为研究对象,针对这篇论文产生的背景、观点等进行探讨。
张天翼首先是一个作家,一般来看,作家研究《红楼梦》往往是与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他们多以自身创作经验和文学主张去观照《红楼梦》的研究,故而梳理张天翼在写作《贾宝玉的出家》之前的文艺思想对于研究其红学观点非常必要。
张天翼很早就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小说。在他的《我的幼年生活》一文中,他回忆自己的家庭以及学校,并提及他的早期阅读,其中包含商务印书馆的童话,以及《岳传》《杨家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彭公案》等。在谈及自己如何做人物描写的时候,他也曾提及在他小学中学时候因喜爱阅读小说,知道了马二先生、凤姐、阿Q等人。但幼年时期的张天翼是跳脱的,诙谐的,好动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自1922年起,张天翼就开始创作滑稽小说与侦探小说。对于滑稽小说,张天翼将之定位为“寻开心的”,目的是“有益于身心”。但在此一时期,张天翼已经意识到生活经验对于创作的影响。张天翼在《小说杂谈》中写道:“我年幼识浅,做起侦探小说来,难免有些不对。”
不久以后,他的文艺思想有所转变,这个转变是以短篇小说《噩梦》为代表的。到1926年的时候,他的这种转变倾向已经非常明显,此种转变或许受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影响。黄候兴在《现实主义的深化》一文中写道:“告别未庄文化,是张天翼走向艺术自觉的开始……逐渐意识到作家对于人的精神解放应尽的特殊责任。”从这时开始,张天翼转而认为文学应当真实地反映人生、描写人生。
这种主张,体现在张天翼创作的态度中,他认为思想与生活经验是创作构成的两个要素。从思想来说,自然是共产主义。1927年初,张天翼在北京大学已经接触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学说,并开始信仰共产主义。至于生活经验,则源自于他的写实主义理念。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李大钊等文学革命先驱就已经打出了写实主义的旗帜,后继者如邓中夏、恽代英等,均有相似表述。对张天翼影响最大、被他视之为老师的鲁迅先生,更是提倡现实主义。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呼吁:“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这也可以视作鲁迅对文学提出真实摹写的要求。由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这其中也有着变化,陈维昭认为:“由‘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其间实质性的变化是‘人民性’概念的引入。”
对于这两个要素,张天翼的排列是有顺序的,他将思想放置于生活经验之上,充分显示了张天翼的创作态度,这种态度在他参与1932年由左联发起的“文学大众化问题”讨论的征文时有过充分表述:
所谓文学革命是造成小白脸文化的,它一面打倒“吃人的旧礼教”等等,一面造出些唱“德先生”“赛先生”,讲社交公开的小姐少爷们。……
可是大众并不停止在小白脸文化上。大众是突过了这小白脸文化又前进了。因此,一种比小白脸文化更进步的文化就应运而生:大众文艺是其中的一种。
这是张天翼认知中文艺进步的方向:文艺应当为大众服务,而且需要去适应大众。为的是给“大众解释这痛苦的来源,使大众知道自己的出路”,以及“是不是有掀翻我们头上的双重压迫的可能,其次,要怎样去掀翻”。
张天翼的创作紧紧围绕这一目的而来。自他1931年在上海加入左联以后,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如《速写三篇》《二十一个》等,包括张天翼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均用漫画的笔法,寥寥数语间给予人物一个定型,而后挖掘其灵魂深处的种种活动。这是张天翼的特长,这也源自他对生活、社会的深入观察和思考。速写三篇中的《华威先生》刻画了一个挂着抗日招牌,而又只会争夺领导权的官僚形象,这正是当时的一个人物典型。其后发生的关于《华威先生》日译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张天翼塑造这个典型形象的成功。
张天翼是左联中非常活跃的作家,创作之外还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如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湖南抗敌总会组织的宣传委员会、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大力宣传抗敌主张。同时张天翼还将自己的创作理念形成文字,以起到影响和引领他人的目的。张天翼在1939年的《观察日报》上发表的三篇“习作杂谈”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考。这三篇文章从创作的角度,谈到了典型人物、典型生活、素材来源等的关系,反复强调对一个人物要“挖掘到他的深处,写的时候当然就表现出我们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对他的批判”。这也是张天翼自我创作经验的总结。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张天翼是非常重视典型论的,同时也注重文艺创作的批判性。可以说张天翼的创作、活动以及文艺理论的总结均有涉及,三者之间,是互相结合的。
通过前文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张天翼的创作中有着明确的目的,他倾向于写实,并且注重典型化,注重对人物灵魂深处进行挖掘,同时这些特性也反映在他的评论文章之中。
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多数红学史家以此为新红学的肇始。在研究方法上,胡适偏重于考据,新红学也因此呈现经史之学的特质。此种研究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仍不是文学本身的理解与批评”。在此时期,有部分学者将《红楼梦》放置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承袭王国维一脉,如佩之《红楼梦新评》,吴宓《红楼梦新谈》,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等等。至20世纪40年代,有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以及太愚的人物论等,均属此类研究的范畴。
1942年的秋天,张天翼因长期工作劳累,肺结核病突发进入第三期,因而辍笔多年。同年冬天,《贾宝玉的出家》《读〈儒林外史〉》发表。从现有资料来看,我们还无法判断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
张天翼研究《儒林外史》并不奇怪,因为他的创作本身就与《儒林外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他为什么研究《红楼梦》却并无明确记载。笔者以为,此应与鲁迅先生有着很紧密的关联。从读《阿Q正传》转变文艺思想,到鲁迅给他发表《三天半的梦》,再到左联时期共同的经历,鲁迅对张天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从创作的角度,这样述说二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文坛上,有好多作家刻意学鲁迅,或被人称为鲁迅风的作家,但是称得上是鲁迅传人的只有张天翼。无论在文字的简练上,笔法的冷隽上,刻骨的讽刺上,张天翼都较任何向慕鲁迅风的作家更为近似鲁迅。
张天翼对鲁迅的摹仿是多方面的,从文艺思想,到创作,到信仰,处处都能看到鲁迅的痕迹。
鲁迅对《红楼梦》的看法多散见于各种文章之中,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专篇论述,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据张晓磊统计,有《论照相之类》《读书杂谈》《谈金圣叹》等24篇文章涉及《红楼梦》。由此可见鲁迅对《红楼梦》的重视。由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阐释角度,我们也可以大致勾勒出他的关注重心:他更侧重关注《红楼梦》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并均有精到论述。比如他提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以此来观《红楼梦》悲剧性的社会意义,这些观点,至今读来仍有指导意义。
对于贾宝玉的出家,鲁迅也曾提出很明确的观点: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墨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
这些观点,或者都是刺激张天翼作《贾宝玉的出家》的出发点。
又如“团圆”,这种思考源自于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曾以《红楼梦》续书为例,专门论证“团圆”问题,称其为“自欺欺人”之举。张天翼对于团圆主义的作品也有批判:“团圆主义的作品虽然有新旧,但老实说,其拙劣是一样的。把事实掩蔽起来的空想的作品,就是有了所谓积极性么?”
鲁迅先生对于焦大也有着独特的思考。他认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可以称之为“贾府的屈原”。对于贾政,鲁迅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提出部分读者会“占据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厉害的打算”。这种论述,与“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是一脉相承的。而这些内容,恰恰在《贾宝玉的出家》一文中都有反馈。
鲁迅对《红楼梦》是非常熟悉的,每每谈及,总有精妙评述。然而鲁迅先生作《红楼梦》评述,大多并非为《红楼梦》而作,都有手挥目送、注此写彼之用,均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评述《红楼梦》之于鲁迅,更多是起到佐证的作用,这是建立在鲁迅对《红楼梦》的深刻认知之上的。如上所引数条,亦可视作他对写实的倡导、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借焦大以引出对新月派诸人的批判等。
鲁迅的这种研究理念,对张天翼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从内容上来讲,《贾宝玉的出家》一文,可视作张天翼对鲁迅红学观点的细化论证与延伸阐释。
如张天翼对于贾政的评论:
他的确是个极可钦佩的长者。作者每一写到了这个人物就用上了很严肃的态度,怀着了很大的敬意。这贾政为人又非常正直,真可以做得一个表率。在外面做事,他真心真意照他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做个好官。在家里,则真心真意照他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做个好儿子和父亲。于是他养成了些合乎这些标准的脾气:严厉,方正,冷板,固执,等等。
在《贾宝玉的出家》一文发表时期,张天翼对贾政的评论是很独特的。其原因在于贾政与贾宝玉之间被人为地贴上了好与坏的标签,贾宝玉是被读者所欣赏的,因此贾政就是被批判的。这种方式将文学作品做了简单化理解。张天翼从人性的角度来解析宝玉挨打,他认为这一切源自于贾政的“爱”,成因则在于“他们有爱,而缺少彼此的了解”。这种解读模式,是非常有深度的,而且是符合人性特点的。不再和别的作家一样,是简单的二元分析,而是挖掘到人物的“灵魂深处”。这种深挖,也显示了张天翼对于人物复杂性的理解。这也正是张天翼的创作主张。在《作者的态度》一文中,张天翼说到:
事实上,一个作者不会象陈独秀先生们的论帝国主义一样——对凡是坏人就认为是一色的百分之百坏,而好人就认为都是一个模子印出的圣人。事实上,作者对他的人物决不是一憎恶起来就憎恶得要死,而一爱起来就一定非眼泪鼻涕直流,弄得连抓笔的手都软绵绵的不可。
这个论述明显就有着鲁迅先生的痕迹。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曾从写实与技法的层面提出《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如实描写”“并不讳事”,从而打破了“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脸谱模式写法,所述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二人对于此部分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而正是这种创作主张,才会使得张天翼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评论小说中的人物,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我们可将此视作张天翼对鲁迅观点的细化论证。
实际上,在《贾宝玉的出家》一文中,与此类似论述的地方有许多,如对于续书的观点、焦大的评价、曹雪芹的创作观,等等,均可在鲁迅先生的观点中找到出发点。乃至于张天翼创作此文的目的,也与鲁迅先生之对于《红楼梦》的运用有相似之处,待下文详析。
除却鲁迅的影响外,张天翼为什么研究《红楼梦》?这自然与《红楼梦》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天翼很重视古典小说,在《谈人物描写》中,张天翼写道:
一个伟大作家去发掘出这些人性,写出这个典型人物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迹,这就是我们先前谈起过的——那个人物直到现在还活着。他不单是存在于过去的时代,不单是存在于别的民族,而且还存在于现在,存在于我们这民族:我们的弟兄朋友之中就有这种的人物。凭这些方面,一个读者即使把那个人物当做同代人看,用他自己的看法而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也还是一样的公平。
张天翼从人物典型化的角度,来谈名著的当代性问题。在他看来,名著的现代解读,仍然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人性的共通,来源于名著对于人性深处的挖掘和探讨。《红楼梦》自然在此行列当中。在张天翼看来,“现世”描写是《红楼梦》的重心,他认为《红楼梦》是写实的。解析《红楼梦》中所表达的真实,以及贾宝玉的出家进程,是为了探寻这“痛苦的来源”,以及探求“出路”问题。这种写作目的与鲁迅的创作之间极为相似。
同时,张天翼深谙内容之于形式的关系。他认为“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内容譬如是人。形式呢是衣裳:长短大小,都要合上这个人的身材”。由此出发,张天翼才会抓住《红楼梦》的主体内容是描写世间事,是一个“两头轻,中间重”的模式,而这重的部分,偏偏是“作者自己所否定的东西”。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张天翼思考的起点。这种观点当然与张天翼对于文学的主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两头轻”,则表现在《红楼梦》的一头一尾上。关于“头”“尾”,张天翼有着明确的创作主张:
因此,我以为——要是拿旧小说那种开篇法做标准,不是那种格式就不得名之为“有头有脑”,则现代作品确有许多是“无头无脑”,要是就那头脑的性质、作用等而说……
请你不要对这种要求发笑,我们的有些批评家,在指导我们创作之际,也曾掏出过一条尾巴插在那里,教一切小说剧本都跑到它那里作结,才算交了差那条尾巴,虽然是用些别的词儿代入“中状元”“成亲”等字样,但都是属于同一血族的,族名曰“大团圆”主义。
不过,认真的作者总不肯上这个当。千篇都用这么一条尾巴,省力固然省力,又会博到“正确”“有积极意义”等好评,但作品本身丧了元气,成了僵硬的东西了。
由此可以看出,张天翼对于传统小说的“头”与“尾”,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太过于僵硬,从而使作品本身“丧了元气”。而《红楼梦》的一头一尾,也在被批判之列。他认为曹雪芹本身的描写着力于真实世间,是“着眼在现世因缘:把因因果果抓得紧紧的,一步一步合理地发展下来”,并“粘住尘世生活”,如此就将“尘外的一头一尾弄得失了色,甚至于一点力量都显不出来”。如此,张天翼的思考重心就转到了《红楼梦》对现世的描写之中,而忽略了“梦”“幻”等内容。
贾宝玉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出家,而他的出家,源于他的苦痛。这是张天翼的论断,也是他解析“痛苦的来源”最重要的部分。
在爱情的角度,张天翼论证了宝黛之爱的性质,能够理解贾宝玉,同情贾宝玉的,“只有一个林妹妹”。宝黛之间是知己。然而这种爱情的不能圆满,来自于薛宝钗的冲击。薛宝钗在“别人身上做了功夫,所以她成功了”,而林黛玉则“只会一味在贾宝玉一个人身上做功夫,所以她失败”。基于这个过程性论证,张天翼得出贾宝玉恋爱悲剧的深层原因:
这么着,这主人公之所以闹了恋爱的悲剧,那根本原因就不仅在恋爱本身了。即使他婚事遂意,说不定他仍旧会有他的苦闷。
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跟别人的不同。可是他实际上又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于是他被限制住,束缚住了,不能自行发展。他在这里绕来绕去总没有个办法。
人家总是要勉强他按照一定的模子去做人,再也不容他有第二条路。可是他办不到。
由于这一点,他跟林妹妹能够相爱。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终至全盘失败。
张天翼认为,贾宝玉的悲剧,起源于他的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是贾宝玉与贾政、贾母等所代表的人群的不同,而结果就是“一个不肯庸俗的人,往往会不见容于世”。因此,贾宝玉的出家就成了必然。
之后,张天翼继续分析贾宝玉出家的本质。他认为贾宝玉的出家的出发点,是为了“摆脱他个人的苦恼”,他仍然执着于这个世界。笔者看来,这个论断是非常有深度的。在这篇文章的题记中,张天翼引用了《金刚经》中的“我相”“人相”“众生相”等佛教词汇,他也正是以这些词汇,来论证贾宝玉出家并非是“断惑证理”,本质上是“退”,而非如“瞿昙”(释迦牟尼)一般是为了追求真理。
张天翼在这个“退”字上,是颇下功夫的。《红楼梦》在叙事上用了仙凡的双重叙事构成手法,从而达到了虚实相映的艺术效果。从小说文本而言,“凡”“实”是表达最为充分的部分,贾宝玉正是存活于这个空间之中。在这“凡”“实”之中,曹雪芹表达了贾宝玉的无奈、坚持与挣扎,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最终将贾宝玉推向了世外。钱穆将《红楼梦》视为“求解脱”之文,这个“求解脱”即是说贾宝玉,也指向了曹雪芹。然而无论如何求,这个世外的解脱仍然呈现着无可奈何之意味,以“退”味之,也是非常合理的。
基于这些论述,张天翼来探讨曹雪芹的创作思考,认为曹雪芹处于矛盾之中,情感与理智表现得并不一致,因而《红楼梦》也具有了双重性:“非悲剧,亦非非悲剧。”非悲剧,当从曹雪芹的创作主观来谈;“非非悲剧”则是从文本的客观存在而言。
《贾宝玉的出家》一文在整体的架构上是颇具匠心的,文章闲言很少,且均围绕着《红楼梦》的悲剧性进行探讨,间或有对人物的评论,对曹雪芹创作思考的探讨,均服务于悲剧性这一核心主题。而这正是“痛苦的来源”,以及创作时代的现实中的“悲剧”问题。
在整体的论证过程中,张天翼试图构建一个逻辑脉络,用以清晰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认知与思考。之所以不嫌絮烦,去提炼《贾宝玉的出家》的文章脉络,是因为在张天翼的论证中,是环环相扣、逐步深入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整呈现出张天翼的表述逻辑。在这个表述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张天翼是从《红楼梦》的文本出发,穿透《红楼梦》的缤纷繁复描写,化繁就简,抓住贾宝玉出家这一主线,来探讨《红楼梦》的悲剧性以及曹雪芹的创作思考。这种敏锐的文学感觉,来自于他的大量阅读与长期积累的创作经验,以及他的反思。在《贾宝玉的出家》一文中,有许多观点均来源于此。
张天翼在作具体文本分析的时候,擅长于抓住对立面,从二者不同之处,去解析情节的发展、作者的思考。如分析贾宝玉的与众不同,则会抓住贾政的方正;分析林黛玉专注于贾宝玉,则会抓住薛宝钗专注于贾宝玉周边的人;分析贾宝玉的出家是为“退”,又会以瞿昙的追求真理的出世为比较对象。张天翼又惯用引申之法,去引导读者去思考何为“圆满”,何为“成功”。如宝黛“结合”之后又如何?如“宝玉出家之后怎么样”?这种种设问,都将读者引入到他的思考语境之中,此种做法颇得《娜拉走后怎样》之妙,从而将一个小说文本问题导入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什么是悲剧?什么是成功?什么又是圆满?而后,他再通过对《红楼梦》的解读,给予读者答案。这种解读范式,将文学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广阔的阅读空间。
张天翼有着敏锐的文学感觉,这在他作文本分析时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善于观察社会、人物,当他将这种能力放置于文学研究的时候,就会展露得淋漓尽致。如他认为史湘云虽“豪爽的可爱”,然而终是“有点俗骨”,又如他对贾宝玉的判断“最高的还是他自己”,再如他对焦大的醉骂“愤怒里还带着痛心”,等等,这些评论均是深入到人物灵魂的。史湘云虽有魏晋之风,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价值体系,仍然会受人左右;贾宝玉的“意淫”是他的本性,虽由心而发,最为真挚,虽是体贴别人,但归根结底却是满足于自我之心;焦大并不会成为一个反叛者,而只会成为一个怒其不争者。如此种种,都建立在张天翼对“真实的人生”以及“真实的灵魂”的创作追求,以及他对于典型化的理解之上。这种追求反映在文学评论中,就成为对人物内心的深层挖掘。
罗炯光在《张天翼文学批评的流变与特色》一文中,曾将张天翼的文学批评特点总结为:会心、精到与本色。笔者甚为赞同。此三者在《贾宝玉的出家》一文中,都有着充分的展示。当然,这种种特点是建立在张天翼将文学作品放置于文学研究的本位上形成的。
张天翼的另一大批评特点是感性与理性的充分结合。此点在他分析宝玉挨打部分时有体现:他在感性上,对于贾政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又从理性分析上得出他们的冲突在于“缺少彼此的理解”,而本质在于两种世界观的不同。这种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使得他抓住了冲突的本质,使得思考更加深入。
张天翼对于《红楼梦》的阐释是文学的。但需要说明,这种阐释是基于读者本位的。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他贯穿的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文中有对曹雪芹创作思考的阐释,但这种阐释,是由文本出发的,如他抓住了曹雪芹在创作中的摇摆:
一个诗人如果——常常是出于不知不觉的——不能真正跳出他个人的“我”,如果他对某一人生相的或爱或憎等等,只是从他个人的种种关系出发的,则他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态度,往往会与他所知证的真理的态度不一致。
这种对于摇摆的判断是非常精到、准确的。但是,他并未将“情”之于曹雪芹的重要性,以及“情”在这种摇摆中的作用提炼出来,他仅从写实的层面,从婚姻及家庭的角度分析贾宝玉的不得不出家,这固然达到了张天翼的创作目的——“解释痛苦的来源”,然而这种解读,却在不自觉中弱化了曹雪芹的思考,缺失了对《红楼梦》的哲学品质的探寻。
这种弱化,实质上是将冲突简单化的过程。张天翼以婚姻的是否圆满,取代了贾宝玉对于“情”的认知过程,从而将“情”单一化为“爱情”,继而将“情”的毁灭给消泯,使得《红楼梦》的悲剧性也被弱化。
罗炯光也注意到张天翼文学批评中的简单化问题,他认为这种简单化的批评源自于左倾思潮的影响,这种评断是公允的。罗炯光通过张天翼对阿Q的评论为例阐释这一点:
把阿Q性格形成的原因,一股脑归于地主阶级思想的毒害,完全否认其阶级出身与具体经历的影响。
张天翼对于《阿Q正传》的简单化批评,与《贾宝玉的出家》中的简单化批评是如出一辙的。
综上所述,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一文,与鲁迅先生的红学观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笔者认为张天翼对鲁迅红学观点进行了充分的细化论证与延伸阐释。同时,基于读者本位的解读,张天翼不免在《红楼梦》研究层面上还有一定的缺失,比如对《红楼梦》哲学品质的探寻等。但是,瑕不掩瑜,张天翼之于红学研究,其独特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① 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页。
② 陈维昭《红学通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③ 白盾《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页。
④ 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原载《文学杂志》1933年第2期,转引自《张天翼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10页。
⑤ 张天翼《谈人物描写》,转引自张天翼《张天翼论创作》,第184页。
⑥ 沈承宽、黄候兴、吴福辉《张天翼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张天翼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⑦ 张天翼《小说杂谈(二)》,原载于《星期》1922年11月26日第39号,转引自《张天翼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⑧ 黄候兴《现实主义的深化——张天翼小说创作的演进》,转引自吴福辉、黄候兴、沈承宽、张大明编《张天翼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⑨ 张天翼《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转引自张天翼《张天翼论创作》,第5页。
⑩ 鲁迅《论睁了眼看》,转引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1][12] 张天翼《文学大众化问题》,张天翼《谈人物描写》,转引自张天翼《张天翼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13] 茅盾先生在《八月的感想》一文中曾回忆“受到不少读者的来信都是对于《华威先生》感到很大的兴味的。”指摘“《华威先生》太谑画化”。1939年,林林在《救亡日报》中发表《读〈华威先生〉到日本》一文,文中提到“这种人型刻划出来,是很有讳言的创造”,但“他出现在日本读者的面前,会使他们更把中国人瞧不起”。
[14] 张天翼《张天翼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9页。
[15] 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吕启祥、林东海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3页。
[16]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转引自沈承宽、黄候兴、吴福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页。
[17] 张晓磊《鲁迅红学研究综述》,《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2辑。
[1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转引自《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19]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转引自《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20] 鲁迅《论睁了眼看》,转引自《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21] 张天翼《关于三个问题的一些拉杂意见》,转引自《张天翼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22] 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转引自《鲁迅全集》第5卷,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23]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转引自《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48页。
[24][25][30][32][33][34][35][36][38][41]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原载《文学创作》月刊1942年11月15日第1卷第3期,转引自《张天翼文集》第十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6、92、93、101、103、103、108、123、122页。
[26] 张天翼《作者的态度》,转引自《张天翼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27]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转引自《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28][39] 张天翼《谈人物描写》,原载于《抗战文艺》1941年11月10日、1942年6月15日。转引自《张天翼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132页。
[29] 张天翼《什么叫做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形式决定内容呢,还是内容决定形式?》,原载《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7月版,转引自《张天翼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103页。
[31] 张天翼《答编者问》,原名《一封信》,在于《文学评论》1942年创刊号,转引自《张天翼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199页。
[37] 叶龙记录整理,钱穆讲述《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40][42] 罗炯光《张天翼文学批评的流变与特色》,《中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