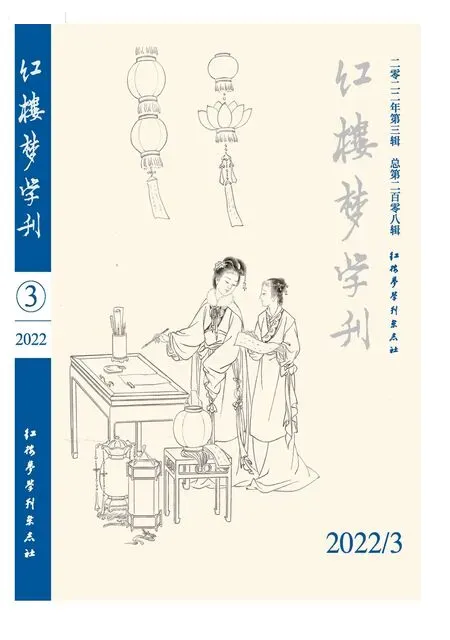简析秦可卿丧仪中的礼仪、活动与开销
2022-11-04王彬
王 彬
内容提要:秦可卿故后,贾珍哭得泪人一般,表示要倾其所有为她办丧事。按照书中的描述,秦可卿的丧事办得轰轰烈烈奢华富贵。那么,丧仪中涉及到哪些传统礼仪,哪些宗教活动、哪些丧仪人物,丧事经费支出多少,旧文解说大多语焉不详。本文从具体的、历史语境角度做了尝试性阐释。
一、番、禅、尼、道
北京旧时丧仪,离不开佛、道两教人士。
这两教人士又可以细分为番、禅、尼、道四类人物。前三类出于佛教,具体说,番是藏传佛教的僧人;禅是汉传佛教的僧人;尼是遁入空门的女僧人。在北京历史上,人死之后,除非赤贫之家,都要请僧人诵经。高等级的是将禅、道、番、尼同时请来对台诵经。次一等的是禅、道、番。再次一等的是禅、道,或禅、番。最次等的只请禅,从来没有单请番、道、尼的。
如果请番、禅、道、尼,到丧家做佛事,至少要搭三座经台,俗称经托子。通俗地讲,是构筑一座高台,后面悬挂三世佛或者三清画像。经台摆放的位置是,禅在正面,道在左面,尼在右面,番没有经台而在地上。但是也有持相左意见的,认为在清代,藏传佛教被奉为国教,因此,番僧也有经台,如果是番、禅对台,则番在上首,禅在下首;如果是多棚经对台,则番在正面,两侧是禅与道。当然,如果只请禅、道两家,则道左禅右。在《红楼梦》中,会芳园临街大门两侧“对面高起着宣台,僧道对坛”,便是这个意思。
在超度亡灵的仪式上,番虽然是藏传佛教,但仍然要比照禅、道,而诵经、拜忏、燃灯和放焰口,从而可以和禅、道、尼对台。但是也有细微区别,诵经的时候,如果经台在灵堂对面,番则坐在椅子上而面向灵堂,表示向亡人说法;禅则是背向灵堂,在佛像下面跪诵。虽然相对于番和道,在经台的安排上,禅被置于次要之位,但是禅仍然是主体道场,可以单独出丧仪。在丧仪上,禅所诵的经文主要有《金刚经》《莲华经》《楞严经》《阿弥陀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药师如来本愿经》,等等。而在请经的形式上,除丧家自请,还有亲朋送经的,由此我们可以玄想,镇国公牛清的孙子牛继宗、理国公柳彪的孙子柳芳、齐国公陈翼的孙子陈瑞文,等等,这些当日与宁、荣二公合称为“八公”的后人,是不是也会给贾府送经?
而僧人与佛事,则集中见于秦可卿的丧仪。第十三回,贾珍请来钦天监阴阳司的人前来“择日”,“推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灵前另有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出佛事的僧人或道士,一位称“一众”,民间讹为“一钟儿”。“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便是五十位僧人与五十位道士,总共一百“众”为逝去的秦可卿做法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认为人死之后会转世,以七天为一期,七天之后可以重新投生。倘若未得生缘,则须再等七日。如此延续至七七四十九日,则逝者必定重生,故而豪邸富室,往往要停灵四十九天就是这个道理。而在重生之前,轮回未定,因此每隔七天,都要延请僧道诵经祈福,也就是“按七做好事”。当然也有天天诵经的,比如这里的丧仪,有时还格外热闹:
这日,正五七正五日上,那应佛僧正开方破狱,传灯照亡,参阎君,拘都鬼,筵请地藏王,开金桥,引幢幡;那道士们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焰口,拜水忏;又有十三众青年僧尼,搭绣衣,靸红鞋,在灵前默诵接引诸咒,十分热闹。
所谓的“应佛僧”,是对出佛事僧人的称呼。而在这一日——五七正五的佛事中,有三种仪式颇为费解,一是“开方破狱”,二是“传灯照亡”,三是“开金桥”。我们逐一解释。
“开方破狱”,也作“跑方破狱”,北京东南近郊是将多张方桌摆成正方形,僧人们围桌而立,随着击打法器而轮流沿桌奔跑,故谓“跑方”。又在每名僧人身前的地上放置一块整瓦,上面用粉笔画道,由正座用九环禅杖依次戳碎,此之谓“破狱”。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中解释这是仿照目连救母破地狱的故事。而在远郊,跑方则不用方桌,僧人们只站成圆圈即可,也是轮流着跑。“跑方有由和尚跑,丧家追的,但不用孝子追。”这两种“跑方破狱”均是郊区的粗鄙佛事,却被贾珍引入府中,可见其人的趣味。
“传灯照亡”的宗旨是以灯供佛和以灯宣法,以佛、法的力度超度亡灵。具体的做法是,在经台与灵柩之间拴有绳索,上系“灯人”,灯人手执灯盏,将法灯送往灵前而由丧家跪接,之后将灯人扯回,如此循环不已,而“为亡人免罪”。灯人高约三尺,身着绸缎彩衣,如果亡者是男性,则装扮成一骑鹤的男童;如果是女性,则装扮成头梳抓髻的女童。女童站在莲花座里,肩扛一朵莲花,法灯便放在肩扛的莲花里。
“开金桥”也作“搭桥寻取香水”,简称“寻香取水”,是为了避免亡者喝秽水的一种仪式。系用三张方桌,下面两张,上面一张,再将两辆大车竖起来,车辕向上“从桌子两端交叉起来,成一桥形,由丧家披麻戴孝捧疏前行,正座率领僧众执法器随从过桥,表示冥中故事。”在这个“由丧家披麻戴孝捧疏前行”的行列里,会有贾珍的身影吗?自然不会。但是,出现宝珠、贾蓉的身影是可以的,想到贾蓉这样的人物,要接连爬过三张桌子,不知他会做何种感想。
接下来是放焰口。先是由正座和尚做“疏头”,上写丧家族人的姓名、年岁,这里肯定要写上贾蓉,作为召请亡人灵魂时念诵之用。随着法鼓慢敲,正座、驳文与众僧相互交替吟唱,之后奏乐,少停,念施食仪文。随后,正座念二十召请,召请各个行业的亡灵,于“此夜今时,来受无者遮、甘露法食”。念到末句,正座以左手紧摇灵杵,右手抛洒斛食——将荷叶饼掰碎了向台下撒。随后再念《骷髅真言》,即北京俗说的《叹骷髅》,然后吹打奏乐,合念《金刚上师诫喻》。最后打着铙钹合唱《挂金锁》。唱完了,念《尊胜真言》毕,下座喝切面铺做的“柳叶汤”,一台焰口至此完事。
在念召请文的时候,亡者的家属,这时仍然少不了贾蓉,要始终跪到那里,召请完毕才可以起身离开。但是佛事,还不止于此。在秦可卿七七四十九天的丧仪上,贾珍不仅请僧道对台诵经,而且还“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这是为什么?大悲忏的全称是《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僧人诵经拜佛,代替亡者忏悔称“拜忏”,这里的拜大悲忏,便是这个意思。秦可卿有什么要忏悔的吗?这就耐人寻思。联想到脂砚斋的有关评点,这样叠床架屋的浩大佛事,或者是某种信息的流露。但是无论怎样张扬,作者的笔端仍然清晰,因为在清代,王公贵族举办丧事,是没有不请番僧的,而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红楼梦》只有僧、尼、道,却不见番僧的踪影。贾珍不是哭得泪人一般,要尽其所有为秦氏办丧事吗?怎么不请番僧呢?这就于理不通。这是为什么?这或者是时代的残酷所致,为了规避文祸,岂止“无朝代年纪可考”,在作者更不敢露泄半点让人指证时代的端倪,从而露出破绽,在秦可卿的丧仪上见不到番僧的身影,这或者,当然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而需要继续求索。
二、“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请灵”
关于丧仪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里,《红楼梦》中围绕秦可卿故后的章节,最为精细也最为精彩。在这精细与精彩之中,不仅推动了故事发展,而且折射出其时的丧事礼仪,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丧仪之中的杠、杠伕与执事数目:
至天明,吉时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请灵,前面铭旌上大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柩”。一应执事陈设,皆系现赶着新做出来的,一色光艳夺目。
何谓“青衣”?青衣是指杠伕所穿的驾衣,因为颜色是深绿色的故称,在这里作为杠伕的借喻。旧京出丧,离不开棺、杠与杠伕。棺,敛以逝者;杠,是舁运逝者的工具,而杠夫的数量则与丧仪保持一种密切关系。在清代,用杠分两类,一类是非礼仪性用杠,一类是礼仪性用杠。非礼仪性用杠,有两名杠伕抬的“穿心杠”,三名杠伕抬的“牛头杠”和四名杠夫抬的“一提拉”。这样的用杠,或者为贫者所用,因为贫而不能为礼;或者为幼者所用,因为幼而没有必要为礼,都是只有送殡活动而无送殡仪式,属于有殡无仪。礼仪性用杠则至少是八人杠,或者是八人杠以上,即:十六人杠、二十四人杠、三十二人杠、四十八人杠、六十四人杠、八十人杠和一百二十八人杠。“六十四名青衣请灵”,便是说将秦氏的灵柩从宁府抬到铁槛寺寄灵而动用了六十四名杠伕。
这六十四名杠伕是如何站位与行走的呢?为了叙述方便,先说杠,具体的做法是:先是用两根主杠把灵柩架起来,之后在主杠两端固定两根横杠,横杠的四角各固定一根小杠谓之“千斤”,每根千斤前后各加一根小杠,行话称“耙”,每耙再固定两根“卧牛”,而每根卧牛各拴两根抬杆,共八根,每根抬杆左右各有一名杠伕,这样灵柩的一角便有十六名杠伕,四角便是六十四杠伕了。
为了保证这六十四名杠伕行动有序,要安排两名指挥杠伕的杠头,杠头手持响尺,称“打尺的”,前后两名,称“对儿尺”。除此以外,还要有四名执鞭压差、八名打拨旗的和十六名徒手随行准备换肩的杠伕。然而,还不止于此,在这些人员之外,据常人春《红白喜事》一书介绍,还要配置一名杠伕背着大白粉,每走五十步便在地上画个记号,表示到此画换班,谓之画拨子。“头拨画‘○’,二拨画‘×’。”换班是一角一角的换,换下的杠伕,两人一对走在灵柩之前。“夏天热,还要有四名杠伕挑着大瓦壶,随杠伕而行,以便供杠伕们饮水。”一架六十四人杠,杠房至少要派三位“了事先生”,一位监督打尺的杠头,一位应酬本家,一位负责跟罩,用油布把罩片包好,放在包袱皮里提至丧家,把罩片置于棺木上,发引时,这位了事先生便一直跟着,到棺木下葬时把罩片撤下来,再将罩片叠好,包上油布,放在包袱里,背回杠房。(六十四人杠的用棺罩不用罩片)如此算来,所谓六十人四杠,加上换班的便有八十名,而其他附属人员至少也有二十二名,三者相加总计是一百零二名。
秦氏的“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请灵”是否也是这样规模呢?
按照旧京请灵的规矩,灵柩一上杠,便不可以落地,因此要安排徒手的杠伕随行换肩。十六名是基本人数,讲究的是在六十四名之外,再有一班六十四名杠伕,也就是两班杠夫,甚至还有用三班杠夫的,那就是一百九十二名杠伕。为秦氏请灵的人员也有这么多吗?这就要分析“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请灵”中的“一般”二字。一般何意?通俗地说,一般即一样,“一般青衣请灵”中的一般也是此意,指穿一样颜色驾衣的杠伕,也就是一个班的杠伕。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书中所讲只是用杠的等级,不涉及换班的杠伕。不涉及不等于没有,联想贾珍“哭得泪人一般”,要尽其所有为秦氏大办丧事,怎么会不安排换班的呢?当然要安排,而且至少是一班,很可能是两班,如果是这样,在为秦氏请灵的丧仪中至少应有二百十四名杠伕与执事,或者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吧!
在《红楼梦》的成书年代,“六十四名青衣”,是一种什么规格的用杠?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这样记载:
发引之仪,凡王、贝勒用八十人起杠,一品大员用六十四人,次者四十八人,再次三十二人,皆有棺罩。至二十四人、十六人者,皆用绣罩片,无大罩矣。
公,低于王与贝勒,自然不可以用八十人杠,最高只能用六十四人杠,而这样的用杠,相当一品大员的规格。何况,贾珍还给他的儿子秦氏的丈夫贾蓉,花一千五百两银子蠲了龙禁尉的头衔,以便发引之时风光体面。有了这样的头衔,秦氏的灵柩前面——走在灵柩前面的右侧,才可以竖起这样的铭旌,在上面大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柩”。而这座铭旌,在发引的前一天,便立在丧居门首,出殡的时候,也由杠伕抬着,其数量,也有十六人、二十四人与三十二人不等。当然也要有执鞭压差负责维持秩序,打拨旗的负责清理道路上的障碍,和对儿尺,一前一后指挥。如果也以最多人数计算,为秦氏请灵的人员则应在二百五十人左右。
这是就杠伕的数目而言。具体到这些人物的衣着,驾衣的颜色与样式,一种将及膝盖的小大褂,杠伕是大襟,执事为对襟。如果是一个班的杠伕则穿深绿色驾衣,如果是两班,为了进行区分,第二班着深蓝色,如果是三班,则第三班着黑色。无路是何种颜色驾衣,都是遍身满印车轮形状的图案,周围是八至十二个大圆点,象征灵车。下身则是土黄或者灰色套裤。脚上是青靴子,头上呢?杠伕是在黑色的毡帽上插一根雉翎。在清代,入品的官员采用红雉翎,帝后、亲王、郡王,用黄雉翎。入八分公者用紫雉翎。翎子的颜色与杠上所用的绳子、垫子,以及拨旗的颜色都是一致的。打响尺的杠头,或者说对儿尺,则是头戴官帽,身穿丧家给的孝衣,在灵柩前后奔波指挥。在这一天,有权势或者有钱的用户,都要求无论是杠伕、执事、还是杠头,一律要沐浴、刮脸、穿新靴子、新驾衣,再加上油杠(新刷一遍漆)、包绳(用新布包杠绳)等,谓之“普新”。上面所引为秦氏请灵的“一应执事,皆系现赶着新做出来的,一色光焰夺目”,便是这个意思。这样一班新姑爷似的簇新人物,簇拥着秦氏的灵柩,突显于送灵的队伍之中,从宁国府出发,浩浩荡荡,焜耀缤纷,向铁槛寺“进军”,在这样的青衣队伍面前,贾珍大概会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他倾其所有为秦可卿办丧事的结果之一吧!
三、秦可卿的丧事开销
讨论贾府的丧事开销,要从秦可卿说起。因为她是红楼中的第一个亡者,而且死得其时,贾府的架子那时还在,故而丧仪风光。
做丧仪,首先要寻找一副好棺木。可巧薛蟠前来吊问,见贾珍要寻好板,便说:“我们木店里有一副,叫作什么樯木,出在潢海铁网山上”,用这样的板做棺材,可以万年不坏,“还是当年先父带来,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拿去。现今还封在店里”。贾珍听了喜之不禁,即命人抬至宁府。众人围过来看时,只见“帮底皆厚八寸,文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当如金玉。”贾政认为这样的板材不适宜秦氏,说:“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敛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然而,此时的贾珍“哭得泪人一般”恨不得代秦氏之死,哪里肯听贾政的劝告?那么,这副板卖多少钱呢?薛蟠说:“拿一千两银子来,只怕也没处买去。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话是这么说,总还是要给钱的,打折五百两总是应该的,然而贾珍仍不满意,他认为他的儿子,秦可卿的丈夫贾蓉,身份低,“不过是个黉门监,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恰好这日是首七第四日,大明宫的掌宫内相戴权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贾珍趁便和戴权说要给贾蓉蠲个前程。戴权一口应允:“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短了两员”,“昨儿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贾珍说明天送到部里,戴权吩咐第二天送到他家里,只要一千二百两。那么,这一千二百两银子蠲了个什么前程呢?按照书中叙述,是一个五品级别的御前侍卫,全称是“防护内廷紫金道御前侍卫龙禁尉”。这样,秦氏的丧仪,便提升了等级,“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列。”级别提升了,排场大了,费用自然也相应提升。至少,请僧道与杠夫的人数,他们的人工费用,是要增加的吧!可惜书中没有说明,只讲述了板材与蠲前程的开支,余者需要我们寻找另案分析。
好在红楼人物续有死亡,可以为我们的讨论进一步提供案例。第六十四回,贾敬“宾天”了,贾珍与贾蓉不免稽颡泣血,把贾敬的灵柩从城外请进城,这一天,“丧仪炫耀,宾客如云”,夹道而观者何啻数万人。
一日,有小管家俞禄来回贾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并请杠人青衣,共使银一千两,除给银五百外,仍欠五百两。昨日两处买卖人俱来催讨,奴才特来讨爷的示下。”贾珍道:“你向库上去领就是了,这又何必来回我。”俞禄道:“昨日已曾向库上去领,但只是老爷宾天以后,各处支领甚多,所剩还要预备百日道场及寺中用度,此时竟不能发给。所以奴才今日特来回爷,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或者挪借何项。吩咐了奴才好办。贾珍笑道:“你还当是先呢,有银子放着不使。你无论哪里暂且借了给他罢。”俞禄笑回道:“若说一二百,奴才还可以巴结;这四五百两,奴才一时哪里办得来!”
此时的宁国府已非往昔,资金周转不灵了。但是却透泄出一个信息,便是“所用棚杠孝布并请杠人青衣”等花销,是白银一千两。贾珍只支出了一半,另外的五百两还没有着落,买卖人便前来讨债了。什么是“棚杠孝布并请杠人青衣”?棚,是丧棚;杠,是抬运灵柩的工具;孝布,指孝服与帷幔之类;杠人,指杠夫;青衣,指执行仪式者,诸如打幡和吹鼓手。这些人,杠夫、执事、吹鼓手之类,衣服的底色是深绿的,因此叫青衣。上面说到,倘出大殡,要用两班杠夫,为了区别,则一班穿深绿,另一班穿深蓝。如果是三班,便再添上青色的驾衣。这些排场,秦可卿是少不了的,因此大概也要再花费五百两,与前三项(棺木、蠲前程、棚杠孝布杠人青衣)合在一起,便是三千二百两了。
当然还没完,因为还有道场——僧人、道士为秦氏做法事,这些活动要多少开支呢?不得而知。我们假设,这些活动的开支是棚杠孝布青衣等人的两倍,那便是两千两。全部四项相加则是五千二百两,在加上办丧事时的招待,姑且以五百两计,则是五千七百两。当然还会有零星开销,也以五百两计,则是六千二百两。如果减去秦氏的樯木板材与为贾蓉蠲前程的一千七百两,则是是四千五百两。第五十五回,凤姐与平儿计算贾母的后事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老太太的事出来,一应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杂项,便费也满破三五千两,如今再俭省些,陆续也就够了。”按照习俗,贾母上年岁的人是应该存有棺木的,不用临时张罗,而且也不需要子女们再蠲什么前程,因此这两项都可免去,凤姐估计的“三五千两”与秦氏的开销,基本吻合。但是,凤姐的算计是在贾府没有抄家之前,而贾母西归恰恰在抄家之后,“虽说僧经道忏,上祭挂帐,络绎不绝,终是银钱吝啬,谁肯踊跃,不过草草了事”而不及秦氏体面。
为秦可卿办丧事所开销的六千二百两是什么概念呢?《大清会典·户部俸饷》记载,亲王的俸银一年是一万两加一万斛大米,一两银子可以领一斛大米。如果把大米折合为银子,亲王的俸银则是两万两白银。以此类推,在京文职,一品官员俸银是一年一百八十两,加上可以支取的大米合计为三百六十两。贾府的丫头呢?大丫头月例,也就是月工资一两,一年十二两;小丫头五百钱,折合半两计算,一年是六两银子。以此为标准,六千二百两大约是一位亲王三个多月,十七位一品官员一年的俸饷,而到了贾府,则是五百十六个大丫头,一千多个小丫头一年的工资。清朝中晚期一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在150到220元之间,以200元计算,则六千二百两白银大约为一百二十万元。
在这样的开销之下,秦可卿的丧仪怎么可以不风光,又如何可以不奢靡呢?
四、“泪人一般”与“出灵不像”
相对于秦可卿丧仪的奢华与富贵,尤二姐的丧仪则十分孤冷、凄清,只有尤氏、贾蓉等人来哭了一场。
而且,尤二姐的灵柩也不能停在贾琏自己居住的院子里,只能放在梨香院。梨香院位于荣国府东北角,当年是荣公暮年静养之所,为了出入方便辟有一座后门通街。将尤二姐的灵柩停放在那里,贾琏很不高兴,“嫌后门出灵不像,便对着梨香院的正墙上,通街现开了一座大门。”“不像”是北京的土语,意思是不像话,不成样子。贾琏在新开的大门两边搭棚,安坛场做佛事。七天以后,该送灵了,送灵那日,“只不过族中人与王信夫妇、尤氏婆媳而已。”
然而,尽管秦可卿与尤二姐的丧仪,在场面的奢华与凄清上大不一样,但分析起来却仍有相同之处,即:尤二姐的灵柩停在荣府的东北角,秦可卿的灵柩停在宁府西北的会芳园,都不是贾府正中的院落,而且都位于贾府北面,只是朝向不同,一东一西而已。
如同贾琏把梨香院的正墙上新开了一座大门,贾珍也只能将会芳园的临街大门打开,秦可卿的丧仪也不能由宁国府的正门出入。在寄灵的铁槛寺,秦氏的灵柩也没有安排在正殿居中的位置,只是被安排在“内殿偏室之中”。这是为什么呢?
《仪礼·士丧礼第十二》记载:
士丧礼,死于適室。
適室,即正寝之室。士须逝于正寝之室,而且要在这里为故者小殓,之后迁至堂上。《礼记·丧大记》曰:“男女奉尸夷于堂”,所谓小殓在室,大殓在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堂的什么位置呢?《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在临终前对子贡说:
予畴昔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周人殡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将死。
楹,是堂上的柱子,两楹之间即堂上居中的位置。东阶,即东边的台阶,也称阼阶,主人由此上堂;西阶,即宾阶,客人由此上堂。孔子的话大意是:我昨夜梦见在两楹之间做祭奠。夏人将灵柩停在对着东阶的堂上,即主位上;殷人将灵柩停在两楹之间,处于主位与宾位之间;周人则将灵柩停在对着西阶的堂上,即宾位上。我是殷人,昨夜梦见了殷人的丧仪,我将要离开你们了,而现在明王未兴,谁会继承我的思想呢?
孔子所说殷人丧仪被后世继承下来,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我国传统的丧仪制度,只有宅第的主人、主人的正室以及相当主人身份的长辈,可以停放在正院、正房居中即明堂的位置上,相当于孔子所说的两楹之间。贾珍的父亲贾敬故后,“将灵柩停放在正房之内”即是遵守了这个礼仪。这是对亡者的最高礼遇,也就是正寝,寿终正寝便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偏室(非正室),则不可以,只能停放于其他房间。未成年的“小口”死后一律停放在院内西侧。暴死于家门之外的,即便是家长,也不能停于正房,而只能停放在院内东侧。这个原则用于身份高贵的死者,倘若是王爷及其家属,也是适用的,只是正房变为大殿——民间俗称的银安殿而已。在清代,王府中的西侧往往构筑一所小院,称吉祥所。府中的太监与宫女在这里养病,府主的姬妾与未成丁的小口也往往在这里举办丧事。《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因为只是公府,不能在府中设吉祥所,然而在举办丧事的时候,仍然要遵循礼制而不能胡停乱放。无论是秦可卿还是尤二姐,均只能停放于正房之外,便是这个道理。在秦可卿是会芳园,在尤二姐是梨香院。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无论是“泪人一般”还是“出灵不像”,其背后都有着强大的礼仪支撑,并不能简单地以人物之间的情感与人物之间的阴毒、倾轧进行解读,而我们之所以要阐释《红楼梦》历史语境的原因就在这里。
①②③④⑨⑩[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3]曹雪芹著、蔡义江校注《红楼梦》,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66、166、178、166、166、181、166、166、167、167、165、167、167、168、169、169、875、875—876、875、739、1482、949、951页。
⑤⑥⑦ 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123、119页。关于斛食,金受申说:“在用晚餐前后,蒸锅铺送来‘斛食’供于灵前。斛食是用木制的一座方塔形状,高三五级,底层正面画刻成抠钉兽环的门样,每级围绕插着‘江米人’,最上级立一旗杆,杆前置多层荷叶蒸饼。送三之际,江米人为亲友分有,名为‘抢江米人’,荷叶饼留作晚间‘放炎口’施食的‘法食’。”散斛食之时,必将焰口座的下边清扫干净,丧家与出份子亲友的孩子,到时将孝袍子和褂子的底襟撩起来接斛食,相传小孩吃了斛食不害怕。
⑧《骷髅真言》也称《叹骷髅》,版本颇多,之一是:“昨日荒郊去玩游,忽睹一个大骷髅。荆棘丛中草没丘,冷飕飕,风吹荷叶倒念愁。骷髅!骷髅!你在涸水边卧洒清风,翠草为毡月作灯。冷清清。又无一个往来弟兄。骷髅!骷髅!你在路边,这君子,你是谁家一个先亡?雨打风吹似雪霜。痛肝肠,泪汪汪。骷髅!骷髅!看你只落得一对眼眶。勘叹人生能几何?金乌玉兔来往如梭,百岁光阴一刹那,莫蹉跎,早求出离苦海劫波。今宵施主修设冥阳会,金炉内才焚着宝香。广召灵魂赴道场,消罪障,受沾福利,速往西方。”参见常人春《红白喜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341页。
[11] 常人春《红白喜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387页。
[12]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
[30] 彭林注译《仪礼·士丧礼》,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23页。
[31] 任平直解《礼记·丧大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32] 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终记解》,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