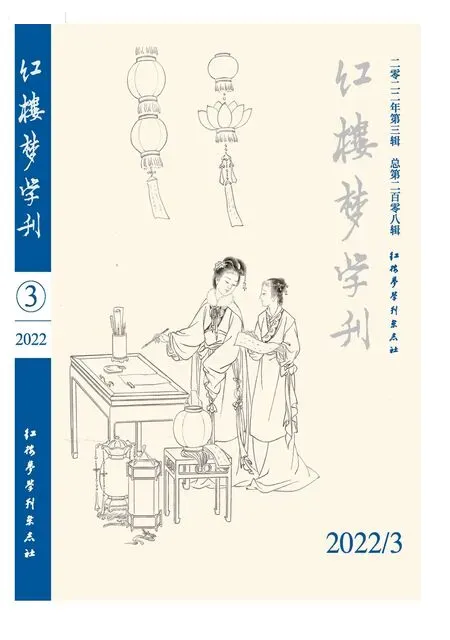学术史视野中《红楼梦》人物结局问题的内涵与意义
2022-11-04朱锐泉
朱锐泉
内容提要:站在历经百年的红学史立场上,本文紧扣曹雪芹及续作者对于笔下人物命运的关注与其人生归宿的安排,试图以此为切口,梳理清代评点者与现代学者之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研究者倾向于聚焦人物死亡、出家等事件类型,这一点需要引起重视。他(她)们又从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等小说艺术诸方面出发,评论创作的得失。至于文本探考与文体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使用,亦是较为显明的特点。由这些看法意见的回顾,可以窥见不同的治学思维与路径,还能够进而总结出人物结局问题的学术意义。本文认为,经典化理论视野的借用,既有助于公允衡估《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功过,也能正面推进有关古代小说名著的缺憾问题的探讨。
引言:在经典与缺憾之间
《红楼梦》中各色人物的结局,在学术史上是一个意义不乏重要而表现有些潜隐的问题。它一方面从属于“古代小说人物研究”“古代小说结尾研究”的专门方面,同时又与《红楼梦》自身探讨中有关“后四十回”的认知评价,紧紧扭结在一起。
就前者来看,不少古代小说甚至经典名著的收尾,往往引起世人诟病。耳熟能详的例子,自然是金圣叹不满梁山英雄招安以后的描写,竟腰斩《水浒传》(这里强调的是从艺术表现而非政治思想方面着眼)。及至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分析了该小说成书方式与题材方面的两点原因,得出的观察为“一大部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
此说影响甚大,然而在欧阳健看来,学术经典笼罩下的观点“共识”与思维定势亟待打破。他认为,施耐庵大胆地突破了传统文艺惯以大团圆收尾的格局,写出梁山泊全体人马在接受招安,接连立下了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的大功后,仍然受到奸臣的嫉恨陷害,或饮鸩而亡,或被迫自缢,风消云散,零落殆尽。由此,其论文呼应了胡适《〈水浒传〉后考》对于后半部的意见,即:“平定方腊以后的一段,写鲁智深之死,写燕青之去,写宋江之死,写徽宗梦游梁山泊,都颇有文学意味。”
联系本文关注的《红楼梦》,鲁迅同样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发表如下高论:“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这一看法,在伴随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问世,而长期盛行的高鹗续书说的声浪之下,显得不无孤寥寂寞。曾几何时,秉持“高续说”学者的逻辑多半是,缘于高氏的狗尾续貂,所以后四十回理应遭受口诛笔伐。然而在当前学界大多数人倾向于后四十回乃程伟元、高鹗在曹雪芹残稿基础上增删、补缀而成的背景下,如何尽可能客观合理地认识《红楼梦》的结局设计尤其人物命运安排,就理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正如新近的研究指出,“人物命运、情节设置曾经是‘高续说’的铁证,而今正处于重新诠释的阶段。”也不应忽视,对于这一段充满论争与反驳的红学历史的回顾及总结,适足成为研究再出发的起点。诚然,看上去“经典”与“非经典”、“完美”与“缺憾”更能构成严密的对应关系,不过,这一段研究史却显示出将《红楼梦》人物结局的具体描写,视为经典体现或沦为一类败笔的迥异倾向,因此似乎提示我们提炼出如题所示,构成评价之两极的名称。
我们当然不是试图就《红楼梦》的“结末”问题,作翻案文章。而只是愿意借用古代文学经典化的视野,抓住人物结局安排的切口,从事有关小说结尾及其包含的名著缺憾问题的深入探究。本文主要考察并试图回答的问题在于:首先,《红楼梦》人物结局研究的多方面内涵何在;其次,作为重要的学术思路及方法,它具备怎样的特点。在此两点基础上,简要归纳这一研究的意义所在。
一、死亡、出家等事件类型:人物结局研究的重要内涵
小说史家刘勇强指出:“对人物命运的关注是《红楼梦》诗美的基础,其中包含的审美理想与真挚情感是这种诗美的核心。具体来说,它表现在作品对宝黛爱情以及大观园其他女儿悲剧命运的深刻描写中。”诚哉斯论,本文则更进一步,努力探察小说对人物命运关注的焦点与表现的过程。
所谓红楼人物的结局,即其在作家笔下,收获怎样的人生归宿,或者在走到命运终点时,出现何种荣辱浮沉的情形。这一问题指涉的文本以后四十回为主,却又包含前八十回。这是因为如秦可卿的例子显示的那样,有关描写的运思用意与匠心旨趣,在前文就有所体现。
众所周知,前八十回通过判词、诗词、灯谜、花名签暗示后文情节、埋设伏笔,至于脂砚斋评语及小说问世同时或稍后的“悼红诗”写作,也是我们厘清人物结局的重要参考。第五回秦可卿的判词与画像,都暗示了其最终系自缢而死。但实际上,曹公受畸笏叟之命进行修改后,秦氏却以病死了结。同理可证作家对其他人物命运的变动改易,故而在研究方法上,不能直接以前八十回文字表露的某些创作设想,作为截然推演后文人物生命走向的依据。
秦可卿在十二钗之中排在最末一位,但却是第一个死去的,也是前八十回之中唯一一个死去的十二钗中人。关于她的死,作品第十三回仅仅用一句话就交代了:王熙凤梦中只听得二门上传事云牌连叩四下,因而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但显然,围绕秦氏故去这一关目,举凡丧事葬仪的铺陈描写,死封龙禁尉、协理宁国府等情节的推展,贾珍、贾蓉、凤姐等人物形象的刻画,皆得以一一跃现纸上。
相对于《金瓶梅》研究者热衷考察主要人物死亡叙事及其背后反映的人生意识,《红楼梦》这方面的研讨略显不足。其实,“死亡”恰恰属于该部小说设置“人物结局”的其中一种主要方式。
早在小说产生的有清一代,议论其人物死亡结局的声音,就一直存在。明斋主人诸联《红楼评梦总评》(载于道光元年刊本《红楼评梦》卷首)之中,有一条专讲人物的死法。所谓“人至于死,无不一矣。如可卿之死也使人思,金钏之死也使人惜,晴雯之死也使人惨,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愤,二姐之死也使人恨,司棋之死也使人骇,黛玉之死也使人伤,金桂之死也使人爽,迎春之死也使人恼,贾母之死也使人羡,鸳鸯之死也使人敬,赵姨娘之死也使人快,凤姐之死也使人叹,妙玉之死也使人疑,竟无一同者。非死者之不同,乃生者之笔不同也”。这段描述和概括颇为全面,更突出了作品的强烈感染力与特定阅读效果,但对黛玉之死似乎重视不足。须知,后四十回中“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第九十七回)乃是全书浓墨重彩表现的剧情。
其次来看姚燮《读红楼梦纲领》。其卷三《余索·丛说》有一条目引用王希廉总评,也是关于小说人物之死。王雪香有言“一部书中,凡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件件俱有”。接着,姚氏也逐一列举人物死因,如“林如海以病死……黛玉以忧郁急痛绝粒死,晴雯以被撵气郁害女儿痨死……凤姐以劳弱被冤魂索命死,香菱以产难死,则足以考终命者,其惟贾母一人乎!”与这段表述类似的,是解庵居士《石头臆说》所云“此书才识宏博”的体现之一,在于“甚至诸般横死,如投井投缳自戕、吞金服毒、撞头裂脑、误服金丹、斗殴致毙,无所不有,形容尽致,可谓才大如海”。以上这些看法,揭示出《红楼梦》在同为安排人物死亡结局的前提之下,又犯中见避一般进行不同死因死况的多样化处理,从而为全书尤其后半部铺设了一层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的氛围,具备丰赡的意蕴与入骨的美感。这份创作上精益求精的艺术匠心,还使我们联想到欧阳健前引文章,同样谈到“在处理梁山泊一百八人归宿上,作者也不肯丝毫苟且。谁先死,谁后死,怎么个死法,都有极其精到的考虑和谋划”。
还需指出的,是载于光绪二年(1876)篑覆山房刊本的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红楼梦偶说》也专列一条参与讨论。粗略考察其论述内容,如突显“不愧忠烈二字”的鸳鸯、“以身殉主”的瑞珠,皆具有道德化的口吻色彩。这也正符合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文天祥《绝命词》)所规定的儒家生死观念。
踵武清人对于红楼角色死亡结局的敏感,为世人所共知者,当举王昆仑的研究。其《晴雯之死》一文提出,“晴雯之死就是预言了宝、黛恋爱之必归失败,宝玉之必出于逃亡”。论者阐述人物结局,是采取了相互比较的方法与思路,故而有助于认知不同角色的个性特色。并且,其论述还采借了小说回目这一文体角度:
黛玉之死是一步一步走向枯萎,晴雯之死是骤然遭遇到残暴的摧折;所以黛玉之死的标题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而晴雯之死却大书特书“俏丫鬟抱屈夭风流”。读者对于黛玉之死在心理上是具有预期状态的,而晴雯之死却给读者情绪上以意外的打击,激起人们中气如雷的忿怒。
后来台湾学者李君侠亦在著述之中,以“自杀、误杀、凶死”一节,列举相关人物事件。而邱露则应该是首次整理出一份《〈红楼梦〉前八十回死亡事件统计表》,相当显豁地呈现出这一重要文本现象。
在“死亡”之外,红楼人物的另一主要结局类型即出家,同样素来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张天翼即以宝玉为题,论述了这一问题:
讲到恋爱,讲到有情人成不成得了眷属,主人公在这一方面诚然是失败的。没有团圆。
然而我们不能说《红楼梦》的结尾没有一个团圆。
贾宝玉毕竟有了归宿,找到了一条出路。他毅然跨到了那条路上去:结果圆满。这就是他的出家。
这个团圆的意义可就大得多,也高得多了。
张先生的文章以宝玉为主,又注意联类而及其他,遂将“出家”视为人物命运安排的一种类型:
而且出家的不止宝玉一个。此外还有甄士隐、芳官、惜春、紫鹃等等。而处理的方法都是一样,一交代了这一步,他们就有了归宿,天大的问题都没有了。
针对后四十回,论者又深感“出家也大不容易”。理由是“譬如贾宝玉罢,已经要出家了,可还得履行种种手续:跟薛宝钗圆房,读文章赶乡试,而且还要留下一个儿子,等等”。从中可见,围绕“出家”,作品其实设计了一连串情节,其中的逻辑与情理,自然也招来了学者们的纷纭聚讼。本来,“因空见色”“自色悟空”,此乃这部“情僧录”既定主旨的一个侧面,但小说人物始终难以摆脱红尘俗世的羁绊,而完全进入对宗教信仰的纯粹虔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说到后四十回的科举描写,胡适、俞平伯归纳的高鹗续书的几点“铁证”,便包含“宝玉不得中举”。段启明更是直陈不满,“后四十回中对宝玉的更严重的歪曲,是完全取消了他的反对仕途经济的性格特征,而着力描写他为贾政升官欣喜若狂”,而同样的,“林黛玉已从一个脱尽俗务的贵族叛逆者”,变成了为日常琐事“操心的小家女子”,同时还让林黛玉对八股文发表了一些利欲熏心的见解。
后来者的分析评判,则更见公允。胡文炜认为,宝玉自始至终抵触科举,入家塾、评女传都是被动、应付;而黛玉随着年龄增长,思想上多少会有所转变,她劝宝玉读书也在情理之中。张惠的见解,尤其不同流俗,所谓“宝玉中举是对《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合理想象,是对宝玉形象的提升,宝玉中举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加深了全书的悲剧意味”。可以发现,不仅关注人物性格、思想前后的一致性,更注意其发展变化,这才是当代红学继续前行的应有方向。
而前贤时哲对于《红楼梦》人物结局的把握,多有从死亡、出家这样典型事件的角度切入,又注意以点带面,连类而论,由此展现出类型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式与学术思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二、形象演变与情节结构:人物结局与小说艺术的关联生发
要系统考察《红楼梦》的人物结局设置,当然无法回避后四十回评价的问题。说起后四十回的功过,俞平伯《后四十回底批评》的评价广为人知,所谓“至于混四十回于八十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这里拟结合人物的命运安排,从形象建构与情节结构设计的创作得失角度,再作厘析。
首先,应该注意到,对于后四十回的人物塑造,无论是胡适挂帅的新红学,还是李希凡领衔的社会历史批评派,都并不缺乏肯定的意见。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样说道:
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后者则在1956年合作撰文中表达,后四十回的主要成就是“在主要人物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性格上发展了悲剧冲突,使得《红楼梦》故事情节的中心——宝黛钗的爱情纠葛,得到了比较合理的发展和结局,基本上保持了前八十回所显示的悲剧的气氛和性质。”“也正是在这个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上,后四十回发挥了它的艺术吸引力,因而和前八十回形成了一个整体而流传下来”。
将前后两部分的内容与描写贯通起来,视为不可割裂的整体,显然有助于客观公允地认识人物之塑造刻画。然而这种结合情节衍生与悲剧美感谈人物演变的思路,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类似童庆炳、段启明等学者,几乎是在此问题上,给予了“失败之作”的定谳。童先生指责“续作在某些方面歪曲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特征,损伤了原作两个中心人物形象的完美”,而段先生也在论著中以“四美钓游鱼”、贾政升官等情节中宝玉的反应为例,强调后四十回里“被歪曲了的人物形象”。
专门阐论人物形象演变的石昌渝,则提出一些持平之见。他说曹雪芹肯定贾宝玉,虽然其中也还有些批评,续作者肯定宝玉和黛玉的恋爱,不肯定宝玉和黛玉的叛逆精神,因而宝玉和黛玉的性格的基本特征被歪曲。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好人不全好,坏人不全坏,性格与环境有机的相联系,并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发展。续作者笔下的人物则走向概念化、简单化、凝固化”。
“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时至今日,脂砚斋第四十三回的这句夹批,在学者中间可谓耳熟能详。他与《红楼梦》作者都反对千人一面,把人写成无以复加的至善或至恶。那么,我们是否能由此理念出发,认识作品中人物性格发展所产生的诸般缺点呢?
诚然,还应该认可一点,《红楼梦》全书的叙写,折射出作者的思致、笔力有不周全、不到位的地方。仅就人物性格言行的刻绘而言,也存在若干“用力过猛”有违情理之处。譬如第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一节,论者多讥其直露,尤以宝玉剖心为矢的。早在桐花凤阁本,陈其泰于此就有评点:“此回败笔甚多,显然与八十回以前之笔墨不同。自是另出一人之手也。”而近些年陈洪的研究,亦指出“其中写‘众人不言语,都冷笑而去’‘老太太呆着脸笑’等处,梦幻意味颇足。可惜处理过实,与黛玉‘孤标傲世’之品格不甚相合,且缺少一些象征性的弦外之音——而这差不多是这类‘明心见性’的梦境描写之通病”。
不过我们还是愿意指出,过多究心此类毛病,会极大地限制对于小说的理解体认,也无助今天站在研究史立场,去权衡前人的所有评论。如果暂时跳出争议,搁置有关后四十回人物结局安排反映的形象塑造成败的话题,回到这一小说艺术方面的问题域本身,我们大可以开拓自身的视野,丰富讨论的面相。
有关荣国府里的经济账问题,有陈大康的新著作出讨论。在此方面,清人早着先鞭。且上溯历史语境,来看对于黛玉死因作分析判断的声音。涂瀛《红楼梦论赞·红楼梦问答》认为“林黛玉葬父来归,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并举文本内证,提出小说叙述“当贾琏发急时,自恨何处再发二三百万银子财,一再字知之”。由此得出“然则黛玉之死,死于其才,亦死于其财也”的结论。对此“石破天惊”式的议论,后来者纷纷质疑。如解庵居士《石头丛话》云此说“实属无谓。四十五卷中黛玉尝向宝钗曰:‘我是一无所有。’则何来此数百万金耶?”后又引用史珑南的话,“未免深文周内,故入人罪”。
还是举《石头丛话》,解庵居士单单肯定王希廉《红楼梦总评》中对《红楼梦》的两点缺憾指认,除此以外则称“其余十余条皆胶柱之见,且多纰缪”。他还举例论述,所谓“又如所批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觉,何以知其死于吞金?似亦疏漏等语。彼独不见夫《左氏传》鉏麑贼赵盾之文乎?此书此事亦正仿此意耳”。可见清人对尤二姐吞金结局的批评,又受到反批评的考验。关于“名著缺憾”的话题,前代小说评论者的话语之间,构成了事实上的对话与商榷关系,力求将真理愈辩愈明。
再如人物结局描写在全书结构布局中的地位,这一重要层面也得到了王昆仑的关注。他的《晴雯之死》一文,就开宗明义地提出,“晴雯之死和宝玉挨打是《红楼梦》故事发展过程中两个高峰,两个转折点”。潘建国之对比明清两部世情小说巨擘,如何拿出五回篇幅,来对李瓶儿和秦可卿的人生进行完结,其实便可进而说解“美人之死”的情节在全篇中的地位意义。这方面的法门一经开启,正可以推动名著人物结局安排的比较研究,走向更趋深广的境地。
其次,上文已涉及前贤运用“悲剧”的定义观念来评价《红楼梦》的人物结局描写,由是得出肯定性看法。此说当然要追溯到王国维1904年最初发表于《教育世界》杂志的《〈红楼梦〉评论》一文。
该文共分五章,其中第三章阐释《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主要就在论述《红楼梦》之悲剧性质,以为《红楼梦》与吾国人之乐天相反,具备“厌世解脱之精神”,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这样力透纸背的见解,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新人耳目。另一方面,今人也已经认识到,王国维的此篇文学批评论文的症结,是全部建立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及美学观点之基石上。他不仅照搬了西哲对于三种悲剧的定义与区分,更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灭绝生活之欲”“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依据。叶嘉莹还进而指出,王氏对于西方悲剧之传统,及美学中美(Beauty)与崇高(Sublime)之理论,也未能有更深刻更正确的理解和发挥,这成为他在立论方面的又一点疏失。
不过,今时今日,我们还是应大加赞许王国维援悲剧理论,入红学批评的思路与实践。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学术史演进的其中一种趋势。前引郭丹曦论文,就此总结道:梳理了学界对后四十回从抑到扬的认识过程,我们发现越是从宏观角度、整体视角考量,对后四十回就越倾向肯定。后四十回价值的重新发掘,最成功的一脉即从整体性、悲剧性角度展开。
郭氏对此一观点未作具体交代,然则事关清末民初悲剧观念流行之背景,实有加以阐述的必要。在据称中国的第一本小说史里,张静庐就明确介绍:
人情好奇,见异思迁,中国小说,大半叙述才子佳人,千篇一律,不足以餍其好奇之欲望;由是西洋小说便有乘时勃兴之机会。自林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著哀情小说《茶花女遗事》以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破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中国小说界大受其影响。
因此,正是伴随西学东渐,欧美小说大量被引进入华,传统小说偏爱团圆结局的特点,才被国人抓住并痛诋。其时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还回顾了《莺莺传》影响下的戏曲作品,从文化批判角度,将大团圆结局与国民性问题联系起来。
至于与王国维的发表相比,时间稍后的俞平伯对此问题虽有模糊意识,却并未明确具体阐论。1921年4月27日他在给顾颉刚的书信中,如是表述:“我想,《红楼》作者所要说的,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在《红楼梦辨·后四十回底批评》中,他又充分肯定有关宝黛结局的叙写,“将宝黛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红楼梦》到现在方才能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至于和那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这真是兰墅底大功绩,不可磨灭的功绩”。
这里还有一个疑难,如果说小说对于主要人物结局的设计,维持了《红楼梦》悲剧的氛围,那么如何看待有关贾家复兴的交代呢?甄士隐不就预言么——“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第一百二十回)。等到君恩浩荡,“宁荣两府复了官,赏还抄的家产,如今府里又要起来了”(第一百一十九回),那么小说是否又会落入窠臼,彻底消减悲剧性的因子?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贾府的家势族运恐怕也不会一直走背字。于是有论者提出,正是在专制社会之下,依附皇权引发了家道复初,因此可以说,“贾府恢复世职,‘沐皇恩’‘延世泽’‘兰桂齐芳’,这不是《红楼梦》叙事结构内涵的主体,却是其内涵升华的最深刻的意蕴”。
在刘勇强看来,小说家不会以成败论英雄,而拥有更超拔的思想层次,续补的部分“也许与原著的具体描写有一定出入,但总体上还是符合曹雪芹的基本命意的。”“在曹雪芹的心中,真正的悲剧可能并不一定是彻底的毁灭,而是‘美中不足’式的、永远难以平复的缺憾。所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能也不一定是家破人亡,而是内心的无法填补的空虚”
因此,自前八十回至后四十回的变迁过程中,主要人物的形象自身确然存在一些扭曲变形,但总体上是承继下来、合理演化。而采借悲剧的观念与学说,对于阐扬作家创作意图、作品美学质素,乃至确立《红楼梦》之文学经典地位,无疑都具备关键性的意义。
从小说艺术的维度出发,文学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否泰、收结笔法的优劣,往往还直接作用于万千读者的阅读体验上。试看出自觚葊《觚葊漫笔》的一段文字:
人无不喜读《红楼梦》,然自“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以下,无有忍读之者;人无不喜读《三国志》(按:实即《三国演义》),然自“陨大星汉丞相归天”以下,无有愿读之者。解者曰:人情喜合恶离,喜顺恶逆,所以悲惨之历史每难卒读,是已。……故余谓读《红楼梦》《三国志》而遗其后半者,不可谓喜读小说。
类似这样对于阅读经验、情绪感受的直接表白,在在揭示人物结局安排的重要。而论者得出的结论,不也是对于那种不加分析一概抹倒,去截然否定古代小说名著收尾的态度的最佳回应吗?
三、文本依据与文体分析:人物结局探讨的其他方法
除去着眼情节流程尤其事件关目,以及侧重小说艺术的维度,这样从内容与形式两端(包括其融合交叉)出发考察作品,《红楼梦》人物结局的研究还包含别的方法论价值,可资借鉴。
回眸红学史有关部分,容易发现众多研究者,内心都葆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原稿”情结。所谓原稿,其由来可能是基于版本的发现,对此清人就在笔记之中有所反映:
戴君诚夫,曾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之后,皆不与今同。荣、宁籍没后,皆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于击柝之流;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故书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言也。闻吴润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
同为关乎宝玉、湘云是否终结连理的命运,等到顾颉刚为俞平伯《红楼梦辨》作《序》,也明文提到俞平伯反对后四十回的回目为原稿所有的“证据”,是既有了“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回目,就不应当再有“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的回目。
可是《红楼梦》及脂砚斋批语的文本面貌实属复杂,前后抵牾处亦多,故而不能仅凭一节一端定论。晚近的研究,如夏薇就较为系统地对后四十回中所谓“与脂批不符”的情节展开详析,其中包含所谓湘云和宝玉的婚姻。她引第三十一回脂批,又从湘云的张扬个性、王夫人的择媳标准、宝玉悬崖撒手般的失望心理等角度,有力地反驳了这一陈说。
再如,我们不能仅依据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中袭人判词的末两句“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就断言“原稿”之中,袭人出嫁必定先于宝玉出家。因为即便是曹雪芹本人,“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一经铺开,自行修改以致变动原先想法的可能就大大增加了。
“原稿”之推测,除了所谓的版本支持与作品内证,也可能有赖于脂批的提示。不妨继续来看吴世昌《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创作》一文。其对“原稿”发表的看法,可谓言之凿凿,语气斩钉截铁:
我们现在根据脂砚斋的评语,知道高氏所补的后四十回内容,与雪芹原来的全书计划和他后三十回原稿中的一些故事,颇有不同。具体说来,只有黛玉之死,宝玉被迫与宝钗结婚这个主要故事,与原稿大致相符,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部分故事是高鹗根据曹雪芹原稿零札改写而成。但宝玉二次入学,贾政升官为粮道,宝玉中举,“沐皇恩”,“延世泽”等等,则显然非雪芹原意。照脂砚斋所见原稿,贾氏被抄家后,有许多人,包括贾赦、宝玉、王熙凤等,都被捕下狱。
诚如新锐学者在清理剖析学术史某些流弊时表述的那样,“当研究者站定‘续书说’立场审视后四十回的人物命运,不免多有微词……而认为后四十回是曹雪芹原著的学者对这些人物的结局就比较满意了。但这种将作者研究与文本研究混为一谈、使作者研究成为文本研究前提的方法不甚可取。”归结起来看,既然是要在一百二十回的文本基础之上考察人物结局,大可以只取中作品的相对完满、自足性。至于后四十回作者是谁,包藏的“原稿”所占比例怎样,其中人物命运的描写又对前文进行了怎样的变易甚至篡改,如是种种,则应另作探究,自成一系。
在人物结局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如果说对于“原稿”的坚持与置疑,是考量文本基础的一种思路,那么,有关小说的繁简笔法与叙事风格,则更见美学、文体学方面的识见。昔人周永保序《瑶华传》,所云“最可厌者,莫如近世之《红楼梦》,蝇鸣蚓唱,动辄万言,汗漫不收,味同嚼蜡”,或许还没有多少同调。而谢鸿申的意见,或许就有一定代表性:
张船山诗集载《红楼梦》后二十四回,系他手所续。鄙意尽可节去。黛玉归天,宝钗出阁,正文已毕,如欲收拾一切,留起数回,仍由冷子兴口中带述,似觉简净。敢质之高明。
同是指出《红楼梦》这一“名著陋处”,张子梁《红楼梦或问》(载于延恕堂藏抄本《评订红楼梦》卷首),先说曹公此作“断断是才子书”,话锋一转,又谓其“较古来诸才子书”“稍逊”,理由是“诸事皆可追踪前人,但行文略欠简净耳”。不过,论者给出此总评之后,并未进行文本举例。实际上,叙事文学不同于含蓄蕴藉的诗词之体的地方,其一正在于酣畅的描摹、铺张的情节与丰富的细节。凡此皆不可粗略绳之以“简净”的标准。即如同步表现黛玉之死与宝钗之嫁的悲喜相形,如果没有巧合、夸张这样恣意的笔墨表现,人物的锥心痛楚、彻骨遗恨就无从传达,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恐怕也要大打折扣。
汝衡《红楼梦新评》认为,小说“其叙黛玉之死,宝玉宝钗结婚,作者一路写来实为书中不可少之结局”,并且还设身处地站在创作立场上提出,“若在笨伯,则必刻意写黛玉情场上之转败为胜,宝钗初得志而后受惩,一起落寻常窠臼矣”。显然,正是今人目见《红楼梦》这样的人物命途设定,才更能折射曹雪芹原书构思的匠心独运、胜人一筹,以及后四十回续写者行文的妥帖与妙处。至于在王希廉看来,“甄士隐说福善祸淫,兰桂齐芳,是文后余波,劝人为善之意,不必认作真事”(《红楼梦回评》),这一观点也深具启发性。受明清八股文“污名化”影响,我们对于所谓“文后余波”的古代小说章法或曰叙事文法之认识,实在亟待更新推进。
据此见出,论析该书人物结局问题之际,研究者固然应以前后照应的文本内证为基石,但不应固执拘泥于所谓“原稿”的情结。至于从叙事美学与文体学的方面,考察相关描写,不失为一条切近文学本位,有助于张扬小说审美价值的思路。
四、《红楼梦》人物结局问题的研究意义
冥飞曾在1919年5月1日出版的《古今小说评林》中,提出自家的总体认知:“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故其书绝未提出一对美满夫妇,而所言者俱是婚姻苦事。”接着,他罗列贾府上下众多小姐丫环的不幸命运,又由诸般凄惨的现象上升到本质层面,发表了“一切好女儿,其精神上肉体上所受之痛苦,皆由夫妇制度直接间接所馈送而来”的观点。这应当代表着前人归结《红楼梦》人物结局问题的深层见解,是所谓从制度源头寻找症结的努力。
迄今学界早已公认,《红楼梦》足堪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范本,小说的评判与阐释、小说史叙述、小说创作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都离不开作为小说标准的《红楼梦》。不过不能因此抹杀这样一种探索努力,即与此同时去“从小说史看《红楼梦》的局限”,揭示其社会描写、分回、回目文字等的粗疏不足。
前人还曾发表这样的观点,《红楼梦》其书“偶或于时日略有矛盾,事件略欠照应,如十二钗中之史湘云、妙玉之来历,未曾明言,不知其何时进贾府,要亦白璧微瑕耳”。只是通过本文对研究史的回顾分梳,不难发现,与人物来历方面的问题相比对,此书的人物结局更加凸显重要性。
试加小结,这一课题的研究意义约有三端:其一,从个案角度说,《红楼梦》人物研究的破局之路庶几得到指引;其二,推展开来看,古代小说结尾问题的深入探讨与公允估量,这一学术路径获得了具体的入口;其三,理论方面古典文学作品的缺憾考察及其与经典化的关系,理应获致更高的重视程度。
这里还想就最后一点学术价值的挖掘赘叙数言。前面《引言》部分,开启了将《红楼梦》人物结局问题的存在形态,置于“经典”与“缺憾”两极之间的端绪。本文还想强调,此书对于各个人物命运的种种安排,与以后四十回表现最为突出的众多结局书写,正跟该小说数百年接受中,逐步趋于“典律化”的过程息息相关。这一过程当然也意味着面对诸般误会曲解、厚诬控诉,由此见证了一段评论史、学术史的嬗变。
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曾谈及对“两种传统”的理解,即“阅读过去的重要文学作品的人不但获得了作品的传统,而且获得了解释作品的所属传统。解释作品的传统渐渐地体现在作品本身中”。因此,文学经典及其问世后引发的评说议论,都在彰显其足以穿越时空隔阂的价值丰富性与永恒性。我们需要留心某一时期人们对类似《红楼梦》这样经典的理解,同时对后代的读者而言,这些解释又构成了经典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所谓经典的累积性,正是历来的文学史书写题中应有之义。
《红楼梦》一书对于完结人物行止的表现,自有不少富于巧思的闪光之处,即便是那些设计安排并不成熟甚至还产生偏颇的地方,其实也正可作为今人从创作或研究角度,进行总结汲取教训的对象。本文认同这样的看法,名著的缺憾应该成为文学经典化讨论的内容之一,不解析经典小说的缺憾问题就无法全面理解经典的涵义,也会影响我们对经典标准的把握,并因此漏掉一些经典作品。只有理解了经典小说的缺憾或曰缺陷问题,才便于我们确定“经典”的衡量尺度。
事实上,围绕《红楼梦》人物命运描写而产生的大量争议与不同见解,都在提示我们,进行梳理的时候,尽可能地既要通今博古,又要心细眼明。同时这也启示着读者和评论者,正犹如“人不可无癖”一样,文学作品也是“真玉有瑕”(此用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回评语意)的。我们在摈弃了吹毛求疵的态度以外,反过来应努力提升欣赏脂砚斋第二十回批语所说“美人陋处”的眼光、素养、能力。如此,方不辜负了时间浪潮淘洗下依旧闪烁真金光芒的经典之作。
①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238—239页。
②⑩ 欧阳健《〈水浒传〉“结末不振”问题新议》,收入《古小说研究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27—144、140页。
③[20]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170页。
⑤[33][43] 郭丹曦《〈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述论》,《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221、221页。
⑥[37]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437页。
⑦ 曹雪芹著,无名氏续,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后面所引小说文本,皆据此书,不再出注。
⑧ 本文强调的是作为整体性文本现象的系统研究,类似讨论“黛玉之死”“晴雯之死”的单篇论文自然不少,可以参看刘晓安、刘雪梅编纂《〈红楼梦〉研究资料分类索引(1630-200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的专题整理。
⑨[27][28][45] 黄霖编著《历代小说话》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361,421、630、636,634—635,427页。
[11] 姚燮、解庵居士和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的言说,见载黄霖编著《历代小说话》第2册,第550—551、623、775—776页。
[12][29] 此文为王氏1943年作于重庆,收入太愚(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国际文化服务社1948年版)。后1962年夏经作者修改于北京,揭载《光明日报》1962年12月8日。本文所引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6页。
[13] 李君侠《红楼梦人物介绍》,台湾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4页。
[14] 邱露《明清长篇家庭小说死亡叙事研究》,河南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第7—8页。
[15] 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文学创作》第1卷第3期(1942年11月),引自苗怀明选编《红楼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150—151页。
[16] 段启明《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几个问题》,《西南师院学报》1978年第2期。
[17] 胡文炜《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宝黛形象》,《辽东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8] 张惠《〈红楼梦〉后四十回宝玉中举正读》,《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9][35][40]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75、152,75页。
[21] 李希凡、蓝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为什么能存在下来?》,《文艺月报》1956年第6期。
[22] 童庆炳《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23] 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219页。
[24] 石昌渝《论〈红楼梦〉人物形象在后四十回的变异》,《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
[25] 陈其泰评,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26] 陈洪《红楼内外看稗田》,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版,第456页。
[30] 潘建国《〈金瓶梅〉、〈红楼梦〉中的美人之死》,《文史知识》2013年第11期。
[31]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11页。
[32]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63页。
[34] 民国9年(1920)泰东书局初版《中国小说史大纲》,陈洪主编《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第1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36] 郑铁生《谈〈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矛盾现象》,《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38][46][47][48] 引自曹雪芹著,陈文新、王炜辑评《红楼梦》(百家汇评本)(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03、700、853、832—833页。
[39] 蒋瑞藻撰,蒋逸人整理《小说考证》卷七引《续阅微草堂笔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41] 夏薇《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9—70页。
[42] 原载《散论红楼梦》,香港建文书局1963年版。选自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又见载《红楼二十讲》,第222页。
[44] 清谢鸿申《答周同甫书》(第二函),载《东池草堂尺牍》卷一,引自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2页。
[49] 刘勇强《作为小说标准的〈红楼梦〉》,《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50] [日]盐谷温著,郭希汾编《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初版,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年再版。引自陈洪主编《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第2卷,第95页。
[51] [美]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52] 曹金钟所著《〈红楼梦〉“矛盾”现象考论》(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部分内容可看成遵循这一学术路向的最新研讨。
[53] 参见李建武《小说经典形成、扩容与明清小说的文学经典性》,《文艺评论》2015年第4期。类似的表达,又见于氏著《〈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文学经典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