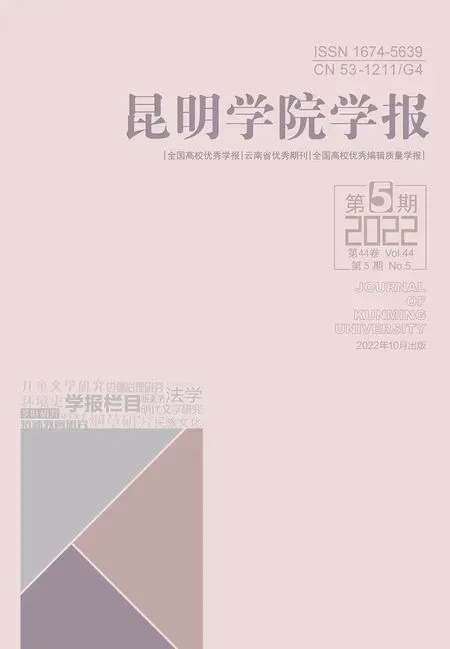《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实证研究
2022-11-01刘文林
刘文林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一、问题的提出
(一)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发展概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1]生态文明建设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是关乎国民生计和建设美好家园的大事。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都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从立法层面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最早源于2015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1号,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解释》)。其中,《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2]早在2016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征求意见稿中,立法者就已经提出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侵权责任方式,之后几经删改,最终未将该规定纳入总则。2020年5月,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在第7编“侵权责任编”第7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第1234条中确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将生态环境这类公共利益的损害纳入民法私益的保护范围,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实体法依据,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司法保障。
从实践层面看,在2020年《民法典》正式确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前,司法实践中就已经在适用该责任解决环境侵权纠纷问题。例如,在“公益诉讼人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苏某某、陈某某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对尤溪县林场熔炼厂周边受污染环境(8.223 1亩)进行修复(按照环保部门制定的相关标准执行)。”(1)参见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4民初124号民事判决书。在“印江自治县华鑫建材矿业有限公司非法占用农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补植复绿不得少于12.662亩,并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验收”(2)参见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黔0625刑初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书。。
(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立法层面和实践层面,我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都有所发展,但是通过梳理有关学理研究现状和司法裁判文书可知,现阶段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的学理研究不足。201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修订实施以后,有学者针对《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司法实践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3]。同年,也有学者针对典型热点个案进行过实证研究[4]。2020年,有学者针对《侵权责任法》第15条在适用9年里所有“环境污染责任”案件中“恢复原状”的司法领域适用情况进行过实证研究[5]。但是,立法新规的实践情况需要结合实施前后的不同情况对比分析,单一维度研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而忽略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或者单纯地研究典型个案等,都会使得研究样本不全,从而造成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不足。而且,《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责任的保护对象限于私益,《侵权责任法》并不直接保护生态环境本身,《民法典》第1234条保护的是侵害生态环境本身的行为,属于公益[6]。目前,专门针对《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实证研究比较欠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二是《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体系尚不完善。《民法典》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问题只是做了大致规定,至于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该如何适用,例如修复方案、修复资金管理、修复监督等问题均没有做出进一步规定,需要通过司法实践探索来进一步完善。因此,本文立足于2015年“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首次司法探索适用,直至《民法典》颁布后的所有环境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全方位、各角度综合分析其适用情况。一方面,弥补现阶段该制度的实证研究空白,为推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学理发展做贡献;另一方面,全面综合分析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探索解决方案,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体系。
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案件司法实践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通过“小包公法律实证分析平台”(3)由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法律应用研究中心研发,利用人工智能、司法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与法学研究深度融合的智能法律服务平台。,选取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23日期间,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或“造成环境污染并且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形,或者裁判结果为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情形。同时,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在筛选了3 571份判决书后,剔除其中侵害法益为私益,原告主体为自然人的民事权益侵害案件502份,最终锁定民事环境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书3 069份。经整理分析,2015年至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呈现以下特点。
(一)案件类型: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主
生态环境损害与私益损害不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行为侵害的对象是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所共享的权益,其利益主体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由众多生活在环境中的个人所组成的“人类”。[2]换言之,生态环境损害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对于侵害“生态环境”这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些构成民事违法行为,法院判决当事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有些则构成刑事犯罪行为,法院在判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也会判决当事人对生态环境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小包公法律实证分析平台可知,从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23日,在 3 069 份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被告人因为刑事犯罪侵害社会公共利益,被检察院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共有 2 655 份,占比86.51%;由检察院、国家规定的机关或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共有414份,占比13.49%.在生态环境损害后,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案件共有1 221份,其中,刑事附带民事1 085份,占比88.86%;民事136份,占比11.14%.在司法实践中,多数生态环境损害案件都是刑事案件,而非民事案件。可见,不仅民事案件中法院适用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中也大量适用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二)案件年份分布:《民法典》的实施助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大量适用
如图1、图2所示,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数量年份分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法院判决被告进行 “生态环境修复”的案件年份分布趋势与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总量分布趋势一致。二是2020年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呈“井喷式”增长。为何2020年前后两年的案件数量呈现突增趋势?探究2020年我国立法情况可知,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7章修改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为正确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分别对《环境公益诉讼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12号,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解释》)进行了修正。由于《民法典》的通过,以及《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环境侵权解释》的修正,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认定有了实体法依据和诉讼法支撑,因此案件数量比往年增多。三是在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早在2020年正式纳入《民法典》之前就已经普遍适用,随着《民法典》的通过及正式实施,其司法适用范围逐渐扩大。

图1 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年份分布

图2 法院判决“生态环境修复”案件年份分布
(三)案由分布:刑事、民事案由均相对集中
1.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刑事案件案由:适用罪名集中
如图3所示,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生态修复责任”(包括替代修复)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10类,其中,非法捕捞水产品罪(370件)、滥伐林木罪(126件)、非法占用农地罪(99件)占主要部分,集中分布在少数罪名。究其原因,通过对比分析该类型裁判文书得知,一方面,在理论上,此类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所涉及的内容要求被告承担起“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因此法官会判决被告履行“生态修复”的义务。尽管有学者主张民法上“恢复原状”不等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二者有着本质差别[7]。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较于与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等案件,其判决结果更容易达成,可通过增殖流放、补植复绿、异地恢复等方式实现。例如,在“燕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燕某在汕尾海域增殖放流价值不低于人民币 23 760 元的鱼苗进行海洋生态修复,并有渔业部门监督指导(4)参见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502刑初18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在“彭金良犯失火罪”一案中,法院判令“被告人彭金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年内在被烧毁的148亩林地范围内按林业主管部门规划植树造林,保证成活率85%以上,以修复生态环境。”(5)参见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8)闽0526刑初2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因此,由于该类刑事罪名的本身特点决定了其适用生态修复责任的便捷性,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罪名集中,主要分布在少数罪名。

图3 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刑事案件案由
2.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由:“生态破坏责任”纠纷独立适用
由图4可知,在414份生态环境损害民事案件中,案由分布较为集中,其中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的案件150件,占比36.23%;侵权责任纠纷111件,占比26.81%;生态破坏45件,占比10.86%. 可见,《民法典》实施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案由分布的突出特点在于“生态破坏责任”纠纷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一项独立的案由,并且以“生态破坏”纠纷作为案由的案件比重也有了很大提高。《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法院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提供了实体法依据,对保护环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图4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由
(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原被告主体相对单一
1.原告主体:检察机关是提起公益诉讼的主要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2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生态环境损害类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为人民检察院,在此不再赘述。《民法典》第1234条:“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通常认为,人民检察院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机关是以上国家规定的机关[6]。何为法律规定的组织,根据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为以上法律规定的组织[8]。因此,按照法律的规定,检察院、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机关、社会环保组织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如图5所示,虽然在414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排名前20的原告主体包含了法律规定的三类主体,但是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诉讼案件就有314份,占比75.85%. 学者江必新2019年的研究显示,检察院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力量[9],时至今日,检察院依然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要主体。而其他原告主体,例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17 件)”“中华环保联合会(11件)”“自然之友(7件)”也紧随其后,逐渐承担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职责。

图5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分布
2.被告主体:自然人占比遥遥领先
为方便统计,笔者将3 069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的被告主体,按照其性质及实践情况分为自然人、法人(公司)与其他(个体户、村委会、专业合作社)。被告为自然人的案件数最多,有2 656件,占比86.54%;公司居其次,有370件,占比12.06%;个体户有35件,占比1.14%;村民委员会有6件,占比0.19%;养猪专业合作社有2件,占比0.07%. 由此可见,实践中绝大多数环境公益诉讼都是针对自然人提起的,在司法实践中环境公益诉讼仍然普遍存在“捏软柿子”“不敢啃硬骨头”的现象[10]。
(五)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形式:生态修复责任成为主力
部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法院并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62份),在其余2 907份案件中,按照法院的判决结果,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责任承担形式主要为赔礼道歉、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替代修复、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如图6所示)。出乎意料的是,实践中法院对大部分案件都会判决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此类案件占比37.11%. 其次,判决被告直接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类案件为占比34.50%,替代修复占比7.37%.不容忽视的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在实践中也被法官广泛适用,其占比为14.95%.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的适用并不多,一方面由于该类案件本身数量就不多,另一方面停止侵害的大量内容要求被告积极作为,需付出的经济成本(如拆除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政治决策、技术支持等原因,法院不会草率做出判决[3]。

图6 责任承担形式
三、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不足
随着2020年《民法典》的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呈现“井喷”之势,但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整体数量较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依然存在适用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在案件类型分布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414件)与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 655件)分布相差较大,绝大多数案件都是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后附带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直接由检察机关、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机关、法律规定的社会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则占比较少。另一方面,诉讼主体上,由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机关、法律规定的社会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占比较少,大多数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行政机关或社会环保组织,自2015年至2022年,近7年期间仅提起过1起或者2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例如,兰州市生态环境局、中山市环境科学会、郴州市阳光志愿者协会等。更多的环保组织自成立以来均未提起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没有充分发挥环保组织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因此,我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呈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占比过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不足等问题。
(二)生态环境修复判决内容不明确
生态修复的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环境的正常功能,包括将环境要素恢复至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的状态和合理期间内维护的义务。[11]态环境修复具有复杂性,需要制定具体可执行的修复方案,才能保证修复效果的实现。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官只是判决被告进行生态环境修复或者支付替代修复的费用,至于如何修复、修复到何种程度、修复日期、监督验收等问题均未做出明确规定。例如,在“闫振江土壤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仅仅是判决被告“治理修复或替代修复被污染的土壤,达到环保标准”(6)参见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1民初345号民事判决书。,并没有做过多的要求说明;在“广元市虎星建材有限公司生态破坏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仅判决被告“在期限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603 122.89元,资金用途为异地补植复绿。”(7)参见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8民初23号民事判决书。以上修复判决内容都不明确,并不具有可执行性。因此,生态环境修复判决要有详细的修复方案,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才可实现。在修复方案的制定上,通过小包公法律实证分析平台的数据可知,实践中法院判决被告按照制定的修复方案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的案件占比仅为6.84%;大部分判决书中都没有具体可行的修复方案,占比93.16%,这种没有具体修复方案的判决书,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效果会大打折扣,很多判决书可能因修复内容不明确而沦为一纸空文。
(三)生态环境修复缺少监督
由于生态环境修复本身的复杂性,生态修复需要制定科学、系统、可行的修复方案。但是,即便有可行的修复方案,还需要有对应的权利人对修复过程监督和修复效果进行评估验收。2015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经过试点以后,2017年12月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在以上两个“方案”中,均有对生态环境修复进行监督的规定(8)2015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加强生态环境修复与损害赔偿的执行和监督。赔偿权利人对磋商或诉讼后的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进行评估,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款项使用情况、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要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2017年12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对该条未做修改。。在司法实践中,只有部分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提出由相关责任人或权利人对生态环境修复情况或修复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大多数法院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据小包公法律实证分析平台的统计数据可知,在法院判决被告直接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的 1 006 份裁判文书中,明确由相关责任人进行生态修复监督的判决书仅有65份,占比6.46%,其余941份判决书均未规定生态修复的监督问题。
(四)修复资金管理不合理
《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规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但是,具体如何管理侵权人赔偿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民法典》并没有做出规定。实践中,对于修复资金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探索中,根据小包公法律实证分析平台的统计数据可知,在 1 006 份裁判文书中,仅有319份判决书对修复资金的管理方式做出了规定。如图7所示,在通常情况下,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的管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图7 修复资金管理形式
一是由检察院管理。该种管理方式是法院判决被告将修复资金支付至公益诉讼起诉人检察院的账户。例如,在“宁波高新区米泰贸易有限公司、郎溪华远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赔偿非法进口固体废物(铜污泥)的处置费 1 053 700 元,支付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公益诉讼专门账户。”(9)参见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3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李某滥伐林木罪”一案中,法院判令“被告李某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横县人民检察院支付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 116 507.00 元,此款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10)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2021)桂0127刑初1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二是由法院管理。即法院判决被告将修复资金支付至法院自己管理的账户。例如,在“邢台市宁波紧固件有限公司、赵建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判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倾倒坑塘水面 407 520 kg危险废物(废盐酸)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2 399 477.76 元、鉴定费 125 000 元,总计人民币 2 524 477.76 元支付至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11)参见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5民初35号民事判决书。
三是由地方财政局管理。例如,在“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与被告张某1、张某2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案件中,法院直接判决被告“交付至重庆市南川区财政局专用账户,用于替代修复。”(12)参见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3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在“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与澄迈中兴橡胶加工厂有限公司环境污染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应急处置费用 363 395 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337 316 元、鉴定费 268 000 元、专家咨询费 7 504.15 元,合计 976 215.15 元,以上款项支付至澄迈县财政局财政性资金账户。”(13)参见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1民初737号民事判决书。
四是设立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即设置生态环境损害公益诉讼资金专项账户,管理生态修复资金的使用情况。例如,“公益诉讼起诉人遵义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肖某1、肖某2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中,法院判决“肖某1、肖某2应当立即向遵义市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预付生态环境修复费 1 606 294.59 元。”(14)参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3民初391号民事判决书。
五是由政府环保部门负责管理。例如,环保局、自然资源局、生态局。在“江苏省环保联合会与被告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判决被告赔偿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 2 428.29 万元,交付至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账户,用于生态修复。(15)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初1203号民事判决书。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曾宏明、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检察院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一案中,法院判令“被告曾某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给付被毁林地20.78亩的生态恢复补偿金人民币 10 390 元,此款支付至龙岩市永定区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管理账户。”(16)参见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20)闽0803刑初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虽然以上管理方式多样,实则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由法院、检察院管理修复资金的方式,会增加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负担,法院、检察院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案件,同时也要收取各种形式的费用,因而无暇于应付管理修复资金的使用情况。其次,法院、检察院对生态修复问题并不专业,由法院、检察院管理,实际修复人的修复工作对接问题可能存在困难。实践中,多数生态环境修复案件之所以由法院、检察院管理修复资金,是因为这类案件的公益诉讼起诉人就是检察院,因此法院只能判决由原告检察院自己管理修复资金,或者判决法院自己管理修复资金。最后,如果交由地方财政管理修复资金,可能会出现入账后被挪作他用、取回困难等问题,无法保证修复资金被真正用于生态环境修复[12]。因此,实践中便出现了由法院、检察院、地方财政管理修复资金不合理,但又没有合适的资金管理方式的问题,最终大部分案件的修复资金问题还是只有由法院、检察院来管理。
四、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体系的建议
(一)推动环保组织积极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比例大致为6 ∶1。其中,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大多数案件又由检察机关提起,这不仅体现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不足的问题,也体现出环保组织积极性不足的问题。究其原因,相比社会环保组织而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其更有能力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承担败诉的风险。而社会环保组织,一方面需要考虑律师费、差旅费以及高昂的鉴定费等费用,需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撑;另一方面,环保组织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败诉的风险更大,一旦败诉,其前期支付的所有巨额经费将付之东流,这对于环保组织而言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实践中,即使有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是具有相当实力和经验的全国性组织,例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自然之友等。此外,地方性的环保组织为了规避风险,要么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么就以自然人为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因此,如何激发地方性环保组织活力,鼓励其积极参与、提起诉讼,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是当下需要考虑的问题。在经济上,为解决其后顾之忧,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应当设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专项基金,支持其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学者提出,如果社会组织败诉,上述相关费用应当由“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或“环境公益基金”支付[13]。在败诉的风险上,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在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协助调查取证、帮助损害鉴定等方式给予支持,尽可能避免败诉风险。
(二)明确具体的生态修复方案
将生态环境修复方案作为判决书的一部分,明确修复内容。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第4.11条的规定:“生态环境修复,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为将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基线状态”。如何将生态环境修复到“基线”状态,需要有具体明确的修复判决。将修复方案作为判决书的组成部分,可使“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判决内容明确具体,提高生态修复的可执行性。例如,实践中有的法院在判决之前已经确定了专业的修复方案,在“丁某某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按照巴塘县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巴塘县拉哇乡索英村2020年2月25日森林火案植被恢复方案》在四川省巴塘县夏邛镇波麻尼开始补植复绿,并承担连续三年的管护责任,三年后株数保存率必须达80%以上。”(17)参见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33民初18号民事判决书。有的法院在判决前没有确定好修复方案,而是要求被告制定修复方案,又如,在“大方绿塘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着手实施对大方岔河水库下游河流水体和底泥造成的污染恢复原状,若十五日内未完成对外委托和制定修复方案,则立即按向其指定的账户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 42.260 74 万元。”(18)参见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5民初148号民事判决书。而有的法院则对之前制定的修复方案给予认可,再如,在“衢州迅通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对广东环科院和广西环科院联合做出的《损害评估报告》和《土壤修复方案》给予认可(19)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9民初90号民事判决书。。因此,对于类似具有创新性、可行性的判决,应当积极借鉴。在制定修复方案时,应当积极咨询专家意见、社会公众意见,确保修复方案的专业性和可行性。
(三)指定生态修复监督管理人
探索以负有生态监督职责的行政机关为主,检察院、法院、社会环保组织、专家辅助人、公众等为辅的生态环境修复监督体系,确保修复成效。《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高效落实,除了需要具有可行的修复方案、内容明确的修复判决外,对于修复过程的实施以及修复结果的验收,还需要具有明确的修复监督管理人。实践中,对于生态修复监督管理人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由检察院作为监督管理人。这类案件大多是由检察院作为原告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例如,前述“大方绿塘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对外委托修复或者期限内未委托修复则支付修复费用,由检察院监督实施。二是由环保部门监督实施。例如,在“辽源市人民检察院诉潘洪滨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潘某某于2022年10月1日前在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山湾村四组非法采矿区域,种植杨树 2 265 株,补种树木当年存活率达到85%,由辽源市自然资源局负责验收。”(20)参见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吉04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书。三是由社会环保组织监督实施。在“公益诉讼起诉人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陈某3、陈某2、陈某1侵权责任纠纷公益诉讼”一案中,法院判决“履行情况由绍兴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进行监督和确认。”(21)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6民初356号民事判决书。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的规定(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内告知对被告行为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本身就具有法定的监督义务,提起诉讼之前其没有履行好自身的法定义务,在其他组织提起诉讼之后,其更应该积极参与诉讼当中,对法院修复生态的判决负有监督实施的义务。因此,应当以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职责的机关为监督主体,其他组织辅助之。
(四)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
生态环境损害的利益是生态环境本身,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胜诉以后,生态环境修复资金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并不属于原告个人,该部分资金应当用于生态修复。但是,如何管理、由谁来管理该部分资金则成为实践难题。由于文中所列举的由检察院、法院、地方财政等作为修复资金管理人并不合理,为科学合理地管理修复资金,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过关于修复资金管理的意见(23)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其中第14条指出“探索设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将环境赔偿金专款用于恢复环境、修复生态、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经过司法实践探索,一些法院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账户”,并且确定了资金管理人,负责将该项资金用于生态环境修复[13]。例如,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董永污染环境罪”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人董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基金专项资金账户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 12 000 元”(24)参见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苏8601刑初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有的法院判令“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受损期间服务功能损失 79 613.8 元,该款汇入遵义市环境公益诉讼专项资金账户。”(25)参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3民初391号民事判决书。因此,以上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的制度,既缓解了法院管理修复资金的压力,又便捷了生态修复资金的使用,更大程度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值得其他法院借鉴。
(五)探索适合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判决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政府机关、司法机关或环保组织的工作,良好生态环境的维护更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为了更好地警示教育公众爱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中一些法院通过了以“履行公益劳动替代生态环境修复”的创新司法判决形式(见表1),既救济了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又对当事人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提升了全民生态文明素养,可谓一举两得。

表1 “履行公益劳动替代生态环境修复”的创新判决形式
综上可知,这类要求被告履行公益活动的判决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案件本身不适合直接生态修复;二是当事人需要赔偿的生态损害赔偿金或者替代修复金的数额不大;三是有专门的监督管理人对公益活动进行监督。首先,如果案件本身就非常适合直接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就没必要判决侵权人以履行公益活动的替代方式教育侵权人。其次,对于生态损害赔偿数额不大的案件,如果直接判决当事人进行支付赔偿金,对于侵权人而言无关痛痒,其完全可以牺牲小额赔偿金继续实施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最后,如果履行公益活动的判决没有专门人员负责监督管理,则该判决很容易落为一纸空文。因此,此类要求被告从事一定时长公益活动的判决,一方面以转移的方式保护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警示教育了侵权人,既提高了生态环境修复判决的可执行性,又激发了民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热情,值得其他法院推广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