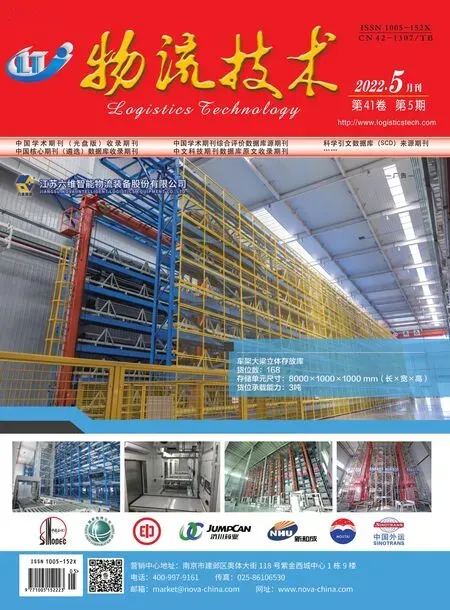秦代主要“物流”成就及其影响概述
2022-11-01湖北物资流通技术研究所
湖北物资流通技术研究所 艾 振
武汉纺织大学 周兴建
前四期里,我们就先秦时期有关仓储和运输的部分内容做了简要介绍。这一期我们将从“物流”的视角重新了解一次秦代,讲述这个朝代的先辈们与“物流”的渊源,总结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运输措施、仓储战略的部署和成就,并反思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1 因交通起家的秦代先辈
史料中,关于秦建国之前一千多年的记载多与交通运输有关。
舜帝时期,在表彰大禹治水之功时,大禹回答:“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大费因此受到舜帝的嘉奖—娶了舜帝给他挑选的妻子,并开始辅佐舜帝畜牧。
夏末时期,大费的五世孙费昌,因不愿跟随夏桀而“去夏归商,为汤御”,随后以商汤专职驾驶员的身份协助商汤在鸣条打败夏桀,
商朝时期,大费的另两个五世孙孟戏和中衍驾驶技术出众,商王太戊“闻而卜之使御”。此后,中衍的子孙们也世世代代为商王驾车,为此很多嬴姓人逐渐身居显位——“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商朝末年,中衍的五世孙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因“善走”,“俱以材力事殷纣”,算是
进入西周,蜚廉的另一个儿子季胜有一个著名的曾孙名叫造父,长于识马用马,精通驾驶,因此“幸于周缪王”。他曾为缪王驾车西游三万里;在徐偃王作乱时,又“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为表彰造父
恶来的后代也因造父受宠而得赵氏。他的一个五世孙叫做非子,善于养马。因此“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闲,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翳(大费)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而恢复嬴族祭祀则意味着嬴族一姓十四氏及更多的平民从此有了共同的领袖,。
要知道,先秦时期车和马都是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大到礼仪、战争,小到日常生活,可以“载重致远”的车、马承担着人员和物资转移的重任,几乎意味着整个陆上交通。它们的发展水平甚至直接影响或代表着国家形象和实力,其地位远非现世可比。而秦之所以赢得自己的姓氏、封号和各种荣誉,之所以能逐步壮大并统一全族,无不因他们的先辈们在养马或者驾驶领域的突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
2 从“物流”角度看秦国的崛起与统一
2.1 武装押运的超级回报
非子得秦地后,秦人一直在与西戎的纠葛中惨淡经营,终于在秦襄公时迎来一次翻身的机会。公元前771年,惯用“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城破被杀。几经波折之后,周平王掌权。面对战后破败的镐京和西戎的袭扰,平王决定迁都洛阳。政治嗅觉敏锐、在周朝救乱中表现积极的秦襄公得知消息后立即响应,“。偌大一个国都长途迁徙了。大宗伯抱着周朝的七庙神主乘车在前,平王御驾随后,各类物资绵延不断,车队一眼无边;数不清的百姓携老扶幼,带着自己的家当车拉肩扛的跟在其中…。公元前770年,立稳脚跟后的平王论功行赏:“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秦襄公成为了诸侯,秦国也在襄公手上正式建国!顺带着,秦国还被赋予了夺取岐山的正当理由,为秦国日后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秦国在这次“武装押运”活动中,获得的回报“不可计矣”。
周王室的东迁让秦国获得了更大的战略发展空间,但秦国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需要考虑如何向中原的政治中心进一步靠拢。所以,处理与挡在东边的强邻晋国的关系成了长久以来秦的政治大事。好在在和亲等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情况下,机会一再垂青着秦国。
晋公元前650年,晋献公死后,他流亡在梁国的三儿子夷吾承诺以河西八城作为酬谢,请求秦穆公送其回国继位。秦穆公欣喜的命重臣百里奚率队,全副武装、小心翼翼的把夷吾从秦都雍城护送回晋国当上了晋惠公,秦国再次当上了大国之君归国继位的护送者。
历史继续往前。晋惠公的继任者晋怀公不得人心,晋国决定迎立晋献公的二儿子重耳回国。在外颠沛流离十几年,历尽人间冷暖的重耳出于各种原因同样选择了求助秦穆公。公元前636年,秦穆公一次性将自己的五个同宗女子嫁给重耳,又派公孙枝率领三千人护送重耳渡过黄河,让他带着秦穆公的无限“恩惠”回国当上了晋文公。就此,秦穆公坐稳了晋国第一救星的交椅。与政治联姻相比,秦国从更高层次上涉足了晋国政治的同时,也通过晋国把影响力渗透到了中原大地。
其实,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各国互换质子盛行,类似的武装押运事件在秦国还有很多,在其它各国也时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哪个史学家把它们作为军事行动来看待为此,我们不禁可以思考:秦国派出的那些不以战斗为目的,只为保护受托目标安全送达,从而获取高额回报的武装队伍,算不算现代服务于金融等机构的那种押运业务,和前朝那种武装送货军——镖局的前身?
不管怎样,秦国抓住难得的几次机会,用长途护送这种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提升了自己的地位,稳固了与邻国的关系,并向诸侯汇集的东方尝试着迈出第一步。
2.2 秦国的通道建设
我们先用一个案例来说明掌握运输通道对秦国的重要性。
秦之行暴于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战国策·燕策二》
秦国正告楚国:秦国占住水运通道,就可以轻松出兵到你城下,即便你人才再多,也来不及反应,就问你服不服?!楚国深以为然,因此屈服于秦国十七年。同样的,秦国以切断运输通道、占领关键运输节点为要挟,让韩、魏国等国被迫“事秦”。
东向主要有崤函通道、晋南豫北通道及商洛、南阳通道三条;南向主要有金牛道、褒斜道等栈道。
,镐京(今西安)和洛邑(今洛阳)之间的一条古老道路,全长400里。西连关中平原,东接中原大地;南北是高耸的秦岭和山西高原。最窄处“车不并辕,马不并列”,仅容一人通过;两侧高崖陡峭,其中有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天日”,险要至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函谷关、潼关,黄河沿岸的风陵渡、太阳渡和茅津渡等重要渡口都分布其中。崤函通道在东周初期即被晋国占据,但它又是秦国东出的必经之路。为此,这条通道成为长久以来秦晋关系的核心。为了打通这条通道,秦国不惜与晋国及后来的魏国战斗了300多年,直到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打进洛阳后秦国才实现了对它的完全掌控。
秦晋七十年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兵者,以此故也。—清·顾栋高
凭借此道,秦国不但实现了东出中原的梦想,还有效防止了它国入侵。事实上,单是通道上的那个函谷关,六国就拿它没有任何办法。
于是六国之士…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贾谊《过秦论》
西起陕晋边界的临晋(今陕西大荔),蜿蜒向东北,到达邯郸所在的冀南平原,连通了秦国和赵国。它依群山、傍黄河,占据着天然之险,又在紧要处建有临晋关,秦国掌控此道之后,诸侯各国无一次敢通过此道攻秦。
起于咸阳,向东南穿秦岭、过武关进入南阳,最后延伸到楚郢都所在的江汉平原,是秦、楚之间的核心通道。通道上的武关与函谷关一样险要,素有“关中锁钥”、“三秦要塞”、“秦楚咽喉”之称。更是被清朝的顾祖禹评价道:“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武关巨防,一举而轻重分焉。”公元前505年,秦哀公助楚昭王复国之后,拿到了楚国赠送的六百里商於之地,武关道也随之归秦所有,楚国此后数次想要讨回未果。通过此道,秦国多次重创强楚。它一面见证了秦国的崛起,一面目睹了楚国的衰亡。
,又称石牛道,是最早见于史书的古蜀道之一。秦惠王伐蜀时,为了打通通往巴蜀的道路,以运送“夜能粪金”的石牛给蜀王为由,骗蜀王遣五丁力士在大、小剑山、五丁峡一带峭壁处,日夜劈山破石,凿险开路打通了1 200里的悬崖栈道。随即,惠王沿此路灭蜀。对秦国而言,它战略价值极高:此道一开,“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
,又称“斜谷路”。古时巴蜀通秦川的主干道路,重修于秦昭襄王时期。它在悬崖绝壁之间穴山为孔,插木为梁,铺设木板以联为栈阁,让原本极其难走的小道成为可通过军队和辎重的驿道。南起褒谷口(汉中市大钟寺附近),北至斜谷口(眉县斜峪关口),蜿蜒穿越秦岭之间,穿褒、斜二谷,全长500 里。《史记》里评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
秦国攻下巴蜀的一个原因在于:拿下巴蜀就等于控制了长江航道的上游。这样就形成了对下游楚国的战略威慑,降低击败楚国、进而统一天下的难度。
(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月志》
于是才有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之类的诸多胜利。
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任水利专家李冰为蜀守,历时14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在岷江上筑建了世界水利史上集防洪、灌溉、运输于一体的惊世之作—都江堰。自此之后,岷江改道成都,进出巴蜀的水路畅通,上游汶山的木材可顺江而下,运往成都,并在这里直接打造成船,装载运输。岷江之上,飘满了运载辎重的船舶。成都也成为秦国真正的集散中心。制约秦军兵马、粮草补给效率的重大短板得到了很好的弥补。
例如,公元前289年他们一口气打下了黄河沿线包括魏国轵邑(今河南省济源县)在内的62座城,只为保护黄河水道的运输安全。
这个“四塞之国”不但在秦穆公时贡献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水陆联运壮举—“泛舟之役”,我国见于史载的首座黄河浮桥竟也由秦国建设。
这些陆上和水上通道一起,织就了秦国扩张的供给网络。
2.3 大国的仓储战略
储粮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有着宏大志向的秦国统治者们当然更加明白。
。公元前659年,出使秦国的西戎人由余感叹秦国的仓储:“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站在由余的角度,秦国的储蓄之多无异于劳民伤财—即使鬼神来做,也要花费很大力气;要是让人来完成,则必定有很多百姓受苦。但它无疑又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秦国的仓储规模有多惊人。十二年后,秦国能轻而易举的救济饱受饥荒的晋国(指泛舟之役),还熬过了第二年自己的大灾之年,同样佐证了这一点。
在形制上,秦国的仓储形态基本有囷、仓、窖三种。一般来说,囷的容积较小,仓的容积较大,都建于地上;而窖则建于地下。这与其它诸国类似,属于时代的特征。
在等级上,秦国粮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类。都城设有太仓,各郡县设有县仓,乡又设有离邑仓。分别由内史属官、县啬夫、仓佐等职官负责,等级严明,便于管理。
在管理上,秦国颁有《仓律》,内容全面而细致。粮食以“积”为单位隔上荆笆,设置仓门。地方仓库一万石一积,旧都栎阳二万石一积,都城咸阳十万石一积。入仓时由县级主管和具体经办人员共同验视、共同封印。所有粮食编有“仓籍”,记上数量、经办人员等信息,供年底或出仓时核对。如发现粮仓漏雨、仓储亏空、库房门闩不严、有鼠穴、有粮食朽败等,都会视情节轻重对管理人员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正如卢鹰所说:“仓政管理法的严密性和系统性都是历史上少见的。从粮食的入仓,贮藏保管与使用分配的每一道程序都制定了具体详细的法令。”
此外,《效律》等处规定了如何晾晒、如何防火、如何处理“不当籍者”和检斤计量等各种问题。《金布律》、《厩苑律》、《田律》等也对特定物品的仓储管理有一定的涉及。
这些措施,从法律层面保护了秦国的仓储安全和运行上的高效,保证了秦军的后勤补给。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质农具开始被广泛使用和牛耕的方式逐步得到推广,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在秦国的统治者们看来:粮仓建的再大,制度定的再好,如果没有稳定的粮食来源,也都是枉然,相较那些等级分明,遍布全国的一个个“人为之”的具体仓库,他们更看好的是更高层面的东西—“天府”。在此基础上,秦国各个历史时期的
为了确保自己的粮仓能源源不断的供给国家用度,他们不惜用两代君王的鲜血夺取了“岐丰之地”这座天然粮仓;他们不惜延缓统一步伐,花费10年时间修建郑国渠用于灌溉;他们拿下巴蜀,并耗时14年建成都江堰,让秦国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收获又一座“天府”…更重要的,他们于困境中选择了商鞅变法,一方面重农抑商,逼迫全体国民参与耕作;一方面“废井田,开阡陌”,鼓励人人开荒,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他们还用优厚的政策招揽它国流民来秦从事农业生产,并将战俘和罪人发配到新打下来的地盘种田,以增加收成…
在这一系列操作之下,秦国没用多少年就从“诸侯卑秦”的状态蜕变为诸侯皆畏之的超级强国。从秦孝公开始,及至始皇,充足的粮食支撑了秦国统一过程中大大小小108次战争。他们“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终于完成千秋大业,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
3 秦统一后的“物流”成就概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合天下;前206年秦三世子婴降于沛公而秦亡。549年打下的天下就存在了15年,…但这15年里,大秦在“物流”上的成就仍然可圈可点。
国家统一了,秦代在法令、度量衡、生产领域甚至思想上都尝试统一标准。在交通上礼仪上,他们定下“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车同轨”。只可惜,司马迁等史学家并没有描述什么是车同轨,它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因此成为两千多年的历史谜题。
西方道、巴蜀栈道、武关道、东方道、滨海道、临晋道、上郡道、北方道和秦直道等9条驰道组成了秦国的主干交通网。作为始皇帝主要的历史贡献之一,驰道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修建标准。
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等于现在的69 米宽),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
秦始皇派兵南征百粤时,为解决军饷转运困难的问题,“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公元前214年作为秦国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灵渠修成。它沟通了湘江、漓江,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为秦王朝统一岭南提供了重要的保证,灵渠凿成通航的当年,秦兵即攻克岭南。
秦代在道路的修建形式上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们修建了多处“上下有道”的复道,也就是我国早期立体交叉道路,意义重大。还在道路两侧夯土筑壁,修建甬道,以提高人员转移和物资运输的隐蔽性和安全性。
另外,秦始皇的也对秦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极大的提升。
比如为了漕运东方的粮食以充实长安,“秦建敖仓于成皋”,在秦汉之后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再如,“始皇帝四年七月,立长太平仓,丰则籴,歉则粜,以利民也。”(《太平御览》)等等。
4 反思及历史启示
我们沿着“物流”的视角简单回顾了大秦的历史,“物流”在大秦的各个历史阶段可谓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其“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地位在两、三千年前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我想,我们一定还会从中收获其它更多的反思和启示。这里,不妨把它留作“思考题”,等后面几期多了解几个朝代之后,我们再来做个对比和总结。我相信,从这些旧历史中,我们会对物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