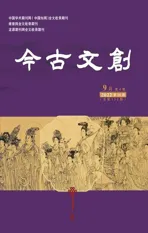论小说《等待》的中庸之道
2022-11-01◎伍月
◎伍 月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0)
哈金(1956—),原名金雪飞,英文笔名 Ha Jin,美籍华裔作家,1999年以《等待》获得美国文学界的最高奖“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小说《等待》再次获得美国最大的小说奖项—— “福克纳小说奖”。英国《每日邮报》赞扬《等待》是一部“优美而又夺人心魄”的作品。
《等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北方一个普通家庭的婚变故事。男主角孔林是木基市部队医院的一名军医,在上学时遵从父母之命,娶了农村姑娘刘淑玉,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让孔林备受煎熬。后来孔林和部队里的护士吴曼娜相爱,准备和刘淑玉离婚。但由于刘淑玉的坚持、刘淑玉弟弟本生的阻挠、部队的规定等原因,这段离婚风波持续了整整18年,三个人也就此等待了18年。18年后,好不容易等来的新生活却并不如孔林想象的那般甜蜜幸福,反而是累累重担,一地鸡毛。由此,孔林再次陷入了痛苦中,对等待的意义、生活的价值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本文拟从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叙述风格三个方面,分析《等待》所体现的中庸之道,领略哈金文学创作的独特魅力。
一、中庸思想的理论来源
在中国,中庸思想是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之一。孔子在《论语》中,最早使用了“中庸”这个词语,但事实上,对“中”“庸”二字的解释由来已早。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对我们研究中庸思想的理论来源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是关于“中”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指出,“中,内也, 从口从丨, 上下通。”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进一步说明, “中”的本义是“以矢著正”, 和古人射箭狩猎有关,是“打中”“射中”的意思。除此之外,“中”还可以作为一种抽象思想加以解释。这种思想早在尧舜禹时期便已有体现。《论语·尧曰》篇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尚书·大禹谟》记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允执其中”和“允执厥中”都体现了尧舜禹在治国理政中融合了“中”的思想。周公时期,“中”又被赋予了“中德”的概念,成为统治者效仿的榜样。《尚书·酒诰》中记载:“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从上述可见,“中”的字义发展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由其简单意义逐渐丰富为道德、哲学意义。
其次是关于“庸”的解释。郑玄在注疏《中庸》时提出:“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魏国何晏在注释《论语·雍也》时写道:“庸,常也。”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中将“庸”解释为:“用,平常也”并进一步引用二程的说法:“不偏之为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从而将中庸引申为一种常定不变的永恒原则,把停留在道德层面的中庸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和“中”一样,“庸”的字义发展也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过程。
从上述解释来看,“中庸”的基本内涵为“致中和”,重点在于内外贯通。即内在要做到至真至诚,慎独其身。外在要做到执中守正,折中致和。在哈金的小说《等待》中,不管是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还是语言风格,都可以发现这种内外贯通的中庸思想,使整部作品充满魅力。
二、主题中的中庸思想
等待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心理体验,作为一种文学母题,等待也被文人墨客反复吟咏,从《诗经》《楚辞》到诸子百家,无一不饱含等待的审美意蕴。等待不仅仅是一个事件,一段距离,更是一种美学思考。与主动出击、热烈追求相比,等待更具有一种温和中正之美,而这恰恰和中庸的“中和”思想相吻合 。《论语》中孔子说道:“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狂”指激进。“狷”指保守。孔子认为激进与保守都不是“中行”,中庸的要义是要坚守适度的原则。这种人生智慧,正是哈金在《等待》中想要表达的中庸主题。
主题的中庸思想首先体现在个体对等待这个行为的选择上。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不管身份背景如何,对于爱情,他们无一例外都选择了等待。首先是孔林,虽然他在吴曼娜的督促下多次回到鹅庄与刘淑玉离婚,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激进的行为逼迫刘淑玉,而是跟刘淑玉讲道理,坦然承认两人之间没有爱情的可能。在年复一年离婚失败的阴影中,他也没有放弃,而是选择等待,等满足军队的规定——“夫妻分居18年后可自动离婚”自然而然地和刘淑玉离婚。
其次是刘淑玉,她的等待分为两部分,等待孔林回心转意不和她离婚,以及等待吴曼娜去世孔林重新回到她身边。可以说刘淑玉是整部小说中最卑微却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人物。在和孔林离婚拉锯的18年里,她像寡妇一样在鹅庄操持家务,对孔家人呕心沥血,以一种温驯沉默的态度来等待孔林的回心转意。18年后,这种等待落空,她不得不和孔林离婚。但吴曼娜的病重和孔林酒醉后说的话又让她燃起了新的等待——等待吴曼娜去世后,孔林重新回到她的身边。
最后是吴曼娜的等待。表面上看,她是整部小说中最富激情,最具活力的女性,在爱情上喜欢选择主动出击。但深入分析文本后会发现,其实她才是那个等待最多、最深的人。她的等待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等待初恋情人董迈,第二次是等待魏政委,第三次也是最久的一次,是等待孔林。她对于这两对主动与被动的等待关系,等待人都没有选择一些过激的行为来加速这个过程,而是自然而然地等待着那个未知的结果。
主题的中庸思想还体现在由于等待过程而造成的距离感上。常言道“距离产生美”,在等待的过程中,等待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时空距离,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距离让等待在渴望与期待中更具美感。孔林和吴曼娜因为不能结婚,碍于部队里的规定,只能保持一种精神上的陪伴,而无法在肉体上结合。在互相等待的18年中,他们在彼此眼中都是相对完美的存在。但当他们结婚后真正住在一起,开始共同生活后,这种距离的平衡被打破,他们不再是彼此眼中的完美的另一半,各种鸡毛蒜皮的争吵开始出现,他们期待中的幸福生活也不复存在。
等待这个主题,不管是在主体行为的选择上还是时空的距离感上,都具有极强的中庸之美。它根植于文中三位主人公的思想中,又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显示出来。可以说如果剥离了中庸思想的内涵,那么这部作品就会失去大部分的审美意蕴,沦为描写男性出轨故事的低俗之作。
三、小说人物的中庸形象
在哈金的笔下,三位主人公虽然形象和性格大相径庭,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体现着中庸思想的影子。
弗劳恩霍夫协会主要由协会的IP-商业化中心进行专利技术转化。在利益分配上,中心收取许可授权收益的25%,发明人获20%,其余归所属研究所。协会还可以低于25%的参股额度投资新成立的技术公司。
其中,最具中庸思想的典型便是男主角孔林。虽然他在无爱的婚姻内精神出轨,在道德伦理上受到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立身处世上,孔林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君子形象的化身。孔林身边的人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好人”“亲切随和”“老成持重”“待人和气”“菩萨心肠”等,可见周围人对他品德的认可。《中庸》第一章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孔林就是这样一个恪守慎独的君子。面对吴曼娜,他时刻提醒自己:你是结过婚的人。当吴曼娜听信朋友的建议,打算邀请孔林去快活一下,进一步发展两人的关系时,孔林委婉地拒绝了。不管是当着吴曼娜的面还是一个人时的独自思考,孔林始终坚持着用理智克制情感,用慎独坚守原则,没有被欲望冲昏头脑,做出违反纪律,让两人后悔的事,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两人的名誉得到适当的保全。
除了孔林,刘淑玉身上也体现着中庸思想。虽然刘淑玉是一个没有文化,样貌老态, 裹了小脚的农村妇女,但在她身上,可以看到至真至诚的母性光辉。《中庸》第二十三章写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唯天下至诚能为化。”大意是致力于某一方面也能做到真诚,真诚会让人所做的一切表现出来,从而感化他人,引起转变,引起转变就能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化育万物。刘淑玉的一生,就是以贤妻良母孝媳的角色服务于整个孔家,她对孔家的真诚,从她嫁给孔林的那一天起开始,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孔林再婚后的生活一地鸡毛,情绪反复的吴曼娜和一对初生的双胞胎让孔林心力交瘁。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淑玉答应孔林,在吴曼娜去世后,会帮他一起照顾两个孩子,不会撇下他不管。朴实的刘淑玉用她的一颗真心,感动了孔林,让孔林最后明白,原来平淡安稳的生活,才是自己最想过的生活。
四、叙述风格的中庸之美
《中庸》第一章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与中国古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学艺术追求不谋而合。“哀乐有节”的审美传统认为要有节制地表达情感。《等待》正是这样的代表,它的叙述风格具有“中和之美”。
首先是语言的分寸感。哈金十分注重小说语言的锤炼与克制,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等待》的英文原文中,更表现在翻译后的中译本里。在《等待》的《译后记》中,译者金亮回忆道,为了保持一种近乎冷酷的叙述风格,他在翻译的时候尽量避免选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译文在选词择句方面平淡如水。然而就是这样极尽朴实的译稿,哈金还是指出一些他认为太“文学味”的语言,认为“此处还应该再朴实”。哈金最不能忍受的是庸俗,用他的话讲:文字描写全在于“分寸”,一过了头就俗了。正是这样极具分寸感的语言选择标准,让《等待》这部小说原本俗套的故事有了更强的可读性。
其次是叙述节奏的平稳舒缓。整部小说没有太大的戏剧冲突,叙述语调沉着舒缓,节奏平稳缓慢。唯一算得上紧张起伏的情节是吴曼娜被杨庚强奸的部分。但就是这样短暂出现的高潮,也在随后对孔林的描写中迅速冷却下来。得知吴曼娜被杨庚强奸后,孔林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增加戏剧冲突,他没有去找杨庚算账,也没有责怪吴曼娜,只会呆呆地看着她,再也没有话,好像在想什么。后面的情节描写也迅速回到惯有的平淡基调,两人默默地咽下了这份苦和恨,回归了看似没有任何改变的生活中。
最后是情感的节制性。小说没有对人物的情绪进行极力渲染或夸张描述,而是通过对主人公反思式的心理活动描写,让读者直接感受到人物当时的情感状态,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对孔林两次心理活动的描写,十分传神。一次是孔林拒绝和吴曼娜共度良宵的邀约后躺在床上的思想活动,另一次是孔林和吴曼娜结婚后,因为琐事吵架,孔林负气出走,在外面的一段思想活动:
孔林渐渐平静下来,他又听见脑子里有个声音在问他:你真的恨她吗?
他没有回答。那个声音继续说: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谁让你娶她了?
实际上,你从来没有爱过她。你不过是一时的冲动罢了。你错把冲动当成爱情。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孔林的太阳穴怦怦跳着,他摘下皮帽子,想让冷风吹醒一下头脑。
那个声音又来了:没错,你是等待了十八年,但究竟是为了什么等?他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令他害怕,因为它暗示着他等了那么多年,等来的却是一个错误。
通过这段心理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其实婚后的孔林一直处于极度的恐惧和压抑中,他害怕自己等待了18年的婚姻到头来却是一个错误。进而也能引发读者的思考,花费漫长的时间去等待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结果,究竟值不值得。哈金在对人物情感精准把握的基础上,巧妙运用简约节制的描写,使得人物的表情达意恰到好处。
五、结语
《中庸》是《四书》之一,是宋代以后封建正统教育的基本教科书。中庸思想源远流长,不仅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还像一条暗流一般,潜藏于许多现当代作品中,等待被发现和解读。本文以哈金的小说《等待》为研究对象,从中庸思想的角度对其进行新的解读。《等待》这部小说虽然用英文写就,但不管是内在的主题思想,还是外在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上,都体现出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中和”之美。哈金将这一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与英语相融合,以崭新的方式书写传统的中国故事,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和感染力,给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正因如此,《等待》这部小说征服了中西方的广大读者,也为华人文学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注释: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第70页。
②(清)朱骏生:《说文通训定声》,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版,第123页。
③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0页,第68页。
④⑤(汉)孙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1999年版,第93页,第376页。
⑥(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1999年版,第1422页。
⑦(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1999年版,第91页。
⑧⑩(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⑪⑬⑭(春秋)曾参、(战国)子思著、胡瀚主编:《大学·中庸》,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第187页,第77页。
⑫⑮⑯⑰(美)哈金著、金亮译:《等待》,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0页,第354页,第209页,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