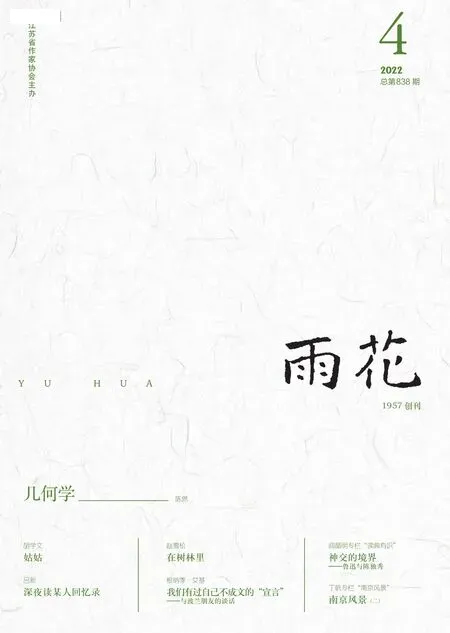天真汉
2022-11-01狄青
狄 青
那天晚上,李琼妮给我打电话,我这边乱,她那边也乱。电话里时而“嗡嗡嗡”时而“轰隆隆”,像是有帮乱七八糟的人在桥底下聚会,又像她正坐在火车里而火车恰好穿过某个深不见底的山洞。完全听不清。我从海马餐厅捧着手机像捧着枚烫手山芋一路小跑出来,站在一棵梧桐树下一个劲儿朝电话里头喊“喂喂喂”,目光却被小街对面一家助力车修理铺扽了过去。那个头发乱成一团铁刨花状的半大小子,两片嘴唇间噙了根纸烟,手里握着扳手正一下一下又一下地与电动车的一侧脚蹬子较劲儿,眼睛却死瞄着眼前一双满满当当被丝袜包裹住的大腿。这双大腿不出意外的话该是属于驾驶这辆电动车的女人所有。夏末傍晚的风像个贼,正绑定那双大腿缠绕,来去无踪。半大小子叼着的纸烟前端的烟灰足有半指长,眼睛却仍旧一丝不苟地只与眼前这双大腿恋战,倒是他手里握着的扳手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掂起,演绎出十分老练的模样。这时电话里李琼妮的半声咳嗽又见缝插针地顶了过来,我立马收敛目光,朝话筒里喊,李琼妮你能不能找个安静点儿的地方和我说话,我这根本听不清。我勉强听到李琼妮那厢挤过来的两个字“是吗”,随即便摁掉了电话,令我一句不耐烦的话未能痛快冲出口。微信提示音却又一下子挤了进来,她说——算了,咱俩甭说了,我这边也听不清,还是打字发给你吧。——董镇那边催钱的事儿了。我用语音回复她,董镇,什么董镇?哪个董……我的话甫一出口,还冒着热乎气呢,脑壳就像被谁猛拍了一巴掌,想起了李琼妮嘴里的董镇是啥意思。想起了就开始站在原地发愣。李琼妮的电话此刻又争分夺秒地顶了进来,铃声猛一下倒冲得很,把我吓得一激灵。李琼妮在电话那头冲我嚷嚷,实际上有点儿像是在对着话筒数落我——还什么董镇哪个董镇,董镇不就是你说长得好看的王囡囡的主场吗!我对她说了,让她回头直接找你,她也有你电话,有什么事跟你谈,钱的事儿最初也是你答应她的。我刚想回她句什么,这娘们儿却又把电话给撂了。我都能想到电话那头李琼妮脸上恶狠狠的模样,胸口立马就堵得厉害。
我知道李琼妮暗恋我,该有些年头了,可我不恋她,明着不恋暗着也不恋,自打认识起就没恋过。我发现有些事本质上只和直觉相关,与李琼妮长得好坏没半毛钱关系(说实话,她长得还算不赖);和她单身且有一套市中心三居室也没关系。喜欢一个女人,得有种被人拍了花子的感觉,也就是不管不顾爱咋地咋地的意思,对李琼妮我显然没那种意思。我还烦她有话不直说,老和我兜圈子,话里话外穷逗愣,倒叫我常替她难受,在这件事情上她一点都不像马一芝。
海马餐厅的老板马一芝胳膊支在脏兮兮的收银台面上冲我说——鱼头泡饼给您上桌了,随后便朝单间那厢甩去个眼色,并故意撩开了嗓门追加道,您还是先把账结了吧,省得一会儿俩人都喝高了我没处要去。我知道这话是冲单间里的张大川喊的。她不知道,这次是我请张大川,至于为啥,自然是与李琼妮嘴里的董镇有关。
我不爱吃鱼头泡饼,觉着好大颗鱼头动辄五六斤沉,铁定是拿药给养起来的。可张大川爱吃。吃席只要有鱼头泡饼,再来个小葱拌豆腐或是卤煮花生啥的便齐活了。我这段日子过得潦草,跟马一芝小半年才做了四五回,此前差不多有一个月冒头没和她做那事儿了。自打杂志休刊,我便转岗为无业游民。基本工资倒是照发,可绩效没了,广告提成也没了。我服务的杂志原先是一本半月刊,封二封三封底加起来每个月有六个广告,这还没算内页见缝插针的那些个广告以及每期都少不了的各类软文。拉广告有35 个点的提成,说是20 个点给客户,15 个点给揽广告的人,我仗着多年攒下的人脉,这35 个点多半都能落自己口袋里。可自打进入2018年,纸媒就像一群活不起的老弱病残,不是自行了断,就是苟延残喘。我服务的杂志起先由半月刊改成月刊,转年又改成了双月刊,后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到出版局办了休刊。之所以没直接停刊,当然是因为公开发行的刊号还值俩钱儿,销了容易可再想申请就势比登天了。好在我手里还攥着两套空房子,一偏一独,都是中心城区学区房,皆系低位入手,原本总价就不算高,当初开发商给的优惠幅度又挺大,做房东令我的生活基本无忧。
没错,当初我在董镇的确对王囡囡讲过,有困难尽管说话,不行就让闺女住我那儿,我有套学区房还闲着呢。当时王囡囡也喝了点儿酒,脸红扑扑的,很生动。她说的话不多,几乎每句话都与她的女儿相关,看得出,女儿是她的骄傲。她说女儿学习特别好,高中想到马城市区去上,可马城市区的学区房价格高攀不起,租都租不起。王囡囡说得神伤,令我陡生怜惜之意,于是嘴边也就缺了看门老汉。
我对她讲这些话时,已然灌下去半斤多白酒,日常我喝46 度以上的白酒一般不会过二两。我记得这话刚说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发现王囡囡的目光死死地焊在我的脸上,眸子里像是有一行行弹幕正兴高采烈地闪回。于是我立马就后悔了,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把说出去的话给扽回到嘴里边,急得满脑门子是汗。大约隔了半分钟,我才从王囡囡热切的目光里挣扎出来,像是在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喝多了,我一喝多就爱胡说八道,他们都知道我这臭毛病,你别,别当真,别当真啊!
王囡囡仨字读起来绕嘴,用马城话发音便是“王南南”。尾声有点儿朝房盖儿上撩。才见面时,我们都管她叫小囡。亲切,但多少也透着点儿轻浮。我们几个人惯常如此,到哪儿都这副德性,见着个有三五分姿色的异性嘴就乱,哪怕人家孩子都能跑着打酱油了。关键王囡囡姿色远不止三五分,收着说也得有七八分吧。我们老几位虽说都与文字打交道,但朝好了讲也不过就是几个融媒体时代行将就木的旧媒体人,还非把自己当文人看。既是文人,便可无行,再出格的话也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记得刚见面时,侯默生便上去凑近了王囡囡的一张脸仔细端详,说道,没成想咱董镇还有这般美女啊!那厢王囡囡的脸立马就红得彻底,身子一个劲儿地朝后缩,眼睛不知所措地寻向地面,仿佛急于要寻条地缝钻下去。侯默生身后的魏云梅一把揪住他脖领子,说道,老侯你咋到哪儿都没个正形呢,逮谁和谁贫,这可是咱尚有刚尚大哥的媳妇小囡,快,赶紧给小囡道歉。
这时尚有刚满脸堆笑凑了过来,指指王囡囡道,忘了给老师们介绍了,我媳妇,她叫王囡囡,没见过啥世面,不识逗。您是侯老师吧,别笑话,她就这人,一碰见场面就不好意思,她也不会喝酒,我今天让她过来,是专门陪梅姐和妮姐的。
李琼妮立马说道,别姐、姐的,我看我未必有嫂子大吧!
尚有刚忙接了话茬,是是,李老师说的是呢,我是这么说话习惯了,咱马城人不都管年轻姑娘叫姐姐嘛。见着十来岁的小丫头也叫姐姐,透着亲啊!
到后来,一桌人也只有李琼妮喊王囡囡叫王姐。我觉得她是故意的。王囡囡的确比李琼妮大几个月,可瞧上去却是比李琼妮要小四五岁的样子。
那天后来的时间魏云梅一直都在和侯默生窃窃私语,还不时“咯咯咯”地笑出声。张大川说了好几回,有悄悄话你们俩不如开房去唠,董镇这边刚好没人认得你俩,躺床上想咋说就咋说。张大川说一次,魏云梅就拿眼皮子翻他一回,却也不真恼。
我、魏云梅还有李琼妮之前见过尚有刚,侯默生和张大川没见过,但也都知道他,他是董镇文化站的干部。马城新闻圈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大家偶尔也会说起他来,说起时必语带调侃抑或奚落——“这人有点意思啊!”“一根筋啊!”“脑洞大进水了吧!”“他怎么想的呢?”“人家姜太公在渭水边钓鱼钓得好好的,他非给弄咱华北来,莫非马城也要改名子牙城?”……说罢,咧嘴一笑,抑或晃几下脑袋,就过去了,谁都不会把尚有刚的事儿真搁在心上。
与尚有刚最熟的是魏云梅,她在电视台新闻部,策划了一档名为“新闻万花筒”的节目,我们去董镇前她在“新闻万花筒”里发了两条尚有刚拍摄的微视频,内容是他在董镇的山里又发现了姜子牙曾在那一带活动的“证据”。连尚有刚的名字都没上字幕,只在微视频播放结束时提了句“通讯员尚有刚视频报道”。就为这几分钟视频,我们却跑董镇来打“通讯员”尚有刚的秋风,的确有点儿不厚道。不过魏云梅说也不是她主动的,是尚有刚死乞白赖求她带几个媒体朋友一起过去。魏云梅说,估计又是让咱帮他发稿呗!
我也发过尚有刚的稿子,都是写他“研究”“考证”出来的姜子牙曾到过董镇以及马城一带山区活动的内容。我给他发时都是将他臆测的部分去掉,前面有关姜子牙在西北和山东的部分保留,后面所谓姜子牙曾到过马城董镇一带山区传道授业的“研究成果”,我只留下少部分尚有刚找到的模棱两可的所谓“物证”及民间传说。杂志刚好有个栏目叫“有此一说”,放里面倒也不算违和。不记得给他开过稿费没,我们杂志起初发稿费就不及时,拖上一年半载是常事儿,后来则干脆不发了,爱咋咋地。
我们几个人当年全盛期自封“吃遍马城小分队”。我在杂志社,张大川在日报,侯默生在晚报,魏云梅在电视台,李琼妮在早报,各有势力范围,互通有无,借力打力。可随着传统纸媒病入膏肓,我们也活得越来越不像人样儿。原本一两周一次的聚会,拉长到一两个月,而且见面基本上就是吃顿饭,找不到下家给托着,连酒都不好意思敞开喝,更甭说原本接下来唱歌跳舞泡澡桑拿足疗按摩那些个锦上添花的项目了。
这次奔董镇前,我们几个已经快三个月没聚了。魏云梅在我们几个人建的“吃货群”里发消息说她攒了个局,约大伙聚聚。她不喝酒,正好开她的七人轿给我们当轿夫。最先回应的是李琼妮,她说尚有刚她见过,那个天真汉莫非又发现了姜太公来咱马城的新证据?接下来我们便先后冒泡,都说,聚聚?没错,聚聚,早该聚聚了。
马一芝想嫁给我,这不算秘密。马一芝单身,她和她老公离婚好几年了,离婚的原因是为了买房。甭看马城经济半死不活,限购却贯彻得十分彻底,不离婚的话,买二套房得付全款。也怪,离了后,二人就都没想再往一块儿凑合。坐定商量,便觉着不如就这样了吧,很是心平气和。反正孩子平日里就由奶奶照看着,二人还像以往一样,逢年过节凑一块儿装模作样地玩一把亲情,他们还达成一致,等孩子考上大学后再把事情挑明也不迟。
我认识马一芝的经过并不复杂,有一回我误打误撞进“海马”吃饭,一个人却要了好几个硬菜,原本是想吃不了打包带走的。马一芝照她自己的说法是个“敞亮人”,见到如我这般貌似大方的生客就会主动上前加微信,既为揽客,也源于她骨子里的“自来熟”。于是我们就算认识了。起先只是在微信上有一搭无一搭说点有用没用的。她爱自拍,朋友圈常发自己美颜过的“大头照”,我给她点过几回赞。某日子夜时分,我微信提示音连着响,点开后发现是她主动送了我四个“抱抱”,临了儿还对我道“晚安”。我那天有点寂寞,便小心翼翼地给她回了两只玫瑰外加两个抱抱,没成想马一芝那厢立马就回了我一个夸张版的红唇外加“么么哒”三个汉字,满屏铺天盖地下小星星,我的心顿时一凛,身体某个部位略略开始躁动。我知道,我跟这女人接下来估摸得干点儿啥了。又拥抱又红唇又“么么哒”又铺天盖地下小星星,我也不能再装了。
说实话,别看我们几个人号称“吃遍马城小分队”,但个个都是铁公鸡,习惯别人给我们买单,每天出门不捡钱就约等于挨了欺负。所以,这回由我请张大川喝酒,肯定是无利不起早。而且,咋说呢,我的狐朋狗友里我也只敢带张大川到“海马”喝酒。说来我都不好意思,我不是对我那帮狐朋狗友没根,我是对马一芝没根。因为我知道马一芝不单爱加陌生人的微信,她还特别爱跟人“上手”。
“上手”啥意思马城人都懂,专指女人对男人动手动脚。女人间动手动脚那不叫“上手”,那叫性倒错;男人对女人动手动脚也不算,那算调戏抑或耍流氓。“上手”的惯常动作一般是女人对男人横扒拉竖划拉,或是假装嗔怪地推男人一把拍男人一巴掌,还有就是抢男人的手机看,而男人一般都要回抢,于是乎二人的手往往就自然而然地绞到一起,身子也变得零距离。这种女人往往爱说自己敞亮,说自己和男人不见外,遇事不拘小节,实则是为自己的没羞没臊打掩护。
刚认得马一芝时,我因为没有防备,就带马一芝去和几个朋友吃饭。没成想一次管够——一桌人就显她能嘚瑟,劝酒时嘴里一堆花活,都是什么“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哥哥你干了这杯酒”之类。那回坐在马一芝另一边的是个诗人,姓白,快七十了。我问老白,你如今天天还健步走吗?老白说每天兜底一万步。马一芝听罢上去就抢人家手机,说,你每天走那么多步,支付宝里能量不少吧,咱俩快加上,我回头好偷你能量。老白显然没料到会有人抢他手机,而且还是个漂亮的中年妇女,脸憋得通红,磕磕巴巴地说,没,没有;我,我没能量。他一只手去夺手机,另一只手则不停去扒拉自己的上衣口袋,那架势像是要从口袋里摸出瓶“速效救心丸”来续命。其实要说马一芝是爱上了老白大约是冤枉了她,因为你就算弄个老蓝老黑老绿老混蛋坐她身边,她照样会如此。当时我就想,这女人要是娶回家,往后余生怕是得过得惊心动魄。
不过马一芝显然对我挺中意,她甚至要与我合股将“海马”旁边的一家奶茶店并进来,把餐厅做大。预算是一百万,她出七十万,我出三十万,股权证上写的却是各五十万,我知道她这么做是想从此把我和她绑在一起。
后来我和马一芝上床,完事后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以后手脚放规矩点,别见个男的就犯花痴。
马一芝说,咋了,瞧不上我了是吧?我是开饭馆的,你那意思让我跟客人都装不认识?
我说马一芝你这种行为往小了说是没羞没臊,往大了讲你就是个女流氓,送去劳改都不算冤假错案。当然,也可能是你脑子有病,有病咱就看病吃药,安定医院我认识人,你这病不治不行,要不有多少老头都不够你性骚扰的。
马一芝没等我说完就猛地扑将过来,把我人整个扑在了她的身子底下,她的嘴恶狠狠地凑到我耳朵边上说,我就是臭流氓,你刚知道啊!知道了就好,赶紧着,再好好伺候老娘一把,让我特舒服的那种。
那阵子水大,新闻说马城上游的几个水库都迫近了库存上限,有溃坝的风险。我们觉得这种新闻报不报与我们没半毛钱关系,因为每年入夏马城周边几个区县和乡镇都会闹一阵子的水患,但好像从来没出过什么大事儿,最多就是冲垮了几间农民垒的猪圈狗窝,淹过几亩农田。结果那天当我们从山里回来途径一条小河的时候,尚有刚就一个趔趄掉到了河里。当时魏云梅还“咯咯咯”地笑,她笑得倒是并非全无道理,因为看上去河并不宽,河水也只是刚到尚有刚的腰部,缓缓站直身子的尚有刚甚至还冲我们尴尬地笑了笑。可就在这工夫眼儿,上游的水就猛地下来了,下来得迅雷不及掩耳,如同脱缰野马,身后还引领着千军万马。我还想说魏云梅你别老笑话别人好不好,可话没等说出口,尚有刚人就不见了。侯默生说了一句“不好”,我和张大川本能地往下游跑,边跑边喊尚有刚的名字,我是想下河去救的,可水下来得实在是太猛了,漫出了河道,转瞬间都漫到了我们几个人的大腿那里,于是我们只得连喊带叫地相扶着爬到了山坡上面。
我们是中午喝完酒之后去的山里。
王囡囡和我们告辞的时候还说以后到马城一定会去看望我们,我们都“好啊好啊”地应着,实则谁也没当真。原本尚有刚执意要带我们去看他的“姜子牙与马城”的主题收藏。尚有刚说他在董镇的镇中心看上了一处空置的平房,足有三四百平方米,想在里面搞个主题展览,但主家要价20万一年,且只能整年包租。尚有刚说他还在筹钱,但他的那些藏品都放在那里了,我们可以先去一睹为快。
我们几个都说,等展览正式开展的时候指定会第一时间帮他发消息,到时候再多带几个记者过来给他捧场,但这次就算了吧,刚喝了那么多酒,还是进山里走走醒醒酒吧。于是乎我们一干人就进了山,没往大山深处走,也没去爬山,就是在背阴的山坡处说笑着转了转,然后就往回返,可谁也没料到的是,上游一座水库的堤坝溃堤了。
后来侯默生说,你知道,我这人从来不说假话,去之前我就觉着有哪儿不对劲儿,却又说不好是哪儿不对劲儿,后来快到董镇的时候又感觉要出事,可就是想不出能出什么事。
魏云梅也说,简直,简直就是活见鬼了,我原先见过尚有刚喝过一斤半都没事儿的,还到歌厅去吼《青藏高原》。这回最多八两吧,我看也就八两,其实我看连八两都不到,怎么就,就……
李琼妮说,我去董镇前连着好几天都没睡好,原本想不来的,又怕扫了你们的兴。
魏云梅苦着一张脸说道,你们这些人都是马后炮,当时我说聚聚的时候,你们可没一个打锛儿的。
我说,行了行了,都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们想过没有,尚有刚人都没了,他老婆王囡囡要是和咱们没完怎么办?
侯默生说,还能怎么办,人都给冲到几十里地以外了,他是自己不小心掉到河里的,我们几个都在场,都能证明。
李琼妮说,我们是能证明,可是,可是人家毕竟是人没了啊,我们多少是有责任的。
张大川说,要不,要不我们给王囡囡母女一点儿钱吧,说是安慰也好,说是补偿也行。
魏云梅说,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钱是一定要给的。
我说,钱咱们肯定得补偿人家。你们也不是不知道,现在上面对吃喝这种事儿抓得有多狠,我们虽说不是官员,可也都算是公职人员,还都是有记者证的人,这事情说有多大就有多大,关键是得安抚住了王囡囡,她可不能闹,更不能把这事儿捅到网上。
侯默生说,只要王囡囡不闹就行,她看上去挺老实的。
我说,所以啊,咱就更不能欺负老实人。要我说吧,咱们甭管她闹不闹、告不告,都先争取一个好的态度,补偿人家钱是一定的。
魏云梅说,这话对。
李琼妮也点头说是。
张大川说,那,那我们补偿她多少钱好呢?
侯默生看着我说,我看饭桌上你跟王囡囡没少说话,要不,要不你去问问她?
我说,行,但那是后话,咱们得先一起去看看人家王囡囡母女,再怎么说这事儿都和我们有关系。
尚有刚的追悼会我们五个人都到了。那天王囡囡母女哭得很厉害,我们五个人的脸看上去比在场的尚有刚的亲属们还要难看,个个如芒刺在背。尤其是我,一直不敢正眼瞧王囡囡母女,手足无措,坐立不安,虽然我清楚,在这件事上,我并不比他们四个人的责任更大。出乎意料的是,尚有刚的家人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尤其是王囡囡,她甚至还跟我们几个人客气了一下,并把我们介绍给了董镇文化站的站长,尚有刚是他手下唯一的兵。
我和李琼妮留下来陪王囡囡,其他几个人先行回了马城市区。
说是多陪陪王囡囡,可李琼妮显然不清楚该说什么好,嘴里一直碎碎念叨着“王姐想开点,王姐节哀顺变,王姐保重身体”之类的话。
日常算是半个话痨的我,这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知道,我肯定得说点什么。
我说,王姐,不是,小囡,我们,我们打算补,补偿一点钱给你,你看……
王囡囡把脸转向我,盯住我看了一会儿,这让我想起那天饭桌上她聚精会神盯着我看的样子。她说,行,要不,要不就三十万吧。
我说,她要三十万。
几个人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魏云梅说,大家AA 吧。
侯默生说,什么AA?我感觉侯默生有点儿装傻充愣。
魏云梅说,咱们一起凑凑吧,要不怎么说这事儿也过不去。
我说,三十万其实不多,这可不算是漫天要价。
张大川道,的确不算多,这女人别说是去单位告咱们了,就是她把这事儿捅到网上去,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大川说得对,这事儿只要捅出去肯定不是小事儿,咱几个好歹都算是宣传口的人,又是工作日去人家那里喝的酒,没事儿最好,一出事儿就麻烦。
李琼妮也说,是呀,而且人家孤儿寡母的,咱们不给点补偿不合适,三十万,我看还行吧。
魏云梅说,这事儿因我而起,这样吧,我拿八万,你们几个自己看着办吧。
八万,实际上比我预想的要少两万。我原先心里想的是,魏云梅拿十万,然后我们四个人一人五万。我之所以这样想,不单是因为这件事倘若细抠起来的话魏云梅的责任更大一些,毕竟是她攒的局,也是她跟尚有刚关系走得最近。再一个原因是,魏云梅在电视台新闻部多年,收各种红包和礼品收到手软,有肉联厂定期给她送肉,都是猪前腿的;有养鸡场隔三差五给她送鸡蛋,都是溜达鸡下的,这么多年下来搞得魏云梅对市场上各种副食品的价格一概不知,只进不出,在我们眼里,她只剩攒钱了。
几个人都不说话,这事儿似乎就算默认了下来。我私下里又对侯默生跟李琼妮说,你们俩就一人出五万吧,剩下那十二万我和大川解决。我以为侯默生和李琼妮会领我人情,李琼妮还好,至少“嗯”了一声,侯默生干脆都没拿正眼瞧我。要说侯默生也是晚报的编委,管着几块版面,马城好新闻奖拿了七八个,为这几万块钱不至于。侯默生像是和谁赌气似的,老半天才唬着一张脸对我说,行啊,这钱我拿,今年也该着走背字儿,钱没赚几个光剩往外掏钱了。
我其实也留了个心眼儿,我是想让张大川多掏那两万。比起侯默生来,张大川不仅经济上宽裕,人也爽快些。
张大川原先是《马城计划生育报》的副主编,眼瞅着报纸办不下去了,就花钱运作到了《马城日报》。按说张大川除了吃鱼头在行之外也没啥大出息,可架不住他媳妇有出息,他媳妇在市人社局分管职称评定,据传给人办事从来都是一把一结,别说多拿两万了,就是这三十万都让他出,对他来说也是毛毛雨。
张大川吃鱼头的动静有点儿大,他不使筷子,从来都是直接用手,而且是连吃带嗦,没有肉的鱼骨头都能被他含在嘴里左吸右嘬到只剩下白森森的骨架,才恋恋不舍地吐出来。之前我看他这副德性就会不自觉地反胃,这才叫真正的“吃相难看”呢。而这次看着一丝不苟与半颗鱼头恋战的张大川,我脑子里浮现的却是王囡囡那张白皙、秀气却又略微显得清瘦的脸,还有就是李琼妮刚刚给我打来的那通电话。
真他妈的邪性啊,好没影儿的怎么就出了事儿呢?张大川将一截已经被他嚼得稀烂的鱼骨头吐在桌面上,一边用餐巾纸抹嘴一边嘟囔着说道。
我说,是啊,大川,今天我请老兄喝酒,其实就是想说说钱的事儿,你老兄能不能多拿两万,刚才我出去接电话,是李琼妮打来的,王囡囡找她催钱的事儿了。
张大川说,唉,既然说到钱了,我就不怕兄弟笑话,我们家是你嫂子说了算,钱都是你嫂子管着呢,我花一分钱都得跟你嫂子申请。我这回拿五万,可全都是我个人的私房钱,是瞒着你嫂子攒下的,再让我多拿一个子儿都没了。再说了,后来我想了想,那事儿就是个意外,我们不能负全责,我看那个王囡囡不是那种撒泼打滚蛮不讲理的女人,当然了,咱该给人家补偿还是得给人家补偿。还有吧就是,咱可说好了,今天的账由我来结,你可千万别跟我抢。张大川看来早有准备,他明白我请他吃饭是为了啥。
没等我接茬,张大川又赶忙追加道,而且吧,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我那五万块钱先前都买了理财,还得俩月才到期,老弟你先帮我把钱垫上,我知道你往外租房子也不差钱,放心,等我理财到期了立马就还你。
我感觉自己的脸色这会儿一定是很难看,我说,大川,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这事儿不是咱们一起商量好的吗。
张大川倒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说,老弟你先别急,别急,我还有事要和你说呢!老侯说了,你这么积极跑前跑后地操持钱,是不是对那个王囡囡有点、有点那方面的意思啊!
我说,我这就找侯默生打架去,保管叫他满地找牙。张大川却是一把拽住了我,说道,就是开个玩笑嘛,侯默生是不太想拿这钱,不过只要咱们都拿了,他最后也得拿,你就随他说点儿怪话去。说完,张大川突然响亮地冲包间外面高喊——买单!
令我没想到的是,事情竟然还远没有完。
魏云梅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
我说,云梅,你是有啥事儿吧,有什么事情不能微信上说啊。
魏云梅说,我是怕微信上说不清楚。你知道我家那不争气的儿子在旧金山上学,现在美国疫情闹得厉害,他想回国来避避,可一直买不到机票,刚托人在那边给他搞到一张票,张嘴就要15 万,还是经停的。我手头暂时没那么多现钱,只能先把那八万凑上了,你放心,这钱绝对跑不了,等稍微过过我就转给你。
我说,云梅咱把话说清楚,不是你给我,是你给人家王囡囡。唉,算了,孩子回国的事儿也重要。
李琼妮和我语音,又是先教训了我一通,我知道你现在有女人,是一个开饭馆的没错吧,我估计你们就是玩玩。你和这个王囡囡也是玩玩吧,她老公没了,你们倒是玩起来方便,瞧你为她这通忙活……
我说,算了算了,您别数落我了,这三十万我一个人先给垫上,你们,你们几个瞧着办吧。没等李琼妮答话,我就把微信语音键给摁了,然后关机。
说实话我没想到王囡囡会到马城来找我。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在“海马”吃过晚饭,正跟马一芝说些不咸不淡的。马一芝暗示她想和我那个了,我装傻不接茬,她于是有点气急败坏。正这工夫,王囡囡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她说她在马城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我说你别动,我这就开车过去找你。
那天的日落像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的日落。太阳依次划过高低错落的屋顶,把天边燃烧得像是珠宝上镶嵌的金属片一样。
王囡囡站在广场的一处喷水池旁望着我,她穿了一身薄呢料的紫色套裙,一只汉白玉的维纳斯雕塑立在她斜上方,这令她看上去有点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我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
我说,你也不提前打电话,还没吃饭吧,走,我请你。
王囡囡冲我笑笑说,吃过了。
她是来马城给女儿办入学手续的。因为女儿中考的成绩优异,马城市区几所高中都争着要她,还免费提供宿舍,可以住校。王囡囡说,人不能总遇到倒霉事儿吧。
王囡囡说,其实有刚是个好人,就是,就是有点那个,太天真,一根筋,专干费力不讨好的事儿,这么多年被他花掉的钱也够在马城买一个小套的二手房了。
王囡囡的身体不丰满,可瞧着非常匀称。我突然有一种想要搂住她的冲动,这冲动里有怜惜,也有欣赏,却是少有侯默生和李琼妮说的那种意思。
王囡囡说,我其实不好意思来找你,是鼓了勇气来的。李姐不接我电话了,而且微信,微信她也把我拉黑了。
我知道王囡囡嘴里的李姐说的是李琼妮。
我说,你以后打我电话就行。
她点了点头,说,你知道我为啥要三十万吗?
我摇头。
王囡囡低下头,又扬起,像是下了决心似的说,我是想给尚有刚出一本书,把他这么多年写的文章,还有他的那些,那些个所谓的研究成果吧,结集出版一本书,印刷得精美一点。我听说现在出书可贵了,十万块钱也不知道够不够。另外的二十万,我是打算把那处有刚在我们董镇看上的房子给租下来,把他一直想做的展览做了,至少展览一年。
王囡囡接着说,其实我也知道,他的那些宝贝在外人眼里就是一堆不值钱的破烂儿,可当初别人都是当古董卖给他的,什么唐代董镇先民祭祀姜子牙用过的陶盆,什么明代马城附近发现的有姜子牙图案的瓦当,连我都能看出那些是仿造的,可他都收着,说白了他就是个天真汉。他说他姓尚,姓尚的就是姜子牙的后代,所以他把这当成自己的事业做,我知道外人都在笑话他,拿他当傻子看,可我还是想圆了他这个梦。所以,我才管你们要三十万,不是我要,是想让大伙儿一起帮尚有刚圆这个梦。
我说,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你放心,钱这两天我就给你转过去。而且,如果你信得过的话,我来帮你做尚有刚展览的布展和宣传,我也可以给他的展览做策展。
王囡囡说,你说话当真?你不是哄我高兴?
我说,不是,是我佩服尚有刚的执着,我也想给尚有刚一个交代。这年头一个人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实在太不易了,管他娘别人怎么说呢,管它值不值呢,只要自己喜欢,那就去做。告诉你,我也是个天真汉。说完,我便很大声地笑了起来,笑得很真诚。
王囡囡说,我看你也像。
我说,你眼力不错,我不是像,我就是。
我在我们几个人的“吃货群”里发了条“群消息”,我说,告知老几位一声,三十万我给垫上了,知道你们都比我困难,晚俩月给钱就晚俩月给钱,可想把这钱瞎了没门儿。到时候别怪我带王囡囡去你们几个单位里闹,她不好意思闹我好意思闹,反正我现在是无业游民。说罢,我把我的银行卡号、开户行、身份证号列在了下面。
我给马一芝打电话。
马一芝说,对了,奶茶店我都谈好了,打算马上就盘过来。你入股的三十万可别忘了,你不说早就预备好了吗,你要是不放心,回头咱找人做个公证也成,不过我觉得咱俩之间用不着。
我说,一芝,有个事儿我正想和你说呢,我那三十万晚俩月给你行吗?我这遇到点事儿,都借给别人了,借给了四个人,我得一点点把钱要回来。
马一芝说,你,你在忽悠我?
我说,马一芝,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今天我和你撂个底,我骂你是花痴,我管你跟男人“上手”,是因为我想和你有将来。你要是就想跟我玩玩,这事儿咱就算了,我也不入股了;你要是看准我这个人了,那你就麻溜地把钱给我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