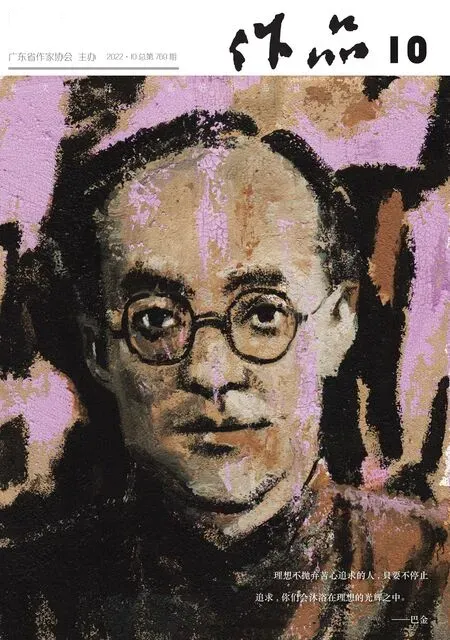草树(散文)
2022-10-28马平
马平
田埂,在乡下人眼里本就是路,至少从前是。它主要是用来给田分界和蓄水,其次才是让人行走,所以,它不可能枉占田土,妄自宽大起来。
我从狭窄的田埂上走过来,至今也没有见过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就是换回小时候的眼睛去看,田埂那些个路也依然都是个短,田收了尾路就到了头。一根田埂要是成了某条小路的一部分,通向大路,再通向场镇,那根田埂才会与众不同起来,比如,谷子打过以后,谷草一般不会丛在上面,把路挡了。
田埂是小路中的小路,要是稍微宽敞一些,还可以种植作物,比如绿豆。作物却只能种在侧边,要不,田埂上,连个下脚的地方也不会有。
还有,不管什么样的田埂,要是生了树,也都得靠边站。
谷子并不从树上结出来,所以,水田里不会有树。今天倒是有了,却是水田改头换面成了果园,或者干脆退耕还林。这是后话。
还说从前,还说田埂。
听见有人在说,田埂边上那棵树,如何如何。
可能是,又有一棵树,选来做草树了。
我老家那一带,把水田叫冬水田。我小时候稀里糊涂想过,水田,春播夏长秋收,为什么偏偏要拿它没有作为的那个季节来命名呢?冬天,水田是闲着的,只管结冰。娃儿们在那冰面上投掷瓦块,比赛谁滑得最远,总会招来大人们的喝斥。
我当时就在那一伙娃儿中间,道理我也懂。冰化了,瓦块就会掉入水中,往后会伤了人的脚,或者牛的蹄子。但是,它不是叫冬水田吗?你让它停在冬天好了。要是那样,冰就会一直不化,瓦块不是就一直不会掉下去了吗?
这些不通的话,我并没有说出来。
今天,我突然想到了“老黄牛”这个词,可以用它来给冬水田打个比方。老黄牛,不就是以“老”来命名的吗?想一想,却又是一个不通。人家冬水田另有春天,老黄牛,它还会有春天吗?
还是百度一下,可靠一些。
冬水田是重要的湿地资源,是川渝陕南浅山丘陵地带冬季蓄水的谷田,不仅给来年水稻提供自给水源,更是保春播栽插、培养土壤肥力、蓄水保湿、增强抗旱的一种特殊谷田。
老黄牛请让一下,田埂上来人了。
春天来了,冬水田结的冰已经化掉,那些瓦块却一直没有惹出什么事来,所以凡事都要朝前看。春光就在前面,春耕开始了。田埂上走来了人,还有牛。接下来,耕田的声音响成了一片。再接下来,育秧,收水,栽秧,布谷鸟从天亮叫到天黑。冬水变成了春水,也从天亮响到天黑。
夏天来了,社员们拄着竹棍或木棍,在谷田里排列成行,用脚给秧苗的根部松土,那便是薅秧。稗子一根一根拔起来,连同根部的稀泥,飞到了田埂上。薅秧歌一支一支唱起来,歌词往往也会带出稀泥。
转眼就到了秋天。
谷子黄了,谷穗上歇满了红蜻蜓,在金黄上面撒上了鲜红。田埂上又不停地来人了,说说话话,指指点点,让红蜻蜓受了惊动,谷田上空漫起一片红雾。不过,总会有几抹红色让黄色粘住,没有起飞,那是红蜻蜓交尾未毕。
红色和黄色分离,那是一个信号。
就是说,要打谷子了。
社员兵分几路,秋收战幕拉开。女社员先把谷田割开,给拌桶或是打谷机腾出下田的地方。紧接着,不同的声音分头响起来。
拌桶的响声,像枪炮的轰鸣,由慢到快。
打谷机的响声,像野兽的咆哮,持续不断。
无论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那会儿都会放了忙假,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谷子已经被女社员割倒,一把一把平躺下来。娃儿们能够派上的用场,就是把谷子一把一把抱起来,交到在拌桶或是打谷机前面作业的男社员手上,这便是“抱把”。
我当然也放了忙假,也在或浅或深的烂泥里来来回回。我的抱把,开初图的是把自己糊成一个快乐的泥人,结果却是,让自己累成了一团稀软的烂泥。
打谷机属于机械,拌桶却还是手工。拌桶上的轮番摔打,打谷机带齿转筒的高速转动,让谷子和谷草完成了分离。
到此,“谷子”名正言顺,“谷草”也才有了名分。
谷子脱落了,谷草被丢放一边,需要把它捆扎起来,这个活路叫“绾草”。绾草,就是用酒杯粗的一绺谷草,在碗口粗的一把谷草颈上扎一道箍,变出一个小草人。那是一个技术活路,换了一个人,就不一定能把谷草绾得结结实实,拖一下都会散开。
绾,那不断重复的标准化动作,把小草人逗得五迷三道,三下五去二,一剑封喉。
一块田的谷子打完了,大家一齐动手,把谷草都拖到田埂上去。大人们在冬水田里走一趟也不容易,一只手能攥五把谷草以上。娃儿们能一手拖起一两把谷草,已经很不错了。我们都学了大人的样子,把谷草在水中涮一涮,把它腿脚上的稀泥淘洗干净。
田,却不止冬水田一种。谷子灌浆以后,秧水渐渐排干,已经开始为种麦子做准备,那样的田叫旱田。旱田里,拖动拌桶和打谷机都有些费劲,却有一样方便,不用担心谷草泡在水里,也就不用把它拖上田埂。
田埂上的谷草一字排开,密密匝匝。
旱田里的谷草随地而立,稀稀拉拉。
无论田上田下,都只是一个过渡。谷草不会长久停留,站立的姿势却有讲究。它们需要站稳,更重要的是,它们需要迅速排水除湿,晒干或者风干。因此,它们的底部需要夸张地铺开。一把谷草头轻脚重,锁定的是头,放开的是脚。
这个活路,叫“丛草”。
红蜻蜓还在谷子上歇着的时候,谷草就已经分到了户头。冬天没有青草,牛主要靠谷草过冬,就是说,谷草可不是分给你家做燃料的。
牛有等级之分,谷田有大小之分,生产队干部据此做一个估算,然后指定哪几块谷田的谷草归哪一家。这样一来,谷草既不可能全被分在自家附近,也不可能连成一片。这样的分配,差不多让谁都觉得自家有亏,总会有人争上一争。要么,他家名下那些谷田太瘦,谷草就像狗毛一样。要么,同样是甲等耕牛,水田和旱田却并没有扯齐。那些话像谷草一样稀松,压实了不过“公平”二字。要讲公平,那就得像谷子那样,先称出谷草的总量,再根据牛的等级来平分,各家各户几斤几两。
但是,晒场正在晒谷子,哪里还有那么大一个地方,让谷草堆积如山呢?就算有,恐怕总量还没统计出来,水气未干的谷草已经沤烂。
牛都没有意见,你哪来那么多意见!
就是风,你都想多抓一把!
你要是再说,就用谷草堵上你的嘴!
要是这样斥责一番,牛会在一边摇头摆尾,人会在一边呲牙咧嘴。
秋天的阳光是金色的,秋天的风据说也是金色的。
谷子是金色的,谁能说谷草不是金色的呢?
牛是各家各户为生产队养的,你怎么敢让谷草有个闪失呢?
一把谷草,它要是一直捂着,就会从潮湿的部分开始霉变。因此,一项新的活路冒了出来,叫“翻草”。
和绾草比起来,翻草要省力得多,不过是把谷草的里面翻转到外面,让里里外外都晒个太阳吹个风。那重复的动作也是标准化的,把一把草轻轻提起来,一搡,一转,四下五去一,一锤定音。
谷草已经属于私家,生产队不会专门把公家的时间为你掰出一块,让你拿去翻草。不过,你可以在出工途中开一个小差,拐到你家那临时的田埂上,顺手把谷草翻上一翻。这会儿,要是正好有人从那儿经过,或许会在另一头把谷草一路翻过来,在田埂中间和你会师。要是你在旱田里翻草,那从田埂上走过的人也会下来帮上几把,说一说天气,说一说牛。无论田上还是田下,一般都不会有一声道谢,也就几把活路,谁会挂在嘴上呢?
人情,却是要在心里记下的。往后,人家要是有个什么让你碰上了,你也会搭一把手,那都不在话下。
四下无人的时候,或者半夜三更,谷草的脚也会偷偷走路,跑到了紧邻的田里,或者更远。谁家都会有一本账,小草人就是跑掉一个都会知道。你当然不能吃哑巴亏,太阳正好,在天上壮胆呢。
人却又骂不得。谷草毕竟不是金子,你犯不着让它轰然一声燃成大火,引火烧身。
牛就更骂不得了。咒骂集体的耕牛,等于咒骂农业生产,这个罪名谁也背不起。
但是,要是没有一个态度,人家会以为你好欺负呢。那就骂谷草好了,个个不得好死。小草人挨了骂,谁都不会吭声。它们并没有死,却依然不会站出来指认,个别小草人是如何跑掉的。
人们已经吃上了新米,而谷草通往牛嘴的路,却不知道还隔着多少田埂。还好,牛并没有张着嘴等那一口草料,它们总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耕牛过冬那样的大问题会有集体研究,谷草如何存放,却需要各家各户早做安排。
没有哪一户居住条件格外宽裕,就是说,没有哪一家会有一个专门堆草的地方。
谷草,只好一再向大树聚拢。
大树,无论在阳光下,还是在风雨中,都一直在人的心上惦记着。
谷草和大树的拥抱,又一次从秋天开始了。
说是大树,其实并不需要它多高多粗。柏树,松树,槐树,桐子树,或是别的什么树,只要身段勉强过得去,只要所生位置离家近便,都有可能被挑出来担当重任。
然而,即便如此,能够站出来的树也并不多。
那些既平顺又宽敞的地方,已经做了田地,或者做了屋基。树,往往都长在坡坡坎坎,边边角角,都不大给人方便。一些眼光长远的农户,已经在房前屋后寻了个合适的地方种下了树,却又不是短短几年就可以成材,就可以把一条牛的命压到它的身上。
所以,还是那些常年被选中的树,经过了若干次考验,可靠一些。
看来看去,目光最终还是投向了田埂。
田埂边上那棵树,如何如何。
你挑中了离你家最近的一棵树,却又不在你自家林权之内,并且显然人家也用不着,那你就得去向人家开口,把那树借一借。人家没有迟疑,就答应了。树闲着也是闲着,你又不会拿谷草把它捂死,是不是?
要是你人缘不好,人家就会找个理由把你拒绝了,那也怪不得谁。
无论那树是自家的还是人家的,这会儿,它都还只是一棵普通的树。
树没什么可急,谷草却急起来了。
太阳烤过,谷草已干,就该抓紧“收草”了。广播喇叭里都在说,天气可能要起变化了。
谷草还分散在四面八方,要让它们归拢一处,就得把它们背回来。背谷子用背篼,背草料和秸秆用背架子,分工不同而已。
收草需要成块的时间,和翻草不一样。你可以向生产队请假,但毕竟是单干,所以你不能算出工。要不,你躲到一边磨洋工还记工分,大家互相攀比起来,怎么办?秋收还没有结束,谷子还在晒场上晒着呢。
收草那天,你可要先观一下天色。要不,雨突然下起来,什么都泡了汤。
没有人能够背起一块谷田,除非那块谷田只有巴掌大。那么,谷草,还得一背架子一背架子往回背。谷草是个胀眼货,看上去架子大,压力并不太大。你就算背了一座谷草山,也不能只顾得看脚下的田埂或小路,前头缓慢移来同样一座谷草山,说不定你们就错不过了。
还有,天上起了乌云,你也要留意到。雨眼看就要来了,你要加快脚步。
一句话,你得时不时抬一下头,看路,还要看天。
谷草,已经来到了大树面前。那棵大树,将有另外一种生长。
那种生长,却要靠人来完成。一个主角一个配角,两个人就够了。当然,多一个配角更好。
他们所做的活路,统称“旋草”。
旋草,就是让谷草像旋风一样绕着树干堆放,一层一层旋着上升。
树脚若有不平,那就需要备下一些坚硬的树枝,用它们先围着树脚捆扎一个结实的底,让你这个主角能够踏实地站上去。接下来,配角把谷草一把一把递过来。谷草在你手中有了方向,头部朝着树干,转着圆圈一层一层堆放。你不仅要用手把谷草交错铺排,还要用脚把谷草紧实踩踏。草堆不停地上升,高过了站在地上的配角的头顶,你就有了滑落下去的危险。这样,你就只好用一只手作业了,因为另一只手要腾出来抱着树干。树干上会有枝枝杈杈,本来就要在即将到来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却被谷草捂进了一个柔柔软软的暖窝。
谷草搭起了一个不断升高的旋转舞台,结果,配角在台下成了观众,却还得打赏一样把谷草抛给你,然后,仰着脖子看着你在台上唱独角戏。
你却不能贪心,把谷草堆放到树顶。到了树的中部,你就得渐渐收小堆放直径,完成一个锥形结顶。你需要用一绺一绺谷草一圈一圈缠绕,直到确信雨水不会渗入。
配角让一个娃儿来做都行,主角却不是谁都能够胜任。旋草的技术难度很高,家里没有行家里手,仍要冒险上阵,就有可能导致中途崩塌,或者结顶稀松。但是,你要是请一个人来旋草,要供人家饭食不说,还等于公开宣布,你家里缺人手。
新米都吃上了,几碗饭算个什么。
人的脸面,和一条牛比起来,又算个什么。
高手请来了,把谷草踩到了脚下。天色已经转暗,却不是已经到了黄昏,而是雨就要下起来。那风却好像是人家的帮手,谷草在风的吹动下更加顺溜起来。雨点已经打在了脸上,说不定那就是令雨天的一个开头,人家却没有大呼小叫,只不过手脚都麻利了一些,抢在雨大起来之前结了顶。
一棵树,就这样谷草加身,成为草树。
归根到底,草树是从谷田里长出来的。
谷草一路走过来,从“绾草”“丛草”“翻草”“收草”到“旋草”,没有谁会在意它们经历了哪些坡坎,消耗了谁的力气,正如没有谁会在意一根谷草的重量一样。但是,当谷草依附大树成为草树,却是谁也不会轻易绕过去,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都还会再次回头,把它重新打量一番。
草树,既是一个并不浪漫的存在,也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那是一树风雨,又是一树阳光。
令雨并不是每一年的秋天都会下。太阳从浅山后面冒出来了,崭新的草树沐浴着绚烂的朝霞,就像一座一座微型金塔。每一根轻飘飘的谷草,曾经都举着沉甸甸的谷穗,所以,由谷草汇聚起来的草树,那是谷子之身,也是黄金之身。从“绾草”到“旋草”,本身就像一个淬炼过程。尤其是“旋草”,不止让谷草镀上了一层金,还让谷草提炼出了一种香气。
草树零散地分布在田边地角,你还在大老远,就能闻到从它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那是把大米喂养成熟的奶香,也喂养着收割之后空旷的田野,让云彩在亮晃晃的水田里留下了鲜艳,也让谷茬在干巴巴的旱田里冒出了嫩绿。
太阳不断升高,草树在阳光下变幻着影子,忽高忽矮,忽胖忽瘦。那些影子,就像是累瘫在地,或者,已经大功告成,需要抱团歇息。你无论多累,却也只能拖着自己的影子,悠悠忽忽走过去,直到一个草树让你活生生吓了一跳,清醒过来。那个草树在冬水田边上,它的影子投映到了水中,让你以为它已经倒掉。
夕阳西下,草树渐渐暗淡下去,就像它的影子站了起来。
那还是秋天的夜晚,青蛙吵个不停,像是要黑黝黝的草树赶紧走开。草树安安稳稳站着,任你呱呱呱呱,它们都一动不动,静默无声。
冬天来了,青蛙就都闭上了嘴。
草树的故事,却突然多了起来。
草树不怕水,不怕霜雪,却怕火。所以,你可能只听到了火的故事。
不知一个什么人,在黑咕隆咚的夜路上越走越冷,撞到了草树身上。他的身上正好有火柴,于是,他摸索着从草树上扯下一堆谷草,划一根火柴点燃,烤起火来。一股寒风过来,那火一躲,立即就把草树引燃了。那人闯下大祸,索性跳到一边,把那大火烤了大半,才借着火光逃走。火光把那人送出了一里路,被窝里的人们都累成了一摊泥,除非房子也被引燃了,没有人会被惊动起来。天亮以后,草树已经不在,只剩一大堆黑色草木灰,让好多张嘴张开却合不上。那棵树没有还原,通体黢黑,倔强地挺立着。
草树主人报没报案,是不是有人因为破坏耕牛而受到清查,不得而知。
草树要是遇上另外一种“干柴烈火”,尽管不会燃烧起来,却会让人嚼烂舌头。冬夜里的野地,要寻一个暖和之处,寻一个踏实之处,自然就会想到草树。它不像那些单独的树,遮不住挡不住,还能够就地取材。
但是,那么黑的夜,草树又没有燃起火光,谁看见了?
一入冬,谷草就又要从草树上下来,走上末路了。各家各户都要从草树上取草喂牛,或者给牛铺圈保暖,这个任务主要由娃儿们来完成。头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我都会在草树和牛圈之间来来回回。我从小就知道,每天需要取多少草投送到牛面前,然后,就只管听牛反刍的声音了。
我还知道,霉变的谷草牛不能吃。那发黑的谷草却也不能乱丢,得抱回家让它做燃料。黑的谷草,照样腾起红的火焰。
取草,要么从草树的中部开始,要么从草树的底部开始。草树要是旋得好,把下面的谷草抽空以后,上面的谷草也不会掉下来。中部空出来了,娃儿们爬了进去,那儿成了他们的草房子,或者舞台。
草树终于被抽光了,那棵大树重获自由,重获孤单。不过,总会有最后几绺草缠在树的上部,在风中飘荡。那是一个宣告,一方面在说一个草树的解散,另一方面在说,秋天还会再来。
田埂,在我眼里一直是路,至少梦里是。但是,它在梦里走了过来,摇身一变,成了地埂。
我老家那一带的冬水田,不知何时消失了。
耕牛也消失了,由很小的机器替代。
我在秋收时节回去,也看不见丛着的谷草了。小草人,它们全都跑光了。
草树,自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种田不用牛了,做饭也不用柴了,谷草便一无是处了。即便在当年,谷草也不用来做燃料,何况今天,老家都用上天然气了。
我却时不时想起草树。我曾经把它一束一束抱起来,再把它一绺一绺撕开来。我亲眼看着它一步一步走过来,再一级一级爬上去。我领教过它的三头六臂,也见识过它的五脏六腑。我体会过它个体的寒微,也参与过它集体的排场。
它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更是一道有声有色的风景。
当年的小树早已长成了大树,却看不出来,谁是许配给谷草的那一棵。或许,它们并不知道,草树究竟长什么样子。或许,它们并不理解,自己同类的高贵之身,怎么会和臃肿的草堆有着那么长久的一个相拥。
我前两年去了一个样板新村,住进了从谷田里撑起来的别墅式酒店。那是谷子扬花时节,夜深了,我刚在床上躺下,就有草树从下方长了起来,拱翻了悬空的地板。我赶紧醒了过来,倾斜的床就回到了原位。我听见了蛙声,下床到了门外。明月当空,灯火闪亮,那架在谷田之上的一幢一幢轻盈的建筑,恍然间变成了一棵一棵沉重的草树,我却看不见田埂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