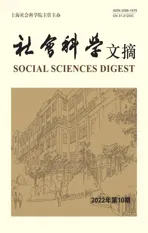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
——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个体精神
2022-10-26陈晓明
文/陈晓明
《平凡的世界》(以下简称《平凡》)已然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难题,它一度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业文学研究者与普通读者文学趣味撕裂的一个伤口。如何弥补这一历史缺憾,未必是要评论家集体检讨才能奏效,可能不如去探讨一下这部作品本身的文学能量。《平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根本缘由在于它投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抓住了当时社会的心理、情绪和渴望。《平凡》不合的是文学变化革新潮流的时宜,合的是当时社会变革现实的契机。它恰恰是去除掉80年代热衷的艺术探索,而专注于写乡村青年的个人觉醒、追求和命运,这就最为直接切合了八九十年代直至21世纪初的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群的需要——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青年渴望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自立于这个社会,打开自己的生活之路。评价《平凡》并不能只是单纯从文本本身的艺术创新性出发;也不能只是从80年代的文学变革潮流中去给出定位;更为恰当的阐释方法,应该是从这部作品和时代的契合方式,和社会意识的互动关系中去建立起有效的语境。
20世纪的土地问题与中国乡村变革
《平凡》能获得如此多的来自乡村的青年的热爱,这根源于他们与农村复杂的情感关系。不管他们未来走上怎样的发展道路,“离开乡村到城市去”,这仿佛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乡村青年的普遍追求。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城市化的阶段,这是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岗再就业的改革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这也引发更加突出的农村“三农问题”。但直到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才成为热点话题,而路遥早在80年代初期就着力关注新一代青年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系。路遥始终关注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问题,不仅思考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历史实践,更敏锐地感受到土地所有制改革后的时代脉动与现实后果——中国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容纳不了已经爆发出自觉生产力的青年农民,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要离开土地。1982年,路遥发表《人生》,反映农村青年与土地的复杂关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高加林对土地的爱与恨,内里隐藏的是现代化进程以及旧有农村体制在高加林身上的撕裂。
而《平凡》通过在孙少平身上注入青年农民摆脱土地的自我独立的精神,化解了高加林的难题,孙少平已经完成了高加林无法抵达的精神超越。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离开土地的青年农民将占据多数,他们如何在城乡鸿沟裂痕中确立自我立足的根基?此时,他们脚底下不再有坚实的土地,而只能依靠强大的自我意识的精神。孙少平正是如此站立起来的。自我的内省意识——对苦难的反复体验,温情的抚摸——人性的美好希望,爱情的召唤——超越现实的想象,这三大要素是支撑孙少平脱离土地在城市立足的精神依据。孙少平的行动与追求乃时代缩影,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自觉选择和感受。《平凡》表现的是中国在转折关头历史性的整体性改变,即整整一代青年农民摆脱土地、重新构想自己命运的当代史诗。它发生在20世纪,恰恰是这个世纪,农民与土地关系演绎了这个民族最伤痛的、也最为壮丽的传奇。
在百年变局中重写乡村中国
《平凡》带出的问题,牵涉到20世纪中国革命与变革引发的诸多难题,例如:进入现代给乡村中国带来的冲击;激进革命改变乡村的土地所有制以及体制与文化的不断变更;现代化带来的工业与农业,农村与城市的深刻裂痕。乡村青年如何成就自我?是在乡村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还是离开土地在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发展?这些问题自从五六十年代就露出端倪,在八九十年代变得十分激烈,在21世纪初期依然突出。所有这些,都使我们今天在反观《平凡》的时候,不得不去思考这样的背景,即“漫长的20世纪”,也就是说,20世纪剧烈变革对乡村中国的冲击引发的问题。
站在改革时代的历史关口,路遥转向他的精神导师柳青,但由于乡村中国历史情势的巨大改变,路遥是在对前辈时代经验的对话与反思中,完成自身的时代思考。就《平凡》对中国乡村历史抉择和变化的表现而言,《平凡》几乎就是《创业史》不折不扣的翻转。后者是在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立论,是在两条路线、阶级斗争的模式中展开历史冲突;前者则是描写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农民和土地都获得了新生的活力,家庭联产承包制否决了集体化的选项。孤独而渴望掌控自己个人命运的孙少平、孙少安替代了集体化领头人梁生宝,这一改变将是无比深刻的且长远的。
因此,《平凡》书写的重大主题是伟大时代的主题,即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历史变迁。启蒙现代性的复归与展开是这一变迁的内在思想脉络,它在80年代重新出场的最大意义,是乡村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他们无师自通地用自己的劳动实干体悟到个体生命自觉的意义,用生命个体确证的行动完成自我启蒙。孙少平的行动与追求预示着20世纪乡村青年强大的自我意识,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的本质意义——这里不再有“普遍理性”作为建构历史主体的依据。他们并非受惠于历史的时代主体,但他们是承担自己命运、努力将世界(文化)视野纳入自身的积极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没有“普遍理性”作为基础,但离开土地的孙少平们所寻求独立的个体精神未尝不是另一种“历史与阶级的意识”。
对20世纪本质性的超离:生命个体的崛起
在“短20世纪”的历史冲突中,“阶级斗争”无疑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演化到20世纪中期以后,成为主导的唯一性的叙事。写作于80年代初期的《平凡》意识到根本性的“历史深度”,这就是阶级论的塌陷,个体性的崛起。它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经典叙事模式,率先建构起“历史与个体意识”。
路遥在《平凡》里始终着力表达的是“平等论”的观念,也正因为这一观念,在完全忽略20世纪的革命叙事——革命的主体、革命的目标的情形下,路遥如此用心用力地去描写乡村青年的贫穷和苦难。而书写苦难的本质与历史意义在于,这里虽然是群体性的苦难或痛苦,但路遥却是把它紧紧困囿在个人的躯体和心灵上。
苦难现在不是作为历史和阶级正义的基础,而只是作为个人生命经验的坚实性本质,它使生命拥有了自我生成的力量——这种生命的自由意志不再需要社会等级的论证,它在个体论的场域内是自足有效的。如果按照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地位的意识,这里显然出现了较大的裂罅。但是,放在“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中,就会可以理解作为青年农民的孙少平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何以能有这种惊人之见。而这种生命个体论是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农村青年自我生长、自我确证、自我救赎的真理。
路遥对苦难的书写并不仅仅是改写了“阶级论”,更为重要的是它迫使20世纪的思想史重新定位:不再是启蒙自觉的普遍理性,而是生命自觉的个体意识——由此路遥抓住了在20世纪变革中发生的不可弥合的城乡断裂的另一历史起源。在这个起源中,乡土中国的青年从自身经历的苦难中领悟到自身命运的全部意义,它的未来指向——他们的个体生命能量和自我肯定性,可以而且更倾向于从自我的受苦受难中成长起来,他们不需要结成广泛的普遍性,他们自觉地定位于生命自足的他者——他们各自的苦难是如此不同,苦难具有自身的唯一性,只有在自我生命的内化中获得炙烤。他们不需要重构社会革命/正义的大逻辑,他们只需要自身命运的小逻辑,并以此支撑着他们的生活延伸。
小说里的每个人都经受着苦痛,但每个人都在承受的基础上,争取自己的生存自由。这是“对必然的认识”建构起来的个体意识,与其说它是中国文化“认命”的天性所致,不如说是中国百姓勤恳厚道的传统使然。对于路遥本人来说,或许还多了一层经历了70年代激进革命自毁后的凤凰涅槃,以及随后持续多年的痛悔、救赎和大彻大悟。
漫长的20世纪与苦难主题的个体化
很显然,这样一种生命个体的自我重建一直在摆脱20世纪幽灵学的纠缠,唯其如此,我们需要用“漫长的20世纪”这种理论视野来阐释其本质要义。本文运用的“漫长的20世纪”可与颇有解释力的“短20世纪”观点构成对话,但后者对于中国90年代以后乃至21世纪初的解释效应却有欠缺。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不断地返回到20世纪中去寻求依据。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所揭示与引申的问题直至今天还发人深省。一方面,是20世纪那些问题远没有解决;另一方面,20世纪的经验是如此挥之不去,是我们的下意识,几乎要形成荣格式的原型意识。
“漫长的20世纪”这表明我们今天的理论批评基础性话语还不能脱离其基本范式。亦即:其一,今天的难题还是在这个基本范式下,即“启蒙与革命”的二元关系;其二,所有的逃逸或超越性的话语,以及以虚构形式出现的文本,或以审美形式出现的文本都与“漫长的20世纪”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三,因为其漫长,它变成了“潜文本”的形式。
在“漫长的20世纪”理论眼光的烛照下,我们方能理解路遥所着力书写的苦难主题。在“启蒙与革命”的二元的叙事中,路遥开辟出第三种叙事:个体苦难的自足精神。苦难是《平凡》中人民的生存常态,路遥笔法精细,写出了农村“市场经济”初始时期的艰难和无情。所有制改革下乡村伦理关系和价值观的改变,是基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正义;遑论“市场无情”“资本罪恶”,根本在于中国乡村的绝对贫困。路遥深刻有力地写出了农民要走出贫困的渴望和决心,他们也不得不和农村的某些传统“决裂”——这不是基于历史理性(革命)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出于个人本位利益的命运抉择。
但路遥在切开乡村向“外面世界”的市场经济生活面时,还是有所欠缺。路遥对王满银这一农民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他对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参与市场经济的进程,还是有所隔膜。《平凡》的可贵之处在别处,质言之,《平凡》提供了一种对生命个体肯定性的价值理念,其内化为个体生命本位;其外化为个人的勤劳致富的实践,不再诉诸集体性的对抗行动。
《平凡》里面当然包含了大量的困苦、贫穷、艰难和挫败——这些描写本身内含着乡村的不平等所折射出的“现代性怨恨”;但正是这样的境遇中,孙家兄弟始终坚持不懈,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始终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信念。这部作品的精神本质就在于它表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肯定性,而在挫败中依然要(并且可以)凭借个体意志顽强改变命运,这或许就是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有乡村背景的中国青年的根本精神。它解决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青年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短20世纪”中国乡村没有解决的难题——离开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强力,穷苦的乡村青年依然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只有孙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响应了战胜命运的精神召唤,而《平凡》就是他们共同命运的启示录。
个体性难题与爱的救赎意义
路遥的现实主义有着颇为坚实的当代性,这是从他体验的中国当代社会获得写作的依据。受苦和战胜苦难并成长为能人,这是要摆脱土地的年轻一代农民的楷模。孙少安、孙少平都体会到“贫穷”“困苦”里包含着的意义,它们是具有内省性的——在对自我生命意义的体验中升华为自强不息的英雄意志。
但是,阶级意识、普遍理性塌陷之后,尤其是革命的目标淡化之后,这些从个人和家庭的苦难中获得生命自觉的个体不再是强大的历史理性支持的某种共同体的“英雄”,而只是个体化的“自以为是”的生命个体。城乡差异、贫富分殊、以苦难为生命根基……这些都可能构成社会性的共同体的障碍。《平凡》描写了友情、同情和爱情——这是乡村青年相互联系的纽带。路遥以此坚固他们存在的根基。路遥在美学精神上承续了革命文学的观念性、想象性和浪漫主义的特点,苦难、个体与爱,建立起稳固的三角结构。
这也能解释为何《平凡》中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主线完全压倒了田福军这条映射保守与改革派斗争的主线,原因在于前者所蕴含的切中青年群体的精神力量。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主线没有斗争的套路,只有成功/挫败的情节起伏,因此,构成小说内在肌理的情绪力量就依靠“苦难”与“爱情”的浪漫化的支撑。“爱情”在这部作品中,并不仅仅是孙少平最后精神的归宿和完成自我救赎的行动,而是具有整体性的救赎意义,几乎所有沉浸在“苦难”中的人们,都最终在爱中获得了赦免和“救赎”,这使这部作品在美学的意义上,“苦难”可以不用再诉诸革命/暴力行动,而是在爱情中获得解脱,苦难在“爱”中获得拯救。小说也因此为90年代以来的乡村青年的自我独立和奋斗提供了精神抚慰,给予了一次想象性的自我超越。
这样,离开土地的乡村青年仿佛永远地享有他们坚实的大地,而维系这大地般存在的精神,乃是20世纪经验的不断再现——它属于漫长的20世纪。然而,历史终归会面向21世纪,《平凡》在21世纪真实到来的场域中,它会失效吗?也就是说,“苦难”与“爱”还能构建21世纪的乡土中国的大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