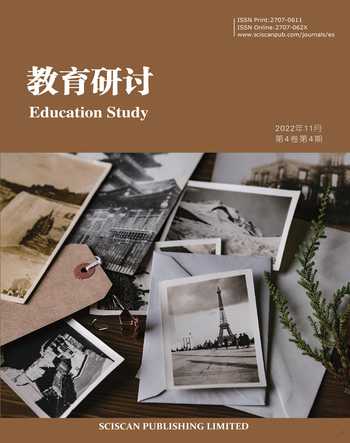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划分标准下教育学学科属性的探讨
2022-10-22贾丽
贾丽
摘 要|教育学学科属性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且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共识。李凯尔特基于历史学的视角,论述了文化科学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目的、作用及具体学科;认识论;方法论等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对二者进行了清晰的划分,揭示出文化科学独特的价值所在。李凯尔特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视角的划分为 我们探讨教育学学科属性提供了参考视角。
关键词|文化科学;自然科学;学科属性;教育学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教育學作为一门以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揭示教育一般规律的学科[1],其学科属性自 产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有人以其研究领域为基础,把教育学看作是一个学科领域;另一部分人则从教育功能的发挥方面把它当作一种技术和方法;还有一部分人试图从知识的性质着手论述教育学的学科属性;[2]也有人从哲学关于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划分标准入手探讨教育学的学科属性[3]。由此可见,关于 教育学学科属性探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对于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他们认为准确的数字和实验是揭示教育规律所必需的,教育学应当建设成一门科学,才能从客观的角度处理好教育现象与教育理论的关系;对于那些把教育研究当作是揭示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手段的研究者来说,教育学应该成为一种学问而不是一门艺术,其最高目的在于显现作为精神世界客观反映的现存真理和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教育学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即客观性和社会性。因此,“教育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就有必要通过一定的分类来加以明确。但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划分标准将其进行领域无交叉的归类。但作为哲学的一个分化产物,关于其属性的争论或许可以从科学哲学家关于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划分标准中找到参照。科学哲学家里凯尔特从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目的、作用、具体学科,认识论基础,方法论等角度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了划分,这些划分的维度和标准为我们探讨教育学的学科属性提供了切入点。
2 文化科学研究范围下的教育学属性
李凯尔特所框定的文化科学研究范围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围而言的。他认为自然即用普遍化的研究方式来看待现实,其形成的知识和规律也具有普适性,自然与价值立场无关,而只取决于它对人的存在是否有影响。这就决定了自然科学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是自然科学知识的逻辑本质。他认为自然科学应该按照这样一个规则去发展:首先,要尽可能地排除那些被称为“普通事实”(即通常所说的常识),然后再根据它们产生出一些特殊的事实或现象;其次,他还强调要注意到自然科学的独特之处—— 它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立体系。这些普遍的事例和对象汇合成类属概念,从属于自然科学的概念之下。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自然科学的概念中不包含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一次性的经验现实的任何特殊性和个别性,而是包括了所有人类共有的一切自然事物的普遍规律。这就是李凯尔特提出的“普适原理”。然而,在李凯尔特看来。所谓普适论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界关系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所不能达到的正是这种具有独特性的经验现实本身。相反,文化科学则从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即从经验现实的个体性)出发,把研究的范围规定为人们只能以非感知的方式加以理解的经验现实,这些经验现实由于其个别性而具有价值和意义[4,5]。换句话说,李凯尔特并不认为实证主义在研究他们所在研究范围内所采用的方法适用于文化科学领域,但却肯定了文化科学中存在着这样一些东西:它们不是对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成果进行客观描述,而是揭示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这是一种关于人的认识。在他看来,文化科学领域的价值是无法用自然科学标准来衡量的。而人们以非感知的方式加以理解的经验现实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因此文化科学研究具有历史性,属于人文科学范围。
教育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6]。清晰划分教育学的研究范围对于明确学科属性和学科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历史研究一面指的是教育历史研究是教育学研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指的是教育史学在教育学研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教育的属性之一的历史性使得教育学学科带有历史性的属性。事实上,我们对于教育理论的修缮和教育实践的考察正是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教育史关于国别、思想、制度、教育变迁等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为教育论提供研究背景,使得教育研究更加精准化和逻辑化。理论研究指的是对于教育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教育哲学这一特定意识形态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与历史性,它是一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从根本上讲,教育哲学理论与教育科学理论是密不可分的。教育哲学是对教育“大问题”的沉思和对“大问题”已有思考的反思(即关于教育的基本问题), 建构起关于教育的基本精神和概念,提供了人的教育思想,而教育科学理论则是教育者在思考教育哲学之后的教育知识。思想决定着知识的运用和实践程度,从二者关系的角度来说教育理论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属性色彩。教育理论的产生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因此教育学的另一个研究范围就是对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直接或间接的应用研究。直接应用表现在“技艺层次”,如提高生产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间接应用表现在“工艺层次”,如通过改革教学方式促进学生的发展。因此,根据李凯尔特对于文化科学的分类标准,教育学研究范围以其鲜明的历史性,应当划分进人文科学范围。
3 文化科学研究对象、目的、作用及具体学科下的教育学属性
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普遍化或一般化的概念,原理,方法及其应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个别地反映社会生活中一般关系及规律性的知识体系。从本质上看,它们都属于价值范畴。目的旨在掌握普遍而有效的规律,作用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身发展,途径是由一部分到全部,即由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从局部到全局,最后达到全面。自然科学涵盖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
历史的文化科学则是依次演进的科学,它把与价值相关的存在和现象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它 们进行描述、解释和说明。但它又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关注的是那些对文化价值有 意义的事物的个性和特殊性。历史科学既不是纯粹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它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一种思想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種世界观。目的在于把握特殊之 物的价值或意义,作用在于理解,途径是从整体到部分,且整体是通过价值联系给定的。文化科学则 涵盖艺术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但他关于具体学科的划分标准也遭 到了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在他那里,历史科学是指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学问。因此,他认为自然科 学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属于一种社会知识体系。他还对社会科学进行过批评。在普列汉 诺夫看来,即使每个特定历史进程的重要性在于它的独创性,这也绝不能证明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 对比的正当性,原因在于在自然科学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些既是自然科学同时又是历史科学的科学,它 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关系不仅表现为各自内部各部分内容上的相互交叉,而且体现出整 体结构上的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然科学同历史科学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地质学, 天文学和物理学等。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就不可能被看作是单一而完整的;它必须考虑 到作为人类认识活动成果的不同形式的差异性。它所涉及的特殊主体绝对不能仅仅被视为是一个副本。此外,地质学家眼中的本质成分例如,岩石类型的复杂性(包括变质程度),地层分布范围的广泛性 以及构造变形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是不与任何类型的文化价值相关的东西,但只有那些东西才能使地 质学家理解和描述地球发展的客观过程。
教育学以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旨在揭示教育规律,其作用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一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正确地面对教育工作,以及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进行教育工作以及教育的实践;包括的具体学科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教育哲学、课程论、教育社会学、教学论、教育统计测量评价、外国教育史、中小学语文或数学教学法等多门具体的教育学二级学科。无论是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作用还是其二级具体学科,终极目的都是指向人的发展。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旨归指向人;就像杜威说的,“教育的过程没有超越本身的目的;它是它自己的”[7]。康德 认为,教育就是教会人如何做人,如何过自由的生活,让人在各个方面都完全自由;[8]雅斯贝尔斯也 认为,教育只不过是知识的传授、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意志的规范,以及向年轻一代传授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功能,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创造和启迪自己的自由天性[9]。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教育活动, 教育是做人的根本标志,是做人的自觉;教育使人更丰盈、更高贵,使人拥有美德与智慧,使人焕发出生命活力和闪烁着生命光彩,因此不可避免教育带有极强的人文艺术色彩。教育学的学科属性是由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本质决定的,所以教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
4 文化科学认识论基础下的教育学属性
李凯尔特在批判性地借鉴吸收了康德、狄尔泰及文德尔班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分类的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科学哲学。作为最早解释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分类的哲学家之一,康德从个体叙事的角度,对自然与自由的区分原则、事实判断原则和价值判断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批评当时的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分类,提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分离,认为自然科学的概括性不能适用于人文科学,只有个人叙述的方法才能适用于实践的历史研究。此外,康德的价值理论和先验方法论思想始终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这一关注价值的研究思想也被李凯尔特所认同并吸纳。狄尔泰作为第一位区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哲学家,强调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他认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应该独立于自然科学。精神科学是指当前所有以社会和历史现实为中心的学科,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其一般用法常常表现为关于人的科学、关于历史的科学、关于社会的科学,构成了精神事实的范畴。因此精神科学因其特殊性,人文性,价值性等特点不同于自然科学, 也同样不可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狄尔泰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一些基本粒子的基础上构想出来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及普遍规律,其研究主题是从假说的角度出发,通过破坏外部实在,破坏各种事物而得出的成分;而在各种精神科学中,人们则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人的心灵与意识方面,它是研究人的思想及其活动过程的学科。研究对象是客观精神世界及人的价值和意义,其核心问题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人的本质在于他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实践能力。人的创造是人类特性得以实现的条件。它的主体是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现实,属于价值范畴,可以作为内部经验的事实而存在。
文德尔班不同意狄尔泰对精神科学的定义,因为他认为狄尔泰在划分中忽略了心理学这门经验科学, 而且仅仅表达自然科学与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的对立是不够的。然后,他提议将“精神科学”与 “历史科学”并将这一概念作为自然科学的对立面。它可以指所有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他也称之为“科学文化”。自然科学属于事实知识,主要研究现实世界,追求规律,倾向于抽象研究,采取特殊的一般 研究方法;文化科学属于价值领域,研究价值世界,追求形式,偏好直观。其任务是通过对特殊事件的 个性化描述来研究特殊的历史事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历史或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在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的科学划分思想的基础上,李凯尔特以价值为基础,将物 质分类原则与形式分类原则相结合,奠定了认识论文化科学的哲学基础[10]。在质料分类原则中,自然 和文化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李凯尔特认为,现实是由自然和文化共同构成的。在这个统一体中,自然是 指那些没有人类干扰的、任由自己设计和发展的现实,它们不受人类干涉、由自己设计和发展的现实, 它们是由自己产生和自己诞生的事物的总和。另一方面,文化要么是为预期目的而生产的,要么,尽管 它已经存在,但由于其内在价值,至少是有意为人们保存的。因此二者是相互独立的,质料对立这一前 提也成为科学划分的基础 . 所以他主张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因此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去认识自然,认识事物及其本质,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不能把世界看作财富,而要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相反,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必须有价值,它既包含着人类的物质生活内容,又体现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内涵, 都可以看作财富,因此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李凯尔特对两者关系问题的分析就是从这个角度展 开的。在其《科学革命》一书中,李凯尔特以不同方式论述了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因为自然与文化的对立,因此自然与文化通过具体的科学表现出来的形式也是对立的。按照形式分类的原则,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也是对立的。他还用了所谓的“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则”作为他辩论的起点。现实的连续性是指每个现实事物都有自身发展过程的历史延续性;异质性是指一个真实的事物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属性,而现实中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同质的,而是不同的。现实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是异质性和连续性的,它不能诚实地包含在概念中。自然科学肯定了现实的连续性,否定了现实的异质性, 从而采取了从个体到一般的方法来寻找现实的普遍性或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历史文化科学肯定了现实的异质性,否认现实的连续性,从而对个体事物采取了特定的叙述方式(或事件)。因此文化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关注个别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而非普遍的规律和方法。
教育学也因其关注对象的特殊性而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普适的教育,更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衡量教育规律的适用性。同样教育因为具有价值性,作为文化的产物,我们在研究教育学属性时无可避免地就得从价值的角度加以考察。事实上,教育研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研究,其最高目的是揭示人的存在的真理和意义,这表现在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判断上。教育事实可以作为表达意义的手段,但事实本身不能自然、直接地赋予事实以意义和真理。因此教育学在进行研究时要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即不要带有偏见、带主观臆断性的价值去判断教育问题和教育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完全避免在对教育事实进行分析时带入自我的主观价值判断,因此人文性和主观性色彩难免会充斥在教育学学科内部。
5 文化科学方法论下的教育学属性
李凯尔特关于文化科学方法论的论述是在借鉴吸收文德尔班的观点基础上提出的。文德尔班认为, 科学的认识目的,就其形式性质和科学分类原则而言,是在一些科学事物中找到一般规律,在另一些科学事物中找到个别历史事实。由于科学的认识目的不同,所以存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综合思维,采用的是规范化的方法;而在历史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个别记述思维的形式,采用的诗表意化的方法。李·凯尔特人采纳了文德尔班的想法,并将其发扬光大。他指出, 文化领域只有个体的东西,自然领域有一般的东西,自然中的个体可以被视为一般概念或一般规律的例子,而文化中的个体永远不能被理解为一般概念或一般规律的例子,所以不能把文化领域的这些东西看作与自然领域一模一样。基于此,他认为,既然自然领域内只有一般的东西,自然科学只能在自然领域中研究,因此只能通过概括来研究;另一方面,由于文化领域只有个别的事物,以文化领域为主体的历史文化科学只能以个别的方式来研究。
教育学的方法论是相对于教育研究的四个基本功能而言的。教育研究有四个基本功能:描述、规范、解释和批评,因此教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解释范式和实证范式两种[11]。其中解释范式的目的在于为 师生提供经验和反思,使得教育情境关注教师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追求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开展富有智慧和想象力的教育行动;实证范式的目的在于防止研究者陷入自我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导致所研究的教育理论带有价值偏见和主观性。所以教育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得出绝对真理,而在于得出人对于教育的认识。从研究对象上看,从研究对象上看,人文科学研究的是指向人的意义、价值、精神世界等形而上的层面,包括对人生命的成长、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自身生命的回归等,其研究价值不像技术工具一样给人们提供物质财富,而在于为人类的发展构筑起一个意义和价值世界,守护人们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故乡,让人类获得安顿自我生命的根基。社会科学从人类社会发展和运动的角度来考察可观察到的人类社会活动背后的客观原则。它利用数据收集和程序处理,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机制、变化和驱动力,目的是在升入考察這些人类社会属性的基础之上,寻找出人类社会的原理原则, 获得关于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系统知识和理论,实现建设理想社会的目标,帮助国家重建社会的一体性,更利于社会的管理。就研究方法而言,大多数人文学科使用的是偏向于理解的意义分析方法,而社会科学引用的方法更多的是经验方法,而不是自然科学。因此,从教育学研究方法论来看,其与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采用个别的方法有着异曲同工的原理,因此其学科属性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
6 小结
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一派试图引入自然科学领域常用的实证研究方法,转变传统的研究范式将其建设成一门科学;另一派则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生俱来的人文烙印使得这门学科注定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可完全用实验、数据等揭示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究竟将教育学划分到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清晰无交叉学科分类标准,分类原则也是众说纷纭。无论是从教育学的研究目的、内容、方法,知识属性还是从各个科学哲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划分标准来看,都未达成共识。但各界学者对教育学学科属性的探讨和已有的划分标准为我们定义教育学学科属性提供了参考视角。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根植于历史科学的视野,认为我们在进行学科领域划分的时候必须考虑历史学的证据。传统的观点认为,在研究历史事件时,价值才是最为有效的引导工具, 因而价值并不是由客体存在决定的,而是由主体想象与评论决定的,故史学的客观性自始便较有问题, 因为史学依赖主体想象与评价,历史必然会有人们心目中主体选择上的任意性,故历史也不能客观;但是, 根据李·凯尔特的观点,历史是由某些群体普遍接受的文化价值来评判的。这样历史学似乎是主观随意的,然而,学科评价更需要以人类经验之前的绝对普遍价值为前提,自然科学也不例外[12]。虽然自然 科学以其普遍的研究方法和对永恒规律的追求,在传统智慧中理应具有自然的客观性,但被忽略的是, 即使是自然科学,本质上也是不断在概括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经验材料,也需要有一个先验指导原则, 决定在比较之前选择哪种观点。只要任何一种客观性对于主体都没有普遍价值的有效性,那么这种客观性对于任何主体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自然科学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客观性,历史文化科学也应该有自己的客观性,历史的文化科学也理应具有其应有的客观性。按照李凯尔特这一观点,教育学虽带有强烈的人文色彩,主观性,但也应有其客观性,其客观性体现在研究者和教育理论价值的中立性上。追根溯源,教育学本质上来说还是一门社会科学,离不开理性与价值判断。因为,与自然科学相比,教育研究不仅注重事实,更注重价值建构。基于实证主义的局限性,教育学回归规范,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解释论和现象学进入教育学领域,与实证主义展开竞争。教育学的价值判断是语境化的。学术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单纯地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树立科学、有目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缺乏了价值判断的研究是无力的,如果不能正确传递出价值观,那么在理论层面则是不可取的[13]。这就要求教育学 在追求经验事实的过程中务必坚守客观公正、不抱偏见的“价值中立”原则,以确保结果的客观性。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同样也必须与“价值中立”原则做出明确区分。经验问题是事实问题,不是争论问题,是真伪问题,价值问题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判断, 它赋予了研究者更高的责任感和使感。理性在价值面前,告诉人们善、恶、美、丑。
參考文献
[1]苏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性质[J].当代教育科学,2015(15):7-10.
[2]陈先哲.教育学:科学抑或人文[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9(1):89-93.
[3]冯信兴.李凯尔特关于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划分[J].青年与社会,2013(7):286.
[4]刘庆昌.论教育学的范围[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33-38.
[5]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7]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3.
[8]涂纪亮.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2):3-10+94.
[9]刘莘.质料与形式:李凯尔特的历史认识论[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43-53.
[10]程岭,王嘉毅.教育研究方法的内在逻辑[J].教育研究,2013,34(12):18-24.
[11]薛晓阳.价值中立与教育研究的学术立场[J].教育科学,2003(4):16-20.
[12][德]亨里希·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M].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3]刘德华.李凯尔特的方法论思想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J].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1-5.
Discussion on Pedagogy Subject Attribute under the Dividing Standard of Cultur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Jia L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Pedagogy subject attribut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there is no consensus so fa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Li Kelt discusses the research scope of cultural science. Research object, purpose, function and specific discipline; Epistemolog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thodolog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 are clearly divided and the unique value of cultural science is revealed. Li Kelts division of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philosophy provides a reference perspective for us to explore the subject attributes of pedagogy.
Key words: Cultural sciences; Natural sciences; Subject attributes; Pedag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