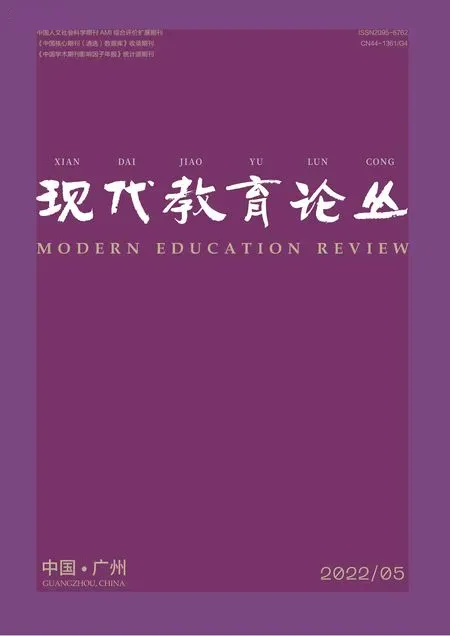书生报国的另一种面相:留美中国学生的价值选择与意义转向
2022-10-21张睦楚
张睦楚
(1.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昆明 650500;2.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杭州 310028)
近代中国面临最重要的议题即是如何摆脱国家的生存危机,如何在世界局势的变迁及胁迫中做出契合自身利益的恰当反应,任何时段均无例外。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次年一月,战胜国集团为了解决战争的遗留问题以及奠定战后和平召开了巴黎和会,当英、法、美三个战胜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论时,以部分留美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团将一份争取中国国家主权的合约方案向大会提出,却遭到了驳回。中国虽为战胜国,但是在山东问题上却依然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神经。随着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的失败,一种激烈的民族意识迅速扩展到了整个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留学生,留美学生虽然身处大洋彼岸,但强烈的民族情绪丝毫不减。与全体国民相同,留美中国学生无不忧思国家未来寻求救亡图存道路,与生俱来的民族意识构成了他们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慰藉。20世纪海外留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其群体能量却不容低估,由于他们在早期直接领略欧风美雨的洗礼,无论是知识结构、加之观念还是行为规范,都迥异于传统士大夫,但又继承了传统士大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1]面对棘手的山东问题,就爱国的方式以及留学生该如何爱国的种种问题,留美学生在美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属于这一群体的声音,在各类活动中积极出谋献策、力陈观点。他们或是通过演说宣讲、刊发评论、或组建相关事务委员会、与其他团体的合作等方式,表达着对这一事态的密切关注。就留学生对“山东问题”的态度来看,绝大部分留学生基于中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且独特的民族意识而产生民族主义情绪,主张采用对日抵抗的强硬方式来应对这一危机;而另一派学生则展现出一种救国的独特面相,他们建议采取一种“自助内观”的方式,来重塑国威。不难看出,这两派留学生的主张分别基于“民族自决”与“民族自强”的理念而形成了当时的价值选择。
一、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士”:留美中国学生的“直觉反应”
1919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就曾接近1200人,①根据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在1918年间秋季的统计,彼时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接近1200名。参见:《留美学生学业统计表》,《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5卷第3期。这部分留美学生虽身处大洋彼岸,但对国际形势相关信息的了解却丝毫不比国内迟缓,他们以急切的心情瞻望着国内的局势与动态。[2]当充满耻辱性质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美国,日本所提出的无理要求,立即激起了留美中国学生的义愤。从总体上来讲,美国自“一战”后所坚持的是不卷入欧洲大陆的权力争斗之中,这样的政策有助于确保美国独善其身,免遭来自欧洲战场硝烟的“毒害”,这种价值选择也称“威尔逊合作式反帝国主义”,此后一直延续到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政府时期,这就使留学生不得不依靠起自身的力量,另寻救国之途。[3]曾对巴黎和会抱有极大期望的留学生,在复杂的国际事态中逐渐认识到“所谓同盟国所采用的以公正和永久和平为基础的崇高原则”从未发生过,并在1919年5月的一篇社评中评论道“巴黎和会只不过是分配战利品的集会(Simply an assemblage for the division of spoils)”罢了。文章评论道“世界已经开始接受并相信战争是一场巨大的道德斗争,同盟国是毫无信用、毫无道德正义感的野兽,与朋友同行时仍会自相残杀,我想象不出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4]
为了探讨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的相关问题,留学生加大了抗日救国相关活动的频次,整个留美学界也被一种慷慨激昂的救国情绪所弥漫。留学生分别于1919年夏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Columbus)举行第十届中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年会,同年于纽约州(特洛伊Troy)举行第十五届东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年会,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Berkeley)举行第十八届西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年会,1920年夏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Princeton)举行第十六届东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年会以及在密歇根州(安娜堡Ann Arbor)举行第十一届中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年会,几乎每一次留学生召开的年会无一不是与“讨论山东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19年夏,西美中国留学生在加州伯克利举行的第十八次夏季年会,中文演讲竞赛环节共五名留学生参赛,留学生朱焕君所演讲论题《抵制日货如何能坚持耐久?》获得演讲二等奖。此后,留美学生于1921年又发表了一系列留学生关于山东问题的声明:“山东会谈陷入僵局(Shantung Negotiations Deadlocked);日本债务施压并试图控制我国(Japan Insisted on Loan and Forces Control);拒绝英美诸国斡旋(Refuse Anglo-American Mediation);会谈即将结束(Conference Negotiation is About to Close),吾在外之留学生坚决抵制日本,保卫北京(Boycott Japan,and Protest Peking)!”[5]1921年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内的大剧场上演了一场名为《木兰从军》的话剧,该剧编剧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张彭春担任,主角由哈佛大学戏剧科毕业生洪深及哥伦比亚大学音乐系学生李华女士担任。这出话剧取名为《木兰从军》,表达了留学生对时局的密切关注,以及中国留学生在“二十一条”公开之后的担忧及抗日决心,最重要的是公开表明了留学生为国从军、誓以武力保卫国土的坚定志向。[6]面对强大的日本,剧中留学生立志提倡武力抗日:“留美学生其责任甚为重大,应极力反对与日本政府所订之密约”、“我们有义务不让日本的‘二十一条’计谋故技重施,我的留学生兄弟姐妹们,我们应当武力抗日!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退让下去?”
韦伯所言:“领土”作为国家的一大特征,对于国家定义的意义在于,在一个给定的领土内,国家是最具组织性的共同体。[7]正所谓民族与国家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民族是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人的共同体,其共同空间载体为国家,国家乃为拥有一定领土、人民及主权的基本组织。国家的国格与领土相辅相成,倘若丧失了领土,国民的人格也会渐渐空无。[8]可见,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之下,几乎全部留学生视国家领土为自我的国民人格,莫不从民族自卫的前提之下出发,警示国人“吾人之大病在于善忘甲午以来所受之伤痛深矣,当时虽震动,过则漠然于心,我退而敌进是以有此不可收拾之隐患”,在此情况之下宜“急起图之”明确“不战(与日本宣战)亦亡,战亦未必亡,等亡矣。与其不战而亡、屈于霸道强权而亡,不若殉人道公理而亡”的道理。由此可见,留学生出于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肩负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虽远居海外,时临国家无端蒙辱,必不辱使命共赴国难。鉴于中国目前的危机,在美留学生无不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斗情绪,几乎所有在美的留学生愿“立即放弃原定的学习计划,请愿回国从戎,回国从军!保全国土!”[9]并立志“日本谋吞中国之毒计时,吾辈留学生誓死效力、力主征战愿为国捐躯万死不辞!”[10]
二、书生报国的另一种面相:倡自强中立的爱国情怀
相同的国家,国人对她的热爱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以“露出臂膀”的“义愤填膺”方式而采取行动,而有的则是以内敛自强的方式来面对。纵观留美学生群体,虽然大部分学生基于高涨的民族精神而主张采用一种“应激——防卫型”抵抗方式,但仍有一部分留学生提出了一种温和的、调和的、折中理智的爱国方式。但无论何种方式,均体现了书生报国的豪情壮志。理论上来讲,“民族自决都是以暴力、抗议为开端的,而民族自强则是以自助、自强为开端的”,越是在文明不开化、文化程度越低的地方,前者的抗拒情绪越是强大、越是激烈;而越是在具有强烈且不可撼动的自信国度中,这种抗拒的反应却是以其他方式排遣的。基于此,留美学生认为留学生最好的爱国方式,并不是口号喊得震天响、紧握的拳头举得甚高,也不是行动要做到最激烈,而应根据现实情况,调整自身爱国的方式。
主张中立的留学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彼时国人抵制日货风愈演愈烈,他们则在一份面向全体留学生刊发的关于山东问题宣传册中,援引了杜威先生对于抗日态度的观点:“倘若国内抵制日货的风潮愈演愈烈,其结果只能是对国内更为不利,因为现今手握日本货的商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中国人”。①原文为:“If the boycott continues,a series of incidents is to be apprehended,saying that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intolerable’for Japan,and disavowing all responsibility for further consequences unless the government makes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the boycott.The destruction of Japanese goods that have become Chinese property-none have been destroyed that are Japanese owned.”John Dewey:Shantung as Seen from Within.China Against Japan.The Publicity Bureau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Champaign:Illinois.Nov.3,1919.p.56-58.这一观点是杜威先生1919年访华时候根据在华两年余的访华经历,撰写的《从内部视角看山东问题》一文(Shantung As Seen From Within)的所节选摘录而出的,大致能够代表这一派别的留学生的对日观点。其实,杜威教授对于留美学生们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早在当年4月27日杜威教授在美国权威周刊《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真正之危机》(The Real Chinese Crisis),文中就讨论了中国政府的衰弱、中华民族士气的激进以及中美、中日关系等问题,他尤为强调了中国今日的危机在于对日偏激的抵制冲突,当今中国轰轰烈烈的全民族的排外运动虽说“并无错误”,但却分明受了“种族的成见而蒙蔽双眼”,同时失却了“冷静之头脑、辨别之能力。”[11]针对当时国内轰轰烈烈地抵制日货运动这一现象,美国的著名期刊《瞭望》杂志(The Outlook该杂志又名《展望报》)[12]也刊登了一则漫画,警告中国民众现阶段轰轰烈烈地抵制日货——甚至是泛化到抵制美货,这些激进的抵制行为不仅对中国毫无益处,也是一种无知暴力且极端的“盲目行为”(Blind Activities)。漫画其意图在于使留美学生对抵制日货行为保持警醒态度,以抵制“某国商品”的不痛快,用以成就国家的大痛快的感情冲动、意气用事是无用的;这类心里觉得不痛快便“拿一两个日本人、拿一两件日本货来出气”的方式绝不是深谋远虑真心救国的爱国青年所应有的行为——即便这种形式上貌似是爱国的,但实际上却是误国的。
或许是由于这一理念的过分冷静、过于和平中立,在轰轰烈烈的武力派呼声当中显得尤为“不合群”,因此留美生这一“尤显特别”的态度随即引发了各类讨论。首先是基于“国家观念”这一核心理念,留美学生们纷纷发表意见。他们列举了欧美诸国的建国历程,积极鼓励动员全体国民开始行动,不仅应从“著作文字”方面对国家进行拯救,还需要从行动上来贯彻执行。留美学生在分析欧美诸国的建国历程之后,反观我国各类实际情况,认为当下我国在对日问题上,未免失之偏颇,国人最应该施行的策略并非是对日作战,而是应实行一种自助的救国方式。留美生倪章祺对此说道“爱国的文字固然可以振作吾国今日之民气,爱国的演说亦然。但反观吾国民国今日动乱之耻,谓国家观念何在?”[13]所谓国家观念,并非是报纸杂志之上的几句口号或者演说词,作为留学生,我们更应该“奋起而行”:“今日之国家大势,即不得谓为事之宜,宜因时更新也,宜因势利导,振奋人心,夫国之不存,家将焉附?累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若至国破种衰,则不得谓之扬名显亲也明甚。于是旧曰杀身成仁、曰见义不为无勇也;曰爱公道、爱真理、讲人道为人类之尽责任之意也,吾(留学生)将行之。”[13]
其次,在留学界也发起了对自强救国方式的激烈讨论。在留学生看来,与日本武力决斗前中国必须坦然承认“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事实。当一个国家受侮,是因为国弱,国弱则不自强,不自强则将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此种救国的方式必定亡国,中国现今受到日本欺辱,与本国自身不够强有相当的关系,倘若“不以全力自存,而但求人之存我,羞也。”[14]如今日本在山东问题上背弃了世间公道,野心早已昭然若揭,“此吾人所当痛自觉悟而每念不忘者也”。但是反观国际公法,国际公法的发声力度大多基于国家武力的强弱,奈日本何?不若自强图之。中国在过去时代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相当荣光的,但近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却位于边缘的地位,当留美学生面对着自己国家地位沦落的这一现实,他们该如何处理对自身民族的情感?是该愤慨,还是面对强大的敌国而自卑?是该怨天尤人,还是该卧薪尝胆?当曾经亚洲的“中央帝国”沦落到了边缘的现实,中国该如何奋起直追?留美学生又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态度来面对这一复杂情势?学生们须如何发奋中国图强?对于以上这一系列问题,留学生或是通过刊文,或是通过充满深情的演说,给出了自身的解答:我们只有奋起而自强,才是对日最好的策略。因为“如果我们除了毁灭以外,没有任何一得,则所有拼命一搏的说法,都只是莽夫言勇!”[15]言毕,留美生则笔锋一转,进一步指出“最强的人或团体,任何事都可作,不必依靠战争获得自我独立,也是由于强有力的人——特别是强有力的国家,则处处亨通、凡事可做;而无力的人与无力的国家则无公理可讲,自然也不配谈公理。但是为了争夺自己的那份利益,于是只有挥舞拳头,只有大声疾呼,也只能以暴力代替讲道理。”[16]
基于此种观点,留美学生纷纷提出“自助式抗日救国”的一系列具体方式。留美学生林和民在留学生中文会刊《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敬告我国学界之青年》一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弱于日本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于吾人无坚固之政府,是故欲御外患;其二,在于教育;其三,在于吾国之政治家与教育家必当注意于国民之实业。因此,为了扭转局面,我国必先有一坚固之政府、强教育立专门学校及发展开矿、筑路制造等攻守器械。[17]1920年,《留美学生季报》又刊登了一则《铁路与国家强弱之关系》一文,也明确提出了具体的救国方案,乃“发达铁路、开塞民智、强势国家防御、富强民生。”[18]胡适在1938年北美基督教①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Chinese Students’Christian Association/C.S.C.A.)是一个规模上能够与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是由在美中国学生集聚成立的全美范围的学生会,是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异邦所组成的最具有影响力及号召力的社团)相比的全国性学生组织,该会于1908年由六名学生发起,到1917年时已经发展到六百名成员。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保持了较高的道德标准,创办了机关会刊《留美青年》(Chinese Students’Christian Journal),该刊物曾几度更名。该协会除了定期举办《圣经》的学习活动和其他宗教集会之外,协会也十分重视社会服务,例如包括为中国人社区服务及为刚到来美国或即将回国的留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据称,该会与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及相关组织保持着松散但十分友好的关系,以致不少中国留学生在美留学时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中国学生会夏令营致辞中也指出:“中国在战争中损失巨大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在教育、科学、工业技术及军事准备方面的全方位落后,”正是由于“他国之蔑视我国,孰有甚于此者,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哉!鉴于此,我国必须一为外交上之醒悟;二为民气之发展,自强之道在于团结坚固之团体,一致对外;三为实业上之振兴,倘若我国民能维持此三者更伸张之,则我国之前途无可忧也。对于山东问题,我国民宜坚持到底,万不可屈己以求人也…我国民闻此其可以自醒矣。”[19]据此论证,对日宣战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中国除了需要在上述事项上努力外,还应认清楚“先有强权方可倡言公理;国愈强愈可保障和平;友邦不可靠,唯自助者天助之。”[20]
当然,留美生为国效力之方策“实属不少”,但由于学生们忙于学业,加之方策多样尚未形成正式统一的讨论,留美中国学生最紧要的任务除了亟须对留美学生相关组织进行完善外;最重要的还应广泛播种为国效力之心,并鼓励吾国国民进取之心。[21]1920年秋季,留美中国学生发表了《留美中国学生会为国效力策》,文中认为现实中由于留学生旅居异邦,虽然不能直接地领导国内民众运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放弃了救国的责任,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机会,更需要做一些能够增进国家胜利的实际事情,例如研究自然科学的,应加紧工作以便战争发生时候,能够在国防上作出种种贡献;研究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应该抓紧研究关于日本的问题,譬如日本的外交形势、日本的经济力量、日本的政治及军事现状、探讨国际情形等情况,以便更好地作战。[22]留美生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理念,意在指出留学生需要采取一种脚踏实地、切实笃定的方式,来改造我们的国家,这样的观念无疑等同于“以小我撬动大我”的改造理念。
理智且冷静的爱国派,除了提倡留学生应将激进的爱国思绪进行冷却,还力倡留学生们应当将爱国主义与世界国际主义相互结合,不排除爱国以一种冷静的方式进行。早在1908年的留美学生年会中,留学生周诒春(Y.C.Tsur)即在留学生年会上进行了题为《忠诚于忠诚》(Loyalty to Loyalty)的演讲,这篇演讲获得了当年演讲冠军。在演讲中,周诒春提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可以相互兼容的理想,他指出世界上不应存在强国欺负弱国的现象,所有国家有必要为着爱好和平这一共同原则而走到一起,因而爱国主义能够从一个共同的国家进而延伸到全体人类的福祉。他对在座的全体留学生说:“等到你持续而有良知地坚持这一原则,中国的希望也就更加光明,亚洲的未来就更有前途,世界的发展也就有了保障。”[23]与周诒春持几乎相同观点的还有胡适,在留学美国的七年时间中,胡适主要形成了世界大同主义思想,他曾对自己的大同主义及世界主义做过两种解释,一是Cosmopolitanism(世界主义精神);另一个是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精神),这两种精神使得他从民族自决的精神取向逐渐转入到“平和爱国”的取向中来。早前在1911年中,留美中国学生即新筹了一个名为“爱国会”的救国组织,胡适曾被选为这个“爱国会”的主笔之一,虽然“爱国会”的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在当时却有利于激发留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便于积极创设各类条件以供留学生抒发爱国之情。在同年8月第三次中文演说会中,胡适便在演说会中进行了演讲,其题目即是“祖国”,表达了他基于“民族意识”取向下对祖国的关心。此后,他的观点有所转向。在1913年初,胡适做了一个关于“世界观念”的演讲,认为世界观念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糅以人道主义者也。”[24]此后,由于社交圈子、文化视野及“智慧天地”进一步扩大,他对当时国民的爱国方式提出了批评。他批评“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士气,而不知民族究作何解。”[25]意识到这一点后,胡适逐渐开始将“爱国”与“爱世界”乃至“爱人类”结合在一起,于是一种超越了国家界限的“世界主义”观念及立场开始确立,他也开始在世界语境下考量中国的自身命运:“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权利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旨在全体世界人民的福祉;在小家的范围之外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旨在全球范围的福祉。”[25]胡适的这种思想提出了“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为基础,来构建其“所不欲施诸同国同种之人者,亦勿施诸异国异种之人也”的思想。[24]实践来看,胡适在此后留学期间热衷参与各类超越国家界限的学会,并在这些场合中屡次发表关于世界大同主义的演说,如“大同主义哲学”“大同主义之沿革”“大同主义之我见”“世界和平及种族界限”“大同主义”等。[26]
很显然,“中国者全世界之中国矣”与“世界者全中国人之世界”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前者在于承认中国可以由他人所侵犯、由他人得以渔利、由他人可以瓜分;而后者在于赞成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独立的一分子,中国对于世界负一份子的责任,亦有一份子的权利。[27]胡适将这一理念进一步下移到了个人的层面,他指出国家一份子的权利恰恰是由个人一份子权利所累加的,他曾在一篇题为《独立》的文章中,强调了人人爱国的事实,大力主张中国人应以独立的精神践行人生义务及爱国责任:“先讲自己一个人,再讲一国,努力造一新国家,不要观望不前,不要你我推诿,不要靠天,不要靠人。因为一人能独立,你也独立,我也独立,那个祖国自然也独立了。列位,来!来!来!来独立,独立,祖国独立,祖国万岁!”[28]这种从“做好小我”以“塑造大我、建造大国”的意识也曾在留学生当年的年会中得到大力提倡。早在1914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女留学生李美步(Mabel Lee)在《留美中国学生月刊》刊登了一份名为“中国式的爱国主义”(Chinese Patriotism)一文,该文曾获1913年纽约(绮色佳Ithaca)第九届东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年会演讲论文一等奖。她在文中提出:“威尔逊总统曾说:‘在美国,最好的爱国方式不仅仅是热爱国家,而是热爱你手边正在进行的工作,争取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独立作用的人,这样我们自己就能使祖国获益。’同样,我们也认为:在中国,最好的爱国方式也是做好我们手中的事,做好我们自己的主人。”[29]
就在留学生李美步的这篇文稿刊登的两个月之后,胡适为了回应这一观点,则另作一文,针对我们究竟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爱国方式的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反思。胡适在1915年初,作于绮色佳的一篇名为《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爱国切莫过了头》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个人看法。他要求大家保持冷静的爱国之心,并对当时留美学界对日过于激愤的情绪作了批评:
假如说我们必须战斗,否则就被征服这个道理是对的话,那么我们则不免陷入了一种爱国的非理智陷阱当中。我的朋友们,我们的祖国只有120,000名勉强受过训练的士兵,我们没有任何海军装备,最大的舰艇仅仅是一艘4,300吨排量的三等巡洋舰,试问:我们该如何面对具有一百万精良兵力的对手——日本?很显然,纸上论战是最空洞的课程,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同学们,我认为我们最该去做的事就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这类留学生最该尽的职责——去学习![30]
这一观点与留学生陈衡哲所提倡的“平和的爱国”主义不谋而合,陈衡哲建议同学们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爱国情绪:“爱国心虽有好处,但万万不能敌它的害处。我还不如劝大家快把爱国心来消灭了罢。‘平和’是一个温静清高的女子,‘争战’是一个很可怕的刽子手,大家大概还是喜欢‘平和’罢。美国的历史大家洛宾生先生(J.H.Robinson)的爱国心有两个界说:一个就是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恨别人的国家——这就是戕贼人类的根源了。我还不如劝大家快快把爱国心来消灭了罢。英国的路氏先生(Bertrand Russell,意指英国哲学家勃兰特·罗素)说真正有爱国心的人,必定不赞成争战,他必定尽力地叫他国里的学术文化胜过别国,到了那步地位,不用枪支,他国家的荣光自然大了。因此争战自然没有立脚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平和正面的人,又应该怎样地为他尽力呢?”[31]陈衡哲所提出的这一观点也为其他留学生肯定,有的留学生也陈述留学生的爱国方式应当“必须是自强的、智慧的、且无条件的(Patriotism Should be Intelligent and Unconditional)”[32]。这种持“世界大同、平和自强、内助自观思想”的中国学生虽不能占很大部分的比例,但在彼时大家“眉头紧锁、紧握拳头”中日之战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之下,这一派留学生所持的思想无疑是较为令人值得深省的,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
此种独特的救国方式在之后留学界中得到了进一步明确。1922年,美国纽约出版了一套名为《中国人眼中的当今中国》(China Today Through Chinese Eyes)的中国文化丛书,其中留学生刘廷芳、胡适、徐有渔、诚静怡①诚静怡(Dr.Cheng Ching-Yi):1881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英国伦敦会牧师。1900年毕业于天津伦敦会神学校,曾留学于英国格拉斯哥圣经学校,归国后担任北京东城米市大街教堂牧师,倡导宗教自立自治,1922年起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总干事至1933年。曾酝酿并发起了一系列基督教运动,如宗教自由运动、国内布道运动、“教会合一”运动等,极力提倡建设本色的“中国教会”,并从中国基督教的实际出发,主张差会逐渐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理权力,通过渐进而非激进的变革,来完成中国真正的基督教变革转型。分别对中国的复兴运动(China’s Renaissance by Timothy Tingfang Lew)、白话文运动(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 by Hu Shih)、儒家“天道思想”及佛教思想(The Confucian God-Idea and Present Tendencies in Chinese Buddhism by Y.Y.Tsu)、西 方 宗 教 思 想 在 中 国(The Im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Made Upon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Contact with the Christian Nations of the West)、在华教会相关问题(The Chinese Church by C.Y.Cheng)进行论述,对中国展开的一系列文化变革进行了重要回顾。这部著作中始终洋溢着一种“世界大同的思想”,留美学生虽然采用了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当今文化进行分析,但是其根本宗旨在于使读者明白“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更有一世界在”的这一普世道理。[33]
与此同时,美国人士也纷纷通过各大报刊媒体,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②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曾于1922年1月9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对国家命运满怀信心》(Chinese Optimistic Over Their Future)文章,文中认为“正是由于大批的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爱国的精英纷纷归国,他们将对政府及国家重建承担着重要义务,这有助于使国家从困难及绝望中复苏过来。”原文为:“Chinese Pessimistic Over Shantung Issue:Students in Washington Express Fear That New Peking Cabinet Will Yield to Tokyo”,翌年又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山东问题的评论,原文为:“A hopeful factor is the increasing group of educated,patriotic young men,largely returned students form America,and modern merchants who are coming into a realization of their responsibilities for government.The very desperateness of the situation also is a help in bringing China out of her difficulties.”Fletcher S.Brockman,Despite Nation’s Ills,Chinese Optimistic Over Their Future,The New York Times,July,15,1923.p.5.留学生创办的《留美中国学生月刊》(The Chinese Monthly)、《留美学生季报》(The Quarterly Report of Chinese Students in U.S.A),也于1919年前后刊登各类评论文章,相关主题紧密围绕着留学生最关心的“国家主题”、“山东问题”、“二十一条”等问题,进行讨论。为便于说明,特将《留美中国学生月刊》中关于山东问题的美方人士相关讨论陈列如表1。

表1 《留美中国学生月刊》(The Chinese Monthly)关于“山东问题”所刊登的美方人士讨论文章
以上作者多为美国友好人士,身兼学者身份,大多对远东问题怀有极其关切的态度。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系主任韦罗壁教授(Prof.W.W.Willoughby),韦罗壁教授作为当时美国学界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曾长期担任北洋政府政府顾问、驻国联使领馆外交顾问,在美国乃至于世界外交学术界具有一定地位。他既是美国知名的政治哲学家,亦是远东问题研究的权威学者,对中国有极其真挚的感情。山东问题爆发之后,他以客观与科学的态度对中、日两国立场予以考虑,以免受人评论有偏袒之故。但即便如此,韦罗壁在文中评论仍然是有利于中国的,不仅因为中国在中日冲突间占有“理”的成分,还因他有着客观中立的正义感。实际上,无论是留美学生抑或是美国社会所提倡的抗日的主张,均涉及到民族精神的复兴,面对强大的日本,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精神”?基于此,留学生给出了自身答案,由于彼时国内局势多样复杂使得留学生具有多样化的救国取向,并进而呈现出了纷杂多样的政治取向,或是基于“征战”,或是基于“内助自观”,因而留学生域外的救国方策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质。进一步来看,就“平和爱国”派留美学生域外救国的种种途径而言,有的或致力于经济建设、或践行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或献身于教育领域,有的甚至对自身留学所负的使命和责任不忘于怀,从而在更深层次考虑文化根源及国民性问题,思考国家建制等问题——以上种种努力均呈现出了救国方向的多样性。但无论救国取向如何多样、救国的具体行动如何各异,这一派留学生对于救国的共同指向均是“非图国家富强不可”,并自觉地将此种使命加诸己身,以自身行动积极投身其中,勇敢实践家国使命。
三、刚与柔的辩证法:精神价值的转向
古语云“多难可以兴邦,无敌国外患者国将恒亡”。[34]近代的种种国难,虽然对民族存亡提出挑战,却也是民族复兴的深刻动力,也是再造国家的重要时刻,更是民族新生之路的开端。中国自辛亥革命起,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封建的皇帝被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便再没有了往日的威慑力。随着威慑力的逐渐散失,政治权威从而出现失落的状态,达到了崩溃的边缘。[35]因此,由于留美生群体的地域特殊性,西方的思想成为了留美学生身上除去民族主义之外体现最为强烈的一种意识——前者的作用体现在留美生倡导对中国的自救式爱国方式;后者的作用体现在留美生对中国的同情之心之上。实际上,倡导对日作战的武力派恰恰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更为关心中国在面临“山东危机”时所采取的一种自保的态度。从外部看,体现出了特殊历史社会背景之下的民族“应激性”;从内部看,是隐藏了排外倾向及盲目情绪,这种情绪与倾向极有可能走到“救国”的对立面。当这种激烈的民族意识与一触即发的民粹意识相互连接,中国近代的发展就极容易陷入一种“混乱而暴力的漩涡”,这也就是学者朱学勤指出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现象,如此一来中国现代化也就离“病灶”不远了。[36]另一方面,主张“自助的”“自强的”对日态度,与其说是一种“怒其不争”而只能致力于“自发的努力”,不如说这种基于自由的、自主的对日态度,客观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等各层面肯定了自己国家的价值,也关心如何在深刻的民族危机之前,重建民族的自信心、寻找民族文化的独特特性、差异性及本源性的价值之所在,这是一种较之为“呼天抢地、口号震天响”式的救国方式的一种更为具有民族内在觉醒意识、更为具有民族自决的自强方式。
实质上来讲,近代留学是近代爱国救亡的主旋律的重要体现,是广泛勃兴的救亡图存、救国于危难的重要产物;近代留学教育既为求学运动,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又与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急转直下的状况有着极强的相互勾连。此种背景下,近代中国留美学生的救国问题,并与之伴生萌发而出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作为一种传统的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表述,是在战时逐渐升温且达到沸点的。当然,留学生对日态度虽然基于不同的倾向、不同情感,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可以相互融合与相互转换的,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对日的方式,其根本都是站在“保卫山东”的立场之上的。留美生群体当中对爱国的情感看似冲突,但实则并不矛盾,这或许是由于对于一个面临危亡的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大致等于“自救”,之后再进行等于“自治”,前者属于自卫型的武器,后者属于自立的条件,首先要先得以“自救”才能言及“自治”,于是留美学生当中所存在的民族自决与民族自强的意识之间产生了某种衔接。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这两者又存在着难以磨灭的沟壑。
基于民族士气而主张武力抗日的派别并不是基于“民族自强”的“自助内观”对日派的对立面,但是就整个留美学生的客观实际来看,前者的影响依然胜于后者。其中的缘由大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所遭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国际舞台上所受到的一切侮辱,产生了一种对外侮的特殊性反应(主要类似于“条件性反射”的抗拒),大多以武力、抗议、暴力为主;另一方面,由于武力、暴力、抗议等模式相较于平静的、自助式的、内发的对待外辱的态度要显得更为激烈、更为“引人瞩目”、更具有影响力,自然得到更多支持者的“垂青”。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民族士气的抗争活动在国内的激烈程度丝毫不弱于海外留学生,有学者认为,这种情绪在山东本地也非常强烈,山东人民对巴黎和会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就抗争活动分类来看,国内学生及人士组建了本地国货维持会、国货团、抵制日货劝导团、抵制日货检查团、山东学生联合会、山东学生救国联合会、学界联合会、抗日救国会、救国十人团、本地救国团等。同时还开展了各类抗争主题的讲演活动,直接运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对国家外交活动进行声援支持。[37]
书生报国的取向与方式如何,无疑是需要放置在近代中国深刻的环境下进行考虑的。近代的国人脑中长时间激荡的民族自决意识是每一个中国人未能绕过的显命题,胡适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并言:“当今民族士气与民族自决的声音已经获得了压倒性的势力,‘国家’——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了第一要义,在现在当下的中国里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38]追根究底,中国近代的民族自决意识是一种情感性的关联,①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这种情感性的关联在于“羞耻感”,这种无处不在的“羞耻感”使得国民在让自己感到耻辱的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割舍的联系,这也是一种非常亲密情感的另类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异常人性化的关联,也是近代国民需要承受的特别情感。转引自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于2015年3月19日在清华大学讲学讲稿,演讲题名为《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这种情感性关联投射于由故土转移到新大陆的留学生身上,则体现为一种轻微程度的“不安感”。②对于这个问题,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这些移居的群体通常会尽力想表现出自己的爱国情怀,尽管没有人会想再回到祖国,比如他认为在俄勒冈州的美籍华人会声援北京政府攻占台湾,以表达自己超高的爱国热情。转引自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生前于2015年3月19日在清华大学讲学讲稿,演讲题名为《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在部分留学生群体上则外化为刚强的、武力的、冲动的爱国情绪。透过中国近代的历史来看,民族士气正切合时下中国之所需,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逼迫之下,无论是国人的精神塑造还是民族国家的建立都亟需民族自决来“帮一个大忙”,因此整个社会不能失却民族士气的存在。①这种民族情感及民族意识形态也为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所认可,他在《近代日本国民的使命观,其诸类型及特质——大隈重信、内村鉴三、北一辉》一文中开篇即指出“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由国民使命(National Mission)、国民传统(National Tradition)、国民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三个因素构成的。传统与一个民族的过去相连,利益与一个民族的现在相关,而‘国民使命’则与一个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国民使命’这一理念,对寻找一个民族将来的奋斗目标时,有着有形的或无形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非常强大”。[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当然,民族意识往往与民族共同的历史遭遇息息相关,民族意识的形成也与民族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基于此,民族主义的情绪也通常有两个来源:第一类的民族意识是来自于外部的压迫及侵袭,属于一种应激性的自我防卫心理。对于一个群体而言,越是受到外部打击,就越是向内部寻求支持。因此,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之间容易生成这种具有血统凝聚特质的向心力,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当国家遭遇危难时,即使身在大洋彼岸远离故邦,但留美中国学生依然“抱团取暖”式地团结一致抗日保卫国家尊严;第二种民族意识则是来源于自身的优越感,这是由于优越而衍生出的群体自豪感、认同感。通常而言,一个群体越是出类拔萃,这种民族意识就越强烈。在这种民族意识的影响下,最倡导民族自决的往往是社会精英人士,因为中国未来的好坏与他们的生活前途息息相关,他们需要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前途联系起来,用“士气”“自决”与“国家”抱团取暖,用民族自豪感来提升自己的认知。对于中国倍受屈辱的现状来讲,这种民族义气恐怕更倾向于第一种方法得以延伸。因此,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决的真正意义,在于“以民族自决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具体来看,第一步是以全体民族积极的奋斗,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脱除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第二步是努力求得中华民国内部的人人平等;第三步是进而发挥济弱扶贫的精神,辅助弱小民族,使其均能够达到‘国际地位的平等’以促进世界大同之实现,发扬出中华民族‘治国平天下’的理想。”[39]
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专制的帝制国家,按照历史的规律,她的下一步自然是应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当时的立国之精神基本得以俱备,但是就组织架构而言,却尚待用自由民主的方式来完成。[40]加之“全世界之交通,非徒以国家为单位,为国际间之交谊而已,与一切人类各立于世界一份子之地位,通力合作,增进世界之文化”的理念逐渐为留学生所认识[41],他们一方面采用激昂的民族士气以爱国,一方面也有一种基于意识深处的“不安全感”,力倡一种内敛的爱国方式。[41]由于受到西方社会温和改良的影响,留学生群体中体现出了“爱国是一种真实的责任感,而并不是需要采用一种叫嚣的、武力的方式”的取向。纵观理智冷静的爱国派对爱国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和激烈的爱国派相比,很显然多了某种程度的柔和感,这种柔和,与其说是冲动的对立派,或者说是一种“隔岸观火”的无力感,抑或是反观自身、自发的努力而采取的一种爱国的方式。此方式也摒弃了一种暴力的、冲动的、激烈的爱国情绪,避免滑入冲动暴力的旋涡——在这个旋涡中,国人极容易兴奋、紧张,受不理智爱国情绪的助推,而失去理智。
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彼时的中国正面临从清末到民初国家政治转型的艰难困境,留美中国学生虽身处彼岸却未“抛弃”国家,纷纷投入到救国建国的潮流中,体现出了近代国家危难背景之下留学生时不我待立志报国的热情。留美学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和作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对国家眷恋的情愫,同时也为中国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具体的、小范围的实例。[42]潘光旦则运用自己学业所长的遗传学来解释关于民族复兴之途所在,他将民族的复兴寄厚望于民族品质的进化。在他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即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复兴,实际上和个人或者一个家族没有多大分别,谁都离不开三个因素: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历史的文化这三个因素。要是一个民族真是上了年纪的话,它的前途当然是不会很大,但假如一个民族只是元气上受了些磨折的话,那么前途便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否则倘若不了解民族演化的道理,或是不承认民族品质的进化关系,纵使看不见实力或元气又暂时不及人家,不足以应付当前危局之处,则无疑是假了文化建设之名而行丧民族元气之实,那就真不知伊于胡底了!”[43]中国,恰是潘光旦口中所言及“只是元气上受了些磨折”的民族,全体国民应认清现实局势后起直追。一名署名为陈业勳的留学生在《留东学报》中也指出,无论是留学西洋、或是留学东洋的留学生,倘若还是置出路问题于幻梦,则不免有自杀的危险。因此,这批留学生“必须做些什么”,这意味着留学生不但不能不置身于社会,还应努力社会改造的事业、努力中国改造的事业。[44]可见,在这种共同的情感激励之下、在国家时值多难之际,几乎全体的留美学生均为增进国家社会发展而努力、为谋整个国家民众的福利、为民族争荣光而努力、为唤醒民众团结救国而努力,这种“国家得到兴盛之日,即是留美学生成功之时”的理念已成为了这一群体在故邦患难中不懈“冲锋”的重要动力。
由于彼时国内、国际局势的多样复杂,使得留学生具有了多样化的救国与政治取向,留学生域外的救国方策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质,从而导致了救国理论主张的多元化,留学界一时间出现了极其繁荣活跃的报国理想。在内外交困的时局刺激之下,救国呼声日益高涨,“书生”与“救国”之间的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对于留美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旅居大洋彼岸,与国内轰轰烈烈的抗议群众相比,数量并不大,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这场救亡大潮之中,成为其中一股重要的救国力量。他们自觉地将救亡使命加诸己身,在求得民族独立争取国家独立主权方面的努力丝毫不弱于国内人民,为探索救国之路依据自身的见识及观念,演绎了自身对于国家应承担的使命角色。[45]至此,留美学生对国家未来命运主动承担起责任、主动寻求国家在危难之际的出路的这种精神,无疑是值得称赞的。在这种精神的确立之下,可以说近代留美学生在爱国精神驱动下的价值选择以及一系列历史活动,折射出了近代留美学生与国家命运的双重互动面相,镌刻了这群留学生们对“我的祖国”最真挚感动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