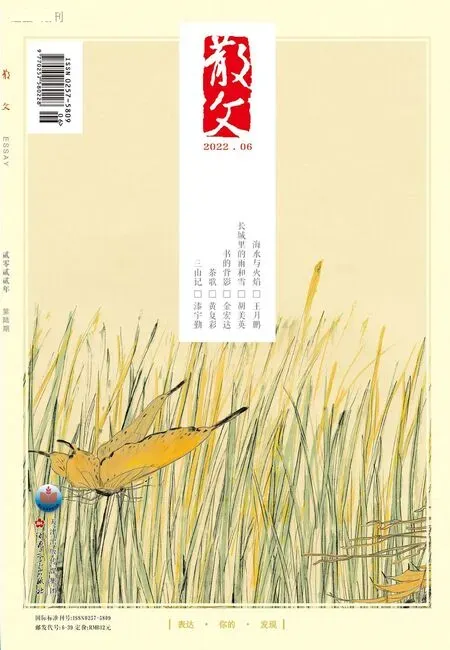老宅里的树
2022-10-21张强勇
张强勇
那年春天我十一二岁的样子,一位堂叔不知从哪里带回来一捆树苗,小树苗连根儿正好和我的身高差不离。看着堂叔在他家院子的房前屋后挖坑栽树,我想要是我也能栽种一棵树苗该多好啊,却终究是不敢说出来。我讨好地跟着堂叔,帮他扶幼小的树苗,有时还学着他的样子,朝着栽下的树坑用力地踩几下土。我看到堂叔拿起一棵树苗,随手扔在一边,拿起另外一棵树苗栽了下去。我看到被扔掉的树苗有明显的异常,像个连体的胎儿从接近根部的地方分成了两个枝杈,树苗的根部还有一个巨大的树瘤,于是怯怯地问堂叔,这棵树苗能给我吗?堂叔说这树苗怕是栽不活,成不了材,你要就拿去吧。我高兴地捡起树苗,赶忙往家里跑。
与树的情缘,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老家很多无主的土地,溪沟旁、田坎边,还有公共的晒谷场,都被勤劳的乡亲们开成了一丘一丘的菜地。我还小,是不敢将树栽种到那些地方的,便在老家宅子的前面寻到了一块小小的空地,找来一把锄头,就在这空地上挖了个小坑。我拿了一把砍刀,就将那个巨大的树瘤切了下来,又把另外的一根看上去病恹恹的枝杈斩断了,就种下了这棵被堂叔扔掉的树苗,还学着堂叔的样子给小树苗浇上了水。
我并不知道椿树的适应能力很强,更不知道,那小小的空地,对于幼小的椿树苗来说,竟然是它的“风水宝地”。那时老宅子的房前没有大树,在离房子四五米远的地方有几株低矮的杜鹃、月季、芍药和杜仲,土坎边还生长着一种叫作菖蒲的植物,它有着热烈而顽强的生命力,那是一种野性的生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随时随地都可以长得郁郁葱葱。杜鹃和月季是没有修剪打理的,由着它们自由自在地生长,该开花的时候开花。我有时想,杜鹃和月季恐怕是风刮来的,或者是鸟儿衔来的。那时,我的父母连生计都是发愁的,哪还有时间和心思种花养草呢?倒是那芍药和杜仲,父亲一有空闲的时候,会走近瞧一瞧,偶尔还会侍弄一番,培培土,浇浇水。芍药花有高高的花茎,开着硕大的花朵,花瓣单薄柔软,吹弹可破,千娇百媚,“艳艳锦不如,夭夭桃未可”。母亲说,那是父亲用来做中药材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曾跟着乡下的郎中做了三个月的学徒。
母亲跟我说,椿树好养活,耐寒,耐旱,适应性强,沾土就会生根发芽,我的家乡随处可见椿树。我的椿树更加热情地拥抱太阳的光芒,更加坚强地接受风雨的洗礼,更加努力地吸收泥土中的养分,它的根系很发达,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一直向上生长着。在它的周边,没有一棵比它还高的树,甚至在它的周边没有树,椿树能吸收着无限的阳光。洗澡水、洗脸水和洗菜水都往椿树的根部倒去,它离房子太近了,只要把门打开,我们就能看到它,就能把水抛洒在它的根上、枝丫上。此外,椿树还吸收着大量的雨水。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这棵树似乎突然长大了,枝条上爆出了绿茸茸的叶芽,它伸展枝叶,吐露芬芳,散着幽幽的清香。我看到那点点绿叶开始疯一般的舒展腰身,小小的幼芽,让我的心里萌生着微微的喜悦。
椿树的美在春天,鲜嫩的椿芽,是赐给我们的美味。
母亲说,椿树在初春吐出的幼芽是鲜嫩嫩的,可以用来做菜。天气乍暖还寒,我就会抬起头,仰着脸,去寻找树枝上的椿芽,看到椿树的芽苞就在枝头上开始萌动,我的心是欢喜的。不知道是在哪一天,在哪一根枝丫上,就冒出一朵一朵嫩嫩的、绛红色的椿芽来,我兴奋地告诉母亲,母亲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细长的竹竿,在竹竿的顶端,绑上铁钩子,站在椿树下,把椿芽钩下来。后来,椿树长大了长高了也长胖了,在母亲的注视下,我爬上高大的椿树,站在树杈上,一手搂住树干,一手用钩子去钩椿芽。母亲告诉我,一次不要摘得太多,够做一道菜就行。
清明过后,天气转暖,温度适宜,阳光和雨水也增多了,椿树的生长速度更快,一天一个样。头茬的椿芽过后,就生长出第二茬,但是椿芽的嫩质、味道与头茬相比,还是差了一些。母亲也会摘取椿芽的内蕊,捡好的、嫩的,用开水焯了,晒干,腌成咸菜放入坛子里。夏天的时候,与萝卜、腌菜一起剁成细末,配上蒜泥,那味道简直好得不得了,倘若来一碗小米粥,味香生津解渴。就是现在,头茬鲜嫩的椿芽,也是我们调剂口味的好食材。
参加工作后,我的椿树已长大成材,树干挺直、粗壮,树皮闪耀着青涩的光芒,树冠圆圆的,远远看去,好像一把张开的大伞,生长得更加茁壮,似乎全身都在蕴藉着无限的力量。是的,它已经长大了,它有着足够的强大。那时的我已经很少回家,偶尔给父母打个电话写封信,大多也是问问父母的身体,劝他们只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不要太劳累了,并没有问起过屋门前的椿树。只是有一天,父亲来信说要把屋门前我的椿树砍了,还说那些专门来乡下买树的人已经打过了好几次主意,能卖四五百元钱。我赶紧回信说家里需要钱我可以寄回去,一定要留下我的椿树。椿树的身上有我儿时的影子,有可口的菜肴,能守望着整个村庄,每当想到我的椿树,我就想到了我的家。可是大山深处书信往返一趟就要二三十天,收到父亲下一封来信时,我的椿树早已倒在了砍树人的斧锯之下。
后来回老家,我很多次都在为椿树之死与父亲理论,不管父亲说出多少理由我都无法释怀,有时母亲也站在父亲那一边,帮着父亲说话。父亲每次都耐着性子和我解释,说椿树会在某一个夜晚的暴风雨中连根拔起轰然倒下而压垮自家和邻家的房子;说椿树每年落在瓦面上的叶子与细碎的枝丫会腐烂屋面的房梁;说夏天的时候,那满树的枝丫和树叶遮住了阳光,房子采光受到影响;还说树木越来越不值钱。父亲说的理由往往是越来越多,也是越来越荒唐,一次又一次,在和我理论的时候,父亲的眼神越来越混浊,眼泪越来越少。
如今我再也不是爬树如猴的机灵少年,那个做主砍树的父亲也跟被砍的椿树一样回归尘土。当长夜梦回,我的椿树还依然挺立在老宅的屋门前,那个机灵瘦弱的男孩仍旧坐在高高的树杈上,微风吹拂、阳光和煦。现在,我的椿树不在了,但我养成了喜食椿芽的习惯。春天里,我就会想起生长在老宅里的那棵椿树。有时想,乡愁在哪里?或许也藏在椿芽里吧。
很多的村庄都是依附着树而生长着的,有大树有小树,有古树,也有刚刚栽种的幼苗。那一座座小小的宅子就隐没在树丛里,笼罩在树荫下。你走近村庄,要先走入那一重重树的围障,才能看到隐藏在其后的人家。儿时村庄的宅子里有许多的树,它常常伴随着一个婴儿的降生或一个老人的离世而落地生根。久而久之,树会像这个院子里生活的每个人一样,融入一个家族的历史。
老宅的后墙外还有一棵香樟树,那是乡村再普通不过的树种,却仿佛是我家的保护神,树冠硕大,直耸云天,黑褐色的外皮,像粗糙的鱼鳞片,从树根一直长到树梢,它日复一日地散发着特有的香樟味。这是父亲小时候亲手栽下的一棵树,一棵现在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的香樟树,它就生长在老家院墙外的东北角。那是一棵让我足以仰望一生的树,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让一棵树直耸云霄,却不能让它老去,它依然冠盖如云,生机盎然。
母亲现在跟着我在城里生活,每次当我回老家时,母亲都不忘嘱咐我:别忘了去老宅的后墙垛子上,看看那棵树。其实,一棵注定能成材的树是无须别人照顾的。但母亲还是常常和我絮叨,不要让四邻的柴火垛包住了树,要将树下的枯枝和落叶清扫干净,以免被邻家的小孩不小心点火烧了树干和树根。我知道,母亲惦念着那棵树,就如同惦念父亲一样。有一棵树让她记挂,在母亲的心里,老家就依然和往常一样,充满了烟火的气息。恍惚间,说不定哪一阵风会送来晨炊和晚饭的清香,送来父亲浑厚的咳嗽声。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夏日里奶奶经常会搬只小板凳,背靠着黑黢黢粗糙糙的树干,奶奶说,背靠着的这棵树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栽下的。现在,奶奶老了,在无事时喜欢细数着家庭里的成员。有一次回老家,在老宅子里,奶奶还特意地要我坐到她身边,扳着手指头和我统计着老宅里的生命。她说老宅里现在有多少口人,养了多少头猪、多少只鸡,说有一天看到一只猫在偷吃干鱼,说大黑狗到了晚上喜欢乱叫。奶奶说:“算上家里喂的猪鸡狗和树,咱家少说也有七八十口了。”她满脸的自豪与快乐,用眼睛注视着身边的大树、牲畜与我。
三毛在《如果有来生》一文中写道:“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是的,如果有来生,做一棵树吧,生长在岁月的永恒长河里,生长在故乡的老宅里,沉默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