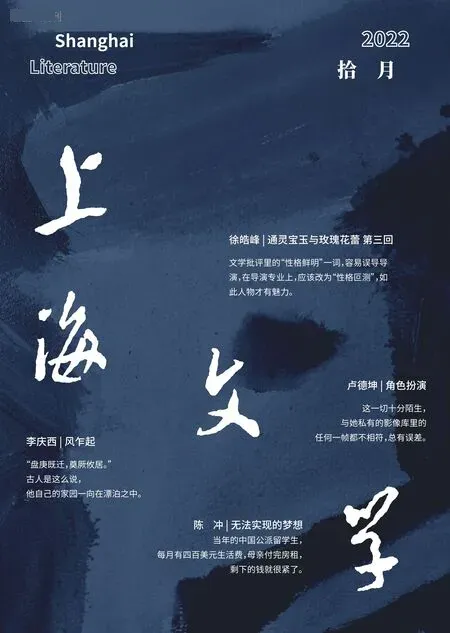试论海派文化的特征
2022-10-21张屏瑾
张屏瑾
研究海派,总要从一个问题开始:海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如果从“海派文学”的角度来定义海派,那么它源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争论,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京”“海”之争。但今天对海派的讨论,通常不会局限于文学场域,而是着眼于范围更广的海派文化,甚至海派精神。这样来看,海派的起源就远远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可以追溯到晚清,而且这种起源与艺术有更直接的关联。十九世纪末就有海上画派,又称为沪派,位列其中的几名画家并没有一个艺术上的统一风格,而是各有各的特点,这可能就留下了“海派无派”最早的伏笔。
“无派”或许确实是海派的一个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派是不可概括的,尤其是从一百多年以后的当代社会,再去回望海派的发展历程,人们渐渐会把海派的特点朝一个方向上去归纳,通常会有如下这些评价: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求新求异、不拘一格、雅俗共赏、多元并存等。这些评价并不难懂,但还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个总体上的方向又是怎么形成的?这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其表象,还须做一些深层次的理论总结。好在一百多年来,海派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再去探索海派文化的重要特征。
一、视觉、空间与物质
海派的起源与艺术有关,一个更重要的环节是京剧。京剧是在中国古老的戏曲艺术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才繁荣起来,成为了风靡一时的国剧。从徽班进京开始,京剧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城市都受到热烈欢迎。欣赏京剧,在北京称为听戏,在上海则被称为看戏。一个听,一个看,从这两个不同的动词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南北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属于现代社会的。但上海人的看戏并不单指看京剧,在晚清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上海出现了戏剧方面的飞速发展。除了京剧,还有话剧的流行,以及电影的引进。话剧被称为文明戏,而电影被叫做影戏,对当时上海的观众来说,看电影、看京剧、看文明戏(话剧),几乎都是“看戏”,有着相同的感觉结构。
既然是看,那么京剧在上海的看点就会变得多起来,伴随着一系列的艺术革新,比如“时装新戏”的出现,这个时装并非指时装秀,而是指改良的“南派”京剧。当时上海的一些著名的演员,如汪笑侬、潘月樵、盖叫天、周信芳等,都热衷于排演时装化的京剧,内容跟当时的国内历史事件紧密结合。比如秋瑾就义后,汪笑侬排了一部叫《秋瑾》的时装新戏;宋教仁遇刺后,《宋教仁遇刺》的时装新戏随即出现了;还有袁世凯称帝后,也很快出现了一部叫《王莽篡位》的戏,而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还有过直接描写“五四”运动的戏。所有这些时装新戏里演员穿的都是时装,而不是传统京剧戏服。
除了话剧的成分外,上海的新派京剧里电影的成分也不少,虽然第一部被拍摄成电影的京剧《定军山》是在北京拍摄的,但大规模的戏曲电影拍摄却发生在上海。一九一八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影戏部,把很多京剧拍摄成电影,演员多是“南派”。梅兰芳曾在一九三〇年去美国考察,重点考察了好莱坞,他回到上海以后,还加入了联华电影公司。而周信芳更是以喜欢看电影著称,他也最善于在自己的戏里模仿外国电影里的人物表现,还曾加入过南国社,南国社的前身则是南国电影剧社。京剧(京戏)、话剧(文明戏)和电影(影戏)这三者在当时紧密交融在一起,演出者和从业人员之间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更重要的在于它们的观众是同一批人,用同一种接受方式、审美趣味和感觉结构,来接受这样的文明戏、电影和时装新戏,这一有趣的状态的基础就是视觉。
周信芳在京剧表演上有一条著名的宗旨,叫做“知道世事潮流,合乎观众心理”,这里的“观众”定义很广泛,不只指京剧的观众,在京剧被拍成电影,或者与话剧有了更多融会贯通之处后,它面对的是城市空间中非常注重视觉效果的观众,通过观众的视觉要求来揣摩观众的心理,这是海派重要的特点。海派京剧于是变得非常“好看”,传统京剧强调写意,舞台道具很少,而在周信芳、盖叫天的京剧里,哪怕是传统戏,也会在道具上做很大的文章。比如周信芳表演《琵琶记》,戏里有一个骑马送行的情景,传统京剧会让人物拿一根马鞭来表示骑马,但在拍摄周信芳唱的《琵琶记》时牵了一匹真马到舞台上。平时在舞台表演的时候,海派京剧也会呈现各种各样的声光化电的新技术,在舞台上放烟火、加设一些灯光变幻、甚至杂技、马术等等。当然,这种做法也被人诟病,这就是为什么“海派”一开始是一个略带贬义的形容词的原因,这种贬义在后来关于京派、海派文学的争论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
与视觉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概念是空间,在特定的空间里才会发生那么多的视觉效果与目光的凝视。上海早期建造了一座“新舞台”,是专门为海派京剧而设的一个西洋式的、话剧式的舞台,这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老北京的戏园子——像茶馆一样,演员在表演,观众随意就坐,吃瓜子、聊天,这显然不适合海派的、话剧化的京剧演出,所以在上海新建了很多话剧化、歌剧化的新舞台。又如“丹桂第一台”,原来是上海的一个茶楼,但在新舞台越发受人欢迎的形势下,它也改成了一个与观众面对面的话剧式的舞台。之所以把这种舞台视为空间,是因为它还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隐喻。汪笑侬在他一九一六年办的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中题词:“历史四千年,成败如目睹。同是戏中人,跳上舞台舞。隐操教化权,借作兴亡表。世界一戏场,犹嫌舞台小。”意思是,世界就像一个舞台,成败兴亡都在舞台上演,观众就在下面看。
空间对于海派文化来说非常重要,它又是与视觉化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上海可以说很早就进入了读图时代。图像是最基本的视觉对象,而城市空间中的图像,最大的重点就是女性的身体。女性形象在中国漫长的传统文化当中,并不会被大规模地图像化,更不会被大量地复制与传播,但在民国初年上海的月份牌、商业广告、宣传画上都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身体形象。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女性形象与过去闺阁中的女性截然不同,表现了新女性,实际上这些女性形象并不是专来宣传新女性的,它的背后就是物质与消费。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些物化的女性形象出现了集大成者——摩登女郎,并迅速成为视觉与空间文化非常重要的符号。
摩登是一个很微妙的词,自有其历史渊源。为摩登女郎最早命名的还是文学家,用文字的方式,如果不是这些文学家,我们将无法直接确定这个符号的存在(张屏瑾:《再论“摩登女郎”》)。也是这个时候的白话文里出现了“摩登文字”,最有代表性的是“新感觉派”的小说家,比如在刘呐鸥的小说里有不少这样的场景:男主人公“我”看到了这样一些开放而性感的女性,这让“我”感到“战栗”,这个“战栗”跟本雅明讲的都市“震惊”庶几有相通之处,首先来自视觉的冲击。为刘呐鸥小说配图的著名漫画家郭建英,更是把这样的场景一幅幅地绘制出来。在上海影响一度很大的“新感觉派”,在文学史里被视为中国早期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他们的这种“摩登文字”与“五四”以后强调写实的小说的确很不一样了,但其实它并不是多么丰富的现代主义,它最突出的一点无非是文字的视觉感。比如在穆时英的小说《Craven “A”》里,把女性的身体部位跟城市的港口、海堤等地理风土联系在一起,看起来非常大胆,内涵却十分单一,我们仅能从中感受到从身体的物化出发的、绝对的视觉权力。
无论是月份牌女郎、摩登女郎的广告效应,还是电影票房,一切都联系着市场。在沪语里有一个特殊的词叫做“卖相”,这是和视觉最直接相关的,即一件东西的表象是否有价值,是否卖得出去,有点像今天说的“颜值”,但它更直接地与商业竞卖联系在一起。这个词充分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物质性,物质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商品属性。海派文化重技术、重商业,以及由重技术、重商业带来的重世俗生活,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我们认为摩登女郎是一个物化的符号,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和上海的城市空间里,男性和女性共同分享着这个摩登的符号系统。无论是现代派作家、艺术家,还是商贾、名流,乃至社会活动家甚至革命者,在这都市空间里,少有不注重自己的“卖相”的。鲁迅在上海生活时很敏感于这一点,他在不少文章里都有流露。就拿著名的“四条汉子”一事来说,他说有一次在内山书店约见“左联”的核心成员,在书店看到外面开来一辆小汽车,车上跳下四条汉子,“一律洋服,器宇轩昂”(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据夏衍后来的回忆,他自己那天并没有穿西装,而且所坐的汽车也没有开到内山书店他们就下了车(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但鲁迅为何会有这样的记忆?我们可以想象,这几位“左联”的领导者,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做派和气质,就是鲁迅所描写的那样——一律洋服,器宇轩昂,这就是摩登。
同样,视觉的对象也不绝对是女性,丁玲的早期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就有对男性的“凝视”。这部小说虽然是丁玲去北京以后所写,但写的是她在上海的感受,也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小说表面看起来是在书写“五四”式的个人情感苦闷,实际上与“五四”小说已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后者多写男女在心灵上的感应和精神上的苦恋,而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在没有进行心灵沟通之前,女主人公莎菲就注意到了男性身体的存在,而且,并不像“五四”小说那样,一个人美好的躯体必然导向更伟岸的灵魂,莎菲看到的是躯体背后没有灵魂,只有一个欲望的深渊。对丁玲这样的作家来说,在这里出现了身心的重大危机,但这并没有使她倒向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并不能解决这种危机,这在后来的历史中也是充分证明了的,这就是丁玲后来转向“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多元杂糅的文化现象形成了光怪陆离的海派文化特色,但这种杂糅不是静止的,空间的意义生产和符号生产之间存在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矛盾,以及强烈的对比,在海派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乃至广义上的红色文学,与海派文化联系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里,空间对比描写是最常见的引发抗争与激进情绪的方法,在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的诗人们笔下,上海一面是“华屋大厦”“娇妻美妾”“鲜衣美食”,另一面是“粗衣陋食”“鄙屋陋室”“面有菜色”;一面是坐汽车的富人们,另一面是林荫道下衣不蔽体的穷人,诗人们于是发出了对这城市的诅咒和对改天换地的革命的呼唤。而在“新感觉派”“现代派”“唯美主义者”等作家笔下,也有都市空间的对比化的呈现,穆时英的代表作《上海的狐步舞》开头第一句就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下了鲜明的定义:“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其实,穆时英的感受与革命文学者的观察角度十分接近,只不过当穆时英要去描写这个“地狱上的天堂”时,他又不由自主地采用了视觉化的方式,又回到他所熟悉的“新感觉”当中去了。在空间的对比上,电影比文字更直观。一九三七年上映的电影《马路天使》,非常典型地表现了上海都市空间的分层,镜头先定格在一个摩天大楼的最底层,再自下而上地慢慢一直拉到楼顶,然后镜头切换,变成一个俯瞰上海的角度,空间的全景就此呈现,从中我们会发现“底层”与“高贵的洋楼的顶端”的鲜明对比。
无产阶级的问题,其实就是物质的问题。上海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是茅盾的《子夜》,茅盾怀着要展现上海社会全景的抱负来写《子夜》,但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然要从最有代表性的空间元素来描写这座城市,于是《子夜》的开头几段,就囊括了技术、商业、工业、景观、空间,当然还有目光,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除了日常生活还没有登场以外,几乎所有海派都市空间的元素都在这里交织了。这样的一段城市空间写照,虽然写的是上海,也可以同步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其他几座大都市里,所以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里提出了“上海世界主义”,认为上海的这样的一种空间、景观与结构是世界性的(李欧梵:《上海摩登》,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不过,这相似的大都市的景观、空间与结构背后的社会矛盾也会有其相似之处,第三世界半殖民地国家又有它更为专属的危机与社会矛盾,茅盾的《子夜》要写的并不是世界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写反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小说,是要表现这样的一些速度、技术、景观、声、光、电背后的危机,也就是《子夜》的男主人公吴荪甫这样的民族资本家的危机。所以,《子夜》不会是一部单纯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式的小说,它必然要涉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理念性的真实。
二、大众文化与海派的两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文化市场日益繁荣,也带来了大众文化的兴起,九十年代是一个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发生结构性的转型的时代,一边是知识分子地位的衰落从而激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另一边是“市民社会”及日常生活命题受到许多关注,而这一切,在现代海派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踪迹可寻。海派文化与大众文化,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
首先需要定义什么是大众文化,或者说,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众文化。日本学者岩间一弘在他的《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一书里认为,依托近代和现代特殊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现代上海诞生了一个非常特殊和复杂的“大众”社会形态,即便从整个亚洲国家的范围来说,在上海诞生的这个“大众”社会都是很有代表性和启发的。他对这个“大众”的基本定义以“新兴的中产阶级”为中心,但岩间一弘认为它又不完全是一个市民社会,而是一种承担特殊功能的大众的社会,“由于媒体、教育、大规模生产技术等的发达,多数人获得了一定的读写能力与生活的富裕,接触同样的情绪及文化,容易将自己想象为某大集团的成员的社会”(【日】岩间一弘:《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葛涛、甘慧杰译,上海辞书出版社)。在他看来,这种新的大众社会既是新兴的精英文化舞台,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某种重要基础。
这一研究颇有见地,比较我们通常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总是与以大众传媒为媒介广泛传播的通俗文学、电视剧、广告、流行音乐等对象结合在一起,不会涉及精英文化与社会伦理共同体的内容,而岩间一弘所说的上海特有的大众社会,则与进步的社会思潮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同样有关。在我看来,上述两种对大众文化的不同理解,在海派文化里都可以找到它的线索,有它的同源性。在海派文化的诸多特征中,“求新”无疑是最重要的,所有时髦、时尚的氛围与风气都离不开一个“新”字,这个“新”里面可以包含各种娱乐样式的翻新,也可以包含思想与艺术的创新与进步,如果说前者更多地与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有关,那后者就是知识分子化和精英化的。当然,“大众”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还是“群众”的前身,是带有社会革命意味的概念,但社会革命的理念出自知识分子,因此这个“大众”也可以被归为思想进步和知识化的产物。
中国现代文艺在上海的风气创新所带来的繁荣状况,对此研究非常之多,且还在被不断地发掘,比如近现代的报刊杂志,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还有电影、戏曲、音乐、美术等。所有这些艺术上的开拓,也都走了两路的“大众”路线,有最新的艺术理念与方法的习得,大部分是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这些新的艺术形式也在迅速下沉,通俗化,融入市民生活。最典型的例子是电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所呼唤的,正是岩间一弘所说,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家国与革命的情怀,而在此之前,在上海,电影早就占据了市民生活和通俗大众文化的主要市场。一九二八年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在上海拍了十多部,一直到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禁演,一九三五年转到香港继续拍摄。这部通俗娱乐电影十分能体现海派兼容并包的特色,挪用了传统及改良戏曲的诸多要素,还综合了杂技杂耍、电影特效等手法。观众层次也很丰富,夏衍创作的“左翼”文学剧本《上海屋檐下》里有一个情节,工人家庭的老父亲来到上海,吃完晚饭一家人打算去看《火烧红莲寺》。从某种程度上,“左翼”电影正是利用了娱乐电影对影迷观众的培养,在这个基础上再对其心理与认知加以改造,可以说是革新之上的革新,批判之中的吸收,体现了两种大众文化之间的关联。
从文化启蒙的角度看,上海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思想史、文化史上一些重要的杂志,如《新青年》,虽不是在上海创办,却是在上海改版,成为重要的革命思想宣传阵地;另一本《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最畅销的杂志,也在上海完成了重要的转变,从刊登鸳鸯蝴蝶派小说到刊登新文学作品;还有一本文艺刊物《现代》,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创刊,是一本追求与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杂志,欧洲、美国及日本等现代发达国家最新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事件,常能第一时间在《现代》杂志上看到译介与通讯,杂志还刊登最新的电影广告、商业广告等等。从《现代》确实可以部分地看到“上海世界主义”的一个投影,而且“现代”本身就是一个抱着自信的自我命名,此时距离辛亥革命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中国人的自我认同,至少在上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的改变与进步,在上一个世纪之初,完全是从文艺和文化层面首先表现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海派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新潮”和“探索”同样成为上海文化的关键词,比如在上世纪“85新潮”的背景下,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探索书系”,许多先锋小说入选,九十年代出版的“大上海小说丛书”以及《上海文学》杂志推出的“新市民小说”也强调城市文化的定位,读者众多。不过后两者中选入的作品今天看来文学史影响力不大,因为这些作品多靠近市民阶层的趣味。上海本土作家的写作,也多带有通俗市民文学的痕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精英化的先锋小说没有关联,两者都指向这个时代的个性要求与社会奇观,在城市空间内发酵。
求新求异是海派文化引人瞩目的一面,另外一面则是安稳、自持、自我保全。张爱玲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确体现了上海人的总体生活追求:注重日常生活、精打细算、稳中求胜。当代小说《繁花》里有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不响。上海人常对世事采取“不响”的态度,其实就是自我保护、审时度势,不表态,先观望。这是非常典型的海派性格,其实也是大城市居民一种普遍的性格。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小市民之间以爱情的名义较劲外,也充满了对现世安稳的强调。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有一个很著名的结尾,提到了《诗经》里的名句“死生契阔”,把这句诗植入到一个完全现代的故事里,尤其是在战争危机感的环境中,反衬动乱年代里,小人物对近在咫尺的安稳感的追求,但张爱玲又对这种追求中隐藏着的虚无意味有所反讽。一九四七年,在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电影《太太万岁》里,一个上海中产阶级的太太,也是用了一种海派的智慧,化解了丈夫出轨导致的一场家庭危机。
在这一点上还可以举《生活》周刊为例,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创办的一本刊物,邹韬奋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编,也是在他主编的时期,《生活》的知名度日益提高,发行量一度突破了十五万份。《生活》周刊的主旨之一是接通平民生活,办有“小言论”“读者来函”等栏目,作者都是普通的上海市民、学生、职员,也有家庭妇女,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一定很高,但都有一定的读书写字的基础,他们发表的内容,大部分是在安稳的生活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包括个人的情感波动,事业困惑以及财产纠纷等,表现出中国最早的一部分城市中间阶层的日常与职业生活的状态。《生活》由此也涉及早期市民生活的伦理状况,包括小家庭、性别、教育与法权等等,是一份宝贵的记录。
文艺作品之中也有了对中国最早的“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的表现,比如施蛰存的小说《梅雨之夕》,写的就是有着固定生活轨迹的小职员的“轨外”心理活动,这情节当然是以市民化的社会为基础的,但《梅雨之夕》又不是通俗小说,而被视作“新感觉派”的现代派书写,可见无论归于安稳—世俗还是归于激进—新潮,海派文化都包含着一种对现代城市生活常态的呈现,这种生活或许是普通人孜孜以求的,也可能是现代派的小说家与诗人的灵感来源。施蛰存等作家的写作在当时就受到施尼兹勒、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仿佛是对西方经典中产阶级叙事的再现。不过,这短暂的摹写很快就被全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大潮所淹没了。虽是昙花一现,海派文化的这一面向,却能在当代历史中几度成为城市生活想象与书写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关于上海城市及海派文化的论争重新开始了,也出现了两篇比较典型的文章,一篇是余秋雨的散文《上海人》,收在《文化苦旅》一书中。这篇散文描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人,语带微讽与自嘲,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另一篇是九十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之前,两位记者写的《大上海,你还能背起中国吗?》,此文也流传甚广。当时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与它对国家所做的贡献相比处于失衡状态,上海本土经济未实现转轨,还有很多束缚,在各方面出现了停滞甚至是落后,因此引发了深深的失落与焦虑。这两篇文章从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观察有相通之处,表现出海派文化的独特性其实是一种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建立在现代社会的进步与优先性之上,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对海派文化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至今仍未停止,例如当下对“新上海人”及“新上海人二代”的讨论:更年轻的一代居民虽然出生于上海,但不会讲沪语,对海派文化也几乎没有了解,他们虽“在”而是否“属于”上海呢,他们将怎样自我定位,海派的特征是否也将因此而发生改变呢?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问题并不会使海派文化的讨论仅仅停留在历史现象之上,而将进一步为海派文化增加新的当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