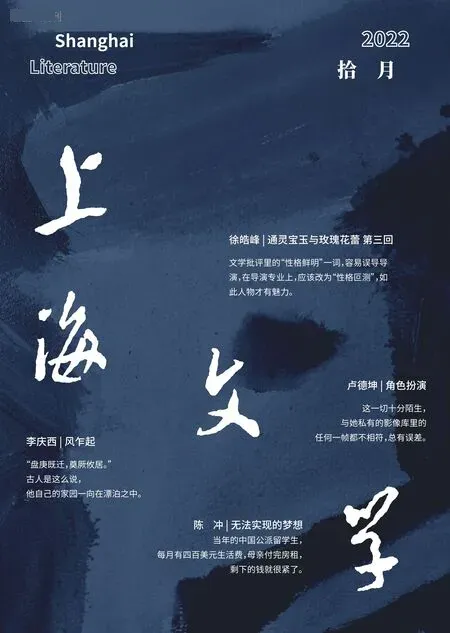无限深渊的入口
2022-10-21草白
草 白
一
最后的日子里,马克·罗斯科把作品画得非常大,足有三米高,他认为观众观看此类画作的理想距离是四十五厘米。由此想象那个场景:扑面而来的色块使得观看者置身于某个内部空间里,就像进入一间黑暗、空无一物的屋子。至此,观看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为命运旅途中的休戚相关者;观看本身也不再是轻巧的、事不关己的行为,而是险象环生之旅。“被迫全然沉入其作品”,宛如进入一个特殊空间,隧道连接隧道,洞穴内部有更深的洞穴,既是深渊,也是禁地。
观看者必须拥有侵犯某处禁地的勇气,才能获致生命极致的体验,就像盗贼在经历九死一生后方可获得价值连城的珠宝。创作者何尝不是如此,那些稀薄、晦涩的块面,边缘模糊的矩形堆叠,以及所有画面中的扩张与收缩,都在指向一个强烈、反常、冲突的戏剧世界,“它们隐含着画家的欲望、恐惧,以及精神的渴慕”。
马克·罗斯科所做的一切只为接近,接近古老神话的形式,接近精神意义上的清澄和透明,接近一条河流的上游。罗斯科从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爱琴海,从图腾崇拜、黑人雕刻和古希腊晚霞中获得启示,还从战争和大屠杀中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样貌。画布上堆叠的、处于漂浮状态的矩形以及朦胧柔和的边缘,便是隶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怪兽形象和变形记,就像卡夫卡的甲虫和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哪怕它们怪异、畸形、东倒西歪,与美绝缘。
罗斯科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抽象派画家之一。画家本人却认为,他画的绝不是什么抽象作品,如果抽象仅仅是指几何色块的话。罗斯科作品的崇拜者与迷恋者渴盼画家现身说法,以此领到通往神秘之城的钥匙,但他对此绝口不提。即使在一本叫《艺术家的真实》的理论书里,罗斯科谈到夏尔丹、莫奈、塞尚等人,对诸多同行的工作都作出恰如其分、条分缕析的阐述,唯独将自身隐藏起来,连艺术家自述之类的文字都少得可怜。
评论者因领不到除了作品本身之外的观看指南,而深感不安。他们想到蒙德里安,后者创作了著名的红黄蓝构图,会不会与罗斯科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对此,罗斯科反应激烈,拒绝做任何比较。他客气地说蒙德里安只是在切割画布,而他在探索色彩的新区域。其实,他很想说蒙德里安什么也不是,他本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罗斯科就像一个暴躁易怒的孩童,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艺术作声嘶力竭的辩护,又拒绝对此作出超出作品本身的阐释。他早期作品中还有便于区别的标题,比如《蓝色的云》《深红上的黑》等等,到后来干脆统统命名为“无题”。
《艺术家的真实》写于“漂浮的矩形”诞生之前,完成后被束之高阁,直到画家去世十几年后被偶然发现,搁置数年才出版面世。当年,罗斯科特意停下创作的步伐,以一年时间去写作此书。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文字与后来“漂浮的矩形”“柔和的边缘线”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逻辑关系,甚至连隐约的“预见”都没有在书中出现。这让罗斯科绘画的专业评论家和普通迷恋者都深感不满,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画家故意神秘化的伎俩。
我的理解是,此书的写作并没能解决罗斯科的问题,就像写作中出现的问题绝不可能通过“创作谈”来解决。而且,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最终的解决之道。这一点,想必罗斯科在完成该书的手稿后,便已明了。此后便是一个命定为神庙画像的人,开启他庄严、静穆、无边无际的沉思之旅,这也是罗斯科在死亡之地的考古之旅。我无数次思考何谓解读罗斯科艺术的关键词,最终发现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就像后人无法诠释他对自身生命的厌倦。这个世上有太多的谜,而死亡可能是其中最沉重最缥缈的一个。最终,罗斯科自杀而亡。他将自己杀死在工作间的浴室里。他倒在血泊之中,两只手腕都被割破了,身旁是一把染血的剃须刀。血管里流出的血很快凝固了,就像画布上凝聚的红,那些深红、橘红、洋红、栗子红,以及红上的蓝色、黄色、青色,都化作缤纷的碎片,化作戏剧舞台上的悬浮物,随时间终结,随晚风而逝。
二
经历过二战、奥斯维辛及原子弹爆炸的艺术家,再也不可能像古希腊同行那样绘制赤裸、匀称、健壮的一切称之为美之化身的人物形象。艺术家在寻找全新的表达。或许,雕塑家贾科梅蒂的经历可以为此提供某种诠释。那是一九四六年某一天,二战刚刚结束不久,贾科梅蒂坐在巴黎蒙巴纳斯的电影院里,忽然发现屏幕上的脸孔不再是脸孔,而变成黑白符号,丧失所有意义。他不再注视屏幕,转而观察起坐在身边的人,他们在他眼中更是发生了惊人变化,变成完全未知的视像。这是一个神奇时刻。这一次偶然的观影体验,让艺术家经历了个人经验史上的“分裂时刻”。
“未知的一切变成了我身边的现实,而屏幕上的一切则什么也不是……现实完全改变了……它们从未出现过,它们是彻彻底底的未知物,它们是神奇之物。蒙巴纳斯的大街就和一千零一夜一样美丽,一样梦幻,一样销魂!”
从此之后,这位“白天工作,夜里将工作成果倒入塞纳河”的雕塑家,开始了疯狂的创作之旅。那些作品不再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它们高挑、畸形、灰暗、独特,好像来自一个世纪大火炉,是焚烧后的残留物;但它们“美得像一枚指针”,既坚硬又轻盈,既颓败又神采奕奕。正如让·热内所说,贾科梅蒂的人像是这个破碎世界的荣耀,它们建立在与众多死者交换过美、孤独和伤痛的基础之上。
与贾科梅蒂一样,马克·罗斯科也在寻找一种全新的情感表达方式,它纯粹,饱含力量,同时也是猛烈的、激进的。他要做的便是在生命与绘画之间重新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一度被战争和大屠杀中断,甚至摧毁,他有责任找到它们,不是陈旧过时的联系,而是全新的,给人压抑、沉重和暴虐的感觉,让人想到一切伟大的悲剧。罗斯科对一切形式的悲剧情有独钟。
BBC纪录片《艺术的力量》第八集里,马克·罗斯科穿着条纹衬衫,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大部分时间都在画室里抽烟。那个画室显得大而昏暗,高过人身的画作竖立在墙边,给人肃穆感。每每画家在镜头前说话或沉思时,都有烟雾在他脸庞及周遭弥漫,好像画家在不断吞吐着一些带气雾状的东西。苦思冥想中的人试图拨开纷繁杂乱的思绪,找到伟大构思中的每一个部件。
马蒂斯的《红色画室》给深陷色彩囹圄中的罗斯科带来某种启示。神奇而天真的马蒂斯从遥远的地方引来一条色彩之河,它们就像漫无目的的时间和不受约束的空间到处流淌,所到之处,画室里所有物体均染上红色汁液,画作不再有中心,因为所有物体都是中心。色彩不再是物体性状和轮廓的分界线,它们融合成一个整体,随心所欲,可以与任何颜色共存、共舞。色彩在马蒂斯那里获得释放,好像有一双无形之手将陈旧的经验捣毁、揉碎,化为乌有。色彩与物体属性分开,成为一种经验性的色彩,与物体本性无关,与创作者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
看过这间浸泡在红色颜料之中的小屋后,罗斯科似乎看见了某种可能性。不仅仅是色彩,任何物的属性都可以获得释放。他还意识到当色彩的使用强烈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一种罕见的驱动力,近乎原始,又凌驾于一切线条、构图之上。马蒂斯的劳作让罗斯科感到兴奋,好似夜行路上的人看到微弱亮光。但罗斯科没有依循马蒂斯开辟的道路行进,他有自己的道路要走,他不是寻找此刻的路,而是一条通往永恒之路。
很多年里,罗斯科过着简朴、近乎拮据的生活,厌恶一切奢靡和浪费。当年,他雄心勃勃地为纽约城最豪华的餐厅之一——四季餐厅作画,只为了让它们在饕餮者上方发出微光,吞噬着他们,以至进食者遭到冒犯,胃口尽丧。罗斯科想通过艺术完成对人心的拯救,尤其是人们在觥筹交错、春风得意之时。
画作即将完成时,他带着家人去了四季餐厅。建筑富丽盛大、金碧辉煌,往来食客衣香鬓影、光彩照人,鎏金菜单上印着贵到咋舌的菜价,这一切都让罗斯科出离愤怒。他悲哀地意识到那里进食的人根本不会注意他的画作,它们只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与一面色彩斑斓、装饰考究的墙壁无异。在富豪和无灵魂的食客眼里,艺术家的生命与信念根本不值一提。他感到羞辱,毅然退回高额订金,重新落回生活的捉襟见肘里。
罗斯科被视为一个暴躁易怒的艺术家,既是精神领域的披荆斩棘者,也是现实世界里的屡屡碰壁者。他庞大的身躯一直向着死亡的边缘倾斜,对人类悲剧命运的感同身受,让他找到强烈的色块和柔和模糊的边缘线。一个人就算从来没有看过什么画,也不了解何谓艺术,在罗斯科的画作面前大概也会受到震动——但凡他在长夜里痛哭过,对人之为人最深层的痛苦、最微妙的情绪了然于心,就不会无动于衷。
一种崭新的艺术就此诞生,它脱离人物和事件、形体与构图,只以几个排列的矩形色块和有限的色彩来安排时间和空间关系里的总和。那里有人类情感中最强烈的狂喜与最深沉的悲哀,它囊括了四海万物的情感,从开天辟地的鸿蒙期,直到近世近代大屠杀年代的人类遭际,并由此往前千秋万载地延伸,无所不包。
任何观看者一旦在这样的画作前伫立数小时以上,他的世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命的悲喜通过汹涌的画布源源不断地涌来。人们或流泪哭泣或心灰意冷,一切情绪情感都被渲染强化,又一一复归至平和、安宁的境地。
未来通道已开启,人们只需心无旁骛、平静坦然地步入其中。
三
罗斯科的画作每每让我想起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代表作——光之教堂。建筑师在教堂墙壁上留下一个十字形切口,光线由此涌入,借此营造出特殊的光影效果,即光之十字架。这一设计成为教堂建造中的点睛之笔,也是“光之教堂”命名的由来。
在美国休斯敦,圣托马斯天主教大学里,也有一座以罗斯科的名字命名的教堂。那里陈列着艺术家晚年所画的十四幅暗色系壁画,以栗色、黑色和深紫色为主,暗黑矩形,边缘锐利。当年宛如云彩般迷人的边缘线,早已从画家作品中消散无踪。这些最后的作品几乎是沉闷的,沉闷而忧郁,就像艺术家晚年的处境。所幸中庭有光,宛如瀑布从穹顶垂落,流光四溢。这个建筑很容易让人想起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大教堂,想起《最后的审判》。或许还有法国南部的马蒂斯教堂,尽管后者全然是别样风格,宛如春日午后牧神的笛声,悠扬而寂静。
BBC拍摄的纪录片里,罗斯科提到参观某个中世纪图书馆的楼梯间时,被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所震撼,那里的门窗都是封闭的,“他们被困在一个房间里……能做的只有拿自己的头去撞墙”,这种封闭的感觉激发了他。这正是他想要带给观众的东西。看到这里,我忽然想到鲁迅的铁屋子,想起里面昏昏沉沉的人们。当年,他写《呐喊》就是为了唤醒。类似的希望大概也存在于为四季餐厅作画的罗斯科身上,他以为艺术可以击溃食欲,给人奋进的力量。这俩人都置身于共同的荒野里,周遭除了冰冷的墓园、暗夜所散发的蓝光以及夜莺的歌声,并无可称之为优美风景的东西。
摆在马克·罗斯科面前的工作是:如何将光亮彻底隐匿在黑暗之中,就像某个时期山脉完全地被云雾所截断,但所有人都知道它们并没有消失。他要表现的是蕴藏着光亮的黑暗,并且以枯槁、冷寂、乏味之极的形式表现它。很多时候,马克·罗斯科根本不知要抵达何方,但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不是走在去郊游或野餐的路上。罗斯科从来不致力于满足观者的眼目之娱,他是大无畏的引领者,以信念之力,将陌生之域变成自我归属之地,吸引更多人进入,获得双重的——视觉与精神的庄严面相。
圣托马斯天主教大学里的罗斯科教堂或许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宇宙中心里一方即将熄灭的炭石,一块黝黑的磁铁,一处巨大的能量场。人群似铁屑,熙熙攘攘吸附而来,沉默着进入某种类似梦境的空间里。昏暗之极,却有隐隐的火光闪烁,那是观者目光所斫出的光亮。
在我的生命旅程中,只在极少时刻有过类似体验。一次在西部旅行时,傍晚时分行走在荒凉浩瀚的沙漠之上。驼铃远去,夕光暗淡,沙砾金色的边缘也一点点被收走。夜空中忽然射进无数条跳跃的光束,好像来自邈远的外太空,其实是沙地上行走之人所携带的手电亮光。人影分散在沙海之中,只有光束穿越时空,在头顶之上交汇往来,好似只要稍一伸手就能抓住那些光亮。另一次在浙南深山里,当地海拔最高的区域,山下已是春深日暖时分,深山之夜竟有细雪飘落,一山之隔已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那一瞬间忽然生出异样感,好像此去经年,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永久地待下去,没有任何分别心。说不出什么缘由,多年来,这两处毫不相干的遭遇总在我心头浮现,冥冥之中与此刻的生活发生某种牵连。
我想,大概是其中流露出的毫无理由的安心与坦然,让我铭记在心。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最想回到那个深山里的房间,以及日落之后荒凉的沙地上。我只愿在这两处来来回回,看沙漠苍穹里翡翠般的群星,深山野地上草木摇落的露珠,以此度过人世的漫长光阴。
四
摆在后来者面前的艺术家的作品,林林总总,蔚为壮观,但都属于永恒的过去完成时。人们无法从中还原整个创作过程,拼凑出精神领域内流宕的轨迹。艺术品不是工厂车间里的产品,有固定而详实的生产步骤;它流动而不可预测,也无迹可寻。一次偶然的失误,甚至一次漫不经心的走神,都可促使奇迹的诞生。这既属于艺术行业的秘密,也是艺术家本人的纯粹欢乐,是上天对创作者的奖赏。
当战争进行到最惨烈的年月,当道德领域的危机在世界各地蔓延,作为艺术家的罗斯科却实现了个人创作生涯中风格的蜕变。他从地下铁及“形而上”主题的创作中脱身而出,走进一个以“矩形”为主导的图像世界,那个世界天马行空,是冒险之旅,直觉之象,更是模糊的集合——罗斯科认为“潜意识代表的并非最远,而是最近的艺术海岸”。
在开启这场冒险之旅前,罗斯科系统性地消除了自身画作中的具象元素,为自己开启了一扇表演之门。他把自身画作描述为“戏剧”,“画中的形状都为表演者而存在”,形状不再是形状本身,与具体可见的经验也无关系,它指向热切的激情、坚毅的自我决断力以及对时代情绪的捕捉。
当代诗人西川曾说过,诗歌不仅要反映时代,更要处理时代。作为艺术家,图像世界的创造者,当面对战争和屠杀,罗斯科敏感地意识到过去熟悉的一切不再能表达这个时代。因为,人们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生活了。一开始,罗斯科选择神话主题,以“鹰”为基本形象,但他很快放弃了。紧接着,模糊重叠的“矩形”,以及像羽毛或白云一样柔软的边缘线,出现了。那些图像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极度凝练的表达,只以两三个矩形和对称的重叠色块组合而成的画面,却充满平面的张力和难以捕捉的呼吸的律动。
如何在平面实现空间深度,而不是超现实主义画派或立体派所表现的深度,这是马克·罗斯科面临的问题。罗斯科的画面中,色块之间并非区域鲜明、一目了然,而是彼此遮掩,形成朦胧、不可见的视觉感;而作为背景的色块又忽地涌现出来,宛如突破重重阻力,从深渊之中浮现而出。除了色块和色块之间,以及色块和背景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还有透明的薄纱般的边缘,好似从层叠空间中透出的光,给人强烈的梦幻感。
正如评论家们所言,罗斯科采取的是模糊化的形式,不像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那样确定与明晰,但这形式因饱蘸着艺术家的情绪、情感,从而被紧紧黏合在一起。画面也不再是大小矩形的组合,而是各种色块的层叠,它们自身便是一个可触可感的宇宙天地。所有命运的狂热与悲喜,都可从中得到印证,正如艺术家自己所言,“一幅画无关体验,它自身就是体验”。
所有风格的演变都来自内心,来自时代经验在人之内心的投射。抓住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本质,在无穷尽的喧嚷声中,辨别出那低沉有力又飘忽不定的声响,辨别出那激动人心又意料之外的部分,便成了艺术家漫长一生的隐秘使命。
五
很难描述翻看罗斯科画册的幽微感受,它让我想起曾经走过的那片绿草地。黄昏暮色中,我出现在那里,不为看风景而来,但我的确走进一个盛大而一去不复返的场景里。随时可消逝的天光,隐约而至的紧迫感,让我感到周遭的青草地好似为我而生,因我而生机勃勃。
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虽置身世界的角落,却好似处于舞台上追光所及之处。一切感受、感知都可得到及时回应,它们在你心里发出回响,就像将一粒石块掷向湖水表面,瞬时激起涟漪和回声。
这些画作,就像湖水,是湖水之上激起的涟漪,涟漪里映照出的黄昏微光;它们是神秘难解的启示,既恢弘深邃,又一览无余。观者全然沉浸其中,被此召唤,去往深渊或梦境的深处。
罗斯科用绘画讲述超验现实的体验。它超越时空,无关因果,在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也在可预见的现实逻辑之外。它是假定情境,是艺术家孜孜以求的“戏剧性”,也是流水之上的神话舞台。
一处幽暗、隐秘的洞穴,也是所有时空关系的入口。观者由此可窥见远古以来人类祖先所经历的种种:洪水、山火、战争、兵燹、饥荒等等,还有无数人影在此雾气中冉冉浮现,他们是阿波罗、雅典娜、普罗米修斯、西西弗斯、阿伽门农,还有哈姆雷特、俄狄浦斯王、麦克白,我们自身踌蹰的身影也置身其中。
艺术家在画面上所做的貌似只是一点点变形,却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艺术宛如神奇的显影液,让一切可见不可见的都显出迷人的轮廓,显出沉静和孤绝的本质,让人心醉神迷。
还是那次西部之行、沙漠之旅,整个旅程好似都在去往一个荒寒僻静之地,只有风、沙砾与灰蒙错置的时空,只有枯竭的河床、昏暗洞穴里的石像、夕晖中摇曳的芨芨草和骆驼刺,好像我们不是为了观看它,而是进入它,在那隔绝的地理时空里体验一种微妙的气氛,体验风景的原始和壮阔。那是所有风景的总和,从最深沉、最古老的大地上流淌而出,一旦出现,永不消失。
罗斯科艺术就如那片原始荒寒的风景,一处永恒的旷野,人们只要进入,便会被长久地滞留其中。那不仅是风景,更是心灵的剧场,猛烈、炽热的人性试验场。它们紧张压抑、无处不在,犹如死亡嵌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