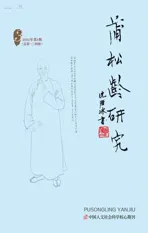《聊斋志异·促织》之版本对比辨析
——以蒲松龄手稿本与青柯亭本为例
2022-10-21郭晓雨
郭晓雨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64200)
《促织》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脍炙人口的重要篇目,尤其作为入选高中语文教科书的必修篇目,也使其知名度陡然提升,其中成名之子“魂化促织”这一凄美的情节更是广为人知。但是,“魂化促织”却不见于蒲松龄原作手稿本,并非蒲松龄的原创,而是出自《聊斋志异》青柯亭本的整理编刻者赵起杲等人之手。由此,青柯亭本对于《促织》的改动是否得当成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促织》版本差异及传播、研究概述
蒲松龄在世时无力刊行《聊斋志异》,手稿本由蒲氏嫡系珍藏,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鲍廷博编刻的青柯亭本问世,对《聊斋志异》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刻印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需要,对《聊斋志异》的文字做了改动,删掉了数十篇,也改动了一些有碍时忌的字句,其中《促织》是关键处改动较大的一篇,与手稿本相比,青柯亭本最大的改变在于增加了成名之子“魂化促织”的内容。概而言之,手稿本与青柯亭本共有十一处不同,统计如下:
第一处:早出暮归,提竹筒铜丝笼。(手稿本)
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青柯亭本)
第二处:拾视之,非字而画。(手稿本)
视之,非字而画。(青柯亭本)
第三处:后小山下,怪石乱卧。(手稿本)
后小山下,怪石卧。(青柯亭本)
第四处:旁一蟆,若将跳舞。(手稿本)
旁一蟆,若将跃舞。(青柯亭本)
第五处: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真逼似。(手稿本)
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逼似。(青柯亭本)
第六处:母闻之,面色灰死,大骂曰:业根,死期至矣!(手稿本)
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青柯亭本)
第七处:儿涕而出。(手稿本)
儿涕而去。(青柯亭本)
第八处: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呑,亦不敢复究儿。(手稿本)
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青柯亭本)
第九处:急趁之(手稿本)
急趋之(青柯亭本)
第十处:由此以善养虫名,屡得抚军殊宠。(手稿本)
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青柯亭本)
第十一处: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手稿本)
(青柯亭本无此内容)
另,三会本中第十处同青柯亭本,其余各处同手稿本。其中,第八处与第十处不同是手稿本与青柯亭本差异最为显著之处,笔者将在下文中对其进行详细论述。就其余几处不同而言,绝大部分于文章主旨上无甚差距,应当是由于传抄刻印时的谬误与青柯亭本整理者的用语表达习惯导致的。就这类差异而言,若原作无语义语法、表达逻辑上的明显错误,应优先采用原作字句。其中第四处“跃舞”较“跳舞”更书面化,第五处手稿本“真”字似多余,此两处笔者以青柯亭本为佳;其余第一、二、三、六、七、九处,笔者以手稿本为佳。
至于第十一处异史氏的评价,“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这段话见于手稿本中,而于青柯亭本则是缺失的,这是因为这段话涉及最高统治者的尖锐讽谏与批评。对于《促织》,一向以中正平和著称的王士禛表示了异议:“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台阁大臣,又三杨、蹇、夏诸老先生也,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惜哉!抑传闻异辞耶?”作为朝廷高官的王士禛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官方主流思想,亦足见《促织》的批判力度之猛烈,出于躲避文字狱等目的,青柯亭本的整理者赵起杲、鲍廷博删掉了手稿本中尖锐的批判,这也是碍于时局的无奈之举,但确乎略损于小说的讽刺批判内涵。
就传播情况而言,青柯亭本的传播范围与影响程度都要远大于手稿本,因此“魂化促织”的故事一直以来都广为流传。20世纪60年代初,张友鹤汇集蒲松龄手稿本与其余多种本子,整理出一部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就《促织》一篇而言,三会本保留了大多数手稿本中的内容,但唯独成名之子“魂化促织”这一情节沿用了青柯亭本,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对青柯亭本“魂化促织”这一改动的肯定。不少学者认为“魂化促织”是对原作的点石成金,也有部分学者在谈及《促织》之时直接采用青柯亭本或是三会本中的内容,对小说的版本问题避而不谈或是语焉不详。第一位站出来为手稿本正名的学者是马瑞芳教授,她在论文《课本中〈促织〉的版本谬误》中指出“魂化促织”本不是蒲松龄的创作意图,课本中应当选用手稿本的《促织》,不可擅改名著。而后,方东流与鲁凌波则在其论文中分别驳斥了马瑞芳教授的观点,并肯定了青柯亭本的情节内容,但其或对马瑞芳教授的论据理解有所偏差,或对青柯亭本卓越之处的分析尚不透彻。综上,目前学界就《促织》版本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尚未有确凿定论,该问题有待进一步辨析。
在笔者看来,手稿本与青柯亭本的《促织》均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堪称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手稿本作为蒲松龄的原作理应受到重视与推崇,但青柯亭本“魂化促织”的改动之所以能流传日久,也可反映出其高度的艺术创造力与感染力。应当说,青柯亭本在蒲松龄原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促织》的艺术张力,二者的接力创作铸就了《促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促织》之所以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绝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出于手稿本的故事基础,青柯亭本的改动在文本中只是极少的部分。切不可因推崇青柯亭本的改动而忽视甚至贬抑手稿本原有的情节。更兼《促织》作为语文教科书中的重要篇目之一,无论是在学者的研究中还是在学生的学习中,都应当强调《促织》从手稿本到青柯亭本的情节演变,这是至关重要的。
二、青柯亭本对蒲松龄手稿本的改动评议
蒲松龄手稿本的《促织》作为作者原作,有着深广的艺术内涵,应当得到高度重视。同时,青柯亭本的再创作赋予了《促织》新的艺术感染力,使其广为流传,也是值得肯定的。若说手稿本的《促织》是一座金碧辉煌的高塔,青柯亭本的妙笔改动则为塔中之夜明珠,金塔无之,已然美轮美奂,一朝有之,不但相得益彰,更添明熠光辉。但切不可因贪爱明珠之故,而置灿烂夺目的金塔于不顾。
(一)青柯亭本的改动与手稿本原作的自洽性
1.“魂化促织”与《聊斋志异》一贯艺术构思的一致性
“魂化促织”的情节虽不见于手稿本原作,但却与蒲松龄创作一贯的艺术构思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就《聊斋志异》的其他篇目而言,人物通过幻化变形以完成其正常形态之时难以企及的理想、愿望的情节十分常见,“魂化促织”在艺术构思上与蒲松龄笔下的其他篇目相得益彰。如《叶生》中,文章冠绝当时的叶生最大的人生追求莫过于考场上的功成名就,然偏偏时运不济,他始终“困于名场”,生活的穷困与科举的失意令他愈发颓丧,幸而遇见赏识自己的伯乐丁公,因知遇之恩,叶生化为鬼魂追随自己的知己而去,不仅帮助丁公之子高中,自己也考上了举人,终于不负平生所愿,然他却始终不知自己已死,直到富贵还乡,妻子告知实情,才在惊惧与无限的伤感中“扑地而灭”。这篇故事中,叶生由人化魂可谓是点睛之笔,也是小说最重要的情节之一,而作为困窘书生的叶生恰恰是通过化为灵魂的方式完成了中举的理想。《席方平》中,席方平父亲的仇人羊某死后贿赂阴司,将席父凌虐致死,刚强无惧、铁骨铮铮的席方平得知父亲在阴间受到迫害,意图身赴冥府,为父伸冤,于是他“自此不复言,时坐时立,状类痴,盖魂已离舍”,果然来到了冥府。这里对席方平离魂的描写与青柯亭本中的“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十分相似。
无独有偶,《聊斋志异》中极富传奇色彩的描写爱情的篇章里,也有众多通过人物变形实现理想愿望的情节。《香玉》黄生出于对牡丹花精香玉的爱恋,宁愿死后寄魂香玉身旁,变为一株牡丹永远陪伴在恋人左右。不幸的是,因黄生所变的牡丹不开花,后来被不知内情的小道士砍去,一旁的白牡丹花香玉与耐冬绛雪也相继伤感而亡。《连城》乔生倾心的知己连城因不满父母所订婚约重病而亡,于是乔生也相继悲痛而死,死后的乔生知道自己化为了鬼魂,丝毫不感到伤悲,反而“犹冀一见连城”,期待着见到同样为鬼魂的心上人。二人果然在冥界得到了还阳复生的机会,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黄生与乔生均是自身变形之后实现了作为人类之时不能实现的愿望,得以与心爱的女子厮守。
由此观之,《聊斋志异》中多有靠人物变形实现其愿望的情节,“魂化促织”与蒲松龄一贯的艺术构思是高度吻合的。因此也无怪乎不知情者将这一青柯亭本增设的情节误以为是蒲松龄原作了。
2.青柯亭本的改动与原作具体细节的高度契合
单论《促织》一篇,从文本的前后照应关系来看,青柯亭本“魂化促织”等改动与原作其他细节十分贴合,极具浑然天成之感。其一,成名第二次找到的小促织有个突出的特点,即“短小”,体积远远小于正常的促织,成名甚至因其太小,险些对它弃之不顾(“劣之”),而这恰恰符合这只促织是尚未长成、身量较小的儿童所化的特征。其二,当成名对这只“短小”的促织置之不理之时,它竟然跳到了成名的袖子里(“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这正是化为促织的儿子担心父亲不要自己,慌忙来到父亲身边。怕人原本是促织的天性,但这只小促织却十分亲人,“忽跃落襟袖间”的描写显示了人的特征,细心的读者在读到此处时已然可以猜到这只促织是成名之子所化。其三,这只促织不仅能轻易战胜其他同类,并且与鸡战斗都不会逊色,更神奇的是,它还能随着琴瑟之音跳舞(“应节而舞”),普通的促织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也完全符合它是由人魂化而来的特性。
(二)“魂化促织”对小说思想艺术水平的强化与提升
1.从被动等待到主动自救的姿态转变
青柯亭本“魂化促织”的改动使得《促织》有了情节上的独特性,这也是致使其后来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手稿本中“促织”只是一只上天派来帮助成名的、通了人性的小促织,而纵观古代小说史,上天派神女精灵来救助困厄者的情节比比皆是,从《搜神记》中的仙女助董永,到《聊斋志异》中的《甄后》《翩翩》等篇目无不如此。而青柯亭本中的改动则不然,成名之子之所以“魂化促织”,不是出于上天的旨意,不是由于成名的凄苦感动了天帝,而是由于成名之子内心渴望帮助父亲解决难题的急迫,这种强烈的情感使得懂事孝顺的儿子化为了一只善斗的小促织。困厄者的救赎不再企望于遥不可及的上天,而是出于自身强烈的情感,出于家人之间的拳拳深情。从“天”到“人”,从被动等待到主动自救,这是一个伟大的改变。同时,读者在得知促织乃是成名之子魂化而成之时,所感受到的震惊与伤感无疑强于手稿本原有的情节,如此一来,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又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2.“魂化促织”对小说批判内涵的强化
“魂化促织”的改动增强了小说的批判力度。皇帝所赏玩的蟋蟀乃是其统治的人民所化,这样的情节隐喻着上层统治者对民脂民膏的尽情搜刮,对底层民众的无情压榨,他们的一切享乐之资均源自底层小农的骨血精魂,甚至这种残酷压迫已经波及儿童,这般血淋淋的事实通过“魂化促织”的情节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反观手稿本中的小促织仅仅是成名因为幸运、被上天所眷顾而得到的,其批判内涵则不及青柯亭本“魂化促织”的情节设置深厚。
(三)“亦不复以儿为念”是败笔还是妙笔
手稿本写成名在儿子苏醒后的表现是:“夫妇心稍慰。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青柯亭本将成名在儿子复苏后的表现改为:“夫妇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手稿本此处的描写笔者十分赞赏,写成名看到蟋蟀笼子空空,心知自己很快又要被县官逼迫,但想到儿子刚刚苏醒,不敢向儿子深究此事,这完全合情合理。反观青柯亭本“亦不复以儿为念”的改动反而会令初读者感到成名有些无情,似乎与其迂讷忠厚的性格不符。但如若从另一个角度揣摩,“亦不复以儿为念”其实也是合乎现实逻辑的,同样具有相当的艺术张力。因此笔者认为,青柯亭本的此处改动并未扭曲成名的个性,而是卑渺的小人物在黑暗现实重压面前的无奈之举。
第一,青柯亭本对此处情节的改动仅仅只有一句话,文中悲伤绝望的感情基调丝毫未变。在井里找到儿子的尸体后,成名夫妇悲痛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二人对着墙角呆坐,茅舍里一丝炊烟也无,这是何等的绝望与寒凉,足见儿子的自杀为成名夫妻带来的悲痛之深。好在不幸中的万幸,孩子并没有死,还有气息,半夜间苏醒过来了,这对成名夫妇而言是莫大的安慰(“夫妻心稍慰”),由此可见成名对儿子十分在意,舐犊之情感人至深,并非个性扭曲的冷血人物。这些要害处的描写,青柯亭本丝毫未动。
第二,关于饱受争议的青柯亭本“亦不复以儿为念”的改动,以笔者拙见,此处并非成名在乎促织甚于儿子,因为成名在意的不是一只小促织,而是促织背后的压榨盘剥、黑暗冷酷的墨吏。但明伦在此处评道:“不复以儿女为念,谁实使之然哉?而俨然为之父母者,方且于宴歌之暇,乘醉登堂,严限追比,小民至死将谁诉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耽于享乐、残酷剥削的官僚群体。皇帝喜爱蟋蟀,要求各地上供,于是各级官员便逐层欺压,最终重担便压在了以成名为代表的底层人民肩上,而成名迂讷老实的性格使其愈发畏惧官府。作为父亲,儿子的安危必然是成名极其在意的,但他并非不愿“以儿为念”,并非不愿赶紧请来医者治好孩子,而是不敢,他没有时间了。面对“严限追比”的紧迫情况,此前成名已被官府杖打至鲜血淋漓,甚至“惟思自尽”,此番若是找不到促织,受牵连遭罪的很可能不只是儿子,而将是成名一家人。毕竟儿子虽然“神气痴木”,但至少还活着,这对于成名来说,已经是一个天大的安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他,权衡再三之后发现当务之急便是要找到合适的促织应付官衙,解决燃眉之急,免得其他家人因此受到牵连,这是符合情理的。
由此笔者认为,青柯亭本的改动凸显了社会的黑暗与小说的讽刺批判力度。成名“亦不复以儿为念”虽无情,却无奈而真实。毕飞宇先生在其著作《小说课》中认为“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成名一门心思都在傻儿子身上,故事又发展不下去了”。诚然如此,“亦不复以儿为念”不仅能推动情节继续向前发展,更是“苛政猛于虎”最好的诠释。儿子已然痴傻,但成名却在乎明天能否捉到促织,并非他想去捉,而是如若不去全家便有性命之忧,这处改动可谓写尽了苛政重赋之下百姓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仅不是败笔,甚至可以称之为妙笔。
值得说明的是,三会本在这里选用了手稿本的描写,即“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但却同时选用了青柯亭本“魂化促织”的情节,这样的选择笔者以为不妥。因为“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是成名之子魂化促织的重要铺垫,如若缺少此处描写,后续的情节未免突兀。宁稼雨教授指出,此处青柯亭本“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的文字较手稿本而言更加完整,具体地写出了成名之子昏迷的情状,对于下文的情节衔接与作品主题的把握意义非凡。因此笔者认为,此处三会本应选用青柯亭本的描写为宜。
(四)“魂化促织”与成名富贵结局的内在贯通
鲁凌波在论文中认为成名这一人物形象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的特征,他提到成名得益于儿子“魂化促织”才过上了富贵生活,是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典型,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笔者看来,成名因儿子“魂化促织”而获得富贵结局对于这一人物性格而言没有丝毫影响。
成名在小说中的形象正如结尾处异史氏所言,一直是“长厚者”,而他之所以能过上“楼阁万椽,裘马翩翩”的生活,其一是出于蒲松龄对笔下小人物的眷顾与关怀,是一种“诗性的温情”。小说中成名“操童子业,久不售”,而又“薄产累尽”,科举失意又生活贫窭,这与现实中蒲松龄的生活境遇有一定的相似性。不仅如此,成名还受到贪官污吏的严酷压榨,甚至儿子也因此遭殃,可谓凄苦至极。由此,蒲松龄基于普济众生的博爱之心与某些方面类似的遭际,给予了笔下的成名无限的同情,这与《聊斋志异》其他篇目中神鬼狐魅照拂眷顾命运凄苦的穷书生、小贩、农人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老实的成名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促织而大富大贵,但这份富贵是作者乐意给予他的。
其二,小说中因促织而收获好处的绝不仅成名一人,还有因献促织而使皇帝满意的巡抚、县官等人,成名的富贵是从他们这里获取的。但与皇帝给予众官吏的奖赏相比,官吏们赏给成名的不过是九牛一毛,因此成名获得的富贵恰恰可以折射出这些官吏因促织而获得的嘉奖之丰厚。这些官吏一无政绩二无贡献,唯一擅长之事便是逐级压榨、夤缘趋奉。手稿本中,一只因侥幸而获得的小蟋蟀便解决了成名的燃眉之急;而青柯亭本则不然,面对走投无路的困境与深入骨髓的压榨,成名之子不得不以性命为赌注,魂化促织来令父亲交差,二者相较之下,青柯亭本中的成名父子付出的牺牲何其巨大!下层百姓离魂舍命的牺牲却成为上层官僚献媚邀宠的资本,由此,青柯亭本“魂化促织”的改动进一步突出了小说对现实辛辣尖锐的批判力度。
三、语文教材选编《促织》的状况与建议
《促织》作为语文教科书中必修篇目,需面对广大学生,因此其版本问题也显得尤为重要。就目前课本中的《促织》选版而言,人教版、沪教版选用的是青柯亭本,而统编版、粤教版选用的则是三会本。概而言之,以上几版教科书均采用了“魂化促织”的情节,但在具体文本细节上则有所差异。这客观上反映了教科书编写者对青柯亭本“魂化促织”改动的认可。
以笔者拙见,教科书中的《促织》选用手稿本与青柯亭本皆可,但应当对小说从手稿本到青柯亭本的改动进行清晰地呈现。如若选择青柯亭本,就应当让学生了解手稿本《促织》的原貌,毕竟手稿本中的内容才真正出自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手笔;如若选择手稿本,则亦需告知学生青柯亭本“魂化促织”的另一番面貌。两个版本之间的对比可以通过思考题的方式呈现,如此亦能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表达自己的见解。
结语
综上所述,手稿本与青柯亭本的《促织》均有着非凡的艺术魅力,蒲松龄手稿本《促织》内蕴深广,青柯亭本“魂化促织”“亦不复以儿为念”等改动亦并非败笔,反而将这篇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巅峰,《促织》广泛地流传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在笔者看来,极力地推崇或是贬抑二者中的其一都是不妥当的,因为手稿本与青柯亭本的接续创作方造就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典范之作。同时,《促织》作为语文教科书中的必修篇目,教师在向学生教授之时务必应当体现其间的版本流变,这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