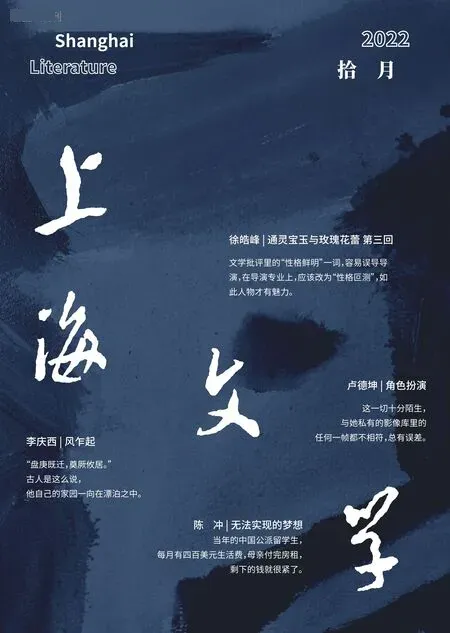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第三回
2022-10-21徐皓峰
徐皓峰
贵族空间
沟口健二的制片厂投资作品,受制于摄影器材笨重、灯光调动不便,空间基本是一个朝向,在一百八十度内解决,如观舞台。
一九四一年公映的《元禄忠臣藏》,军部特批款,耗得起胶片和人工,他的摄影机拐弯了,超出一百八十度的局限。有钱后,表现将军府的奢华,别的导演就在美术置景上花钱了,沟口健二是延长摄影机运动,增加空间层次。
层层叠叠的房屋布局,点缀着急行的侍从,显出是一国首邸。
曹雪芹的时代,电影远未发明,而曹公已有电影思维。写林黛玉进贾府,黛玉的这双眼,如沟口的长镜头般,不留意具体景物的奢华,而是写一层层的空间、一茬茬的下人。当不知道有没有尽头、还要走到哪儿去时,黛玉被一位白发老太太搂住——贾母出场。
贾母没人介绍,搂住黛玉便哭。脂砚斋评为:“千斤之力写此一笔。”——评对了。空间带来的力量。
胡金铨一九七九年公映的《空山灵雨》,表现“古刹名寺”的华丽,也是不在意建筑的材质造型,而是拍空间层次。随着两个贼的行进,空间越来越多,几乎对观众达到催眠效果时,突然观众眼中一醒,一僧现身拦住两贼——贾母的出场方式一般。
两个贼要偷的是镇寺之宝——唐朝高僧的书法。一叠纸,没什么可拍的,显不出贵重。拍接近书法过程的层层空间,空间的恢弘感,让书法贵重了。
贾府的层层空间,改了林黛玉的世界观——空间变了,以后的日子,跟以前的不同了。对于读者,人景双新,贾府是新见,黛玉也是新的,她不是在林家的那个小姑娘了,曹雪芹没交代她的本来性格,读者第一眼看到的她,是一个应变的女孩。
读者以为她敏感计较,之后发现她时不时地豪迈一下,说话幽默、办事痛快——这该是她的本色吧?
但要顺序地写成:一个地方官的大小姐,活泼爽朗,被京都贵族生活震慑,失去底气,变得敏感多疑——交代清楚她原来什么样,进贾府变了样——就是一般写作水平了。
曹雪芹不交代前史,让读者在之后章回发现她有另一面,造成阅读惊诧,猜出她原本个性。这样有趣,读者无法预知她命运了。
性格即命运——知道性格,就知道命运了,因为命运转折时,会按性格来。但她有两个性格,命运转折口,到底是豪迈起作用,还是敏感作祟呢?
无法预知的人物,才是叙事的主角。
性格固定的,是配角。文学批评里的“性格鲜明”一词,容易误导导演,在导演专业上,应该改为“性格叵测”,如此人物才有魅力,情节生出悬念。
希区柯克一九六四年电影《艳贼》,特吕弗喜欢其片段,觉得剧作上有欠缺,跟希区柯克直言。希区柯克强调,这部电影可是赚了钱的!
特吕弗认为男主角是败笔,一心拯救当贼的女主,行为绅士,性格单一。希区柯克说不单一,男主对女主有兽欲和控制欲,特吕弗婉转地说,你只是在选演员时,挑了一张性欲旺盛的脸,一张脸肯定是不够的,还得做情节呀。
希区柯克说,他的原始构思里有,男主兴奋地等待女主新一轮犯罪,不为抓捕归案,为抓把柄,从此可以要挟她。他的追查,起因是为失窃的朋友出头,动力是和一个女贼做爱的遐想。
特吕弗认为太棒了,为什么不拍?希区柯克说美国有审查制度,那种遐想,触犯道德,通不过……是不想在口头上输给特吕弗吧?
所谓的原始构思,可能是对谈时即兴想到的。那种不良遐想,他之前的电影里很多。
特吕弗介绍,希区柯克是一个善于自我批评的导演,但他不在影片刚失败时做自我批评,等他拍出一部大获成功的电影后,他才会跟像我这样的朋友,谈论上一部电影的败因,绝对真诚。
感慨,英国人的口才已经很厉害了,但还是没有法国人会说呀。
将本专栏的名字写成“《红楼梦》中的导演课”,因为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学电影,便听到如下说法:
《红楼梦》是导演手法大全;拍戏拍不动了(没好主意),就查《红楼梦》吧;《红楼梦》本是剧本写法,不需要改编;《安娜·卡列尼娜》(一九八二年版英国剧集)没拍好,拍贵族,还是得按曹雪芹的来,才像样啊——那是俄国贵族,怎么会有这种话?
我只是把当年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电影界声势最大的事件,是北影厂拍了《红楼梦》六部曲,汇集二三代行业高手。耳熏目染,一时间,场工也在聊《红楼梦》。
七十年代末,港台文化传入大陆,代表叛逆与时髦。八十年代初,艺术院校排斥港台文化,认为俗和山寨,转向列侬和《坏血》。宿舍里,不好意思看古龙小说、周润发录像,但可以看金庸,因为有一种说法,其《笑傲江湖》写令狐冲学琴一段文笔,得《红楼梦》真传。
拿《红楼梦》扛事,清朝已开始,《儿女英雄传》便说是文笔得《红楼梦》真传。八十年代中,情色侦探小说《昙花梦》畅销南北,也说是——是,就能看了。
香港导演李翰祥一九七七年拍了戏曲片《金玉良缘红楼梦》后,一九八三年来大陆拍清宫题材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
因为听说是拍过《红楼梦》的导演,格外受尊重。《火烧圆明园》有国人跟洋人战斗到最后一卒的热血场面,学校组织集体观摩。之后的《垂帘听政》可能缺乏教育意义,学校没组织。拍的是京城老事,老人们会掏钱带孙子辈去看。
银幕上,妃子跳舞,皇帝说:“手柔、腿软、身段美!”顾命大臣背后说政敌:“他一翘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两宫后妃平日要干活,趴在大炕上,一边一个地缝被子面,召见大臣,手里的活儿不停,一边舌舔线头一边问话。
太接地气啦!
影片中段,看出是香港导演拍的,来自武打片盛行的地方,出现了“顾命大臣暗中聘用江湖上的四大高手,要在皇帝遗体回京途中,将慈禧劫下来”的情节。
四大高手十分尴尬,皇家回京的队伍人数太多,大部分是军队。他们四个站在山上,傻了。顾命大臣向上望,责怪的眼神,潜台词该是:“还等什么,为什么不冲下来?”
看这架势,导演应该真拍了冲下来打斗的场面,可能后来自己也觉得过分,没剪进成片。成片用画外音来圆这事,说这四人早被慈禧一派收买,所以没冲下来。
皇帝遗体回京,要按照皇帝还活着的礼仪,乐器是摆设,不演奏,抬着走。影片中是按出殡拍的,披麻戴孝,一路哀乐,大把大把地撒纸钱——
李导在香港成名,青少年在北京上学,当年时尚,文艺青年要深入生活,采集俗话俚语。拍此片用上不少,是青春纪念吧?《红楼梦》人物对话是北京腔,有一些下人俚语,那年此片也被称为“得了《红楼梦》真传”。
遍地真传,《红楼梦》太扛事了。
看李翰祥文集,清宫研究文章占大篇幅,他是内行。拍电影,为何不按研究的来?
脂砚斋批语里,有个笑话,一人自称见了皇帝,皇帝左手金元宝、右手银元宝,人参不离口,以缎子当厕纸,掏厕工发了财。
外行的想象,高昂而快乐。或许李导认为,电影毕竟是大众娱乐,内行的知识无效,外行的想象等于票房。
《红楼梦》本是儿童文学
我们这代人,错过了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小时候看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迎来了《猫和老鼠》,六一儿童节,在人民劳动文化宫立多台大电视,循环播放,居委会组织去的,看得我们简直觉得受到人格侮辱。
什么意思呀,真把我们当小孩啦?
很羡慕“八〇后”,能享受各种动画片。我常想,全世界都找不出“七〇后”这么奇怪的小孩了吧?
我们从小把自己当大人,幼儿园高班,已不愿在父母面前装嫩;小学三年级,班干部开会,那种成熟的气场,足可以解决国际纠纷——我们是有病吧?
直到看了北大学者金克木的《书读完了》,才释然,老先生揭示《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十本书,不要认为是博士后看的,汉代算起,两千年来,它们是儿童文学!
要在十岁前学完,一大半书目要能全篇背诵。
两千年不是小数,或许改变了基因。我们的父母是“四〇后”,他们一代才彻底不读这些书,我们是不读的第二代,但遗传的力量,让我们大脑异常,跟全世界儿童拉开距离。
我们对匹诺曹、格林童话不耐烦。四岁时,爷爷奶奶教认字,上小学前,不少孩子能半猜着看《日本帝国的毁灭》、写蒋介石的《金陵春梦》、写军统内幕的《沈醉回忆录》——《红楼梦》也是儿童文学,其中情色场面,大人断定小孩不看,会自动屏蔽,跳过去。
被父母带去别的大人家做客,一般情况,是先奔着书架去,翻几本。得那家大人称赞,父母有面子后,再跟那家小孩玩。
那家孩子的玩具,一般是装电池的塑料火车、铁皮手枪、橡胶士兵、跳棋、拼图、三十多本小人书——蹲在地上合伙玩这些,两个孩子都有耻辱感。
俩孩子,一个掌握蒋介石的隐私,一个掌握日军的死穴,但为了两家大人的交往,要扮幼稚。俩孩子的真正对话是:“你觉得活着有意思吗?”“没意思,但人这辈子,眨眼就过,忍忍吧。”
“七〇后”成年了,彼此试探:“我从小就没觉得自己是小孩。”得到回应:“我的视力、智力长到能识别父母时,觉得他俩才是小孩,我不是。”对上暗号,成为朋友。
《红楼梦》第二回介绍贾宝玉七八岁,第三回介绍林黛玉为六七岁,幼儿园高班或小学一年级。贾母问黛玉读什么书,黛玉回答,刚读完“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读完”的标准,是可以全文背诵。
黛玉六七岁,背下了约五万四千字,这个水平,完胜贾府女孩。黛玉顺口回问,贾府女孩读什么书,贾母答:“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瞎子罢了!”
像是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贾母没这么低端,是没好气,感到别人家孩子灭了自家孩子,一时不快。一时间,她还是把黛玉当成“别人家孩子”,黛玉也听出来了,这恐怕才是她入夜后哭泣的原因吧?
曹雪芹先写贾母一见黛玉就搂着哭,万般的亲,但现实打脸,遇上事,还是本能地疏远。如此贾母形象立体,否则姥姥宠爱外孙女,是人之常情,一味宠爱,贾母和黛玉的关系单一,后面就没戏了。
这份生分如定时炸弹,在全书后半爆炸,黛玉病重,贾母说了狠话,任由她死去。
曹雪芹手法多样,写贾母跟黛玉的“亲”,是热水里窜冷气。写贾母与王熙凤的“亲”,是破坏礼节,越不敬越亲。
好解释,京城里今日还是此风气,多年同学重见面,嘴里没好词,挖苦你现在、揭短你过去,聚的人越多,话越损。
携来的丈夫、夫人有外地人,外地没此风气,旁观会奇怪,问清楚是二十多年没见了,更奇怪:“你们不熟了呀,怎么刚见面就冲着翻脸来呀?”
他们不知,对于北京人,说损话可以弥补二十年鸿沟。脂砚斋也话损,赞美曹雪芹构思巧妙,用词是“狡猾、毒”。
黛玉对王熙凤的第一印象是“放诞无礼”,贾母介绍王熙凤是“泼皮破落户”,骂人的话——无赖、卑贱,王熙凤不怒反喜。
凤姐初登场,有亮点,不出彩。等她谋财害命时,才大放异彩。此处不出彩,为一般人情,因为彩要留给贾宝玉出场。
凤姐亮相后,贾母要黛玉去两位舅舅住所拜见。大舅贾赦、二舅贾政,黛玉都没见着。
写其居住环境,就是写其人。电影尤其如此,一个人的居所造型就是他的内心实况。贾赦不正经,居所不是正式房屋,隔下片花园,改装了游园歇息、冬日养花养金鱼的十几间房。
贾赦的夫人为邢夫人,她接待黛玉,叫下人去书房请贾赦。明清习俗,书房是男人的独立空间,下人能进去打扫卫生,夫人是不能进的。
贾赦不出来,叫下人传话,怕见了黛玉,想起黛玉过世的母亲,徒增伤感,让黛玉不要生分,把这里当家,有需要就直说。
话是情深义重,往后看,发现贾赦不是情深义重的人,他就是懒得理黛玉,不知在书房玩什么呢。他不出来,完全在邢夫人计划外,邢夫人很没面子,不顾黛玉还要去二舅处拜见,苦留黛玉吃晚饭。
黛玉明白这是邢夫人一时情急,绝不能在这儿吃,给邢夫人台阶下,说下次。邢夫人急过后,恢复理智,见黛玉懂事,松口气,要真留下,不去二舅那儿拜访,倒不好办了。邢夫人把黛玉送出仪门外,等黛玉的车走远了,才回门。
照理,长辈送晚辈,不用出门,止步在门槛内。小辈的车一动,离了门,长辈就可以回屋了。车远了,还站门口遥送,对贵客才这样。
对黛玉行大礼,是邢夫人心中有愧,觉得对不起这小孩。
此处未写一笔心理活动,纯外观写法,很是电影剧本。剧本的写作思维是“外在等于内在”。居所的异状,是此人本质;出格的行为,就是心情。
二舅贾政人正经,住得也正经,皇帝赐的匾、祖辈国公级享用的款式,在他这儿。贾政和儿子贾宝玉都不在家……两舅舅都见不着,即便理解大人们有事忙,而在六七岁的小女孩心里,又重了一份生分。
晚饭,是在贾母处。贾宝玉从小住在贾母房里,白日去庙里还愿,回来吃晚饭,见了黛玉,发狂把自己的佩玉给砸了。
此玉是出生时带来,叼在嘴里。迷信地看,是跟他性命同体,玉毁则人亡,急坏了贾母。饭后,贾母安排黛玉和宝玉都跟自己同住,房大,他俩分睡两隔间。
入夜后,黛玉一直哭。宝玉的婢女袭人来安慰,黛玉说自己来第一天,就让宝玉摔玉,自己成了个不吉利的人,怎么住得下去?
黛玉没说假话,但也不是真心底牌。小姐对丫鬟会交心,不会彻底交心,尤其来的第一天。袭人会劝人,说宝玉的混蛋事多了,没人惹,也发狂,你别往自己身上揽责。为让她停哭,袭人说起佩玉的种种神奇,以转移她注意力,还要拿过来看。
袭人是“拿个新鲜玩意儿哄小孩”的做法,黛玉是囚禁在儿童躯壳里的老灵魂,对玉不感兴趣,更不愿被当小孩哄,说明日吧。黛玉的眼泪,跟宝玉摔玉无关,是因贾母语言不当。
回述一下摔玉过程:
宝玉见黛玉,问她读什么书。被贾母甩过一次臭脸,黛玉再不敢说能背五万四千字了,说不识几个字。
借冷子兴、黛玉母亲、王夫人、贾母之口,反复交代贾宝玉“是不读书的”,真人出场,宝玉却向黛玉拽起书袋,说起《古今人物通考》。读者惊诧,他竟是读书的!
电影剧作的常规技巧:之前介绍的信息和之后的现实,要截然相反,以形成悬念——在评书技巧里,叫“蔫包袱”。
“响包袱”是笑料,听众不耐烦要走,艺人甩出个笑料,哄堂大笑后,又能多坐一刻钟。“蔫包袱”是一个明显的前后不一致,听众警觉“不对呀”,又能多坐一刻钟。蔫,指全场突然安静了一下,听众费心,都在想。
贾宝玉出生时口里衔的玉,串上绳,挂脖上当佩玉。贾宝玉问林黛玉,你出生时有没有玉?黛玉说没有,贾宝玉一下发狂,佩玉扯下,砸地上。
因为兄弟姊妹出生都没玉,贾宝玉因此觉得这玉不是好东西,应该人人都有,人人平等——这是贾宝玉的艺术家天性使然。艺术,要突破人生原有设定。生来的独特、受到的独宠,让贾宝玉不耐烦,摔玉,是他潜意识要打破这份狭隘。
贾母为劝宝玉,编了个瞎话,说黛玉也是衔玉出生,黛玉妈妈过世前,舍不得女儿,要求拿玉当陪葬,等于女儿陪着自己,黛玉尽孝心,把玉给了母亲。
宝玉听到自己不是“独一份”,心里平衡,不闹了。此处蹊跷,说到黛玉和她母亲,竟然没写黛玉的反应——这是个“蔫包袱”,读者会起疑。
之后安排住宿、调度下人,一直不写黛玉,经过好大一场,直到夜深,才重写黛玉——失眠,流泪不止。
妙笔。
为何伤心?肯定不是应付袭人的那番话。曹雪芹没详写,留白处理,因为他觉得读者的生活经验够,足以看出来。
“七〇后”能看出来,“八〇后”或许能看出来——“〇〇后”“一〇后”就看不来了吧?不可思议,脂砚斋也没看出来,认为贾母编排黛玉母亲那番话没问题,哄孩子就这样,还发表感慨,从“小儿易哄”引申到“君子可欺以其方”,说成年人也好骗,只要用对方法——
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没的可说,还要硬说,凑出批语就是胜利。真不敢相信他是曹雪芹的朋友。
上世纪七十年代,幼儿园体系没完全恢复,“七〇后”大多是寄养在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是生于一九一〇年代的人,清朝刚完,老理都在。耳闻目染,我们这拨孩子多少还知道些老理。
初读《红楼梦》,震惊于贾母言论,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老太太不是善茬”。贾母名为贵妇,看来却出身不高,养成了霸道习气。霸道,为处理急事,可以违规僭礼。
为哄宝玉不闹,贾母糟践自己刚过世的女儿,拿来编瞎话。死者为大,按理是不能拿来说事的。况且黛玉就在跟前,当着黛玉,编排她妈,还是辞世场景。可想黛玉的震撼,对这位外祖母,她是怕了。
后面,不管这位外祖母再怎么安排、多体贴照顾,她都哑然无声。直到夜深人静,方哭泣。
总结一下,黛玉伤心处:
白日里,王熙凤对黛玉好感,主动帮忙,说不像贾母的外孙女,像是嫡亲孙女,欢声笑语中,抹平亲疏。贾母也乐得其说,但一见黛玉才学盖过三个亲孙女,立刻怒了,毫不掩饰。外孙女和亲孙女区别大了。
两个舅舅,对自己不以为然,竟然懒得见。白日有事,起码晚上在贾母处吃饭,可以来看一眼吧?也都没有。
看来两位兄长对亡妹情义不深,父亲林如海在贾家地位不高。林家已用完了世袭,退出贵族圈,毕竟低人一等。
要仰仗的外祖母,品质粗鲁,对亡女的感情没有想象的深,并不可靠。表面是受尽照顾,其实陷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境地,难怪黛玉要哭。
金克木先生介绍,写国君、贵族争斗的《左传》,都是儿童文学。《红楼梦》当然在儿童的阅读能力里。中华儿童的阅读能力,也太强了吧?
金克木先生解释,就是这么强,古典书籍是有意为儿童写的,甚至成人思维难理解的,换成儿童思维便能看懂。
京城老习俗,是四岁懂事——可以教字和人情世故。我们这代人四岁,被教育“不要议论别人的父母,尤其不要提别人过世的父母”。
四岁孩子,已能看懂黛玉心思。《红楼梦》里写黛玉入贾府,入门进法、上炕坐法、用餐吃法、告辞走法,都可当范本,教育儿童。
我的小学,十岁读《红楼梦》的同学,大约五位。一班总计四十人,比例高,男生没有,都是女生。上初中,是考学,同学换了一拨人。语文课本有《红楼梦》选段,为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老师解释“葫芦”二字,为“糊涂”的意思。有女生抗议,说“葫芦”指“阴阳”,意思是“阴阳师乱判阴阳案”。生为阳间,死为阴间,此回书有“给亡灵录口供”的事,葫芦解释为阴阳,似乎也对。
女生自称五岁开始读《红楼梦》,老师表扬了她,之后明显话少,糊里糊涂了结课程。
宝玉原不能娶黛玉
京城老理,小孩四岁懂事,除了识字与世故,还要知道人伦。人伦,就是男孩要知道从小一块长的哪个女孩能娶,女孩要知道哪个男孩能嫁。
京城人家,过年过节走亲戚,往往是二十几个小孩一起玩。新加入个男孩,女孩们不动声色,上前询问你妈和我妈是什么关系、你爸怎么称呼我爸,很快分析出是不是做丈夫的人选。
不是早恋,是必备的生活常识——表亲可婚配,亲上加亲,堂兄妹不能嫁娶。小孩从小要择清楚,交往上好有分寸。
林黛玉称贾宝玉为“表哥”,民国的小说电影里,“表哥”一词等于情郎。一九八九年公映的影片《古今大战秦俑情》,有民国拍电影的场面,两个明星演情侣,“表哥、表妹”地叫。
由爷爷奶奶带大的“七〇后”,四岁时要明白“堂、表”。好不容易才择清楚,小学、初中回到父母身边,发现白忙了,父母告诉,新社会的婚姻法高度完善,表亲也不能结婚了。
一番幻灭,原来都不行。唉,被爷爷奶奶误导。
父亲一支的亲人称为“堂”,母亲一支的亲人称为“表”。林黛玉称贾宝玉为表哥,因为是妈妈这支的亲戚,宝玉父亲和黛玉妈妈是兄妹。
但婚配关系,不从女孩计算,以男孩为准。在宝玉的角度,黛玉不是他的表妹,黛玉是他父亲这支的亲戚,是堂妹。
堂兄妹不能婚配。
这点,两个小孩都知道。宝玉和黛玉只是语言亲近,身体上忌讳,绝不接触。有学者说两人“两小无猜,从小搂着睡觉”,那是看第三回不仔细。
黛玉和宝玉是“紧挨着”睡觉,一个里间一个外间。把里外间“紧挨着”,理解成了“一张床上搂着”。细看第三回,两人各自床榻旁,各有同龄丫鬟、成年女佣守着,人多眼杂,搂不上。
宝玉日后四处风流,但绝不碰黛玉,从小的禁忌。他情不自禁,碰过宝钗胳膊,宝玉的母亲跟宝钗的母亲是姐妹,宝钗是“正确”的表姐,可娶。
宝玉碰宝钗胳膊,碰一下即收手,从此不再碰。因为宝钗是正妻人选,对于正妻,婚前要规矩。
宝玉放浪,止步于钗黛前,她俩是他的禁地。
《教父2》里丰富的人际关系,拍《教父3》时,制片人不让延续。导演没招了,攒出“堂兄妹孽恋”的戏份。意大利人跟华人一样,也是大家族聚居,小辈分男女密集,容易出事。教父的女儿爱上了教父哥哥的儿子。
违背人伦的狠料,不打磨,等于废料。讲故事,跟说事不同,说事是说清楚性质和结果,讲故事不能一步到位,要切出多个层次。脂砚斋批语里有段是不错的,说写作的关键,是“留墨”,不要在一处写尽,要留着墨水,别处再写。
《教父3》的堂兄妹孽恋,如下:
堂妹爱堂兄,唯一理由是“小时候就喜欢你”,主动找堂兄,堂兄就跟她好上了。堂兄怎么这样?为了在观众理解上,堂兄的行为能成立,导演表现他一贯风流,堂妹来了,惯性使然。
心有顾忌,自我警告“绝不能做”,最终失控,还是做了——是乱伦戏的写法。俩人都没心没肺、百无禁忌,剧本就写死了,情节上难以为续。
但导演是科波拉,观众赞叹,不愧是大导,敢把剧本写死,必有翻盘大招。
没招。教父发现后,要侄子离开女儿。侄子不以为然,教父作交换:“离开我女儿,我的教父位子给你。”侄子爽快答应。
好上和停,决心都下得太快,都是一步到位。不“留墨”,观众会来不及认同这对男女,会认为侄子白得了堂妹,还拿堂妹换老大,又白得了老大,买空卖空,真不是汉子。导演也知道这样不行,为弥补,让一个黑帮老大评说:“噢,我知道了,你俩是爱情!”
女儿的角色不能只是好上和被喊停,还得有点作为,但编剧没想出事件,只能让她演情绪。女儿跟教父发火:“你为什么不支持我和堂哥?”又对侄子发火:“你为什么不理我?”
加戏,只为填充女儿戏份,导演没给教父和侄子写词,让他俩凝视不答。对他俩的凝视,观众会读解成:“姑娘,你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不知道你在乱伦吗?”
唉,剧本写崩了,怀念一九七〇年代的科波拉。该怎么写《教父3》?看黛玉和宝玉吧,能找到那些欠缺的戏。
贾雨村——宝玉日后的白手套
《红楼梦》第四回,先写黛玉入住第一晚后,次日清晨拜见李纨——宝玉的寡嫂。宝玉有位哥哥,十四岁中秀才,二十岁病死,留下孤儿寡母。写李纨,为了解释宝玉为何受骄纵——贾府刚失去最优秀的继承人,刺激大,生怕宝玉也夭折。
但这句话,曹雪芹永远不会直接写出来。小说技巧,不能直接写因果。要把因果,转化为情况。
黛玉拜见李纨,看了个情况。李纨是个被她父亲耽误的人,李家原是文化世家,女孩都读书,到了李纨父亲这一辈,信奉起“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李纨读书,只让识字。
读书的标准,是从读“四书”开始,进入文史哲群书。“四书”之前,学《百家姓》《千字文》,叫识字。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写农村孩子上学,一般是识字,看懂账本、契约就行,但随着乡间诉讼日多,要进一步读书。因为讼书除了引用法律条款外,还要引用“四书”里的名言。县官都是读书人,讼书写得有文采,容易赢。
多花学费,为了省诉讼费。请讼师的费用高,自己孩子能写讼书,打官司成本降低一大块。
写李纨,为了交代宝玉的特殊地位。如仅此而已,一人一用,便不是曹雪芹了。笔锋一偏,批判起“女子无才便是德”。李纨不读书,丈夫一死,她就没事了,寂寞度日,成了无用之人。
笔锋又一偏,给日后宝黛交往落下伏笔。文中交代,黛玉和三位“亲孙女”(贾府女孩)一起读书,由李纨这位大嫂陪着。由李纨陪伴,无是非,也无趣。黛玉是才女,李纨拘不住,三个亲孙女又跟她差太远,才华使然,她必要一遍遍地找宝玉。
交代完黛玉,重提贾雨村,写他已在应天府就任。他重开仕途,没费一分钱,由贾家全盘办理。贾家为何助人为乐?
清朝贵族的后代们,讲旧日辉煌,自称一年做的事中,九成是白做,不求回报。今人难以想象,说一成、三成,还好理解,说九成,就过分了。“十件事里,九件是为别人,一件为自己。”都这么说。
不敢信,您家怎么维持?能算清账吗?
近年来,好莱坞狂出书,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数据,原来好莱坞百分之九十四左右的电影在影院里是赔钱的,以卖DVD、卖电视播放权来回本。但赚的是大赚,好莱坞靠百分之六左右的片子盈利,百分之九十四左右不赚钱的片子也有用,用来维持这个行业。
好莱坞肯定能算清楚账。
信了京城老话。
《教父1》中,老教父一天到晚忙,大部分是给别人白做事,强调不收费、不要回报,这不是买卖,你我之间是朋友——跟林如海、贾政一样,他俩跟贾雨村强调,咱们之间不玩官场上那套,帮你是读书人之间的道义,看你有才华,我不帮你,对不起我读的这些书。
看晚清的官场记录,大量贪污腐败案之外,还有许多清白仗义的事,曾国藩、徐世昌都是意外得助,白来便宜,起的家。
帮人,只能是无偿付出,不求回报。因为求也求不来,时过境迁,别人有没有能力回报?没法预计,也就没法布局,只能相信概率。贵族帮人是常年操作,千人中一人能回报,其实就够了,像好莱坞只靠百分之六左右的电影赚钱。
教父帮忙,跟被帮者说:“或许有一天,可能那一天永远不会来,我将需要你帮个忙。”——林如海、贾政也是这个意思,但面对贾雨村,永远不会把这句说出来,说出来就失去文雅了,这便是贵族与黑帮的不同。
这句话,要贾雨村自己悟。
贾雨村重上官场,贾府不会指导他,也要让他自己悟,像种树,种下了就不管了,看你能长成什么样。成大才,可大用,当贾府的盟友,如肃顺提拔曾国藩、荣禄提拔徐世昌,这种是咱们文化里最好的一面,仗义清白。
中才,当白手套,干脏事、当替罪羊。是文化的阴面,不能持久,干完一二件脏事后,立刻当替罪羊,早点结束。脏事不能一个人干,这人结束后,别人顶上。盟友难得,一二人足矣;白手套得一堆,脏了就换。
小才,就不用了,反而会带来麻烦,最初帮他,当白做好事了。
从后面的章节看,贾府对贾雨村,是照着盟友来培养的,可惜他没经过测试,不堪大用,只能做白手套。但他这个白手套有些特殊,贾政自己不用,是留给宝玉长大后用的。
贾政会安排贾雨村跟贾宝玉几年见一面,以确立主从关系,但不会直说,要说成“宝玉向贾雨村学习”。这种做法,香港商战电视剧继承下来,老板儿子成年了,拜访公司元老,说:“叔,我爸让我跟您学习。”意思是,以后你听我的。
贾雨村的第一个测试,当官后,逢上一桩杀人案:
本地冯公子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个女子,没想到人贩子同时卖给本地豪族薛公子。两家争那女子,冯公子被打死。薛公子带女子去了京城。
这是一年前的事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贾雨村正义感爆棚,要发通缉令。一个门子(衙门内差人)使眼色阻止。雨村引门子回后堂问话,门子自报身份,原来是旧相识。
旧时寺庙,为学子提供食宿、图书馆、读书间的服务,无偿或低价。贾雨村落魄时期,只能住庙,因而跟庙旁邻居甄士隐结识。这位门子是庙中和尚,还俗当了差人。
几年前,贾雨村第一次当官,不会当,被罢免。对他的不会,曹雪芹用了“恃才侮上”一词,仗着自己能解决棘手问题,而要挟上司。
不知贾雨村当年是如何恃才侮上的,通过门子便可看到。门子第一句话便语带嘲讽:“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贾雨村真想不起来,谁能想到和尚当差,相貌服装都不对了,怎么识别。
门子不依不饶,更加嘲讽:“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得当年葫芦庙里之事?”
贾雨村住庙,是依靠庙里住持,跟小和尚们不会过多来往。而门子是势利小人,当初雨村是个穷书生,门子应该也懒得理他。两人几乎是生人,而门子以老熟人自居,没有一点人情温暖,反而以知道雨村旧日落魄状况而自鸣得意。
项羽得天下,要“衣锦还乡”,兵败自杀,因“无颜见江东父老”,可想而知,家乡的人情温暖,是他这辈子最嗨的东西。因为他是楚国贵族,从小受乡人尊重。
不是贵族,则是“英雄最怕老邻居”,穷小子在外面成功了,回家乡会遭嫉恨嘲笑,不会觉得你“真不容易”,会觉得你当年不如他,凭什么你后来成功了?以笑话你种种不堪往事,来找平衡。
贾雨村经过被罢官的历练,懂得了小心,显得热情,不顾上下级关系,对这个不是朋友的人,以朋友相待,请他落座。
此处细节精彩。门子却不敢了,可见两人当年没有一点交情,之前语气不恭的重话是试探,门子自己也心虚。在雨村一再请求下,门子落座,偏着身子,坐一半椅子面,表示恭顺。
雨村询问,门子详说案子。
同一个事,曹雪芹写了两遍,在手把手地教怎么做电影剧情大纲。之前的案情介绍,是事件,这一遍是讲故事。两相对比,多出来的是要点,没这些,成不了剧本。
冯公子争女,被打死。确实冤,但观众不会同情,因为毕竟是买卖妇女,你只是在争货。做大纲,要改变事件的性质,让此女对冯公子有特殊意义,不再是“货物”。
曹雪芹下笔狠,竟然写冯公子本是同性恋,一见此女,被掰直了,发誓余生只和此女好。极度浪漫下,要给女子一份体面,表示不是买卖,按照迎娶标准,将人贩子家当女孩娘家,要择好日子再来接。
情节不能光是外部事件的硬转,要从心理变过去,新生情节要和人物心愿相反,如此才会让观众愕叹。
导演总要求编剧“有力”。有力,不是事件大,而是观众反应大。大事多了,而观众往往无感。事与愿违,才能有力。
冯公子的伟大爱情,事与愿违,人贩子没感动,反而起了贪心,利用不来接的三天,将女子二次出售,卖给了薛公子。人贩子拿两份钱,是准备携款逃到外省,不料两家都得了消息,给堵住痛打。
两家都不要钱只要人。薛公子没有伟大的爱情,一是贪美色,二是霸道惯了,“敢跟我争?”的心态下,让仆人将冯公子打死,掳了女子上京城,赢了这事。
——故事做到这份上,还不够拍电影,欠这女子的心态。门子讲述,被冯公子重视,女子反应是“我今日罪孽可满了”。一句千斤,从小被拐卖、被殴打,找不到起因,只能认为是自己的罪孽。可怜之人觉得自己可恨,罪有应得,是写可怜写到极点。
得知冯公子犯了浪漫病,非要找好日子来接,她立刻转忧。等待的三日,成了戏眼,最能让观众动情。
冯公子被打死,她是什么表现?一般编剧会写成哭天抹泪,曹雪芹留白,写她“不知死活”。不写,是最大的悲伤。
兵法里有“走为上计”,写故事,也是能逃就逃,观众预料到的,就不写了,观众自己会无限放大。
这故事讲的,也有瑕疵——门子是所有的信息来源,他一人亲历的太多。此女为贾雨村恩人甄士隐丢失的女儿,是门子认出来的;人贩子来应天府,租房子租在了门子家旁边。
都太巧了。
当然,是旧小说一惯作法,介绍背景事件,往往让一个人把什么都说了,以节省笔墨。今日看,粗糙了,面对这样的大纲,导演会让编剧给稀释一下。他是门子,了解案情是本职工作。他说的,不需要亲历。
甄士隐女儿丢时才五岁,时隔七八年,能被门子认出,真是奇迹。小孩生长,面目差别大,多少孩子都长裂了(走样了),亲妈认丢失的孩子都难认出。门子能认出,是一个牵强的理由,因为甄女眉间有一颗痣。
这颗痣影响后世,多少影视剧写“时隔多年”都是这招。一角色的少年、青年,或青年、晚年,生理变化是硬指标,一个演员没法完成,得换演员出演。为观众好识别,便点上一颗痣,简直泛滥成灾。
一九九三年电影《叛逆大师刘海粟的故事》,写刘海粟年轻时的一个人体模特,晚年和刘海粟在黄山上相见,换成老年演员出演,对刘海粟莞尔一笑。导演想煽情,而观众只看到一颗耀眼大痣。
用痣、胎记、疤,都是越描越黑。此时,编剧要会“逃笔”,不要写是门子认出来的,写人贩子招供,偷的是甄家孩子就行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就不要圆了,简单处理最好。
抢走甄女的薛公子,其母亲跟贾政的夫人是姐妹。贾雨村向甄士隐报恩,要秉公执法,夺回甄女,给薛公子判刑;向贾政报恩,则要给薛公子脱罪,任由他霸占甄女,是徇私枉法。
门子的建议是,徇情枉法。因为秉公执法没用,薛贾两家有能力推翻结果,惹怒了他们,你就当不成官了。
贾雨村的反应是“低了半日头”。初中时看此文,觉得他陷入人神交战,对得起良心还是保住仕途?中年后再看,认为他想的是:好呀,终于知道什么是“恃才侮上”了。第一次当官时,我真太蠢了。
门子在帮贾雨村做决定,这也是当年贾雨村对他上司干的事。低头,不是沉思,是心绪复杂,不想让门子看到自己表情。
等抬头,已想好,这门子留在身边,一定生祸,要及早除去,放逐到远方。想好后,索性大度,请教门子办法。
门子目的,是企图当师爷,成为贾雨村离不开的智囊,于是尽情展露才华,说出全盘谋略:
先下发通缉令,捉捕薛蟠。再让薛家谎报薛蟠已死,请巫师做法,请冯渊鬼魂显灵,说是自己索命。最后判决薛家赔偿冯家些钱,便可了断此事。
贾雨村的反应是——笑道:“不妥不妥。”初中读此文,觉得贾雨村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用了门子的计谋,还不说好。后来,认为贾雨村是真的被门子逗笑。
黑泽明一九五〇年的名作《罗生门》里,也有给亡灵录口供、作为断案证据的事。但那是日本,日本没有科举,没有中国的文官制度。贾雨村是进士,为文明的代表,不能玩怪力乱神,他要请巫师进衙门,就贻笑大方了。
贾雨村的笑,是更加确定门子不能用,见识如此低,谋略形同儿戏,却妄想给我当智囊,实在可笑。
贾雨村如何修正的门子方案?曹雪芹未写怎么圆,贾雨村肯定比门子高明。但只要企图帮忙圆,就不高明了。案子了结后,贾雨村给贾政、王子腾分别写信表功,语言节制,不过是说“令外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几句。
节制成这样,也多了。王子腾是京营节度使,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里王家的代表,薛蟠的母亲、宝玉的母亲是他的两个妹妹。对于贾政、王子腾来说,杀人者薛蟠是他俩的外甥。
案子能了结,薛蟠母亲、宝玉母亲高兴,贾政收到贾雨村来信,则会这样想:“这么会办脏事?可惜了。”于是不再管贾雨村,让他追随王子腾,干脏事去了。
贾雨村该依法查案,让贾政、王子腾自己想办法保护薛蟠,双方不要有任何沟通。不管贾政、王子腾有没有圆过来,他都不要帮着圆。
不会出现“得罪权贵,自身难保”的情况,贾政更不会觉得“培养了个白眼狼”,这是门子级别的想法。到贾政这级别,见贾雨村秉公执法,反而会欣喜。毕竟,他培养贾雨村,是想找个支持贾家的外援,不是为了给傻外甥平事的。
荣禄提拔徐世昌,徐世昌是不给荣禄办脏事的。曾国藩不碰脏事,让同事胡林翼和弟弟曾国荃碰。《红楼梦》后半,写贾政到外省做官,严格自律,绝不附和地方官场习气,结果办事困难,受同事排挤,最终被上司诬告,结束地方官生涯,回到京城。
他在京城做官老练周到,能不知道地方官场的习气?地方上要真有他想做的事,一定入乡随俗地办成。但他不想在地方上有作为,于是处处高风亮节。地方上失败,赢在京城。有了优良操行,就可以担大事承大责了。
受地方官上司诬告,被皇帝降职,都是暂时现象,是必要的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