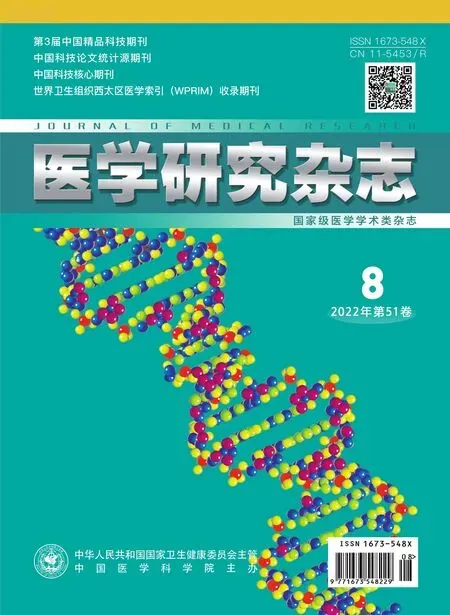结直肠癌微环境的免疫抑制机制及相关治疗研究进展
2022-10-19崔婧雯李袁飞
崔婧雯 李袁飞
大量研究表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强烈依赖于其所处的周围局部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而免疫监视及免疫逃逸系统在微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逃避免疫系统的杀伤,肿瘤细胞会招募免疫抑制性细胞、分泌免疫抑制性因子、激活有关信号通路等重塑并形成免疫抑制的微环境,来促进自身生长、增殖、侵袭和转移,并对免疫疗法和其他抗肿瘤治疗产生耐药性。另有研究表明,肠道中微生物群落也与一些免疫反应有关,在TME免疫调控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探讨了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各种机制,并总结了目前靶向结直肠癌肿瘤免疫微环境(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TIME)的治疗方法,指出了靶向TIME在结直肠癌治疗中的意义、潜力和可行性。
一、免疫抑制性细胞浸润
在CRC发生、发展过程中,多种免疫抑制性细胞在肿瘤细胞分泌的生长因子、趋化因子、细胞因子的作用下被招募到TME中,主要有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骨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调节性T细胞(T regulatory cells,Treg)、调节性B细胞(B regulatory cells,Breg)等。TAM是CRC中检测到的最丰富的细胞类型,分为M1型和M2型。M1型(抑癌型)具有促炎特性,通过激活核因子-κB通路在宿主对肿瘤细胞的免疫防御反应中至关重要;而M2型(促癌型)具有抗炎特性,主要分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0、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等介导辅助性T细胞(T helper cell,Th)2型免疫反应,抑制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细胞)迁移,以及上调转录因子叉头盒蛋白P3(transcription factor forkhead box P3,FOXP3)的表达促进Treg的分化,一般来说TAM更接近于M2型,因此制定策略将M2型逆转为M1型可以提高抗肿瘤免疫反应能力。MDSC是一类具有异质性的骨髓来源细胞群,在TME中它们成熟受阻,停留在各个分化阶段,分为多核MDSC和单核MDSC,后者可以进一步分化为TAM。MDSC抑制T淋巴细胞免疫的机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MDSC会下调T淋巴细胞受体αβ链的表达、调节T细胞G/G细胞周期、增加Fas配体(Fas ligand,FasL)的表达抑制T淋巴细胞增殖,促进T淋巴细胞凋亡。
Treg是一类维持外周耐受性和限制炎性反应的T淋巴细胞亚群,其特征是高表达CD25(即IL-2受体α链)和FOXP3。Treg在大多数癌症中与肿瘤生长和不良预后相关,但是在CRC中的预后价值一直有争议。研究发现,在CRC中,Treg根据FOXP3的表达水平可以分为两种亚群,即FOXP3(hi)抑制型和FOXP3(lo)非抑制型,FOXP3(lo)Treg不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并分泌炎性细胞因子,与FOXP3(hi)Treg比较,伴大量FOXP3(lo)Treg浸润的CRC的患者预后更好。研究表明,免疫共刺激分子OX40可以直接抑制FOXP3的表达来直接影响Treg的分化,因此它可能是Treg的一个治疗靶点。
肿瘤相关肥大细胞(tumor-associated mast cells,TAMC)是近年来发现在CRC中另一种与不良预后相关的免疫抑制细胞。研究发现,结直肠癌中TAMC和Treg在TME中共定位并且两者相互作用可以触发免疫抑制。在人类CRC和小鼠息肉病中TAMC诱导Treg下调IL-10、上调IL-17,来促进自身脱颗粒释放抗炎性细胞因子抑制T淋巴细胞反应,促进肿瘤进展,因而靶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有助于控制CRC。与Treg类似,近年来有研究发现,B淋巴细胞也可在微环境中获得免疫抑制表型,分化为Breg细胞。它可以通过表达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分泌IL-10、IL-35、TGF-β等参与免疫耐受的发展与维持。但是需要更多的研究鉴定其表面特异性标志物以及明确调控它们分化的机制。
二、免疫抑制性信号通路的激活
CRC细胞会发生许多信号通路分子基因突变。与良性腺瘤和正常组织比较,TGF-β在CRC中表达明显增加,尤其在免疫不活跃的共识分子亚型的间充质型,可以观察到明显的TGF-β/Smad信号通路的激活。研究表明,TGF-β/Smad在CRC中可以调节T淋巴细胞、NK细胞、TAM、B淋巴细胞、先天淋巴样细胞、DC等许多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细胞的功能来帮助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小鼠模型中,药理抑制TGF-β信号可以产生比阻断免疫检查点更快速而持久的Th1免疫反应,并有效阻断肿瘤转移定植。
IL-6/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通路是CRC炎症相关过程的信号通路,其过度活化会下调免疫诱导因子干扰素(interferon,IFN)、IL-12、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的表达,上调免疫抑制因子IL-6、IL-10、TGF-β、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达。Hidemitsu等研究表明,IL-6/STAT3通路也可下调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的表达损伤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的抗原递呈功能,用IL-6受体抑制剂体外阻断IL-6可以恢复DC的功能。针对IL-6/STAT3通路的治疗目前最有效的是STAT3抑制剂BBI608,其联合化疗的Ⅰb/Ⅱ期的控制率达83%,目前正在进行Ⅲ期(NCT03522649)以及联合ICI的临床试验(NCT03647839)。此外,Wnt/β-连环蛋白(β-catenin)通路和Ras/Raf/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EK)/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ERK)通路的异常激活也与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有关,是免疫治疗的一大阻碍。
三、免疫抑制性代谢的增强
在TME中为了满足对营养和能量的要求,CRC在内的大多数癌细胞会经历代谢重编程,包括有氧糖酵解增加(即Warburg效应)、谷氨酰胺“酵解”、脂质和蛋白质合成增加等。这些代谢改变不仅会剥夺对T淋巴细胞和NK细胞增殖和功能发挥重要作用的营养物质,而且产生的代谢产物也会影响TME中的免疫反应。在体外培养基中,有氧糖酵解产生的细胞外高乳酸会降低细胞内PH诱导NK细胞凋亡,抑制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增殖并损伤其产生IFN-γ的能力。
一些氨基酸分解代谢水平的增高是TIME的一个标志,微环境中的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 amine 2,3-double oxygenase,IDO)、精氨酸酶会分解大量色氨酸、精氨酸,这些氨基酸的代谢会阻断CD8T细胞的激活,并诱导CD4T细胞向Treg分化。另外,在CRCTME缺氧、缺血、炎症条件下,细胞表面酶CD39和CD73活性增高,ATP大量水解,同时腺苷脱氢酶与腺苷激酶活性降低,导致腺苷无法及时分解代谢大量聚集在TME中。一项对人类结肠癌标本的原位微透析分析表明,CRC胞外腺苷浓度比正常组织增加了20倍。高腺苷浓度的长期存在会通过A、A腺苷受体(adenosine receptor,AR)的介导调节T细胞免疫,触发并维持免疫抑制效应。
研究证明靶向代谢物、酶或者相关转运受体可以抑制免疫抑制性代谢,如糖酵解抑制剂(1,2-脱氧葡萄糖)、IDO抑制剂(epacadostat)、谷氨酰胺分解抑制剂(CB-839)、CD73拮抗剂(BMS-986179)、AAR拮抗剂(CPI-444)等。CB-839是一种谷氨酰胺酶抑制剂,其与西妥昔单抗在耐药的CRC细胞模型中显示有效,说明CRC患者可能受益于这种靶向肿瘤生存所需“燃料”和信号通路的联合治疗。近年来研究发现,免疫检查点会影响TME中肿瘤细胞与T淋巴细胞之间的代谢竞争,因此ICI联合代谢抑制剂可能也有协同抗肿瘤效果。
四、新生血管异常
肿瘤血管是肿瘤营养输送及肿瘤细胞转移的通道,肿瘤血管密度是影响包括CRC在内的众多恶性肿瘤临床预后的重要因素。其中VEGF在调控血管生成中起主要作用,也是主要的免疫抑制因子。临床前数据表明,靶向VEGF(如贝伐珠单抗)可以减少肿瘤部位的Treg、MDSC,增加效应T细胞(effector T cell,Teff)的浸润,并同时增加PD-1等免疫检查点的表达,这为血管生成抑制剂联合ICI提供了理论基础。
靶向血管生成素(angiopoietin,Ang)-2是另一种血管抑制策略。Ang-2由内皮细胞产生,作用于酪氨酸激酶受体Tie-2参与血管重构,并促进VEGF的血管生成作用。与VEGF不同,Ang-2/Tie-2对T淋巴细胞没有直接影响,但它可以刺激TAM M2的极化和分泌IL-10,诱导Treg扩增间接抑制T淋巴细胞。目前Ang-2抑制剂AMG386(Trebananib)已进入临床试验。另外肿瘤相关内皮细胞(tumor-associated endothelial cells,TEC)也参与了微环境免疫重塑。此外缺氧会激活缺氧诱导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在TGF-β共同存在的情况下,HIF-1可直接与CD4T细胞的FOXP3启动子区域结合,上调FOXP3的表达,诱导Treg的形成。因此TEC或者HIF-1可能是未来CRC的抗血管治疗靶点。
五、免疫抑制性基质
1.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tumo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CAF是CRC间质中数量最丰富的异质性细胞群体。CAF是TGF-β的主要来源,CAF分泌大量的胶原蛋白、牵连蛋白沉积形成瘢痕组织,作为物理屏障阻碍T淋巴细胞、NK细胞浸润肿瘤。另外CAF可以分泌大量的趋化因子,尤其是基质细胞衍生因子(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SDF)-1,其唯一受体是C-X-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4(C-X-C motif chemokine receptor 4,CXCR4)。在临床前模型中抑制SDF-1/CXCR4轴可以观察到肿瘤中大量T淋巴细胞浸润,逆转免疫抑制。
2.结直肠癌干细胞(colorectal cancer stem cells,CCSC):CCSC是一群具有自我更新、多能分化和强致癌性的一小群细胞,近年来它被证明拥有强大的免疫调节能力。其可以通过抑制DC和NK细胞的增殖和激活来对抗宿主对转化肿瘤细胞早期免疫反应,并抑制细胞因子产生之后Teff的活化和增殖。在体外培养基中,用IFN-γ、TNF-β预处理CCSC会使其具有更强的免疫抑制作用,诱导更大肿瘤的形成。针对CCSC的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淋巴细胞、双特异性抗体(solitomab)等免疫靶向治疗已经被开发出来。另外一些特有的信号通路和表观遗传调控因子与CCSC的干性密切相关,它们可能是未来的治疗方向。
3.外泌体:外泌体是细胞分泌的直径为50~150nm的脂质双分子层囊泡,作为细胞间通讯分子可以调节TME中的免疫反应,其富含多种免疫活性物质,如FasL、PD-L1、IL-10、TGF-β、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等。由于外泌体具有低免疫原性和细胞毒性、靶向性强、生物相容性高的特点,作为纳米载体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考虑利用它进行抗肿瘤药物传递。
六、宿主相关因素-肠道微生物
作为人体的“第二基因组”,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在CR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近年来研究表明,它们也可作为免疫和代谢调节剂影响机体抗癌免疫反应。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产肠毒素型脆弱拟杆菌(Eeterotoxigenic-bacteroides fragilis)和其释放的细胞死亡毒素、脆弱芽胞杆菌毒素通过激活Toll样受体和NOD样受体,增加IL-6、TGF-β的产生,诱导Th17细胞和Treg的产生。并且Fn表面的Fad2蛋白可与NK细胞和T淋巴细胞上的T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域蛋白(T cell immunoreceptor with Ig and ITIM domains,TIGIT)的结合诱导免疫细胞耗竭。而一些保护性的细菌,双歧杆菌可以下调DC激活T淋巴细胞的阈值,使较少的抗原也能产生T淋巴细胞免疫应答。
海氏肠球菌(Enterococcus hirae)可以增加肿瘤中记忆T细胞的数量。被称为抗癌界的“明星细菌”——嗜黏蛋白艾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Akk菌),是一种药物敏感型患者中大量存在的有抗肿瘤效果的有益菌,其可通过腺苷-AAR途径促进Th1细胞的分化,并且可通过IL-12促进Teff杀伤肿瘤细胞,改善免疫应答反应,增强ICI的疗效。Tanoue等在小鼠结直肠癌移植模型中鉴定出11组与PD-1单抗治疗效果有关的菌株,并且这些小鼠免疫相关结肠炎的发生率也降低。因此一些肠道微生物群不仅可以促进免疫治疗的疗效,还可减少免疫不良事件的发生。粪便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在既往ICI治疗失败的黑色素瘤的Ⅰ期试验中得到了初步证实,目前正在验证是否也可以用于CRC。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肠道菌群与结直肠癌TIME的关系,它们可以作为抗癌治疗的突破口,克服免疫治疗耐药,成为未来抗肿瘤治疗的一部分。
七、展 望
本文综合讨论了CRC微环境中几种主要的免疫抑制调控机制并指出了潜在的治疗靶点。由于CRC微环境的复杂性我们对癌细胞免疫逃逸机制的认识仍有限,需要更多的试验研究和临床证据。并且在未来可以将多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来探索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协同的关系。鉴于所有的免疫疗法和大多数传统的抗癌方法都依赖于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反应,靶向CRC的TIME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治疗手段,无论是单独或联合其他抗肿瘤治疗,都有可能在未来造福结直肠癌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