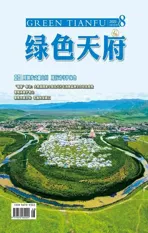成都新物种背后的浪漫故事
2022-10-14蒋珂李家堂王跃招巫嘉伟
○文/ 蒋珂 李家堂 王跃招 巫嘉伟

青年刘承钊,刚获得博士学位

钊琴湍蛙
国际著名动物学研究期刊《Zoological Research(动物学研究)》刊登了由中国科学院李家堂研究员团队和专委会秘书处等共同发表的中国西部湍蛙属一个新物种,命名为钊琴湍蛙Amolops chaochin Jiang,Ren,Lyu,and Li,2021。
“湍蛙”,顾名思义,是一类擅长生活在湍急流水环境里的蛙类。而“钊琴”二字,则取自中国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刘承钊和胡淑琴的姓名最后一字。为何要用两位的名字合并命名?源自背后浪漫的故事。
87年前,也就是1934年。青年动物学家刘承钊先生刚从美国康乃尔大学荣获博士学位,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时局动荡中的祖国,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发展做贡献。
很快,刘先生回到中国,并进入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任教。刘先生对两栖爬行动物由衷喜爱,教学之余,他就在住地附近观察两栖爬行动物,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
就在那几年,他认识了在东吴大学读书的胡淑琴同学。胡同学十分仰慕先生学识,同样也关注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毕业后,胡同学选择了留校任教,并与刘先生喜结连理。从此,世界上有了这么一对共同追求动物学研究事业的模范伴侣。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日军入侵上海,相距不远的东吴大学被迫由苏州迁往浙江湖州。

▲1935年9月,刘承钊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观察乌龟产卵和孵化的记录

▲1937年,刘承钊等迁至浙江湖州时,在碧浪湖畔采集标本。后排左一为刘承钊,后排右二为胡淑琴

▲华西医学院内刘承钊的铜像,位于图书馆旁

▲华西医学院内刘承钊和胡淑琴的故居
1个月后,日军再度逼近,学校被迫关闭。在刘承钊先生的带领下,生物系18位学生和包括胡淑琴在内的4位教师于当年11月15日,星夜启程西迁。他们途径芜湖、汉口、重庆等地,用尽一切办法,尝尽各种艰辛,历时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在1938年1月27日抵达成都。随后,刘先生一行在成都主城区华西坝的华西协和大学(也就是现今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复课。
复课半年后,刘承钊先生开始筹备野外考察工作。仅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的野外考察就有13次之多。这些工作在交通便利、社会稳定的今天看来,似乎并不难,但在当年,实属不易。那时,中国西南山地区域的交通条件还欠发达,野外工作非常艰苦。然而,刘先生却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梦想——能在中国西部山区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特别是在自然环境下研究其生活史。
当时研究经费极为缺乏,刘先生常用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工资,充当野外考察经费。作为妻子的胡淑琴教授,一方面要照顾家庭并兼顾大学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还作为刘先生的助手参与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
感恩于妻子无私地付出,刘先生于1950年在《华西两栖类》一书中,用夫人的名字命名一个新物种,胫腺蛙Rana shuchinae,种加词“shuchin”正是胡淑琴的英文名,“ae”是以女性人名的语法后缀。在科学界看来,用一个人名字来命名一个新物种,是对这个人最崇高的敬意。刘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我以我妻子的名字来命名这个蛙类物种,以纪念她对我研究工作一如既往的帮助(I name this frog after my wife in recollection of her faithful aid throughout my studies)”。

▲1940年刘承钊等在峨眉山采集的钊琴湍蛙雌雄抱对标本,历时80年,如今仍完好地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

▲1973年,刘承钊在查阅蛙类标本

▲刘承钊(左二)和胡淑琴(居中)及子女,摄于1960年左右

▲刘承钊与胡淑琴位于青城山的墓地
刘承钊教授于1955年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并在2021年荣获“四川省百年百杰科学家”称号。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胡淑琴教授的辛勤付出。
到青藏高原考察,是刘先生的毕生心愿。1973年,受国家委托,他负责组织了青藏高原综合科考两栖爬行动物分队,由于年事已高,他未能如愿参与野外考察。
3年以后,先生带着这份遗憾离开人世。14年后,胡淑琴教授主持出版了中国著名的两栖爬行动物学专著——《西藏两栖爬行动物》,以此告慰刘承钊先生的在天之灵。
1992年,胡淑琴教授离世。为纪念两位科学家,其骨灰一部分撒在他们1938年到达成都后,第一次开展野外科考的目的地——峨眉山;剩下的则合葬青城山,供后人瞻仰。
说回湍蛙。中国西南山地环境中最不缺的,就是星罗棋布的溪流,这些地方正是湍蛙生存和演化的理想栖息地。1938年8月,刘承钊先生在峨眉山采到一种湍蛙,这些蛙类个体和刘先生的朋友、美国著名动物学家C. H. Pope在1929年,依据福建武夷山的标本命名的崇安湍蛙如出一辙。没想到,在遥远的四川峨眉山被再次发现。
随后,刘先生在峨眉山开展了大量的实地研究,于1941年发表了关于峨眉山崇安湍蛙的生活史研究论文。此后数十年里,除了福建和四川,崇安湍蛙在我国安徽、重庆、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江西、陕西、云南和浙江等多省被记录到。
近些年来,随着分子系统学研究的发展,不同科研团队发现我们所认知的“崇安湍蛙”,存在明显的遗传分化,是包含着多个隐存物种的复合种。
自2019年以来,随着成都市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调查的不断深入,调查团队在成都市西侧的崇州、大邑等地采到了疑似崇安湍蛙的标本,通过与中山大学合作,进一步获得了可供比对的武夷山地模标本,也就是可以拿真正的崇安湍蛙和成都的标本进行对比,确定两者是否是同一个物种。
结合分子系统学和形态学数据研究成果,我们惊喜地发现,刘先生当年所观察过的“崇安湍蛙”,包括四川成都市(崇州、大邑等)、乐山(峨眉)、雅安(天全)、绵阳(安县)以及甘肃(文县)、贵州(毕节)等地分布的种群,其实是一个未被人类描述的新物种!

▲湍蛙属部分物种的分子系统树,其中红色竖线标注的为新种钊琴湍蛙所在支系

▲1965年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和标本馆成立后,由胡淑琴担任首任主任,指导学生们开展研究,队伍逐渐壮大并延续至今
基于刘承钊先生对“崇安湍蛙”长达2年的持续研究,结合他的野外笔记和相关论文,感动于他和胡淑琴教授携手追求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我们决定,用两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这个新种,并取他们英文名字Ch'eng-Chao Liu和Shu-Chin Hu的最后一个词“chao”和“chin”,合并为钊琴湍蛙Amolops chaochin。以这样科学表达方式,让二位再次携手同框。
迄今为止,中国记录有515种两栖动物,成都就有33种。钊琴湍蛙的科学命名,也提示我们,一些被认为广泛分布的物种,特别是迁移扩散能力较弱的两栖类动物,很可能有地理隔离造成的遗传分化,并存在隐存种,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现和研究。
今天,刘承钊和胡淑琴两位前辈所建立的研究团队依然活跃在国内外学术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所采集的科学标本,仍完好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与这些标本一起贡献于科学研究的馆藏标本数量已接近12万号。可以说,两位先辈付出终生的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随着国家的发展强盛和科学家们的持续努力,正在发扬光大!
作为钊琴湍蛙的模式产地,中国的超大城市——成都,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很高的区域,这里不仅有着潜在的未知物种等待我们探索研究,还仍然维系着数量众多的已知物种的良好生存发展。我们用近几年的调查监测数据结果,对比上世纪40年代,也就是80年来的研究记录来看,以成都作为模式产地的钊琴湍蛙种群数量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
即便是在喧闹繁华的主城区,公园城市内的多个湿地公园,甚至规模更小的社区湿地仍能让两栖动物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较好地繁衍生息。譬如,我们在锦城湖公园里,就发现了至少5种成都本土的两栖动物,包括泽陆蛙Fejervarya multistriata、黑斑蛙Pelophylax nigromaculatus、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饰纹姬蛙Microhyla fissipes和四川狭口蛙Kaloula rugifera。有些地方,夏天的日子里,依旧是“听取蛙声一片”。
希望两栖动物多样性能成为成都立足中国生物多样性之林的一张王牌,更成为城市幸福美好的一张绿色名片。
(图片来源:蒋珂、任金龙、陈广磊供图,部分图片引自文献)

▲成都市崇州鸡冠山的钊琴湍蛙生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