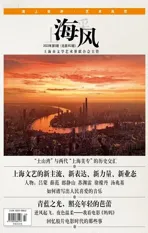薛范:我性格倔强,决不后退
2022-10-11金波
金 波

薛范先生病逝的噩耗传来,我一连几天沉浸于哀痛和他的歌声之中。他坐在轮椅上、躺在病榻上,一次次充满激情地回首往事的话语;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分,仍心牵歌曲译配、音乐演出的痴情……在我眼前闪烁,催我泪下……
“薛范只是个符号”,感谢文联
对自己的译配生涯,薛范先生曾以“只重耕耘,不问收获”概括。近十几年来,当相继获得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上海翻译家协会“特别贡献奖”、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时,他冷静又动情地谈起“收获”。
一次,聊到薛老唯一一次访俄,他撇开话题,滔滔不绝。薛老把这次访俄视为自己长期致力于中俄友谊的一部分。接着话锋一转: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上海获奖者中,草婴翻译小说,任溶溶翻译儿童文学,王智量翻译诗歌;像我搞歌曲翻译,报中国译协终身成就评奖,从未有过。上海市文联、上海翻译家协会考虑到我的翻译在俄罗斯的影响,及其对中俄文化交流、中俄友谊的促进,所以促成我忝列其中。
说歌曲翻译是小儿科,这不仅是薛范先生的自嘲,也多少反映了此项艺术再创作活动以前的地位。薛范先生进一步“论证”:音乐学院有门音乐学科,研究作曲、音乐理论、音乐史、歌剧、交响乐、配器,歌曲算什么?下里巴人!同样,翻译家里,草婴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冯春翻译普希金,翻译歌曲也是小儿科。翻译歌曲是音乐界的小儿科,也是翻译界的小儿科。
薛范先生一再表示,是上海市文联抬举我!
1997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在北京亲手为薛范颁发象征最高国家荣誉的“友谊勋章”及荣誉证书。这枚友谊勋章的分量,薛范先生明白:以前,中国翻译家获得的是高尔基勋章、普希金奖章,而且属于纪念奖章,有哪位获得过这样的友谊功勋章?“颁给我俄中友谊勋章时,没提我翻译歌曲,而是‘为增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理解,作出了杰出贡献’ 。”
薛范先生访俄期间,又被授予“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金质奖章,俄罗斯媒体盛赞他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市文联艺术促进中心、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承办的祝贺薛范翻译生涯60年音乐会,2013年10月30日在上海音乐厅举行
相当部分读者、听众或观众,长期阅读文学翻译作品、欣赏吟唱外国歌曲,却往往叫不出译者名字。对这有趣的现象,薛范在1950年代就感同身受。他幽默道:“吃鸡蛋,谁会关注哪只母鸡生的?”直到1994年,北京相隔三四十年后第一次举行俄罗斯歌曲音乐会,进入花甲之年的薛范引起轰动。音乐会结束后,不少观众眼含热泪向他问好,有的甚至失声抽泣。薛老出乎意料,“我还这么有名气?”
类似的场景经历多了,薛老从享受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青春的记忆,青春的信仰,俄罗斯情结。他借用一句歌词自我调侃:千万别相信哥,哥只是个传说,薛范只是个符号。
遭遇挫折不放弃,自解心结
薛老耿直爽快,语言犀利,个性十分鲜明。多年前,初次与他接触,耳闻他与别人谈话时来了句:“请关注我,而不是我的轮椅。”不禁暗自思忖:这位老先生恐怕不易打交道。以后的交往证明,我的闪念无疑是假象。
犀利,在于他历经磨难的旅程,在于他深刻的思考,在于他的快人快语。
薛老讨厌刨根问底式的采访、程式化的报道:“现在写残疾人的奋斗,都是一个模式。自卑,经过别人鼓励,学习保尔·柯察金,然后振作向上。如张海迪、吴运铎。作为残疾人,我不要看这类报道,千篇一律。文艺作品里都是成功者,还有没成功的呢?多得是。我成功了,正好遇到那个时代。如果是现在,我就不一定会成功,别人会问你什么学历、大学,外文怎么学的……”
我故意将他一军:那是您这颗“种子”好,1950年代也有不少奋斗的残疾人,“薛范”不也没几个?
薛老沉默片刻,又斩钉截铁:“性格决定命运。我性格倔强,充满进取心。有的人一次次受挫,放弃了,我决不后退!我相信命运,不信上帝。”
我不禁又回味起珍藏脑海的那个片段。一次,与薛老、禾青老师等准备在外用餐。饭店门口,台阶挡道,旁边的专用道高低不平。薛老没有下车让我们搀扶或背进门。只见他驾驭着电动轮椅车,缓缓上了专用道。发力、上坡,接近饭店门口时,车晃了晃,旋即马翻人仰。没等众人回过神上前相助,薛老已手拉着车翻身而起。我的感受用震撼表达毫不为过。
学生时期的一场音乐会,让薛老“开了窍”。片段终了,我对薛老感叹:那次您驾车冲上斜坡,我对您的了解也“开了窍”。像您这样的年龄,谁敢?车倒了,您爬起来,神色不变。
薛老道出了对音乐的热爱促使他成功之外的另一“奥秘”:“因为我不知道命运之神究竟对我怎么安排。假如我命中注定要成为翻译家,那我外文也不用学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机会等待有准备的大脑。机会就是命运,抓住了机会,就可能改变命运。我努力,也有失败的心理准备,不会遭受失败而垂头丧气,因为这也在意料之中。我与别人不一样吧。”

薛范在家中写稿
“一些写我的文章,都集中在我怎么翻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采访的人第一次听我说,而我真正的粉丝却问我:薛老师,怎么这么多人写来写去、翻来覆去就是这些内容?”解析了性格与命运,薛老“回旋”到诙谐。
薛老本名闻声远。1953年《上海广播》7月号发表的他第一首翻译歌曲《和平战士之歌》,译词与配歌分别署的是闻声远、汪靖英。两三年后,他编辑或译配的一系列作品集,均以“薛范”的署名呈现于读者。
闻声远与薛范,是他以20岁为分水岭的两座人生里程碑。前者多的是艰难、苦闷,后者涵盖了他事业的起飞、辉煌。
考取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结果因为体检时医生没做特别注明,学校把他当身体健全的考生录取。残酷的现实却是因为下肢残疾,报到这天他被学校拒收。“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考不取是我没本事,可我考取了……”回到家,他两天没吃一口饭。
1956年,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更名上海外国语大学。很多年后,上外请薛范去讲课,他旧事重提:几十年前我考取了你们学校,可学校拒绝我入学,我现在反而作为客座教授来讲课……
我们如果认为薛范不无得意、出了口气,那未免武断,因为薛老当时的前言后语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明白无误的是,薛老被拒收的心结,直到后来才由他解开。
一天,他收看一档电视节目。屏幕上,有位教育家在谈中国教育,认为中国大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是在证明早已被别人证明的知识。就像做选择题,A、B、C、D,都有标准答案。你必须符合标准答案。薛老心有灵犀,听了顿时心平气和。
他豁然开朗:我没有读大学,我高中毕业后获得的所有知识,都是靠自学,没人给我标准答案。自学让我善于思考,这是我的长处!为什么有的人学了没长进,因为不动脑筋。老师怎么说他就怎么学,不思考。我自学中国古典文学,各位教授在书本上的注解不一样,我在书店里查到的注解又不同。到底谁对、谁正确,必须自己判断。一时无法判断的,则会放在心里,经常思考。
薛老又引申到同样没有老师的歌曲翻译。歌曲翻译与小说、散文翻译有什么区别呢?要靠自己摸索。比如押韵,什么韵脚好,“我一生都在摸索”。他自学音乐,学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作曲、和声学。外国歌谱没有简谱,都是五线谱,五线谱不识怎么翻译?都靠看书自学。“那时除了吃饭睡觉,都扑在学习上,天天泡上海图书馆。弄一杯水、一只面包馒头,早出晚归。”
当年上海图书馆在黄陂北路南京路口,薛范家住黄陂南路,虽然在常人眼中距离不远,但对靠手摇轮椅车和拐杖行进的他,是“这么长一段路”。薛范天天在图书馆,研究中国历史,看《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可不能外借。“我能取得些成绩,靠的是勤奋自学、思考。读者读了《别了我的文学梦》,一定不会想到,我这个翻译家学习范围这么广泛。”
先天严重残疾的约翰·库缇斯,靠奋斗成为轮椅橄榄球运动员、室内板球健将、澳大利亚残疾人乒乓球冠军,他还是国际著名的演讲大师。这位无腿超人在向听众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时发问:“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残疾!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残疾!有的人的残疾看得见,有的人的残疾看不见!你的残疾在哪里?”
我们敬佩薛老,因为他让我们羞愧地看到了自己的残疾。
只要歌声不消失,薛范不逝
每位文学翻译家,都是饱尝辛劳的创作者。薛范先生一生译配各国歌曲约2000首,其中的艰辛,他人更难体会。
薛老的《歌曲翻译的探索与实践》,2002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收入《薛范60年音乐文论选》。这是他几十年来在音乐学、翻译领域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建树。《薛范60年音乐文论选》出版前,薛范对我坦言:“我的《音乐文论选》虽然可能学术价值不高,但具有开创性。”“别人看不懂,也没兴趣看,将来卖不掉。外国歌曲翻译、研究后继无人。”

20世纪50-90年代薛范编译出版的部分外国歌曲集
薛老译配反复推敲、精雕细琢,如何求得译词既不失原意,又与曲相般相配,他称只能意会,“说不清楚”。他也会举些简单的例子佐证:比如《没人要的孩子》,歌词原文“没有妈妈的亲吻,没有爸爸的笑”这句,被薛老处理为“没有爸爸的抚爱,没有妈妈的吻。”他解释:本来很普通的句子,翻译很简单,也押韵,为什么要换呢?因为音乐在起作用。
“当然,有些话可以说得很清楚。如我常说:歌曲翻译首先姓音,音乐的音,其次姓文,而诗歌翻译姓文。翻译诗歌,要根据原诗怎么押韵、有多少节奏等,但到了译配就不行。译配还有个音,所以难就难在这。”国内有位翻译家曾提出,莫斯科夏天夜短,《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里“长夜”应该翻译成“傍晚”或“夜晚”。薛老一脸无奈:“我与他争论什么呢?他很有名,但不知道歌曲翻译还有个音。”
上海翻译家协会多次提出要举行薛范作品研讨会,薛老都谢绝了:开研讨会,大家来捧场,影响怎么大之类,你从理论上怎么研讨?翻译家吴钧陶认为薛老的翻译随意性比较大,即创作的成分比较多。薛老对此回应:吴钧陶懂音乐,也翻译过歌曲,这是内行话。但吴钧陶是从诗歌翻译的角度来理解的,他不太了解我为了“唱”。薛老认为,现在网上翻译歌曲者很多,但译得好的很少。
为了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领会外国优秀歌曲的魅力,特别是俄苏歌曲的家国情怀、英雄主义豪气、理想主义色彩,并从中了解什么是“译”和“配”,薛老应邀到学校、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讲解。耄耋之年,病弱之躯,他对音乐的痴迷一如既往,令人惊叹。
今年8月4日上午,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查明建受协会委托向薛范先生颁发“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魏育青也专程来到薛范先生家中祝贺,并带去上海市文联夏煜静书记的关心、问候。颁奖程序结束,薛老又兴致勃勃地对大家侃起草婴、吴钧陶、翻译与译配,探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与夜晚。
8月11日,上海音乐出版社领导费维耀、孙宏达等前往薛老家中看望。当时薛老状态不太好,躺着,脸色苍白,在即将离家住院前数小时,获得了此生最后一项荣誉称号——“上海音乐出版社终身成就翻译家”。
薛老曾对我说起一段艺术家的佳话。
在电影《甲午风云》中饰李鸿章的王秋颖,患肝癌临终前想最后见见“邓世昌”李默然。李默然中断工作,赶往医院。王秋颖仍昏迷着,病房外,医生、护士不准李默然进去。李默然央求、争辩。突然,只听王秋颖喝问:“谁在二堂喧哗?”李默然分开医生、护士,推门而入,单腿跪地,低头道:“回大人,属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李默然回忆这片段,泪流不止。薛老看了也泪流满面:“他俩对艺术的痴情、对艺术的忠诚、对艺术的追求都表现在这一刻。我的一生也是这样,我不是翻译匠,我一生痴心艺术、追求艺术、忠诚艺术。我们年轻时都把保尔·柯察金的话当座右铭: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人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回想往事,我对得起这两句话!”
薛老是在长长的睡梦中远行的。9月1日,经医生特许,家人、沈文忠副主席等赶到医院探望,他已沉睡了一天多。之前几天,薛老通过微信与粉丝相约:如果我能活着回家,我们再办场音乐会……
“将来我死了,我翻译的歌如果人们还在唱,那我就活在他们心中,我满足了。”录音器里,传来薛老的声音。
著名翻译家冯春告慰薛老:“您的音乐会长存在人们的心中!”
只要歌声还在回荡,薛老与歌迷同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毛时安的评价和追忆,引起广泛共鸣:薛范先生在中国的文学界,在中国的音乐界,在中国的翻译界,是一个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存在。他用他的歌曲翻译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文学艺术爱好者。
“我深深地感激他。在我人生最灰暗痛苦的时候,是他翻译的世界名曲拯救了我的灵魂。”毛时安在18岁到28岁的十年间,经常伫立于鞍山新村家里的阳台上,“一次次在月光下偷偷地唱他翻译的歌曲……他身残志坚,从不向命运屈服低头。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是一个文化上的‘英雄’。”
1994年,薛范先生60周岁,恰逢上海作协举行成立40周年庆典。毛时安把轮椅车上的薛范推上舞台,与赵长天、赵丽宏等一群作家一起,围着薛范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场1000多个作家把掌声献给他,他那么安静地坐在我们中间。今天他告别了我们,告别了他深深眷恋的时代、祖国和人民,但是他翻译的那些人类最优美的歌曲,将永远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