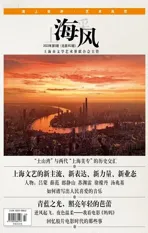《我和我的同学们》的编剧
2022-10-11陆寿钧
陆寿钧

电影《我和我的同学们》获奖后,谢友纯和吴贻弓、彭小莲两位导演合影
上影在1986年拍过一部名为《我和我的同学们》的影片。
关于剧情,《上海电影志》作了如下介绍:“高一(4)班的布兰对体育活动从不关心,一些男同学故意捉弄她,选她为体育课代表。她上任后,决心抓好班里的篮球队,保持冠军称号。一次比赛中,因主力周京舟参加市里比赛,班级球队败阵。她难过地提出辞职。后来,在全校冠亚军决赛前,周京舟因与她意见不合,赌气宣布退出球队。决赛进行到关键时刻,班上另一名主力队员摔倒受伤,布兰心急如焚。此时,周京舟毅然重返赛场,最后终以一分之差险胜,球队再次夺得了冠军。不久,周京舟随父母迁居大连,布兰和同学们依依不舍,到码头送行……”
从这简单的介绍中,我们也可看出,这是一部朴实自然的影片,《上海电影志》对其作了如下评价:“影片生动地反映了当代中学生的生活,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中学生群像。”拍摄此片的导演彭小莲、摄影刘利华等主创人员,当时都是首次独立拍片的新人,此片却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1987年优秀影片奖,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少年儿童片奖,第二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儿童少年故事片奖、导演奖、摄影奖。而其编剧谢友纯在电影志中却没有一行字的介绍。
谢友纯是我们上影文学部的老编辑,他1960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分配到当时的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了,要比我早进天马厂三年。我是在1970年代末才转行到上影文学部当编辑与他同事的,从干编辑这一行来说,他的资历要比我深20年,该是我的老师辈了。我和他以及后来成为他爱人的杨兰如,同住在天马厂的集体宿舍内好几年。他来自安徽农村,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杨兰如来自江苏启东,我的老家在上海的郊县,彼此都属“乡下人”,尽管性格各异,却由于处世的态度大致相同,所以一直平等友好地相处着,他们把我当成小弟,我把他们看作大哥大姐。他们成家于“文革”中,都已年过三十岁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兰如大姐心直口快,友纯兄却显得比较沉闷。到电影厂来转行从事导演的兰如大姐又肩负着组织的期望,来“掺沙子”改造电影厂的。我到现在还都不明白,她是如何会爱上出身不好的友纯兄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她爱对了,友纯兄一辈子都忠于他的事业和家庭。不知怎的,我在友纯兄编剧的《我和我的同学们》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布兰身上,似乎看到了兰如姐中学时代的影子。他们家庭的和睦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儿子鸣晓在如今电影面临多种挑战的境况下还能接连不断在执导电影,都是值得他们欣慰和自豪的。这些,可都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作为资深老编辑,“文革”后,友纯兄一直在上影文学部负责上海地区的编辑组工作,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组的组长周泱是他在天马厂文学部的老同事,相互熟悉,工作起来方便;二是兰如大姐经常要下摄制组出外景,他要照顾还在上学的儿子,就不能再出去组稿了。而我所在的编辑组负责西南地区的组稿工作,一年中常有半年时间要去外地组稿,所以,我们虽成了文学部的同事,交往却反比以前少了。我如今都不清楚有关他编辑业绩的情况,包括如何写出《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个好剧本的。只是一直为他高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也能与大家一样,放开一搏了!可他的处世仍然是随遇而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哪怕在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后,仍然安于默默无闻。说真的,连我都无法为他写下点什么。直至他逝世后,我才想起该为他留下点什么……
2016年1月30日中午,友纯兄在家里招待家乡客人吃中饭时,突发脑部大出血,瞬间就走完了他80岁的生命之程。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生命常会如此脆弱。兰如大姐谢绝了上影退管会为他开追悼会的提议,只通知他生前的一些亲朋好友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我也在被通知之列。我得此噩耗,大吃一惊,我们同住一楼,常在电梯中见面,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在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他的几位特意从北京、安徽赶来的侄子、侄女。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因谢家出身不好,在1949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内,连遭家难,而谢友纯总是向他们伸出援手,助他们上学上进,为此在这年关“春运”紧张的时刻,他们也要想尽办法赶来为叔叔送行。我也见到了他的几位现在上海生活、工作的老乡、老同学,他们向我回忆了谢友纯在求学时代的一些事,他因出身不好,上中学、大学,都要比一般的学生花出几倍的努力,还要靠侥幸才能实现。上影老文学部的同事被通知去的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我,另一位是85岁的老编剧黄进捷,老编辑马小浩因病而让他夫人来了。其他的都是谢友纯儿子、中生代知名导演谢鸣晓的好朋友,其中有黄蜀芹的儿子郑大圣。大圣告诉我,他一知道谢伯伯在医院抢救,忙冲去医院,可已经晚了。还有现为华山医院领导的鸣晓高中的同学,他也尽了力,但死神早就抢在了前面。可见鸣晓的这些“发小”都是够朋友的!上影的退管会来了两位同志,代表单位来表示悼念和慰问,因家属谢绝开追悼会,所以也没有带来单位的悼词。

谢友纯和刘琼南下深圳组稿时合影
在告别仪式上,司仪让家属致辞,鸣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代表家属讲了简单的几句话,却催人泪下。他说,他年少时,一直难以理解父亲的低调为人处世,长大后才开始明白。在父亲去世后,他查了网上有关父亲的资料,只是一些“碎片”,现在父亲走了,唯一能与这个世界上还有联系的是上海电影博物馆中展出的电影《我和我的同学们》的一张剧照。然而,父亲生前一直感恩上海这座大城市能接纳他……
作为回应,85岁的老编剧黄进捷在送行时,哭着对谢友纯的遗体高声说道:我从部队复员进上影文学部后,李天济是我第一位老师,教我写喜剧电影。你是我第二位老师,为我的剧本做责编,精心扶植成了我的几个电影剧本,只有我知道,你为我花出过多少的心血……
作为回应,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没有一个在告别过后就离去的,一直把他的灵柩送上了灵车,目送着他离开殡仪馆去火化升天……这是我所参加过的追悼会、告别会中首次所见。
于是,我早就冲动得一定要为友纯兄写下点什么,留下点什么。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远不止“上海电影博物馆中展出的电影《我和我的同学们》的一张剧照”。
我们电影厂文学部从事剧本编辑这一行的人,从来都明白自己是在“为他人作嫁衣”,所以扶植成功一个剧本了,“做成一件嫁衣”了,常不再把它放在心里、挂在嘴上。我连自己为哪些影片做过编辑都说不清楚,更不要说友纯兄的编辑业绩了。他比我更看得明白,生前不留下任何有关材料,所以,鸣晓在父亲去世后,查了网上有关父亲的资料,只是一些“碎片”,连《上海电影志》在记载上海每年出产的故事影片时,也只有编剧、导演、制片、摄影、美术、录音、作曲和主要演员的名录,而从未提及编辑。鸣晓哪能查得到有关他父亲的材料呢?好在比友纯兄大五岁的黄进捷有良心,在他送别谢友纯时,哭喊着说出了“你是我的第二位老师,为我做责编,精心扶植成了我的几个电影剧本,只有我知道,你为我花出了多大的心血……”
黄进捷从部队复员到我们文学部后,起先是当干事,但他聪明好学,喜爱喜剧,又善于与人相处,在拜喜剧大师李天济为师后,在他退休前的那些年里,竟连续创作了《好事多磨》《取长补短》《大丈夫的私房钱》《阿福哥的桃花运》四个喜剧剧本,拍成电影后,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都相当不差。我也是黄进捷在友纯兄的追悼会上说出这段动人的话后,才知道这四个剧本的责编都是谢友纯。我还知道友纯兄的另一件事:在他逝世后,有一位外地的作家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在1980年代,他曾为上影写过一个剧本,通过朋友介绍寄给了谢友纯,此剧本虽上影没有拍摄,但在谢友纯的精心扶植下,在另外的一个电影厂投拍了。他问起我这位老编辑的情况,想与昔日的有恩之人取得联系。当我告诉他,谢友纯刚“走”后,他在电话中长叹了一声,久久没有出声……
友纯兄在天马、上影文学部当了三十多年的编辑,一直在全心全意地扶植作者,以此来支持文学部几任领导的工作。他从来都与世无争,把名利看得很淡,是文学部公认的好编辑、大好人。我尊重他的意愿,不再去查列他所担任编辑的几十部电影的名目。据我所知,他一生只独立创作了《我和我的同学们》这一部电影剧本,一不小心得了那么多奖,我想也可证明,他不是没有编剧能力,只是一直在忠于他的编辑工作而已。
1996年,友纯兄退休后,彻底让自己“边缘化”。我见到他的情形通常有二:一是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他从报亭买下几份报纸,一路看回家,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他仍然关心着;二是与杨兰如一起,按时去喂流浪猫,风雨无阻,坚持了二十年。我望着他那一头白发,不知怎的,常有一种心酸的感觉,他却总是那样自得其乐。我是在他的告别会上,听了他儿子鸣晓所说的“父亲生前一直感恩上海这座大城市能接纳他”这句话,以及他侄子、侄女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后,才对友纯兄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们文学部有的老编辑,退休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把自己编辑过的剧本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并提供了不少不为人知的珍贵材料。而大多数的老编辑,尽管在重铸上影辉煌中都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却历来只字不提自己的成绩,哪怕在这个人生过程中所遭受过的磨难和委屈,也以一笑了之,我因难以做到,所以更佩服他们。而如友纯兄那样,还要如此感恩,其中的深意,至少是值得我去深思的。
我给友纯兄和沈寂先生都写过悼文,写沈老的那篇很容易发表了,而写友纯兄的这篇离他逝世已有六年,都难以公布于世,原因是显而易知的——他名气不大。虽然友纯兄和他的家属从不奢望谁不应该忘记他,但我见到兰如大姐和鸣晓时总感到于心有愧。前几天我又见到年已80多岁的兰如大姐拉着拉杆箱喂野猫回来,我同她开玩笑说:猫外婆,今天见到多少“子孙”?她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今天见到了一个大好人,关心地问我,这么大的年纪了,天又这么冷,还要出来捡垃圾?是不是子孙不孝顺?我能帮助你吗?我听后笑弯了腰。我们照例又拉起了家常,我回忆起我单身时,她和友纯兄家里烧了好吃的菜,常拉我去改善生活。她认真地想了一下说,不记得了。她说她只记得她在生鸣晓时少奶,我从家乡买了好些水产品送她……对于这对如此善良的夫妇,我无言以对。回家后,我重写了这篇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