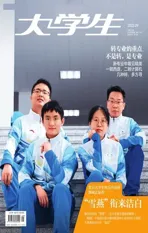城市废墟探险
2022-10-09孙杨袁姝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孙杨 袁姝(北京外国语大学)

探索城市的B面
一行人越过黑夜里还亮着灯的区域,静静注视着在荒漠中蔓延的无边黑暗。大漠的风刮在铁皮上,此起彼伏地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他们比预计时间晚很多才进入废墟,潘然想赶紧上楼找个房间扎一顶帐篷睡下。在找楼梯的时候,她突然进入了一个空间,跟之前穿梭的小办公室储物间截然不同,“这个空间一进去,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你就感觉非常大”。她亲身体会到了什么是豁然开朗。
潘然判断自己来到了一个与原先不同的空间,心脏加速狂跳,跟她一起去的朋友打开红光手电,宇宙飞船就这样映入眼帘。“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内有一架废弃的航天飞机,这座来自前苏联军备竞赛时期的航天飞机是暴风雪计划的一部分,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解体后被废弃。
潘然觉得全世界城市废墟探险者心目中的顶级胜地,可能就是暴风雪机库了。她在她的豆瓣日记中回忆这次特殊的废墟探险:“暴风雪在我的bucket list(遗愿清单)上独占鳌头已经太久太久……穿越无人区单程39公里,负重15~20千克,中间还有俄罗斯军事禁区,一旦被抓,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真正提上议程大概是去年底,从找队友,到反复确定徒步路线,再到买装备、有计划地进行训练——中间还在美国纽约阿巴拉契亚山脉中进行了一次模拟——到真正出发共耗时6个多月。”
亲身体验废墟探险和从照片、视频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宇宙飞船比在视频里看到的大,也和照片完全不同,超出想象。
潘然从2015年开始探险,她曾只身穿越全长11公里、完全黑暗的纽约州废弃交通系统罗切斯特地铁,也曾在探险纽约城派拉蒙旗下的废弃剧院时被钉子划破手、从一楼摔进地下室。更惊险的是,她曾两次和枪击案擦肩而过。
当然,废墟并不总是耗费巨大且惊险连连。潘然也曾探险过位于宾州和新泽西交界处群山峡谷之间的废弃蜜月度假村,欣赏夏日落在心形床上的清晨微光;在温哥华的西点格雷住宅区坐在泳池边吹着海风目睹夕阳西下;在背靠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小镇,意外发现森林中满谷等待自然吞噬的甲壳虫车墓。
废墟顾名思义,是废弃的建筑物,潘然总结她去过的废墟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特别安静,那种正常人类社会里面没有的安静;另一个是气味,凝滞的空气里尘土的味道、泡过水的纸张的味道、生物死亡腐烂的味道,各种各样的味道涌入鼻腔,让人想到“陈旧”这个词。
虽然探险的建筑物可能早已被众人遗忘,但它们并非都是无人看管的,也并非都被彻底地废弃。它们的所有权,有的属于某政府,有的在某公司或私人手中。
如果说城市A面是与社会建立联系和关联的那一面,那废墟探险对潘然来说,就好像一个隐藏的秘密基地,让她注意到了城市的B面。
在去往费城市中心的街上,潘然一行人去了一个废弃剧院探险。从里面出来后,潘然他们看着主街上这5座废弃的建筑物错落有致地插在高高矮矮的写字楼之间,外表看来与其他高楼大厦并无二致。当地居民似乎看不到这些废弃建筑,在其附近抽烟、吃街边摊买来的热狗,或西装革履地站着聊天。当然,也可能是早已习惯了和这些废墟朝夕相处。
在一个地下系统入口的小溪口,潘然欣赏过“像是走入外太空”的景色;在废弃的儿童精神病院里,她看到一面照片墙,贴了好多小朋友的照片。她在自述探险经历的摄影文集《废墟美国》中这样说道:“这众多废弃的建筑曾经的主要用途虽然已经消失,但是它们并未死亡。从一扇破碎的窗户,一个充满泥水的下水道,或者一道攀满爬墙虎的栅栏,我溜进一座又一座城市的B面。”
平行空间
你可以一眼从喧嚷的人群中发现孙晨:眼睛微微眯起,注视人的时候全神贯注,带点观察审视的意味。
孙晨是90年代生人,他接触到的城市废墟探险者也大多是同辈人,他们的探险行列里不乏导演、诗人等艺术从业者。
孙晨说,探险之前他会去搜索废墟的相关资料,也会经常读相关的书籍,看清朝、民国时期的照片编成的影集,去博物馆等,通过这些个人的亲身体验,他逐渐对北京的整体规划和历史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与城市的不同角落建立了联系。
2017年,孙晨开始摸索着探险城市废墟。他最初是从贴吧接触到城市废墟探险,第一次探险的是首钢,目前完成了近百处,他的个人探险地图上的“北京”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小红点覆盖了,每个小红点标记着一次探险。
对于孙晨来说,废墟探险能平复自己激动或烦躁的情绪,好像进入城市的一个平行空间。在废墟里他可以用这个时代的视角去审视20世纪的城市建筑群,人的生活习惯与物件携带着岁月的风尘出现在眼前,他会把自己想成当时物品的主人,想着当时的社会与风貌,再看现在的社会,便多了一分充实。
失衡的建筑美学
“除了照片什么都不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是城探圈不成文的规矩。
但从城市探险存在之初,就一直有人打着“艺术创作”的名义,在废弃的建筑内随意破坏,涂鸦、扔彩色烟雾弹等。
光是2015年到2018年间,潘然见过的破坏事件就数不胜数:有创作光绘(以光的绘画为创作手段的摄影作品)时不小心被烧掉的底特律学校,被涂鸦和损毁的火车墓地,纯粹为了好玩被砸毁的整座罗德岛教堂等。类似事情的发生使越来越多想保护废墟的人选择将探险地点保密。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保密地点,但在猎奇探险风格成为热潮的当下,有些建筑仍无法幸免于难。不论是国内或国外、公开废墟或废弃民宅,都多多少少会出现墙面有大幅涂鸦,垃圾被随意丢弃的情况。
除了对涂鸦、焚烧等行为的反抗,疲于应对将废墟探险视为“网红打卡点”的从众人群,也是潘然、孙晨这类资深探险者不愿意公开探险地点信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间尘埃的收集者
潘然觉得城市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相辅相成。费城在过去因为靠河,水力发电是工业的重中之重,后来工业重心转移,电站就被废弃。潘然认为,废墟有点像一个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影子,她在城市探险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每个发展时期被废弃的建筑的模样,通过废墟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触碰到一个城市的发展轨迹。
从废弃民宅的走道间穿过,探险是个人的旅行,所有的欣赏与观察发生在个人的头脑中,可在这样的行走中,人又分明走入了他人曾经生活居住的痕迹之中,原本的私密空间在时间的作用下成为一种不会冒犯到彼此的公共空间。孙晨觉得废墟探险和文学小说阅读的确有些共同之处: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在和作者跨时空交流,这和废墟探险的过程有重合之处。
孙晨感动于城市探险中见到的矿山工厂和员工宿舍,有时会看见生活的痕迹。衣被位置如初,学生证、画报有的发黄发脆,有的发霉或长了青苔。孙晨有次去翻阅桌上发脆的账本,发现记账的格式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见旧书里面夹着的老式车票,很有意思,就相当于找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和钥匙。”
潘然在许多个百无聊赖开着车兜兜转转的日子里,常在不经意间看到一些老旧的农庄、谷仓或者民宅,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整片荒原之上。她回忆在密歇根州环线偶遇的时间胶囊民宅,正门堆放了许多诸如烂床垫、衣物和木板之类的垃圾,朝向林子的后院里摆着一张保存相对完整的沙发,还有秋千、婴儿车等物品。从工作室踏入客厅,她和同行者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两张沙发、桌子、壁炉、书架,甚至咖啡桌上的笔筒,所有物件都完完整整地立在客厅中,除了积压的灰尘和稍显破旧的地毯,一切都完好如初,仿佛主人只是暂时去远方旅行了几年。他们甚至发现了一整箱柯达8毫米电影胶卷,其中有1929年这个家庭的新生儿学习走路的录影,也有1970年春天的家庭录影。
潘然觉得这样的城市废墟探险如同阅读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她将探险者比作是时间尘埃的收集者,“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天涯何处似吾家)”。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费城、纽约,潘然说,大部分时候没人会抬头看,或者低头看,好像大家并不关心别人在做什么,也不关心自己所在的城市是什么样。潘然觉得可能这是都市人类的通病,习惯性地忽略周围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更关心网上的新热点。有一次,她从一个废弃地铁站出来,地下很冷,回到人类世界的时候,地面上很温暖又很热闹,沿河的地方酒吧、饭店灯火通明,人声喧嚷,喝酒聊天,就好像去另一个世界打了副本,然后重新回到眼前。
这些繁华的都市依然在生长,赋予人们很多温暖的体验,但潘然依然会眷恋珍视废墟及废墟所代表的另一面。她认为那些冰冷的、黑暗的、尘土气味的记忆与会面也有被发现和存在的意义。
刷新界面,孙晨又分享了他在场的另一片废墟。
镜头上移,灰尘如蔓生的青苔一样生长在沉默的砖瓦墙垣上,这里没有生命的声音,但这里仿佛又有许多生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