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奏一部情感随想曲
2022-10-09刘兰若香港都会大学
文/刘兰若(香港都会大学)

大厂聊天
冯婉秋,今年27岁,此前曾被一男同事称为大龄女青年。她曾在北京的“鸭厂”“牛厂”待过几年。这是行业术语,可能也就那些程序员和急着找工作的大学生们才知道。
冯婉秋在业余时间有个爱好,就是跟男程序员在网上聊天,网上联络的人有几百号了吧。认识的人多了,冯婉秋也发现了一些规律,她用文艺青年的视角将这百十几号人分成了四类:
一是指点江山型,譬如张口谈房子、车子、北上深户口,股票自然也是不能略过,工作更是。冯婉秋听到了好多故事:比如一个程序员说他中学时代悬梁刺股,曾去电子厂打工,他一针一线缝成的编织品被运往伊拉克;另一个小leader说今天和哪个部门大佬battle了,大胜一场;一个面霸说自己收到了某大型外企的offer,但是不想去,嫌公司太远……
二是风花雪月型,也叫戏太多型。一个认识了没几天的大龄程序员,对冯晚秋说他在出差的飞机上哭了,因为对她的思念……
三是妄谈风月型,这个类型的人也不少。冯婉秋一开始还会大骂一通“渣男必死”,但见得多了也就麻木了,现在一般都是冷处理。
四是光风霁月型,也就是不烟不酒不渣的正常男人。
刻烟吸肺
冯婉秋觉得自己在厂里待得挺凑合的,与其被男上司男同事男后辈PUA,不如当个闲散王爷。她不愿甘于人后,想“不蒸馒头争口气”。她咬咬牙没日没夜地打工,终于凑钱买到了一张香港的录取通知书和机票。
她来到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依然习惯性失眠。躺在床上,虽然周围一片漆黑,但她知道床单整齐地铺着,就像粉色的翻糖蛋糕,紫色的被子,配色温柔,远离职场,令人倍感舒适。
冯婉秋睡不着,在记事本里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她的感慨:
“阿明,香港晚秋的月色真美……几个月前的中秋节,我本打算在庙里烧香拜神,可是这里的天气阴晴不定,刚出地铁就被大雨拦住。我一边躲雨一边看表,过了好久才雨后初晴,幸好没有误了吉时。天空闷闷的,雾蒙蒙,就像我们见面时的感觉。庙里的香火摊收了,我烧不成,只好对神仙们恭敬地鞠了几个躬祈福。听说这里的月神和红线特别灵验,供奉处我没有刻意去找,不过也真没看到,哎,无所谓啦,我知道缘分这种事求不来的。毕竟第一次没什么经验,还搞得浑身汗津津的,真讨厌下雨。有时好羡慕你这个南方人,假如你来这里念书,一定比我这个北方人要习惯。”
“对了,为什么我无所谓呢?因为我心里已经拥有了一轮明月。天涯共此明月,就好。”
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冯婉秋,一个伤春悲秋的冯婉秋。
她加了快一千个人,但她依然忘记不了一个人。什么叫作“刻烟吸肺”啊!
初恋男神
一切伤春悲秋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冯婉秋有一个缺点,就是怀旧,就像很多人不是十成十地喜欢别人,却总妄想在感情里长袖善舞,藕断丝连。
“在做什么?”
“挣钱,准备娶老婆。”
“满脑子都是钱钱钱,一点情调也无。”
“情调能当饭吃?能当钱花?”
冯婉秋一想到这个男人要娶别的女人当老婆,便怒向胆边生:
“你真的比他差远了!”
“那你跟他结婚吧,去天堂。”
冯婉秋看到一句回敬般的气话,可是凭着自己多年来的文字敏感度,觉得好像哪里有些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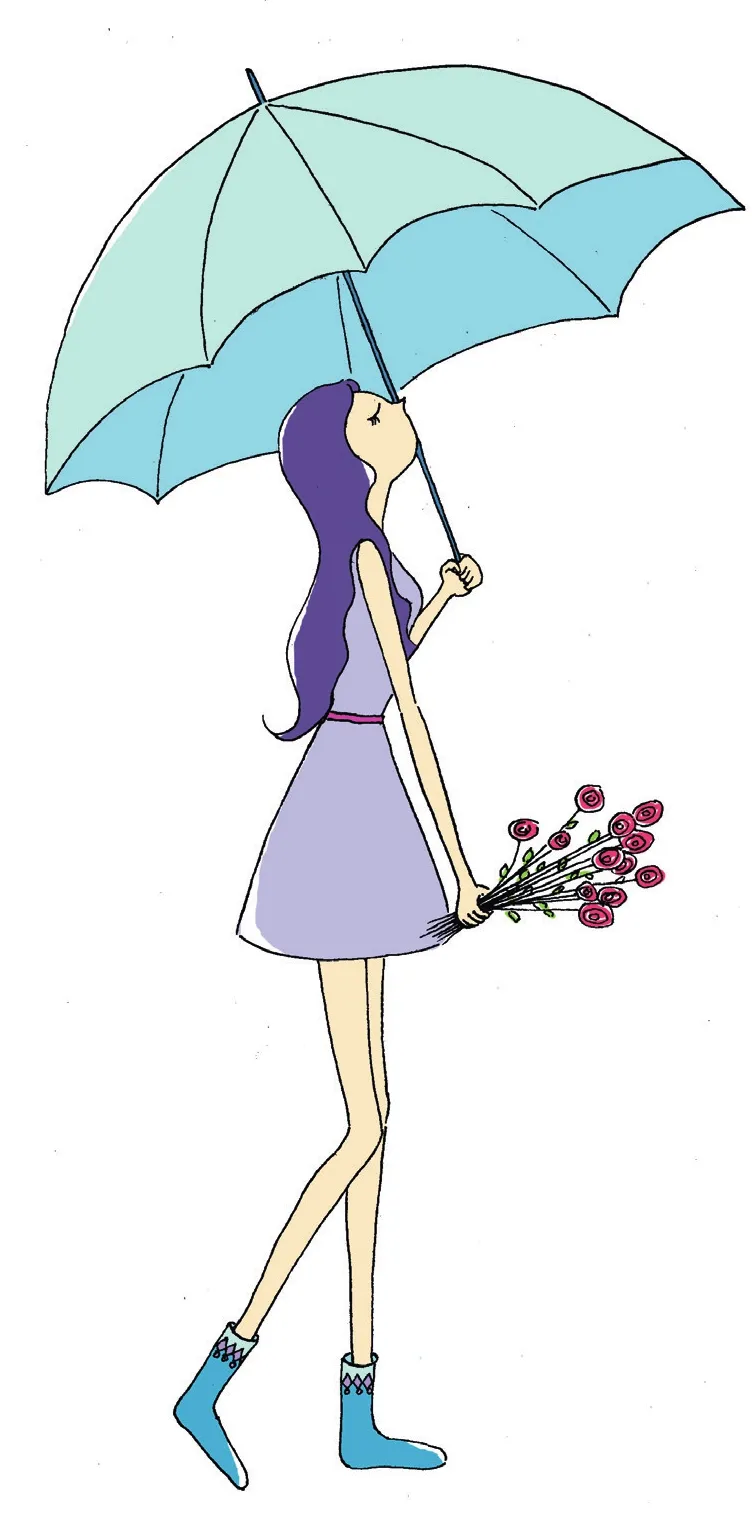
“你说什么?”
“他死了。”
“你说什么!”
“你的男神初恋,他死了!”
告诉冯婉秋这个消息的是她的前男友阿华,“男神初恋”是阿明。
冯婉秋和前男友的相识也是颇有戏剧性。更有戏剧性的是,冯婉秋后来才知道,阿明与阿华曾在一个大学实验室紧挨着共事,是同门!她不记得是二零一几年了,总之是一个南方城市的晚秋。她那已经脱单的男神初恋先是奚落了她一顿,又短暂地拥抱了她一下,便匆匆离开了。可谁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呢?冯婉秋在偌大的校园里哭了一路,哭累了,便坐在道边,一个叫阿华的男生可能很久都没有看到一个女生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姿容甚丽”,便凑上去递了一张餐巾纸。
一张纸成千古恨。
莫非缺乏恋爱的男女,真遇到感情都变得行为异常?在那一日,三个未来打工人竟上演了韩剧般的戏码。
江南烟雨
冯婉秋本以为自己会像林俊杰的《江南》里唱的那样,寻死觅活,要死要活,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可当事情真正发生了以后,她只是觉得有点儿晕,手臂很麻木,也没有天旋地转,只是眼前一黑。
她缓了缓,定了定神,继续打字问道:“怎么死的?”
冰冷的手机荧幕上蹦出一行字:“听说是在光棍节的时候,他们公司连着一个月通宵加班,积劳成疾,累死的。”
“对方正在输入……”的字眼停留在阿华的手机许久。
冯婉秋停顿良久,才在屏幕缓缓打出一个:“哎。”
“哟?还以为你会哭天抹泪呢,别想了,在香港有时间找找新对象。”
“哦。”
她哭了?但是好像也没有哭出来。她已经拥有成年人的理智了。
她甚至有点想笑。就算认识一千个一万个程序员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好像和时间没有什么两样,一维地浮现着。离开的就是离开了,甚至也不能再相逢,但又会遇到新的人和事,循环往复,所以有什么可哭的呢?她在心里试图说服自己。
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吃点什么……阳春面、牛肉面、或者是这里最local的车仔面,因为和他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餐就是一碗面!她晃晃悠悠地、随便进了一家,外面刚下过小雨,屋里冷气袭人,甚至能看到在冒烟儿,她打了打寒战,恍惚中随手指了一碗面,付钱的时候还多给了老板一张500元的大钞,多亏了老板的诚实提醒。她呆滞地注视着手机里的那些对话,滚烫的面端来了,雾气氤氲着眼镜片,混着滚烫的珠泪。
月光朝圣
冯婉秋吃完这碗抑郁的面之后,莫名地想登太平山顶。她19岁的时候来观光过一次,可那次的记忆实在太糟糕了,她只记得山上的冷风好大,还有她的家人们本来在车上好端端地坐着,不知何故与邻座吵了起来……她摇摇头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凭着残存的记忆找到车站,在大巴车上层靠窗坐着,胡思乱想了一路。
“我总是乐观地想,你非要和我断联,把我所有的联系方式统统该删除的删除,该拉黑的拉黑,甚至连支付宝都不可以给你发红包。可一位老教授对我说断联不是真的,心里还是有的。
如果人生能够有选择,我该如何和你重新开始呢?其实我也并不清楚。假如我仍然和你保持联络,假如我没有一个人来体验生活的辛苦,甚至我真的与你走到最后,我们就都会幸福吗?答案似乎也不尽然。”
下车了,冯婉秋改坐缆车。数十条“粗壮”的钢铁缆线永远平行,她和他却像两条相交线,分离后渐行渐远。她望着窗外,黑漆漆的,但白天是绿色葱茏。“你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生,你带给我希望,我渴望你的火光照在我身上,但你的身影却逐渐消散。我并不后悔认识你,那个帮我筑梦的你……”有时佳句总会天然偶成。
终于到达山顶,亮光刺眼的都市暴露在她眼前,她好想喊出来:“(别丢下我走了)”,用韩语,用日语,哪怕是用什么高棉语……总之想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山上的风依旧很大,又是一个十五的夜晚,月亮圆圆的,晶晶亮亮,好像他的眼睛。她有些豁然开朗,又吟起一句诗:“我不要摘下月亮,我要它挂在天上!”白月光真的成了白月光,永远地挂在了天上。
冯婉秋,今年27岁,好像不仅仅是在为他祭奠,更像是在进行着一场诗意的朝圣。

亲爱的阿明:
我站在山顶,看到维港一边是墙面斑驳,破旧褪色的九龙城,另一边是灯火辉煌,鳞次栉比,天堂般的中环,像佝偻的背包老人与西装革履的白领。斜晖脉脉水悠悠,光点不断冲击着我的双眼……这个魔幻的都市好像在热烈地展示着: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啊。
和你相识时我还是学生,好像一只未剥壳的鸡蛋,对这种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有着天真的向往,感觉自己年轻得风华正茂,可以获得一切,尤其是幸福。我和你确实实现了这种所谓的梦想:穿梭在钢筋水泥浇灌而成的城,行走在白炽光灯永不熄灭的职场路,奔跑于冰冷的程序和数据之中,欣赏过凌晨5点半的企业园区景色。
那景色与我现在看到的这些钻石雕刻般的摩天大楼别无二致。我仿佛能看到,每一面透着光的玻璃幕墙后,都有一个打工人的辛苦背影,在废寝忘食地敲击着键盘,任时间无声无息地流淌。不止你我,所有人对财富的渴望就像香港30多度的天气,能蒸出米饭的香气,热气腾腾。
在南方的几年,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一样租过夏天蚊虫遍布,冬天没有24小时热水的房间。
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数不清优秀的人、卑劣的人,还有好多和我一样夹在中间的人,心中充满压力、愤怒、迷茫,但也时常心怀希望。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相亲,那气氛好像市场,婚姻变成了公事,男女变成了商品,挑挑拣拣。
不知道你有没有遭遇过女生的遭遇,被异性欺负......
疲惫不堪。可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啊!正如《七宗罪》里的终极追问‘Life is tough,isn’t it?’但你好幸运,反倒是解脱了。
你问我什么是寂寞,还发给我一首聂鲁达的诗,我回应你寂寞就像《小李飞刀》里的阿飞在数十七片梅花。我不知道我究竟喜欢的是诗,还是你。那个时候的感觉真好,可惜回不去了。我真的很羡慕你,因为现在,无论是梅花、春天还是樱桃树,你都可以在那个世界里看到了吧。
我想起前同事的一句话,颇有日本俳句之味道:希望某天下班时能看到傍晚的夕阳。
无论谁离开,但我的夕阳还要望。
永别了!
冯婉秋,依旧是那个打不死的冯婉秋,伤春悲秋的冯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