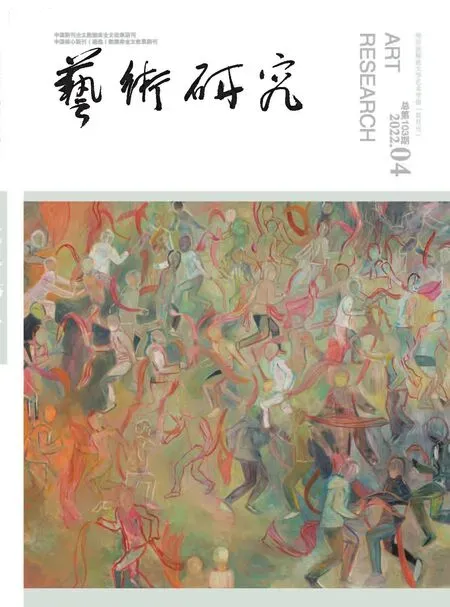境真源于神似 意远根于情深
——北大荒版画三十年(1958-1988)
2022-10-08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何 颖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在北大荒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受到精神文明的滋养以及艺术力量的鼓舞,北大荒版画异军突起而轰动艺坛、饮誉中外。北大荒版画不仅揭示了北大荒的美、北大荒人的美,更展示了垦区事业蓬勃发展的壮美景象。这些独特的美的现象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只有的北方黑土地才能孕育出来的美学特质。
北大荒版画是一门与新时期相结合的艺术,它的成就不仅在于艺术作品本身,更在于其创作群体用事实印证了艺术科学领域的根本性规律,蕴含于艺术群体与学派、画家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关系。北大荒版画群和其他学派版画创作群体内,前者的发展周期更长久,并且表现更为突出,北大荒版画家们内心对黑土地高度热爱,并且通过个性的版画语言,表达内心对黑土地风情的偏爱,表达更深刻的个人生活感受。北大荒版画在长达三十年发展征程中,随着国家新兴版画运动,创建新的发展序列。
北大荒自古以来有着较高的开发难度,第一代北大荒人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顶风冒雪、手拉肩抗,在荒凉了几百年的土地上建立起一片片良田。北大荒版画的成长和发展总体看分为三个标志性的演变时期:第一时期是1958年至1968年;第二时期是1968年至1978年;第三时期是1978年至1998年。
一、原汁原味的北大荒版画(1958-1968)
1958年,为北大荒版画的发展创造机会,随着十万转业大军的出现,党组织对转业大军进行号召,即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逐步开发北大荒戍垦戍边,并且形成大量的国有农场基地。十万官兵建设共和国最大商品粮基地——北大荒,在此背景下诞生了北方地区独特的艺术群体——北大荒版画群体。拥有艺术才华的战士艺术家,需要以艺术语言倾吐对于荒原沃土、边陲风光以及火热垦荒的挚爱之情。而艰苦创业的劳动大军,也需要精神文明的滋养,艺术力量的鼓舞。
“北大荒”是时代精神的表现,更是北大荒土地的荣誉,在长达数十年的发展中,黑土地建立新的文化旗帜,是特殊时期、特殊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地域艺术代表。首代北大荒版画创作群体代表人物包括:晁楣、张祯麒、杜鸿年等。晁楣是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北大荒版画的策划和领导者,正因他傲人的版画创作成绩多次成为全国美展的评委会委员和全国版画展评委会主任。晁楣是多个版本画集、版画创作的作家,获得国家文化发展终身将等殊荣。
1958年9月《北大荒文艺》《北大荒画报》等作品出现在社会群众的视野中,而晁楣和张作良两人就是上述作品的缔造者。1959年编辑部新增张桢麒、吴哲辉、郝伯义等人,还从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的错划为右派的队伍里调来了张路、张钦若,与此同时,还吸纳了在农垦报社工作的李亿平、徐楞,以及合江农垦局的廖有楷、杨凯生等。形成的创作群体以《北大荒画报》为中心,组成了一支美术工作大队。尽管最初从事版画创作的只有晁楣、张桢麒和张路,但不久,几乎所有人都加入了版画创作的行列,正是在他们的卓越成绩和坚持努力下成就了北大荒版画的历史地位。

《第一道脚印》(1960年)晁楣 套色木刻版画36.2cm×30.2cm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本阶段下,北大荒版画有效融合人和自然,坚定劳动场景主导,综合表达人物动作、劳动场景等形象,突出表现开荒场景的张力,画面强调艺术形态的力度感。这种艺术表现反映了军人本身特有的魄力、坚强和干练。例如,晁楣作为北大荒版画的首批作者,对行业的发展产生奠基作用,套色木刻版画《第一道脚印》则是晁楣早年的作品,更是北大荒版画代表性更强的作品类型,这幅版画作品刻画了拓荒者在北大荒的真实环境,表现了军人在北大荒坚守勘看的尽职尽责场景。人物身后留下的脚印,一道道脚印坚韧而深沉,映现了他们征服自然、改变荒野的决心。第一代北大荒版画的创作题材紧紧围绕开荒建设和垦区生活,体现阳刚、壮美的美学特质,奠定了北大荒版画的整体艺术基调。晁楣的作品来自生活,境真意远。垦区的大地洒满了他的汗水,布满了他的脚印。
北大荒版画的整体风貌是雄厚遒劲的,艺术气质是气势恢宏的,画面色彩绚丽迷人。相比于晁楣的版画,这一时期张桢麒的版画整体风貌上并不是以雄大壮丽为主,但是在色调和情境营造上独具一格,符合这一时期版画创作的和谐画面感。其代表作品包括:《黎明》《烧荒》《牧归》《母校来信》《两个黑人妇女》等。在上述作品中,《牧归》内的13个作品成功进入中国美术馆收藏名录;在1963年,《塔里木河暮歌》作品出国参加俄国造型艺术展;1967年《打麦场上》进入联合国中国现代绘画展;在1979年,《艳秋出猎图》获得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美术展览上获得三等奖,同时获得“鲁迅版画奖”,并出版了《张祯麒版画选》。
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版画画家将自身因素与外界因素相融合,凝练地创造出了粗犷、壮美的时代艺术。代表性更强的是艰苦奋斗精神诉求,其一方面是北大荒精神价值观、主体理念的表现,同时更是垦区人立足的基础。垦区人坚定自身意志,发挥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意志力,快速在艰苦环境中生存,并帮助区域迈入繁华的年代。北大荒的艰苦环境强韧了版画家们的坚韧性格。虽然垦区人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但是过去艰苦奋斗的点点滴滴依然保留在人民的心中,并且做到与时俱进,为艰苦奋斗赋予新的定义,坚持富而思进、富而思源发展思路,形成“富而不奢、富而不惰”的社会风气。
地域风格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其中包括自然景观与气候特色,生产与生活方式特色,人情风俗与心理结构特色,种族与人群聚落方式特色,地区性的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环境特色等。所有这些外于艺术家的客体因素最终通过艺术家主体发生作用,但它们有力地制约甚至支配着主体,因此对艺术风格的形成归根结底出于主、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对象如何影响了艺术家,艺术家又怎样把握了对象。

《北方九月》(1963年)晁楣 套色木刻版画 40.4cm×60.2cm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二、版画群体的新生力量:北大荒知青版画(1968-1978)
1968年,为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一批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来到了北大荒,最终成为北大荒版画群体中的新生力量。他们在第一代版画家的指导下,继承了第一代北大荒版画的创作思想,继承其创作风格和特点。目前为止依然存活大量的第一代版画家,包括李亿平、杨凯生等人。他们都是车四五十年代下的成功转业的官兵,在他们的努力下成功创造北大荒版画;最后,六七十年代城市只是青年逐步进入北大荒,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输出价值。
这一时期,北大荒已然成为世人赞美的北大仓,北大荒版画的创作主题也转向迎合人们心之向往的美好前景。从题材创作的角度分析,北大荒版画不再局限在垦荒的现实生活,并朝着丰收喜悦的方向改变。虽然版画的整体风格依旧,但这一阶段则更多地迎合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创作版画作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辉煌。本阶段下,能呈现版画作品的延续性作风,然而对应的刻画场面、画幅等有所提升,保持更丰富的色彩感,造型方面也表现更强的创新性,所以作品也被称作“新北大荒版画”。当前新生代的版画作家以张朝阳、刘荣彦等人作为代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浪滚动不息,这一期的北大荒版画创作者均为下乡知识青年,因此从创作者的层面分类也被称为“知青版画”。他们就好比泻水置平地,自东西南北流,让我们看到繁华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切换。他们原本红极一时,似乎主宰沉浮,但当生命的根须一旦插入那广茂而苦涩的土地,膨胀的头脑便开始收缩。在风吹雨打的艰苦劳作中,他们就不能不思考自我的价值和前途,并将思考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当响应号召的热情渐渐冷却之后,他们又何尝不想返回城市继续深造,他们在等待时机,而其中有些具有艺术才能和基础的青年,获得意外的机会,通过版画艺术领域展示自己的才华。正因如此,知青版画成为独特的艺术现象。知青版画渗透在知识青年的实际生活,同时也朝着北大荒农业不断迈进,以此反馈丰收的喜悦之情,也是赞美情感态度的表现。版画创作在方法上进一步增加场景构图特色,在确保首代版画整体风格的前提下,画面场景塑造更关注的是大场景的使用。色彩表现上更加丰富,造型上更加精确和写实,充斥着刻意的人工雕琢之美。

《牧归》(1960年)张祯麒 套色木刻版画48cm×23cm
虽然知青版画在国内并不是北大荒所独有,但最具有代表性和作品最为突出活跃的仍是北大荒版画。在北大荒垦区的支持和宣传下,对北大荒版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早年北大荒知青版画组织人员郝伯义甚至提出:“1971至1976年期间,我们都会创办美术创作班,通过分散搞创作等方法收集作品,合计创作版画、油画、中国画分别200多幅、50多幅、60多幅,并且挖掘80多个具备独立创作能力的年轻作者,国家、省出版部门为垦区出版了30余册画辑(集),还有一批作品参加了出国展览”。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有陈玉平、周胜华、李璞、赵晓沫、陈宜明、王合群、王兰、张喜良、赵雁潮等。他们的作品能摆脱帮理论的影响和帮模式的规范,从垦区生活现实出发,一面较真实地反映了知青的精神状态,如陈宜明的《归歌》;一方面介绍垦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情况,代表作品是陈玉平的《耪雪催春》。画风承袭北大荒画派第一代作者的风范,多系油印套色,但总体观之,作品尚未达到前代作者的水平。作品分别进入1974年“东北三省版画展”和“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等活动,并且入选《广阔天地绘新图版画选》名录,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遍地英雄》(1971年) 张朝阳 套色木刻版画 55cm×80cm
三、版画群体的融合发展:北大荒风情版画(1978-1988)
北大荒垦区版画有较强的创作能力,这也是首代版画家的艺术作用下所产生的结果,而晁楣、张作良等就是辅导的重点人物,第三代版画家与以往不同,创造了全新的、色彩绚丽的版画作品。第三代版画家年轻而开放的包容性,他们东北地区与的其他版画群体交流往来,包括阿城、大兴安岭等,后期逐步发展成为黑龙江版画。1988年“乌苏里江行——北大荒风情版画展”开始转变为“北大荒风情版画”,并发展为第三代北大荒版画的新目标。
首代北大荒版画家是本土的原著,代表人物包括李元军、张春喜、张良武、李健、于承佑、王训月等,这些版画家的文化视阈和思想传达更为广阔。而这一时期的版画作品采用水印木刻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方法更易于描绘北大荒逸趣横生的田间生活,也呈现了焕然一新的视觉效果。从版画整体风格看,保留原始的画风,选择夸张的变形表达方法,在产品制作时,则选用柔和水印和丝网印制,以此呈现更甜美的外观。在本创作手法上,北大荒版画家的代表人物是郝伯义,其结合新疆本土特色,融入国外水印套色技术,成功地在过滤纸上以水印、油水叠印等技法创造了水印套色版画的新样式,在国内北大荒版画中掀起热潮。
1982年美术馆组织“北大荒风情版画展”,此时三代画家作品出现在公众视野,现场作者34名,作品多达94幅。这是一次以第三代版画作品为主的展出,他们的平均年龄尚不到30岁,年龄最小者仅17岁。版画作品突破传统油印木刻的限制,通过水印套色的方式呈现不一样的产品感觉,在首都美术展示后备受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北大荒版画便曾出国展览,经《版画》双月刊介绍,北大荒版画印刷品进入日本。在国际上展示了中国东北地区崛起的地域美术的独特魅力。
北大荒版画群体的成员大都是身处基层的业余作者,与专家们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地位、专业素质也有很大差别。不过,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作为版画群体艺术不能突破现有的局限,向更高层次攀登的理由。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版画群体曾经造就过不少有成就有影响的版画艺术家,目前许多群体自身也在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他们已经充分显示了在普及版画创作方面的优势,他们也一定能够表现出在提高版画艺术方面的卓越能量。群众性的版画群体创作在我国已经存在发展了60多年,还可以追溯到新兴版画运动初期的三四十年代。在80年代,群体创作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已经充分显示了它在培养版画作者队伍、推动版画创作方面的巨大优势。然而在后期的发展中,也面临诸多难题。如果提高群体创作质量,把群体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群体艺术的群体风格和强化群体画家的创作个性是解决众多问题的首要关键。
群体风格即群体艺术从整体显示的共性特征,亦即群体自身差别于其他群体的艺术“个性”。没有这种差别,就失却了群体艺术存在的主要价值和意义。群体风格应该着重强调地域特色,因为如果没有地区性,那就没有民族性艺术的独特发展空间,更没有世界性眼光的关注和聚焦。现代绘画意识对艺术的本质要求是多元化、多样化,它同强化地域性和民族性本来应该是具有同一性的。艺术作品呈现了艺术家创作时的头脑中的客观世界,也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写照。因此,群体风格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地域风格,呈现群体所在地域的文化、自然环境、民俗风情、生活环境、历史演变等,客观因素本身需要考虑艺术家群体特点,保留基础的创作思维,通过持续的创作和发展,能融入客体和主体元素。然而主体结构中,关于群体风格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群体成员之间共同或比较接近的美学思想、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等群体风格共同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当群体中代表性画家的独特个人风格,逐步演变为群体性的集体呈现,标志着他带动了、影响了地域性的群体风格,并成为艺术发展最终导向。
北大荒有着丰饶的土地,有着浓厚的艺术特色,成功培养三代作家,在本土有着类似的题材、组织创作模式、地域特点等,造就了他们别于其他地区的创作共性,但由于三代人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生产、生活环境,以及画家修养气质,审美观念的差异,必然在审美追求上出现某种交叉或背离。因此,北大荒版画既有继承的一面,显示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也有异化的现象,呈现出一种嬗变的趋势。北大荒版画群体及其学派已有60年的历史,它对当代版画发展的影响至今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乡情》(1983年) 郝伯义 水印版画47cm×69.5cm
四、结语
北大荒版画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显著成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异于其它画派的美学特征。在强大的时代潮流冲击下,文学艺术领域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蜕变,出现了一个文艺思潮迭起、美学思想嬗变、艺术观念更新、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全方位、多元化裂变的新局面。纵观我国版画领域的展览、创作和学术研究,能够窥见中国当代版画发展的多元化新形态。中国版画在向内的主体审美意识探索与向外的技术、媒材的不断延展中逐步凸显出一种自主的当代意识。北大荒版画成功的发展经验,为北方艺术创作领域奠定了丰厚的艺术底蕴,在经历了单纯的版画语言的探索和创作题材的现实化影响后,中国版画开始了新一轮的本体语言的回归和主体精神的自觉。版画艺术家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题材,汲取传统的营养和力量,与当下的文化语境发生联系,逐步建立中国当代版画语言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