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识与心性
——唯识宗的心性学说及其对宋明以来儒学的影响
2022-09-29张庆熊
张庆熊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佛教讲“意识”,儒家讲“心性”。尽管这样的说法大体上刻画了佛教和儒家各自的特色,但需要注意佛教中也有“心性”的概念,特别是佛教唯识宗从“八识”的角度论述“心性”,建立了它自己的一套论证体系。纵观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我们发现宋明以来儒家的心性学说采纳了很多佛学的概念,吸纳了佛教唯识宗从“八识”的角度论述“心性”的思路。通过对佛教唯识宗有关“八识”和“心性”概念的梳理,我们不仅能了解唯识宗论述心性的理路和所遇到的问题,还能更加清楚地认知宋明以来儒家的心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其难点和争论问题。同时,我们还能回过头来看到佛教唯识宗在中国思想史发展上的功过。
一、 阿赖耶识与心性
佛教唯识论建立了一种八识的理论。我们通常所说的“心”,按照佛教唯识宗的看法,由八种“识”联合组成。其中,前五识指感识,它们是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触识)、舌识;第六识指思维的识(意识);第七识指形成自我观念的识(末那识);第八识指藏识(阿赖耶识),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潜意识”。“藏识”的梵文为“laya-vijāna”;“laya”是储藏的意思,“vijāna”指“识”,“laya-vijāna”意为能像种子那样储藏起来的意识,音译为“阿赖耶识”。藏识含藏“一切种”(所有种识),它们是现意识的原因。种识会“异熟”(Vipāka),可以转化为现意识,而现意识又可以转化为种识(潜意识)。“藏识”、“种识”、“异熟”这三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刻画阿赖耶识的特性,用语虽然不同,但所指的对象相同。
在唯识宗“八识”的学说中“阿赖耶识”最富有创造性,但又留下最大谜团。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阿赖耶识”相当于大脑中的潜意识,表示生命体的意念会像种子一样储藏在潜意识之中。生命体有欲望,有意念指导的行动,有在行动中形成的经验。生命体把已有的经验、学过的知识保存在记忆之中;当生命体遇到新的问题和处理新的事情的时候,会通过记忆参考以往的经验和知识;由于生命体的这种意识活动长期的积淀和反复的练习,形成其活动方式的基本模式和特性。如果把“八识”视为心的总体,把“种识”视为主导心的活动方式和形成其基本特征的根本因素的话,那么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心性是由种识决定的。
当我们说到“性”(品性、性状)的时候,大致从两个角度考虑:一是从存在物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看,二是从导致这种基本特征的原因看。植物的品性与种子关系的比喻很能说明这两点。我们说到农作物,如果它的品种优良,就可能长得好;如果它的种子不好,它的品性也会不好。某品种的小麦具有抗旱的品性,遇到大旱天还能茁壮生长;如果是不耐旱的品种,遇到大旱天就会枯萎。对于植物的生长,当然还受到外在条件的影响。佛教唯识宗把外在条件称为“增上缘”或“助缘”,如大旱天浇水有助于植物的生长。因此就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品性而言,种子是主要原因(“因缘”),浇水、施肥、除草等是次要原因(“增上缘”、“助缘”)。当代的农业研究工作者为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种子的基因改造上,古代的农民不懂基因,但也知道要挑选优良的种子储存起来,来年播种。
唯识宗借用种子与其所生长植物的关系作为比喻来解释心性的变异及其主导因素,其相关的术语有“异熟”和“熏习”等。有关心的性状,唯识宗使用许多不同的概念加以刻画,如:“清净”、“污染”、“有漏”、“无漏”、“有障”、“无障”、“有蔽”、“无蔽”、“善”、“恶”、“有覆无记”和“无覆无记”等。但大致上说,唯识宗把“法”(dharma,在此指广义上的一切事物)划分为四种类型:“法有四种,谓善、不善、有覆无记、无覆无记。”(1)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150、150~151页。有关心的性状唯识宗也大致按照这四种类型加以划分。(2)如果要确切地追究,这些概念并不能按照现代伦理学中的德性伦理或规范伦理的方式来理解,因为它们涉及宗教上的修行和业报的观念。“清净”“污染”“有漏”“无漏”“有障”“无障”“有蔽”“无蔽”更突出与修行和业报的关系,“善”“不善”则着重用于评价众生的德性和道德行为的好坏。然而,在唯识宗那里这两者显然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在此,“清净”“无漏”大致可以归入“善”的一类;“污染”“有漏”大致可以归入“不善”的一类。“有障”“有蔽”属于“有覆”,“有覆”即“有障蔽”;“无障”“无蔽”属于“无覆”,“无覆”指不起障碍和遮蔽的作用。“记”指有关善恶性质的标记。“无记”指非善非恶,即在善恶的性质上的不确定。“有覆无记”指(在转识成智和涅槃成佛的道路上)起障蔽的作用,但(在伦理的善恶位值上)不确定。“无覆无记”指(在转识成智和涅槃成佛的道路上)无障蔽作用,并(在伦理的善恶位值上)不确定。
唯识宗主张阿赖耶识的性状是无覆无记。对其缘由,《成唯识论》中有如下解释:“此识唯是无覆无记,异熟性故。异熟若是善染污者,流转还灭应不得成。又此识是善染依故。若善染者互相违故。应不与二俱作所依。又此识是所熏性故。若善染者如极香臭应不受熏。无熏习故染净因果俱不成立。故此唯是无覆无记。”(3)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年,第150、150~151页。
这段话有点晦涩,但对于理解唯识宗有关心性的思路很重要,所以需要重点解释一下:
首先,唯识宗主张种识的特性是“异熟”,即种识会变异和成熟。种识的“异熟”将决定佛教所说的“流转还灭”,也即六道轮回和涅槃成佛。如果种识在其善或染污的性质上是固定不变的,即善的种识总是生成为善的现行,染污的种识总是生成为染污的现行,排除了其在生长过程中变异的可能性,那么“流转还灭”就没有可能性了。其次,唯识宗主张第八识是前七识所依托的。如果种识在其善或污的性质上是固定不变的,就会产生排他性,即如果它是善性的,就不能成为污染者的依托,反之亦然。然而,按照唯识宗的看法,前七识有善有恶,这样如果把种识确定为绝对善和绝对染的,它就不应作为同具善染二项的前七识的依存之处。此外,种识是可以受到熏习的,如果种识的善性或污染性是绝对强烈和坚不可移的,就会像极香或极臭的东西一样不会受熏习而改变。如果没有熏习,那么佛教所说的种识与现行之间善染品性变化的因果关系就不能成立了。根据以上三条理由,唯识宗主张阿赖耶识只能是无覆无记的,即阿赖耶识在转识成智和涅槃成佛的道路上不起障蔽作用,并且在伦理的善恶位值上不是固定不变的。
二、 能变与心性
唯识宗结合三种“能变”论述心的性状。唯识宗不是笼统地主张心性善或心性恶,而是把心分为八个识,并把它们归结为三种不同的能变,然后逐一谈论其性状。这集中体现在世亲菩萨《唯识三十颂》的以下三段话中:
(1) 初阿赖耶识,异熟一切种,不可知执受处了,……是无覆无记。
(2) 次第二能变,是识名末那,依彼转缘彼,……有覆无记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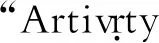
这三段话表明:第八识(阿赖耶识)是第一能变,它的基本特征是“异熟”和含藏“一切种”,但它的执受(Upādi)、处(Sthāna)、了[别](Vijaptika)等情况隐秘而不可知,它的性状是“无覆无记”。第七识是第二能变,它是被称为“末那”的“识”,即自我意识,它的特点是依存于第八识和前六识,作为潜在意识与现行意识之间过渡和转变的枢纽,它的性状是“有覆无记”。前六识是第三能变,前六识指一种思维的识(第六识)和五种感识,思考和认识外部对象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不善的,还可以是这两者都不是,即非善非恶的无记性。
“无覆无记”、“有覆无记”和“善不善俱非”分别对应这三类心识的性状。这三种心识有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是“能变”;既然是能变,那么其性状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都留有转化的余地。但是这三种能变存在重要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由隐到显、由内到外、由因到果的差别。阿赖耶识处于潜隐的状态中,它作为种识是其余七识的因缘;末那识(自我意识)处于中间状态,它一方面依仗于阿赖耶识(以阿赖耶识为内缘),另一方面又以前六识为其外缘;前六识的功用是思考和感知外部世界,因此前六识处于最外端,把意念落实为行动,产生“意业”、“语业”和“身业”的“果”。由于前六识的功用产生外在可观察的明显效应,即处于结果的位值上,因此可以用“善、不善、俱非”对此做明确的伦理价值上的判断。末那识产生“我执”和“法执”心态,认定自我和事物的存在,阻碍了对佛教所主张的一切皆空的真谛的认识,但它“依彼转缘彼”,因其一半处于内缘的位置上,其外在的效果还不明显,所以被认为其性状是“有覆无记”。而阿赖耶识尽管始终处于潜在意识和现行意识之间像爆流一般的“恒转”过程中,但它处于内和隐的状态,还没有发生爱憎烦之类的情感感受,还没有像现行的意识那样通过意念、语言和肢体行动发挥作用,它本身不阻碍六道轮回和还归寂灭,所以唯识宗主张其性状是“无覆无记”。
三、 心所与心性
唯识宗结合六种“心所”论述心的性状。“心所”的梵文为“Caitasa”,中文亦译“心数”、“心所法”,指按照心表现出来的特征对心的各种行相的分类和命名。《成唯识论》中对“心所”有一个解释:“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故名心所。”(5)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329页。由于唯识宗已经把心划分为“八识”,“八识”可理解为心的八个主干(“心王”),而心所是依附和相应于心的这八个主干的心理活动的表现形态,所以称为“心所”(心所有法)。简而言之,“心所”意为“心所属”,相对于“心王”而称“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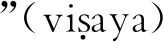
唯识宗的心所概念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相当难理解。这里除了古今译名不统一等语言上的原因外,还与唯识宗的相当独特的分类思路有关。常听到这样的批评声:唯识宗把心所分为六类共计五十一个,太支离破碎。这样的批评有失公允。如果明白其分类思路的大旨,就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唯识宗谈到六类共计五十一个心所,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存在一定的主次和从属关系。这可以从“遍行”等有关心所分类的名称及其具体说明中看出来:

其次,唯识宗主张“遍行”的心所类是八个识都具有的,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每个识单独就能履行这五种行为,而必须理解为它们需要协同合作才能完整地实现这五种功能。前五识的感性认识需要借助第六识的概念思考的整合,而前六识要经由第七末那识(自我意识)的统调而储存于第八识(藏识),而第八识又会作为习惯性的势力从种识的潜在状态中激活起来对现行意识产生作用。就此而言,这五个遍行的心所在三种“能变”中发挥的职能有所区别:在第一能变(阿赖耶识)中是储存和初始发动的职能;在第二能变(末那识)中起到中介和统调的职能;在第三能变(前六识)中发挥概念思维和感性知觉的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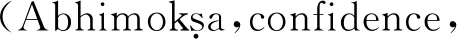
此外,唯识宗在划分心所的时候考虑到“认知”与“伦理”的区别。“善”、“烦恼”、“随烦恼”的心所类属于具有伦理品性的心所类,(8)海德格尔把对“操心”(Sorge)作生存论意义上的研究作为“基本伦理学”(die fundamentale Ethik)的核心。这说明他注意到此在的“操心”(在佛教唯识宗那里为众生的“烦恼”)与伦理上的善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不是后者决定前者,而是前者决定后者。中国老一辈哲学家熊伟把“Sorge”译为“烦”。在我看来,熊伟明晓这层意义而特意借用佛教的概念。它们与“遍行”和“别境”的心所类有所区别。尽管道德意识与知情意有关联,但不能说任何知情意都附有伦理上的品性。特别是就纯粹的认知活动而言,它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中性的。一个人集中注意力,做出判断,进行逻辑的推理,可以为善的目的服务,也可以为恶的目的服务,但就其认知活动而言,它本身不善不恶。在唯识宗看来,心识的“烦恼”的性状主要是伴随着第七识(末那识)的“我执”和“法执”的心态而产生的,因为认定自我的存在和对象的存在,为了自己的生存状况而担忧操心,就产生“我痴”(自我的迷惑)、“我见”(对自我的盲信)、“我慢”(自我傲慢)、“我爱”(自我偏爱)这四种根源性的烦恼。并且,它们在前六识中会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形成“贪”、“瞋”、“痴”、“慢”(傲慢)、“疑”、“恶见”的六个“烦恼”的心所,以及“忿”、“恨”、“覆”(掩饰)、“恼”、“嫉”、“悭”、“诳”、“谄”、“害”、“骄”、“无惭”、“无愧”、“掉举”、“昏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这二十个“随烦恼”的心所。


四、 种姓、习气与心性
在《成唯识论》中有关种子起因的三种观点的讨论与心性的关系最为密切,并也最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因为这里涉及“心性本净”(9)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111、105~106、105、105、110页。和是否人人都有佛性以及都能成佛的讨论。在此“心性”问题与“种姓”(10)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111、105~106、105、105、110页。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关系到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转变,以及从佛教的心性学说到新儒家的心性学说的转变。我们先谈这三种观点:
(1) 一切种子,皆本性有,不从熏生,由熏习力但可增长。(11)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111、105~106、105、105、110页。
(2) 种子皆熏故生,所熏、能熏俱无始有,故诸种子无始成就。种子既是习气异名,习气必由熏习而有,如麻香气华熏故生。(12)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111、105~106、105、105、110页。
(3) 种子各有二类。一者本有,谓无始来异熟识中,法尔而有,生蕴、处、界功能差别,……此即名为本性住种。二者始起,谓无始来,数数现行熏习而有,世尊依此说有情心,染净诸法所熏习故,无量种子之所积集。……此即名为习所成种。(13)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111、105~106、105、105、110页。
第一种是《成唯识论》谈到的十大论师中护月等所主张的观点,认为一切种子按照其本性而言本来就有,前七识的现行对第八识藏识中的种子的熏习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它会影响其增长,但不会影响到种识的本性。第二种是十大论师中难陀等所持的观点,认为一切种子都由熏习而产生,所熏、能熏都是自无始以来而有,种子可视为习气的不同名称,种子的性质完全由熏习决定,种子与现行之间互为因果。第三种是玄奘所认同的护法所主张的观点,认为既存在先天固有的本有种,也存在后天形成的新熏种。那些能生起并保持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不同功能的种子属于“本性住种”;那些由于无始以来一再受到现行的熏习而生成的种子属于“习所成种”,世尊释迦牟尼依此说众生的心是由于受到染净事物的熏习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众生的藏识是由此而形成的无量种子的积集之处。
从逻辑上说,这三种观点之间的差别在于对藏识与现行之间因果关系认定上的差别。按照第一种观点,藏识中含藏的一切种子永远起因缘(原因)的作用,而现行的熏习只能起助缘(辅助条件)的作用。这正如麦种总是生麦苗,浇水和施肥只能促进其生长,但不能使得麦苗成为稻苗一样。按照第二种观点,藏识中含藏的种子与现行的熏习之间始终处于互为因缘的关系中。现行的熏习对于种识来说能起到因缘的作用,这正如麻布上本来没有香气,但能通过花香的熏习使其具有香气。用另一个在中国更为流行的比喻来说,心犹如一面镜子,心性本净,染上客尘,使其污染,时时抹擦,使其清净。种识就是习气,而习气是可以改变的。一切种识都处于净与染之间的转变过程中,而朝哪一个方向转变取决于修炼。按照第三种观点,藏识中含藏的种子需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性住种”,这类种子对于现行来说始终起因缘的作用;另一类是“习所成种”,这类种子与现行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缘。用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话来说,这好比“第一天性”(第一自然)和“第二天性”(第二自然)。(14)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170页。“第一天性”是自然界中本有的万事万物的本性,这包括生物界的各种物种,由基因决定生物的基本种类和品性;“第二天性”是习惯成自然的习性,这包括人的习性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第二天性既然是通过人的习惯养成的,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和移风易俗来改变。当然,对于佛教而言,“本性住种”不是指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种的分子结构或基因,而是指佛教宇宙观中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在藏识中的本性;而“习所成种”的侧重点不是人在社会世界中的习性,而是人的内在的心理习性。佛教向往的是“出世”,因而把重点放在内心的修炼和禅定上,努力使得“习所成种”去除污染而变得清净。
从“心性”与“种姓”的关系上说,以上三种种子起因说实际上都持印度传统文化中占强势地位的“种姓”立场。世亲建立的唯识论不是否定这种种姓论,而是建立“种识”与“种姓”的纽带关系。传统的印度社会盛行种姓制度,分为婆罗门(僧侣贵族)、刹帝利(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吠舍(普通雅利安人)、首陀罗(土著居民)四个等级,此外还有被认为是贱民(“达利特”)的“第五种姓”。这种在社会上的等级制度也影响到佛教在修行上的等级划分。以上提到的《成唯识论》中的护月、难陀、护法等论师尽管在种子起因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是都赞同一切众生在修行上具有的先天的种性区别。他们都认同众生所具有的种性决定了他们各自修行将能证得的果位,并认为存在如下五个种姓:1.声闻种性,只能证得阿罗汉果位。2.独觉种性,只能证得辟支佛果位。3.如来种性(菩萨种姓),能证得菩萨和佛的果位;4.三乘不定性,通过修行究竟能达到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和佛这三乘中的哪一个的果位是不确定的,要看所遇到的条件。5.无姓有情,也称一阐提种性,即此类众生不具有三乘种子,不能修成三乘果位,无论怎样修行都不能得到佛教的解脱。
以护月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最能为“五种姓说”辩护:“诸有情,既说本有五种姓别,故应定有法尔种子,不由熏生。”(15)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105页。然而这种观点与唯识宗所尊重的《阿毗达蘑经》和《摄大乘》中有关阿赖耶识与现行的诸法“更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这个论断明显不符。以难陀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有助于维护种识与现行之间互为因果的观点,但与“五种姓说”有所冲突,因为藏识中先天固有的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的说法可以为“五种姓说”辩护。而如果一旦主张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都是由于熏习而生和都可以净染转化的话,那么“五种姓说”就不能成立了。难陀等为了维护“五种姓说”又提出“二障种子说”(众生本来具有的种性差别,不是依据有没有无漏种子,而是依据有没有烦恼障与所知障的种子而建立)。然而,对于二障种子仍然可以提出种识与现行之间因果转化的问题,从而难陀等的说法显得自相矛盾。以护法为代表的第三种观点看起来比较全面,但骨子里还是在为“五种姓说”辩护:众生的修行虽然有助于走上佛教所说的解脱的道路,但能否修行成功和取得什么样的果位归根到底是由他们各自先天的种子的性质(本性住种)决定的。
玄奘在为以护法为代表的第三种观点辩护时还特意辨析了“心性本净”的问题。他追问“心性本净”究竟是什么意思。心性犹如一面镜子,本净,由于沾染尘埃而变得污染。这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现在要问:“心性本净”中的“本”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这个“本”究竟是指作为现行意识的因缘的“本识”还是指超越一切流转变化的事物的“真如”?用专门的术语来说,是指“有为法”还是指“无为法”?在佛教唯识宗那里,“有为法”指处于因果链之中的生生灭灭的事物,一切属于有为法的东西都在业报(有为)的作用下轮回不已;而“无为法”则指超越因果轮回法则的东西,它解脱了因果链,无为而恒常。在玄奘所赞同的这一派看来,本净的心性是“心空理所显真如,真如是心真实性故”。(16)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111~112、111页。这种真实的心性属于“无为法”,即超越了一切处于种识与现行之间流转轮回的“如来涅槃法”。如果把“心性本净”的心性理解为“有为法”中的心性,这将导致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上解说的困难。如果把本净的心性理解为本来纯净的心的本识,并主张人人都有相同的本来纯净的“本性住种”,就难以解释为什么现实世界中有善人有恶人,就会把做了许多坏事乃至贪婪成性的人也说成是“圣人”。因为按照上述观点,所有的人就其本性而言都是圣人,而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处于因果业报的过程中,应该按照其种识习气和行为表现来评价是不是圣人。有的论师以“相虽转变,而体常一”(17)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111~112、111页。的论点来解释为何本净的心性转变出净染善恶不同的心相而心性仍然保持常一的清净。在玄奘看来,这种说法如同与佛教相对立的数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恶心、无记心与善心本来都是清净,由此会得出善的因将结出恶的果之类自相矛盾的说法。然而,按照因明的逻辑原理,种子与现行的本性与表现应是一致的。总之,按照玄奘所赞同的护法这一派的观点,对于“心性本净”应该区分“无为法”与“有为法”。对于“无为法”而言,“心性本净”的说法能够成立;对于“有为法”而言,对处于种子与现行转变过程中的一切事物而言,“心性本净”的说法不能成立。用现今的哲学用语来说,这里有双重本体论的味道:一方面真如是本体,另一方面种子是本体;真如是无为法的本体,而种子是有为法的本体。无为法高于有为法,涅槃是超越轮回的最高境界,而种子作为有为法中的本体仍然处于恒转的轮回之中。就心性本净和种姓说而言,护法这一派赞同一种折中的立场:一方面不否认终极意义上心性本净,为众生的修行树立了最高目标;另一方面又坚持在恒转的有为法世界中存在不同类型先天固有的本有种和后天形成的新熏种,这样就能为“五种姓说”以及不同的修行果位的论点辩护。
唯识宗的“五种姓说”传到中国后受到很大抵制。中国老百姓大多不认同种姓差别的立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中国哲学中“性本善”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天台宗、华严宗等佛学流派大多不同意众生的本性有根本差别,而倾向于认同“心性本净”的观点,主张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性,甚至能够“顿悟”和“立地成佛”。
五、 从新儒家对唯识宗的吸纳和改造看“八识”与“心性”
唯识宗从八识的角度论述心性对中国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产生很大启发作用。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中国儒家在先秦时期就展开有关人性的讨论并初步建立以思孟学派为代表的心性学说,这主要体现在《中庸》和《孟子》中。这种心性学说有卓越的见解,但论证上还比较素朴。到了宋明时期通过吸纳佛教的心性学说而在论证上逐步体系化和精致化,这特别体现在阳明学派的心学体系中。到了近现代,熊十力通过吸纳和改造佛家的唯识论建构新唯识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中国儒家的心性学说。我在此的用意并不是叙述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史,而是想通过对这段思想史的分析对佛家唯识宗的心性学说做一个评价,作为本文的结语。
中国在先秦时期发生过有关人性问题的热烈讨论: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主张“性本恶”,告子主张人性善恶不定,如水依势而流。“人兽之辨”和“义利之辨”是中国先秦儒家的主要着眼点。孟子主张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恻隐之心”的本心,而禽兽没有。荀子认为人与动物在趋利避害的本性上是一样的,但人有社会属性,可以通过社会的法治和教化来培育人的良好的习性,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关键所在。在有关仁义与功利的关系问题上,孟子强调“义”高于“利”,认为发扬人性中的“善端”和把“义”放在首位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荀子主张要兼顾仁义与功利两个方面;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一派更强调法治奖惩下的功利的作用。总而言之,先秦诸子在人性问题上虽有争论,但都重视人性的社会维度,都没有先天的“种姓”观念,在原则上都承认人人都有完善自己的品性和成为圣贤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印度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
然而,相比唯识宗从八识的角度论述心性的学说,中国先秦的心性学说还比较素朴。孟子在论述人的本性的时候已经联系到人的本心和良知。就此而论,在孟子那里已经开始把人性与人心联系在一起,并已经从融贯天地万物的本体上思考人的本心和本性的问题。但是与佛教唯识宗相比,孟子并没有辨析这里说的人的本性与人的心识的关系究竟如何,孟子在谈论修身养性时也没有联系到包括人的潜意识和现行意识在内的整个人的心识是如何转变的问题。显然,在这些方面,随着思想史的发展,到了宋明时期情况已经有所改观,这与佛教的影响分不开。我们可以觉察到,明代的心性之学背后有佛教的影子。明代心学的近亲是佛教禅宗,但它的许多关键概念和论证的思路一直可以追溯到法相唯识宗那里。(18)韩廷杰在谈到唯识宗的源流时指出:“宋以后,中国佛教进入衰微时期,唯识宗也不例外。但至明代,唯识宗又兴盛发达起来,关于《成唯识论》的疏释比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唐代还要多。”(参见韩廷杰释译:《成唯识论》,第743页)明代的心学的兴起与唯识研究的复活可能并非巧合。明代儒道佛三教合流,彼此借用很多。尽管明代佛教中禅宗依然是主流,但对禅宗“不立文字”导致的流弊的批评声已经相当强烈。这可能影响到佛家的心学。我没有看到王阳明直接谈到过唯识宗,但从概念框架上看这里有某种关联性。明代儒家中有研究过唯识论的学者。明末王船山在《相宗络索》一文主张“含而末发”的“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即体性上的“真如”,并尝试用他的“气”论改造唯识论。(参见《船山全书》第十三卷,长沙:岳麓书店,1996年,第539页。)
唯识宗区分了人的心识的三种“能变”和六种类型的五十一个“心所”,大大丰富了有关心识的学说。作为第一能变的藏识的观念有助于说明人的习心的基础和来源的问题,便于形象地阐释人的思维方式可以像种子一样在人的潜在意识中长期积淀而成为一种惯性的力量和模式。作为第二能变的“末那识”有助于说明自我意识的形成问题。“我执”和“法执”的观念有助于说明自私自利之心的“小我”的根源,同时也有助于激发中国儒家想到需要区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我”和一味追求个人的利益的“小我”。宋明以来中国儒家经常使用的心识中的“末发”和“已发”的概念,这也多少受到唯识宗的启发。它与唯识宗区分“藏识”与“现行”的观念有关。藏识中含藏的“种识”是“末发”,而前七识的现行意识是“已发”。唯识宗还提出“如来藏”的观念,这导致区分两种本体:一种是“俗谛”中作为现存事物的本原的“种识”,另一种是“真谛”中作为“心真实性”的“真如”。在唯识宗那里“心空理所显”的“真如”是高于现实流转世界中的“种识”的真正的本体。
王阳明心学集中体现在他的“四句教”和“咏良知”的诗句中。“四句教”如下:“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咏良知”中的一首如下:“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可以说这两首诗阐发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但如果不联系到佛教,特别是唯识宗的相关概念,就难以透彻理解。唯识宗主张,阿赖耶识就其潜在状态而言在道德品位上是“无覆无记”,这可让王阳明等宋明儒家想到本心就其“末发”状态而言是“无善无恶”的。再之,按照唯识宗作为终极本体的“真如”是超越善恶、没有形象、无法用言辞表达的,由此联想到“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说法和“咏良知”中的“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的描述,存在诠释上的脉络关系。唯识宗针对心识的三种能变探讨心所的不同品性,如对前六识(思想判断和感性认知的心识)区分善、不善和不定的三种不同的品性。前六识是“已发”的现行的意识,有欲望、目的、意图推动,有利害算计,有造成的后果,因此王阳明提出“有善有恶心之动”的论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王阳明在此对佛教的以“空”为终极本体的学说做了重大改造,主张本心及其良知才是真正无尽的自家宝藏。他指出“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与佛教的重大区别。当心发动的时候,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并对其是非曲直做出判断,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在此体现出来并被体认。在王阳明看来,习心无论如何甚嚣尘上,但作为“乾坤万有基”的良知依然是自家的无尽的宝藏。儒家不抛弃它,坚持人人可以通过格物的工夫成为圣人,而佛教抛弃了它,成了“沿门持钵效贫儿”。
在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过程中“天泉证道”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既集中表达了王阳明心性之学的要义,又凸显阳明学派中的意见分歧。“天泉证道记”涉及一些相当特殊的概念,如果联系到佛教对中国心性学说思想发展的影响,就比较容易理解,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王阳明学派中的钱德洪(1497—1574)与王畿(1498—1583)之间的争论。“天泉证道记”有多个版本,《传习录》中记载的“天泉证道记”如下:
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19)邓阳译注:《译注传习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490、490页。
首先,这里说的“利根之人”是什么意思?佛教中有“六根不净”的说法;“利根之人”在佛教那里本来是指六根清净的人。联系到唯识宗,“利根之人”指“本性住种”清净的人,这种人有利于从本原上悟入涅槃真如。当然,王阳明使用这个概念时赋予了新意,“利根之人”在他那里是指良知炯明的人,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从而直悟本体。王阳明并不认为“利根之人”在于具备优良的“本性住种”,而在于修养功夫深厚。他说人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所以要教导人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成熟后,心识上的蒙受污染的渣滓去除得干净时,就能通过自己的良知体悟天地万物的本体了。
“天泉证道”的难点在于“心体”这个概念,这里看来需要区分“本原”意义上“人心本体”和通常意义上“人心本体”。这有点像佛教真谛意义上的涅槃真如与俗谛意义上的纯净的心识。这个问题看来与《成唯识论》讨论过的“心性本净”的两种观点相关。如果把“心性本净”直接理解为原本纯净的阿赖耶识或原本无漏的“本性住种”,那么就会得出类似于王畿的说法:如果心之体是善的,心之意也应该是善的;如果心之体是善恶不定的,心之意也应该是善恶不定的。钱德洪则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20)邓阳译注:《译注传习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490、490页。钱德洪的这一观点若要成立的话,必须说明本体论意义上的“天命之性”的“心体”与通常意义上的“意念上见有善恶在”的人的“习心”之间的关系。
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中国现代新儒家熊十力那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对佛教唯识论的改造。在熊十力看来,佛教唯识宗说的超脱轮回的“真如”本体和处于因果链和业力流转之中的“种识”本体是一种双重本体论,并且在逻辑上不能说明虚寂轮空的“真如”如何产生出“种识”,以及像爆流一样流转中的“种识”如何能进入到“真如”。熊十力解决这种双重本体论的办法是区分“本心”和“习心”。在他看来,本心是本源的生命力,唯识宗所说的超脱轮回的“真如”本体是不存在的,本体总是在大用流行中,贯通人己内外和天地万物的真正的本体应被理解为“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唯识宗所说的“种识”应归于“习心”;习心虽然来自本心,但习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由习气浇灌而成的。阳明心学中的作为“天命之性”的“心体”应链接《大易》中所说的“乾元化生”和“大化流行”来理解。这种本体是大用流行。人的本心与天地万物的本体相通,可以通过良知来体认。
总的来说,中国儒家不满意佛教沦空滞寂的世界观,而持一种“天行健而君子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中国儒家追求的不是出世的涅槃而是入世的兼济天下。这导致中国儒家与佛教在心性修养或修炼方面的重大差别:中国儒家非常重视人的心性的社会维度和知行统一的修养方式,而佛教则看重人独自静思默想的修炼。在佛教唯识宗中那里,一个人的意识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而在中国儒家那里,人总是生活在人际关系的世界中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的说法:家教好,这家的孩子品性就好;家教差,这家的孩子品性就差。社会规范、社会风气和文化教化会影响那里生活的人的品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习气一代接一代的长期感染和积淀塑造在那里生活的人的心性。而且,中国儒家反对“种姓”观念,主张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以通过修养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而成为圣贤。
佛教唯识宗有关藏识与现行意识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作用,它有助于说明习心的形成问题。考虑到人是社会中的人,藏识与现行意识之间的关系应不局限于个体自我的范围之内,而应有主体际的维度。我们可以把“种识”理解为一种惯性的的思想观念,它们借助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语言而保存在人际社会中。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有死的,他死后当然也就没有对他的思想观念的记忆了,但是他的思想观念通过他生前的交往保存在主体际的语言中,会继续以某种方式对他人和后代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思想观念还活着。正如麦种不是继续保存在麦穗上而是掉落在土壤中或储藏在仓库中一样,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可以保存在社会共同体的记忆中或书写在书本上而流传下去。人类社会是具有社会规范、文化教化和价值观念指导的社会。佛教称之为的“种识”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的“原型”(archetype),它们塑造社会规范,培养社会风气,对人生发挥指导的作用。
虽然佛教唯识宗的心性学说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或缺陷,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对推动宋明以来中国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它开拓了对心识的知情意等多方面认知功能和储存功能的了解,它有助于说明习心和习性的形成问题,它提供了一套十分细致和非常丰富的有关心性的概念系列,它让我们了解在这个问题上各派论师各自振振有辞的论理辩难。可以说没有唯识论的传入和研究,就不会有新儒家心性学说的发展与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