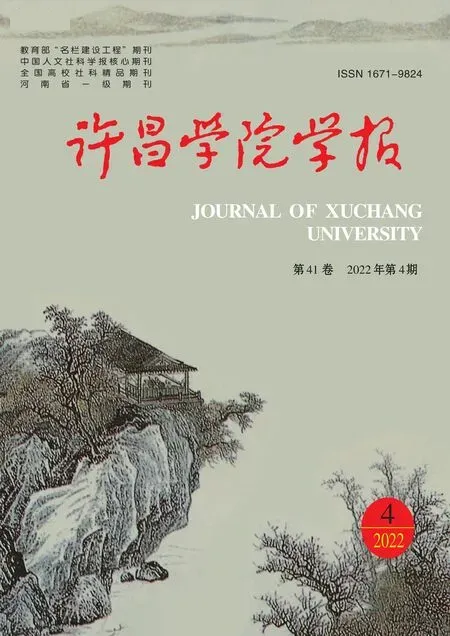论晏殊词在明代词选评中的接受与正宗地位的确立
2022-09-26魏若君
魏 若 君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晏殊是宋仁宗时期政坛和文坛的领袖,他与其门生故旧一道,通过自身创作切实推动了不同于唐代的宋型文化发展定型,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流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晏殊词在北宋声名颇高,如南宋曾季狸《艇斋诗话》言:“晏元献小词为本朝之冠。”[1]324靖康之变使南宋士人心态发生极大转变,南宋文士虽对晏殊词中体现的艺术成就仍持肯定态度,但其富贵闲雅的特点已很难引起共鸣,晏殊词的接受也随之进入沉寂期。元代词体衰微,于此大环境下,晏殊词与晏几道词被合称为“晏词”,没有见于文本的对晏殊词的单独评价,至此晏殊词的接受跌入谷底。入明之后,随着词创作的兴盛,批评家对晏殊词的接受发生了转折。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多,其中曾素芸的《晏殊词接受史研究》和张中秀的《词论、词选中的晏殊词的研究》两篇硕士论文,梳理了从宋至清晏殊词的接受史,并对各时期的接受状况进行了分析,展现了晏殊词在历史层累过程中的经典化历程;张琛的《宋代二晏词接受史研究》则对比了晏殊、晏几道在宋代的接受情况。本文试图以明代思想文化变化为背景,通过分析明人对晏殊词的选评,勾勒晏殊词在明代词论中走向正宗的演变轨迹。
一、明人对晏殊词闲雅风格的确认
论及晏殊词的风格,宋人多视为闲雅。吴曾《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对宋代词人的评价云:“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2]469李之仪在《跋吴思道小词》中云:“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3]310均把“闲雅”视为晏殊词的风格特点。所谓闲雅,即指一种娴静文雅、从容安舒的状态。经过宋初六十年的休养生息,仁宗朝政局安稳、繁荣开放,晏殊作为仁宗在太子时期就陪伴身边的旧臣,仕途尤为顺达,得以拥有相当丰裕的士大夫生活。这便是晏殊闲雅词风形成的社会基础。
明人对晏殊词闲雅风格的肯定主要通过词选表现出来。除《花间集》《草堂诗余》等改编本外,流传至今的明代词选有《类编草堂诗余》《天机余锦》《花草粹编》《词的》《古今词统》《古今诗余醉》等六种,这六种词选共选晏殊词九首,分别为《蝶恋花》(帘幕风轻双语燕)、《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玉楼春·春恨》、《踏莎行》(小径红稀)、《浣溪沙》(青杏园林煮酒香)、《踏莎行》(细草愁烟)、《破阵子·春景》、《渔家傲》(楚国细腰元自瘦)和《诉衷情》(青梅煮酒斗时新),晏集中的大量宴饮祝寿词无一入选。这九首作品中,除《破阵子·春景》以明丽活泼著称外,其余词作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晏殊词“闲雅”的风格。
首先,晏殊词“闲雅”风格根植于宋朝士大夫阶层的闲适生活之上,这种闲适基于富贵,又超于富贵。晏殊在评价寇准“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和李庆孙“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等诗句时,笑说如此诗句为“乞儿语”[4]133。而晏殊“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这样的诗句,虽然只写亭台楼阁,但其中景致又非寻常人家可以想见,同时观景之人亦须拥有闲雅志趣才可见此景,如此才为真正的“富贵气象”。晏殊词的闲雅风格正是以这种“富贵气象”为背景的。《蝶恋花》(帘幕风轻双语燕)从思妇闺房轻轻摆动的帘幕写起,随着女主人公的步伐先观览宅院中的造景,可即使如此,思妇心中愁绪依旧难以开解,于是“百尺朱楼闲倚遍”[5]61,希望得见归人。正因无事,思妇之心只能寄于游子之身,游子不归,则思妇之愁连绵不绝。于此宅院之中,思妇看到的不是锦缎朱楼,而是斜阳青苔,此足以见女主人公有观察生活中幽微之景的雅趣。晏殊用纷飞的柳絮、浓云下的薄雨做比,写出思妇连绵交织却并不厚重的愁绪,而这种愁绪本身便是雅致的。其次,闲雅通过哲理性思索表现出来。以词抒怀,喟叹生命有限,抒发忧患意识,源于冯延巳。历代也多有词评家认为晏殊之风近于冯延巳,刘攽有言:“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6]292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7]111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一词,写暮春之景,抒伤春之情,虽展现了作者对于美好事物终将消逝的无奈,但并未一味沉浸在时光易逝的伤感中,而是转换视角看到燕子归来的生机。在这里,晏殊书写了哀与美共存的世界,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观照。也因此,晏殊词较晚唐五代词多了一分通达疏朗之感。
在继承宋人对晏殊词闲雅评价的基础上,明人对这一特点进行了更多维度的分析。夏树芳在《宋名家词序》中指出,晏殊等人的词是“立朝建议,大义炳如”之余“风雅之别流,而词坛之逸致也”[8]2。这一将“雅”提高到“风雅之别流”的高度的评价,既展现了文体意义上词在历史发展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也说明了明人承认晏殊词符合各个层面上“雅”的标准。沈际飞则从读者论的角度分析了读者在阅读晏殊词时,也需怀有闲雅的心态,才能真正领会晏殊词的独特风格,如“斜阳送波远”一句,“望之澹然,其中甚切。不许速领,必数过之”[9]5342。只有读者在闲暇的时光和悠然的心态中细细品味晏殊之词,才可领会词中描绘的“澹然”景色。总之,明人对晏殊词的分析更为细腻,对“闲雅”风格的认知更为一致。
二、明人对晏殊词玄超与逼真特点的提出
明人论及晏殊词的特点,“闲雅”之外又发掘出了“玄超”。夏树芳《刻宋名家词序》言:“兹刻《宋名家词》,凡十人。捃摭俊异,各具本色。余得而下上之。辘轳酣畅,若同叔之玄超,小山之流媚,柳屯田之翻空广调,六一居士之清远多风,几最按拍。”[8]2所谓“玄超”,即玄远超脱。《说文解字》释“玄”曰:“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10]188玄本指黑色,黑色似乎可隐藏一切,神秘难测,所以“玄”字又引申出神秘而难以捉摸的意思。《说文解字》释“超”的本义为“跳也”[10]69,引申义是超出一定范围之外。不同于由规则和实体圈定的实在可知的世俗生活,“玄超”两字连用,展现了一种不拘于世俗之中,由心灵解放而带来的超脱之感。不同于五代宋初其他文人多用词描绘实体的美,晏殊词基于生活本身而不囿于物品之中,反以一种出乎其外的视角对生活进行观察和书写。晏殊本人对生活“超以象外”进行观看的视角即是其“玄超”词风的来源,当其时,地位和关系所构成的桎梏已不存在,许多槛内人“望断天涯路”也难以解决的问题都烟消云散。晏殊在追求自由时的表现不同于魏晋名士展现的桀骜姿态,他是以一种更为圆融的心态面对当下的处境。郭子章《豫章诗话》载:
晏元献公为京兆,辟张子野为通判,新纳侍儿,公甚属意。先字子野,能为诗词,公雅重之。每张来,即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之词。其后王夫人寝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碧牡丹》词,令营妓歌之,有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之句,公闻之,抚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斋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无复谁何也。[11]272
此文叙述了晏殊与侍儿的故事。晏殊因夫人不悦而将侍儿逐出,后读张先词作引发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之感,遂将侍儿召回。从逐出侍儿来看,晏殊对内院之事不甚关注,颇具儒者风范。而召回侍儿时,感叹“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又颇有道家的超世脱俗之风。晏殊在经历内心的拉扯之后选择委屈夫人而顺从己意,希望由此得到真实自由的自己,但他也明白外部世界不可能全如他夫人一样一味让步于他,因而更多时候晏殊希望通过庄子“心斋”的方式来达到精神的自由,这种精神的自由并非通过对抗外在来达到,因为一个试图和外在不断斗争的精神是无法达到真正安宁的。因而晏殊词中既有享受富贵生活的惬意与自在,亦有面对人生流转起伏的超然心态。晏殊本人也展现了许多对立的品质。为政,一方面他更偏向保守,甚至因此而被后世诟病;另一方面,他提拔了诸多贤臣名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皆成为推动北宋两次新政的中坚力量。论词,《珠玉词》中多描写歌儿舞女之容貌姿态,但他却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的词作和柳永的市井俗词不同。生活中,他虽以太平宰相闻名于世,爱好酒筵歌舞,但同时《宋史·晏殊传》也记载他“性刚简,奉养清俭”[12]10197。宦海沉浮中,出身清贫的晏殊并未在身处高位时畅言心中的激动,在被误解和打压时也不会愤而号啕,他的喜悦和失落都适可而止。一方面,晏殊以老庄的超然旁观世界,也旁观自己;另一方面,晏殊用儒家的方式和准则为人处世。于礼克己而内求自在,这是晏殊在融合儒道两家思想后找到的在现实生活中通往和谐与自由的路径。体现在晏殊词中,《珠玉词》收词一百三十八首,涉及生活的不同方面:其中祝寿词能让读者感受到对生命本身的认可;写歌妓神态身段的词中,能看到其展现的人体和谐之美而无流俗之感;表现离愁别绪时,看到的是晏殊心中对人生必然经历分离的无奈。但无论是写喜还是写悲,晏殊的情感态度都是平和的,这种“平和”不是为了达到中庸而在写作时故意克制的结果,而是晏殊认为人生本就是欢喜与悲伤的结合体。因而在读晏殊词时,没有撕裂和冲击的体会,更多的是和谐之感。不少人评晏殊词只评其闲淡,但夏树芳更深入一步地看到了这种平和心绪下面的基础:唯有以一种玄超的视野注视世界,才能怀有如此平静和谐的心态和盈盈脉脉的风度。在对晏殊词风的把握中,可以看到明人对晏殊生命观念的解读较前人更近一步,晏殊词中展现的哲思和澹然都是晏殊以“玄超”为基本点在观览人生后留下的释怀的喟叹。
逼真是明人对晏殊词特点的又一发现。“真”是构成优秀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但审字核句,细论晏殊词中“真”的体现,则始于明代。文学作品想要达到逼真的境地,既需要作者笔力深厚,勾勒的景色事物让读者感到如在目前,还要求作者本人性格真率,描写自己当下的心态情感时不加矫饰。晏殊以词闻名,笔力自不必多说。性格方面,欧阳修《跋晏元献书》评道:“公为人真率,其词翰亦如其性。”[13]1924认为晏殊文如其人,真诚率真。但欧阳修并未举例子进行说明。明人吴从先则对《玉楼春》中的“逼真”之处做了细致分析,其词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5]77吴从先曰:“上是闺中相对景,下是闺中相思情。又‘五更钟’‘三月雨’两入神。又:相思无尽,直吐衷情矣。又:春景春情,句句逼真,当倾倒白玉楼矣。”[14]1134所谓“闺中相对景”,就是闺中思妇眼中春天的景色。本词起笔第一句就是思妇在长亭送别时看到的“绿杨”“芳草”“长亭路”,三个名词连用,勾画出春天城外无法洗脱的荒芜之感,少妇的孤独之感也随景色一同生发出来。而当思妇回到家中,“相对景”就成为被栽培在庭院中的花朵,虽然美丽,却囿于庭院之中,在三月细雨的笼罩中生出淡淡哀愁,这时少妇的形象于孤独之外多了几分无聊和无奈。在这二重“逼真”的景色转换中,“闺中相思情”的微妙变化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同时,晏殊对游子的心理描写也极为逼真,“年少抛人容易去”[5]77一句,一反古来写分别时依依不舍之态,写出了年少游子离家远行时心里充满探索未知世界的激动和期盼。正因游子根本无暇顾及身后之人,思妇之思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此基础上,晏殊以思妇的口吻直言:“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5]77这一对内心情感的直切表述,毫无扭捏之态。正因如此,沈际飞评此词:“爽快决绝,他人含糊不是。”[9]5336晏殊在此词中塑造了一个真诚直白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她对内心情感的表达毫无矫饰,说出读者不便言说之情,因而读者更觉其逼真。此外,吴从先还评《蝶恋花》(帘幕风轻双语燕)道:“上叙心事伤春不自见,下拟归期早晚未可知。又:伤春情绪为之计归期,最堪写出真情。又:上曰未见,下曰未知,无非模写春怀种种处。”[14]1161而对词颇有研究的杨慎亦称此词“景真”[15]。卓人月则在《古今词统》评《相思儿令》曰:“‘春来依旧生芳草’,何其逼肖。”[16]197感叹晏殊词中的景物描摹逼真神肖。况周颐曾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17]6自南宋之后晏殊本人受到的观照并不多,纵览《明词话全编》,明人评选的晏殊词不过《玉楼春·春恨》《破阵子·春景》等十二首,其中四首只录其词而未有评述,但有评述的八首词中有三首被明代词论者评其有“逼真”的特色,可见明人对晏殊词“逼真”特色的发现和重视。
明人对晏殊词风格的确认既源于文本,又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明代心学发展,儒道进一步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明人敏锐地察觉到晏殊以温暖色调写萧瑟之感的手法,于闲雅的表达中体现玄超之致。而晏殊词中描实景、抒本心的真诚和明人崇真的评词标准也相契合,使明人发现并确定了晏殊词“逼真”的风格,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对晏殊词风格的确认。
三、正变视野下对晏殊词的定位
“正变”确立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时间为轴,将“正”和“变”看作原始和后继的关系,这种区分方法源自先秦崇源始、立统绪的思想。虽然关于词的起源在研究上一直模糊不清,但不可否认中晚唐之际的“大多数作品都已被稍后的《花间集》、《尊前集》等流行词集所选录,表明了当时人们对这些作品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性质的共同认识”[18]124。而这些作为范例的词,大多具有明显的女性化特征。北宋词人多在这种“正变”视野下将晚唐五代婉约词视为正宗,词的功能作用也被定为娱宾遣兴。从另一个维度上看,“正”也有正直、正见的意思,其与“邪”相对。词体兴起的晚唐五代时期政权不断轮转,词风接五代而下的北宋最终也落得个“仓皇辞庙”,因而南宋士大夫在进行历史总结时,就将声色艳丽、直白表露情感的一类词作看作亡国之音,从这个角度来说,宋王朝南渡之后,在“正变”的择取中愈加偏向后一种。这两种正变之论在宋金元时期一直存在,并有所交锋。宋人对词体正变的划分更看重其音乐性,宋人按乐谱填词,李清照在《词论》中犀利地指出:“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19]220认为晏殊词不能完全合音律,因此其词只能算作句读不葺的诗。刘攽在评晏殊词时讲道:“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木兰花》皆七言诗,有云:‘重头歌韵响琤琮,入破舞腰红乱旋。’重头、入破皆管弦家语也。”[6]292综合两则材料可知,晏殊对音律虽了解却不精通。到了明代,词乐失传,明人填词不再考虑音乐的因素,而是以前代成熟的词为底本,对其平仄韵律进行分析总结,形成词的“格律韵”。词在律化之后,评词和作词的门槛都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评论者对词作正变的划分,就会集中于词作风格这一标准,而对于词作优劣的品评,也与词作所反映的情感内容联系更加紧密。于此基础上,明人认为既不清拔又不媚俗的婉约词最能够代表词的本色之美。

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24]385
在这段论述中,王世贞把一直被视作“倚声之祖”的温庭筠、韦庄放在了变体的位置,这正代表了明代中后期词学思想的两种转向:其一是词作所求之“真”不是简单的对现实景观进行精细的刻画描写,注重艺术构思也不会影响作者真诚情感的抒发,“真”的标准在于词作中可见作者性情。其二是“婉约词”的内容不应只涵盖闺阁之事,而是抒发一种婉转的神思。《诗眼》中记载了晏几道和蒲传正对于晏殊词是否为“妇人语”的争论,陈继儒《诗余图谱序》对此进行了评论:“诗祖《三百篇》,《离骚》特文之余也。词,诗之余也。曲,又词之余耳。诗文发乎情止乎礼义,若旁溢而为词,所谓提不定、撩不住,谑浪游戏,几不知其所终。故晏元献公未当作妇人语点入词中。”[25]255认为晏殊之词婉而不媚,是士大夫的婉约词而非妇人语。此外,钱允治、胡应麟和陈子龙等人都对这种评价标准给予肯定和继承。由此可见,明代不同词论家对词的正体范围的圈定有一点出入,但晏殊之词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可被归为正体。这是因为,中国古人认为文体有高下之别,诗降而词,词降而曲,因而诗的立意内涵近于词会被视作文体的堕落,反之则值得称赞。然诗词之别在古代文人心中根深蒂固,主流观点认为词可近于诗却不应失其本身的婉转姿态。由此以观,晏殊之词既不流于艳俗,亦不过于清雅,即使不写绮靡浮艳之景,依旧与诗不同。如著名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5]7二句,王世贞评曰:“非律诗俊语也,然自是天成一段词,看诗不得。”[24]1458此二句不写闺中之景,而是流露出对生命的观照。晏殊对此联十分珍爱,在诗词中都曾使用,但相比而言,其词的流传度远高于诗。此即因为“无可奈何”的迷茫之情,花瓣飞落的轻盈曲线,“似曾相识”的模糊之感,“燕子”本身的女性化形象都和词的柔婉气质更为贴合,用词体表达此般婉转的心绪正合于词体风格的定位。深受儒家“诗教”影响的晏殊在写诗时必定注重诗歌意义的表达,因此他的诗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后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晏殊试图通过梁园纳才的典故使诗的立意从个人情思扩展到招贤纳士这一公共政治场域,然而诗中颔联和尾联之间情感转换过于迅疾,整首诗给人以断裂之感,因而《浣溪沙》之词名远高于《示张寺丞王校勘》之诗名。总之,晏殊词正体地位在明朝的延续和进一步巩固,既有赖于晏殊词本身的清丽婉约之风,也与明人不通宋乐,单纯从词体风格内容评判词之正变的考察模式有关。
综上而言,明人对晏殊词风格的认识在宋以来闲雅之评的基础上,又发现了玄超、逼真的特点。这三种特点均与晏殊的生命观念相契合,也与明人对词之“正体”的认识息息相关。在明人对晏殊词风格的定位中,可以看到有明一代士人既深受“温柔敦厚”的儒家思想的浸润,又常以老庄之学的超然心态解读世间事,儒道互济已然成为士大夫的思维方式。明人对晏殊词别出心裁的解读,既有助于今人更加准确地理解晏殊词的丰富内涵,也有助于今人把握宋词的发展脉络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