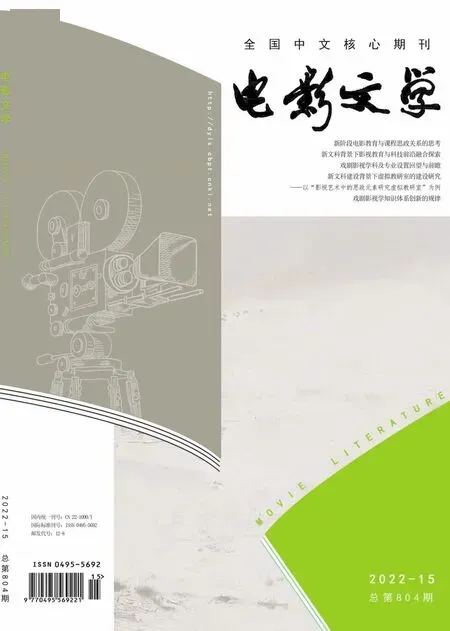《驾驶我的车》三重互文下的叙事艺术
2022-09-23郝蒋彤
郝蒋彤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驾驶我的车》是日本导演滨口龙介2021年执导的新电影,改编自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第一部同名短篇小说《驾驶我的车》。电影讲述的是著名舞台剧演员家福在碰到妻子音出轨后,却假装浑然不知。直到妻子去世,家福始终逃避与妻子音的交流。在一次戏剧《万尼亚舅舅》话剧演出中,剧场为家福雇用了一名司机渡利,并且家福偶然碰到当年妻子的出轨对象高槻。在与高槻的交流中,家福听到了妻子生前一直讲的故事的结局。家福也渐渐地在一次次的车程中和沉默寡言的女司机渡利互相倾诉自己的内心。两人在故事最后往返渡利故乡的旅程中,彼此尘封的往事与心结渐渐打开。这部电影的独特性在于影片架构于多重文本之上,其中小说《驾驶我的车》的改编作为主体叙事线索,男主角家福对戏剧《万尼亚舅舅》表演与独白,形成了与主线相融的复调叙事结构,片中的音乐也与故事共同建构了电影主题。电影文本与音乐、小说、戏剧文本之间频繁的互动,随即牵扯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
1966年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研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文章《词语、对话、小说》中,首次提出了“互文性”一词,以此表达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的关系。在其后的《符号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互文性”(或文本间性)概念,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此理论问世之后受到了众多理论学者的关注、解释与延伸。值得强调的是热拉尔·热奈特对于互文性的研究,他以结构主义为研究基点,在克里斯蒂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本性”这一概念,指的是文本之间与其他文本存在着明显或者潜在的关系的所有要素。实际上热奈特的“跨文本性”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同属于“广义互文性”,即文本之间的相互进行不断的交流和互换,共同构成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社会和历史文本本身就是文本。当互文性理论进入电影艺术领域中,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影像的文本之间的关联性,后来的文本参照现有文本,现有文本某种程度上源于对其他文本的参照,大多数电影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互文。互文性理论开阔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视野,也使电影艺术从其他艺术形式与文本之间建立更好的互动关系,从而拓宽电影思想与艺术表现力。对影片《驾驶我的车》的“三重互文”的叙事策略进行分析解读,考查互文性理论在多元文本层面对现代电影创作的意义。
一、多文本互文建构故事世界
互文性理论如今早已从文学中跳脱出来,用以解释音乐、美术、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中的不同文本之间相关联系、相互影响的现象。不同文本和媒介间的互文推动了故事世界的不断形成。故事世界需要核心作品成为运转主轴,核心作品通常能够获得最高的市场利润和流行度,或能够成为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而电影往往能够在这两方面超越小说、漫画、电视剧等其他媒介产品进而成为核心。在电影《驾驶我的车》中,小说文本显然不能构成完整电影故事世界的叙述,如果将整个电影故事世界比作一个人,小说文本就是骨骼,电影文本就是血肉,而音乐与戏剧文本就是心脏,而这四种艺术文本之间的互文赋予了它生命。
(一)音乐与电影的互文:形成电影原始素材
热奈特在著作《隐迹稿本》中曾论证过五种跨文本性(互文性)的关系。其中提到乘文本性,表示文本B对蓝本A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是文本对蓝本的改造。改造方式主要区分为仿作、戏仿、扩写、承续等不同类型。《驾驶我的车》电影编剧与小说的作者村上春树是对于音乐极其热爱和敏感的人。他曾公开表示自己作品灵感来源披头士的歌曲,歌里讲述了想成为明星的女人为自己寻找司机,当找到司机时,才告诉他自己没有车的故事。将此音乐文本作为蓝本A,则会发现作为文本B的电影中也出现了相似的桥段。家福因为视力原因让渡利当自己的司机,在此之前他从没让除妻子外任何女人开过这部车,车就是属于家福自己的私人空间。影片的结尾,司机渡利开着本属于家福的车独自出现在银幕上,也互文了“找司机的人自己没有车”这一情节。此外,电影继承并发展了音乐文本的潜在主题暗示。电影作为副文本在标题上选用与原音乐文本一致的题目,引导和调控着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互文性的任务就是要指引读者沿着作者以及编辑者、出版者提示的路径,最大限度地还原“作者的意图”。歌曲的词作者保罗·麦卡特尼曾解释:“DRIVE MY CAR”是对“性”的委婉说法。延展到电影中,“性”的主题被无限延长,影片开始第一组视听序列是妻子音曼妙身材的一个剪影镜头,配合口中陈述的关于“七鳃鳗”的故事。导演刻意将这组带有强烈欲望性的序列放置在前,其目的就是在观众的眼中蒙上一层关于“性”的薄雾。让观众在之后观看中始终思考“性”在这部电影中的含义。
原音乐文本中简单的情节和主题显然不能满足电影艺术的叙事容量。但不能否认电影从音乐文本中积累了素材,并与文本产生了深刻的互文关系。
(二)文学与电影的互文:建构基本叙事框架
文学对于电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电影艺术从兴起之初就能看到文学的影子。20世纪初法国艺术电影运动的领导者们呼吁电影应该从古典文学和戏剧中寻找高尚的题材进行表现,从而改编了一大批大仲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文学的确在各方面滋养了电影艺术的发展。作为最先被应用到文学研究中的互文性理论,在文学与电影高频次互动的影响下,互文性也被学者与创作者拿来研究文学与电影文本之间的关系。文学与电影跨媒介互文推动了各自门类的向前发展,尤其是包含众多文字、叙事与表意符号的电影,从片名、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等都可以与文学文本产生互文联系,从而生发新质。
《驾驶是我的车》由导演滨口龙介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在改编的过程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导演对于文学文本不同的解读或评价方向。在此就要引入隐性元文性概念,它是指不同于蓝本A艺术形式的文本B对于蓝本A进行的解释、补充与评论。电影中整条叙事线索基本沿用着文学文本,但在与司机渡利相遇前,电影增加了家福发现妻子音的出轨和因病去世的情节,这样处理将妻子人物形象具象化的同时也给文本增添了冲突感与暧昧性。在影片的结尾增添了家福提出要去渡利的故乡的段落。作为整部电影的核心段落,主角家福和渡利对往日的和解与释怀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小说中渡利帮助家福走出了困境吗?渡利说:只能由自己想方设法吞下去、坚持活下去。家福却说:而我们都在表演。可以看出小说中家福是没有放下过去的,过往始终是他的心结。但在电影中,家福哭着对渡利说:“我想要道歉,为没有倾听,为不够强大,我想要她回来,想要她活着,想要和她多聊聊,我想见她!”这句话虽是对渡利讲的,但这表明了家福在最后打开了心结,敞开心扉,愿意倾听妻子、愿意沟通、愿意去将自己真正的情感表露给亲近的人。电影的结局才真正地为小说画上句号。
(三)戏剧与电影的互文:呈现复调叙事结构
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在电影《驾驶我的车》中被穿插在叙事的各个重要部分。电影中大段的戏剧排演与电影文本显现出双重故事内容,家福练习万尼亚的对白成为自我表达和建构的方式。对于这种“片中戏”,即第二重叙事层面被包容在第一重叙事层面中,就是溶入式复调结构。可以看出互文理论和复调理论都强调文本之间的联系和有机性,在只考虑文本间关系的前提下,暂且可以将复调叙事结构纳入互文关系的讨论范畴。
当第二重叙事层面的戏剧《万尼亚舅舅》融入到第一叙事层面的电影《驾驶我的车》时,这种复调结构也产生了主题上的互文性。戏剧通过万尼亚的觉醒展现的是人的精神危机与失去生活意义的困境,由此放大到整个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电影中音的出轨、家福的软弱、高槻的愧疚、渡利的迷茫,每个角色经历的事情都是现代人的精神症候。当电影中的出了问题的角色去演绎戏剧中人物的时候,这种病症无疑是加强了,电影的主题也在互文作用下深化。
二、符号间的象征互文
符号与象征在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视野下指它们与被指涉对象间建立的某种关系。它们不指涉单一独特的实体,但唤起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意象和概念,它的意义来源于与其他符号的组合关系。不同文本内符号间的联系不仅会帮助导演完成叙事表达,同时也会激发受众对于其意义的想象。符号互动运用到电影中发展了电影语义表达系统。在这部多文本相互联系的电影《驾驶我的车》中,符号间的互动固然是频繁的,对于符号间象征性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发掘电影的审美与主题含义。
(一)“性与欲望”的隐喻
小说中家福开的是一辆黄色的萨博900,而在电影中呈现的却是一辆鲜红色的萨博。这样的改编似乎只是为了在电影中让“车”这个道具符号更具有视觉穿透力,更适合电影的表现。但是如果把色彩符号置于整个日本社会文化之中,红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日本文化当中“红”(日文“赤”)被赋予了“神明色”“辟邪”“禁忌”“女性”等含义,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红色的负面意义已经逐渐淡去,但是其中代表的“女性之味”并没有被弱化。红色象征年轻女子,“赤”是形容年轻女性散发出来的华丽气息。家福开的车是15年前妻子年轻时送的红色萨博,相比于黄色或者其他颜色,红色更能代表着当时妻子对家福的爱与欲望。而这种强烈的爱与欲望就成为之后家福与妻子之间的壁垒,家福不愿直面妻子出轨的事实也拒绝沟通。也正因如此这辆车也就成为家福心中的“孤岛”。
其次不能忽略的是妻子音讲述的“七鳃鳗”的故事,在这里“七鳃鳗”的故事也形成了独立的文字符号。在家福的叙述中,妻子只有在性行为结束后才会不由自主地讲述这个故事,所以故事的诞生就已经和“性”有了密切的联系。“七鳃鳗”的故事里的小女孩趁喜欢的男孩不在家,经常潜入其家中并在最后一次进行了自慰行为。比照电影剧情,多次的潜入可以理解为妻子音曾多次想要进入家福的心,男孩总是不在家则对应家福拒绝与妻子音沟通,最后小女孩的自慰行为就是电影中音的出轨。所以“七鳃鳗”的故事和其中的小女孩就是音性与欲望的投射。
(二)“现实生活”的讽刺象征
《万尼亚舅舅》当中有一张“非洲地图”,这张地图距离俄罗斯是非常遥远的,没有人知道这张地图上描绘的是对或是错,它代表的是对未来的期盼,就像医生阿斯特罗夫一直在种树,为了之后的人们能幸福地生活。但是遥远的非洲也好,未来美好的生活也罢,都没有对自己现实的生活有任何改善。万尼亚舅舅的觉醒也正是意识到了自己在现实生活的无意义性,所以作为道具符号存在的“非洲地图”象征着对现实和当下生活的讽刺。
电影中家福知道妻子背着自己频繁地出轨,家福却选择视而不见,甚至逃避与妻子的沟通。但是家福又经常和妻子音录制的磁带不停地对台词,在家福的精神层面上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自己内心情感的释放,将自己对妻子的不满以万尼亚舅舅等身份发泄出去,透过磁带这个媒介实现自己与妻子沟通的欲望。所以当家福不再表演万尼亚角色的时候,还保留着练习台词的习惯。磁带这个道具符号浅层上指代的是妻子音但是深层次上却是家福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同时是电影中渡利父亲的人物符号也与“非洲地图”起了相似的功能。
电影中渡利的父亲是缺席的,没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我们只能从渡利的叙述中发现这个人物。家福问渡利:“你计划留在这里吗?”渡利回答:“我姓恒理,来自我的父亲。这在岛根和广岛都很常见,虽然我从未见过他,甚至不清楚他是不是还在世。”这句对白的含义就是渡利还是想寻找自己的父亲。但是她从未见过父亲,她又该怎么寻找呢?寻找父亲这件事本身就是荒诞的、讽刺的。父亲对她来说更像是一个“彼岸”似的符号,追求“彼岸”但是永远到不了“彼岸”。就像现实生活一样,人们总在追求精神的启示、人生的目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没有这样的答案。
三、人物形象设置互文
戏剧《万尼亚舅舅》作为电影的一部分来看的话,万尼亚与两个扮演者家福与渡利、索尼娅与扮演者李允儿是直接相关的。把它看作是独立在电影文本之外的戏剧文本的时候,人物间的互文关系就会被延展。对于电影来说,基于人物间相似的世界观、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的互文,使不同人物跨越艺术媒介、时间与空间限制而产生深刻的含义。对于观众来说,这种互文方式打破了单一文本的静止状态,增强不同文本互动的同时也将受众拉入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激发观众对于文本含义的理解和思考。
(一)万尼亚人物形象
戏剧文本中的万尼亚是一个可怜的人,他将自己的一辈子无私奉献给了自己的姐夫谢列勃里亚科夫教授。他把教授看作是艺术、文化、精神的领袖并愿意为之牺牲自己,可是当退休后的教授回到庄园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崇拜的原来是这么的空洞与虚伪。万尼亚形象象征着失去生活意义后发狂与陷入精神危机的人。
电影当中的家福与万尼亚有相同的情感际遇,对于爱人的爱而不得、对情敌的恨与报复、对救赎的渴望。家福通过万尼亚这个角色之口来讲出埋藏在面具之下真实的“真我”。通过台词来研究会发现这个“真我”下的家福是有愤怒的时候(家福:“你毁了我的生活!我因为你的过错牺牲了我的生活!你是我最可恨的仇人”),是有软弱的时候(家福:“索尼娅,我很痛苦,如果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痛苦的话”),也是有无力的时候(家福:“我现在47岁了,如果我能活到60岁,那还剩下的这漫长的13年让我怎么往下过啊”)。这样的结构方式,实现了双重身份下的不同文本间人物的对话,加深了戏剧与电影互文的深度。
电影中的角色高槻也关系到了戏剧中的万尼亚。在戏剧中万尼亚曾因愤怒开两枪射向教授,失败后又偷医生的药想自杀,但是都没有成功,万尼亚控制住了自己。电影中的高槻与各式各样的女人发生关系、爱上了家福的妻子音、遇到有人偷拍的时候的暴力倾向,这些事情让家福认为他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也就有机会能够进入万尼亚的角色当中。就像家福说的:“正因为这样你可以屈服于契诃夫的文本、屈服于演员搭档、屈服于自己,回应文本。”当万尼亚与高槻实现互文后,万尼亚的精神形象再一次被加强。
(二)索尼娅人物形象
索尼娅在戏剧中更是让人喜爱的一个角色,她虽然承受着失去“偶像”的痛苦和爱而不得,但是她始终非常坚强,一直在照顾周围的人也安慰着同样痛苦的万尼亚舅舅。索尼娅平衡着整部戏剧中各种力量之间的碰撞,就如剧中所说:“她是一个能干的女孩儿。”她象征的就是拯救,一种将人物从枷锁与困顿中解放出来的力量。
电影《驾驶我的车》中妻子音绝大多数时间是以声音的形式存在于电影里。在妻子死后留下的磁带中,录入了《万尼亚舅舅》当中除万尼亚外其他角色的台词。电影在选取段落进行表现的时候很大一部分都是妻子对于索尼娅角色的对白,妻子音成为电影里第一位索尼娅。回顾电影,妻子音承担着自己的女儿的去世以及家福对自己封闭的巨大的痛苦,音的出轨一部分是自己的欲望使然,另一部分希望通过自己的出轨,让家福打开封闭的心,重新注意到自己。音为家福录制的磁带刚好在人物对话的间隙能够让家福将自己的台词说完,也许音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甚至比家福更胜几倍。音像剧中的索尼娅一样不断试图拯救痛苦的家福(万尼亚)。
李允儿是戏剧中的索尼娅角色的直接扮演者,允儿原来是一位聋哑舞者,因为身体原因流产了,不能再跳舞了。允儿的经历是痛苦的,但电影丝毫没有将允儿的痛苦放大,现在的允儿有一位爱她的丈夫和喜欢的戏剧演员工作。允儿的聋哑则映照的是剧中索尼娅的“失语”,索尼娅经历了很多的不公与痛苦,她为自己的爸爸和医生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可是她从不抱怨。在电影中允儿的痛苦遭遇与“失语”者形象和索尼娅形成高度的互文,成为电影里第二位索尼娅。这种互文性也衍生出导演对于沟通的看法:沟通不需要语言,重要的是对方的反应。
索尼娅在契诃夫的剧本里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村上春树的笔下也是“有点丑”,电影中的渡利就是这样的形象,和其他人比起来都是有点丑的。渡利作为第三个索尼娅与原文本重合度最高,同样失去了母亲并且在艰难的生活面前,她比家福更加坚强。在电影叙事中,也是渡利帮助家福打开了心结完成了救赎。
将戏剧与电影文本对照解读,电影文本充分地运用了互文关系来建构主要人物形象,在互文性语境的场中人物的符号特征都被强化了。不论是万尼亚形象代表的人精神困顿现实,或者是索尼娅形象的善与拯救,电影融合吸收后让单薄的人物关系和形象更加丰富、立体。
四、主题互文下的悲剧艺术
主题互文性指一个语篇的互文本是用以理解的所有他者文本,其中一些文本中的共享命题内容的相同主题模式,语篇之间具有“共同的主题”被解释为主题互文关系。这种主题间的互文性可以被分为共同主题和主题指涉两种类型。电影《驾驶我的车》在主题上与戏剧和小说不同程度产生了互文性,尤其当把戏剧文本当成电影文本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时候,戏剧本身的主题融入了电影之中。这种主题互文也增加了电影文本的多义性,扩大、加深了电影表现的广度与深度。
(一)精神的困顿
在《万尼亚舅舅》中这股悲剧感集中体现在剧中人物精神的困顿上。剧中的万尼亚为教授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当偶像形象坍塌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在这不属于自己的47年中,他同样也失去了爱情。更可怕的是,知道真相后的万尼亚该怎么度过自己的余生?他想反抗、毁灭或死亡,但不论是杀掉教授或者杀死自己都失败了,最后只能答应继续供养教授。荒诞的现实反映的正是万尼亚精神的困顿。在电影里,家福为了不让妻子深陷在失去女儿的痛苦中,他把所有的爱寄托在音身上。家福以为音也爱着自己并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当他发现妻子出轨后,家福愤怒但怕失去妻子,一直逃避与妻子沟通。家福恐惧知道真相后会像万尼亚一样失去人生的意义。正是这份恐惧和愧疚让家福陷入精神的困顿中无法自拔。人物在精神与生活上的困顿是滨口龙介想要通过《万尼亚舅舅》和《驾驶我的车》讨论的共同主题之一。
(二)“本我”的觉醒
关于“本我”的觉醒是电影与戏剧讨论的共同主题之二。“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哲学的根基,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谈论的哲学话题。认识自己的实质是本性的探讨,也就是弗洛伊德理论中关于“本我”的概念。“本我”的觉醒代表的是人直面真实自己的勇气。《万尼亚舅舅》中“本我”的觉醒表现在教授虚伪偶像的坍塌,那电影中家福的觉醒则来自对病逝妻子的深深愧疚。家福在妻子生前一直在戏剧中扮演万尼亚的角色,妻子死后,家福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再继续表演万尼亚了。家福说,“契诃夫的台词是危险的”,它能将演员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展示出来。而真实的家福,心底存在着对妻子的爱、对她出轨的恨,也带着对软弱的自己拒绝和妻子沟通的痛苦,这一切构成了家福的“本我”。影片结尾家福与渡利的对白:家福:“我本该受到伤害的,我放任一些真正的东西溜走了,我被深深地伤害到了,分散了注意力。可是,因为我假装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听从我自己,所以我失去了音。如今我明白了,我想要去见音,如果这样做,我想跟她大喊大叫,斥责她,因为她一直在欺骗我。我想要道歉,为没有倾听,为不够强大。我想要她回来,想要跟她多聊一聊,我想见她。”家福的释怀就是源于他对于自私、软弱、封闭的“本我”的接受。
(三)语言的消解
语言的消解是滨口龙介通过电影与戏剧的互文表达的另一个主题指涉。不同于共同主题,主题指涉是通过在电影关键场的表达中直接演绎戏剧文本实现的。电影中表演的《万尼亚舅舅》是一群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演员,他们说着日、汉、英等不同语言,甚至其中索尼娅这个关键角色是让韩裔聋哑人扮演的。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懂对方的语言。滨口龙介说:“如果对话失去了沟通意义,我们就不得不强迫自己专注于反应与情绪上。”导演通过这个形式表达对传统语言对话和沟通形式的思考。人与人的沟通、情感、关系会存在各式各样的爱恨与隔阂。语言或许并不是传递情感最有用的方式,最好的是“行动”,是让对方感受到你为彼此关系发展付出的行动。这种行动比传统意义上的沟通要更加关注对方给予你行动的反应。人只有敞开心扉感受对方的情感并予以反馈,人与人的生活才不是无意义的。
本文从互文性理论出发,以电影《驾驶我的车》中对于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和戏剧《万尼亚舅舅》的“三重互文”现象进行分析,通过电影文本与其他艺术文本的互文激发了电影表现潜力,让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三重文本之间所隐藏的信息与导演的创作意图。同时,电影《驾驶我的车》的成功,也说明了这种文本互文仍然是当下电影创作中具有生命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