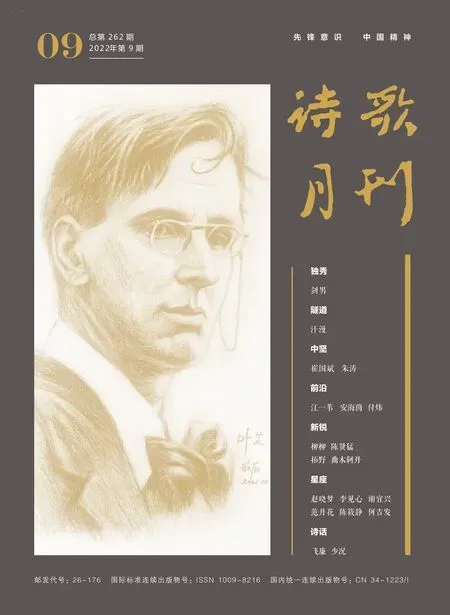明亮的中午(组诗)
2022-09-22剑南
剑南

有声诗歌
春天的庭院
柳条如一件鼓满风的宽袍
悬挂在大青山水边
庭院中老父亲仍在准备粗茶淡饭
老米酒仍立在临窗矮柜
燕子重返去年旧巢
仍是甜蜜、恩爱的一对
老母亲仍在老父亲一侧生炉煮药
听到燕子轻轻呢喃
他们仍旧把燕子当成自己的儿女
今年的春真是浓稠
月季都如胭脂一般殷红
像那些年流行的天鹅绒
他们忙完手头事情
又开始整理庭院的花草树木
当他们站在梨树下,两束
如雪的白发如早前的梨花避过时光围剿
在庭院中又一次开放
散步
回南江河小住,每天清晨都能碰见
一个在河边散步的老人
老伯每天都起得早啊。但他的回答
让我吃惊:每天都是今天
南江河从幕阜山西侧拐到这里从来
就是这样安静地流淌,它
可以不经过这里,直接顺着西侧的
开阔地前往平头坝,但事物的改变
何曾都有它清晰的道理。我
喜欢这个散步老人的话:每天都是
今天。我喜欢这个老人重复的
不需要计算的生活,就像南江河拐到这里
日复一日地躬着腰身
山中细流
两条不知所终的细流从层积的落叶里
涌出来,这突然冒出的清流
在一片高大、铁青的冷杉间各自流绕
像轻抚着森林安静辽阔的睡眠
有克制的欢乐,也有无法掩饰的冷寂
不像高处的树枝,细叶交织
明亮的中午
在一个明亮的中午,五十岁的中午
我在烟雾中看见
四十岁的自己正匆匆赶往一个地方
依稀是一场葬礼
离世的人已睡进樟树岭最好的棺木
我在一群表情严肃的人中间
刹那间两鬓斑白
而不远处,三十岁的自己正肩扛着
一袋粮食走在山路上
因不堪重负,人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跌进路旁一道沟壑中
醒来时,却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
坐在中学时的教室里
教室百叶窗外
白天和黑夜走马灯般交替
我抱着用米袋改做的书包坐着
又突然看见少年时的自己
在黄昏山坡一边放牛一边看小人书
隐约听见离世多年的父亲
在山下焦急地喊我,我想大声回答
张开嘴却发不出一丁点声音
路边摊
春天有一条长长的飘带从江边飘到
公路一侧,路边山坡上
垂下的白花檵木飘出淡淡的花香
塑料布支起的路边摊内
左边是黄瓜、辣椒、茄子和番茄秧
右边是一小篮的地米菜
苗条柔弱的蔬菜苗,青绿的地米菜
一个清亮的春天的早晨
显得新鲜而芬芳,但相对塑料棚内
忙碌的母亲,我更喜欢
那个伏在方凳上写作业的少年
青春的脸上长满青春痘的少年
当他偶尔过去帮母亲分拣各种蔬菜苗
风就替他翻开那些彩色的书页
刮春泥的女孩
下雨了,女孩坐在门前刮布鞋底部的泥土
雨中开满了新年的桃花
其实李花也开了,在河两岸,和桃花一样
油菜也披上金黄明亮的衣裳
但女孩只顾用瓦片轻轻地刮着鞋底的泥土
女孩刮下的泥土中,有草屑、落叶,也有花瓣
我看见女孩刮着刮着脸颊突然变得绯红
花朵一样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交响
森林中有无数件乐器。有流水、洞穴
有通天的闪电、彻地的暗泉
有开放的花、结籽的果
也有飞禽走兽和拔节的苗、生长的根
蛇爬上树干,众鸟停止鸣叫
像一曲单弦被风吹动。流水来到崖边
枯枝从头顶坠落,像一个人
到了命运紧锁的中途,一管洞箫从他
胸腔中伸出。从悲恸大响动
到细微深呼吸,我喜欢森林中这样的
磨合和练习:既不过分压抑
也不恣意放纵,就像
此刻山中,一群登上栎木光秃枝头的灰喜鹊
突然带给我花开满树的喜悦
秋天的河岸
河流瘦了,像一个老生唱起自己悲凉的身世
落叶落在青瓦上,无所依靠
落在蛛网中,被看不见的东西纠缠
落在流水上的,不得不接受随波逐流的命运
好像薄雾笼罩的黄昏是虚拟的
好像彼岸不过是眼中映出的虚幻的镜像
好像万物没有在风中松动
沙石没有在下陷,肉身没有空洞一些
落木没有被夕阳羁押,无情的流水年年从身边流过
也从不曾有人从中打捞起故乡的物什
油菜花田
在一大片油菜花中
一个农民挑着粪桶正在穿过
他要穿过油菜花田
去浇灌他的青麦苗
油菜花中的蜜蜂在他经过时
嗡嗡地飞得远远的
退避在旁边的人也
紧紧捂住自己鼻子
一片油菜花中飘着新鲜的臭
挑粪桶的人红着脸
心怀愧疚放慢脚步
只有他的矮秆小麦
还站在比油菜花田更远的山腰上
齐刷刷地伸着长长的脖子
松鼠
在一片松树林中,一个小男孩看见松鼠
在搬运松果,瞪大了眼晴
而松鼠仍在他面前来回搬运果实
我见过松鼠的警惕和机敏
只要人一走近,它就会收起髙翘的尾巴
迅速躲进树林或爬上树干
但在那一刻,我不知道松鼠和小男孩
彼此是如何做到相安无事的
远远望去,只见小男孩的眼睛里
有一汪清亮的水,看上去和短暂不安后的
松鼠的眼睛没有什么两样
梦中遇见父亲
昨夜梦中,我梦见四十年未见的父亲
穿着一件绿色大衣出现在一个嘈杂的火车站
隔着十来人距离,我怎么也挤不过去
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个人孤独地消失在人流中
想起父亲生前说火车的命其实也很苦
只有快速奔跑才能扛起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
我盘着双腿坐在黑暗中,只觉隔着死亡的距离
一列火车正在我体内轰隆隆地开进又开出
南瓜秧
老屋倒了后,母亲在废墟上栽了几株南瓜
春天刚刚过去,就爬满了荒芜的残垣
废墟上的南瓜长得茂盛
这个现象母亲也解释不清楚,我想是不是
老屋曾收藏过它们,它们也会
和土屋日久生情,当老屋倒塌
南瓜秧置身其间,它要用藤蔓
紧紧抱住与它相依为命的砖瓦,为它们开出
金黄的花朵,纪念那些逝去的光阴和生命
感谢雪使黑夜一再消隐
向晚的雪正在下
镇上店铺门扉紧闭,屋顶上的白烟
越来越浓,姐姐牵着我的手
去老瓦山给重病的姑妈送药草银背蕨
我们赶在黄昏前到达严家塅
感谢雪使黑夜一再消隐
黑蚂蚁
几只黑蚂蚁从柘树根部爬下来
蹚过草丛来到我的脚边
相对小蜥蜴以及嗡嗡叫的野蜂
好像只有蚂蚁是无畏的
它们爬上我的鞋
这对它们来说可能是翻山越岭
要用去漫长的时间
我的脚在其间动了一下
我看见它们立即剧烈晃动起来
而当我止住脚的动静
它们很快就从鞋面爬上了裤腿
并在一块褶皱处停了下来
褶皱的上方有我刚才吃饼干时
落下的一些饼干屑
蚂蚁们爬上去又落下来
每一次的攀援都以失败告终后
我看见它们倔强地昂着头
像借用了人类共同的姿势
想起那年父亲带他去玉门关
春天来到,日子越来越长
七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彻底暗下来
少年想起那年父亲带他去
甘肃玉门关,晚上十点半
太阳还挂在天空,他看见茫茫戈壁
在阳光蒸腾起来的水汽中
如波光粼粼的大海,不理解为什么
古人要说它春风不度,并
将它描绘成一个孤远、荒凉的世界
父亲说日子的短长是生命
与生活周而复始较量的结果,唯人
要永远被它所驱赶
那年少年十二岁,他不知父亲生命
只剩下九十余天。他问父亲
人生怎样才算是完美,父亲告诉他
蓬草随风飘摇是一生,胡杨
千年屹立不倒也是一生,万物都有
它刚刚好的一生,只要短到
可以接受,长到可以忍受。至此
他才明白,为什么时间恒在,却总有人
将它剪成一截截、一段段
走在峡谷
走在峡谷,看见一条小溪从层积落叶中流出
仿佛自己浑浊的灵魂
也从腐旧的生活中缓缓爬了出来
看见一棵枯松倒挂悬崖
仍不悔自己半生借着蛮力与命运倔强的较量
看见一粒草籽被鸟雀带往天空
坚信不知所终的飘泊终有它宁静的去处,把
生活的奔波寄存于天空中的白云
像获得自由,把生活的孤寂寄存
水边野花,像在经年咆哮的时刻找到幸福
这个走在谷底的中年人,再
没有往下的余地,但他仍然走得坚定而从容
人们站在高高的谷顶,只看到他
如一只小小的蚂蚁在蠕动
致从丁香旁走过的少年
丁香花已经开过,只剩下嫩绿的枝叶
山中没有雨巷,也没有油纸伞
那个紧锁着眉头、从旁边走过的少年
他是否感觉到寂寞是有长度的
他是否也和我一样,看见一些曾经失去的东西
在时光中打着一个又一个的结
紫藤
几根细小的茎,嫩嫩地倚靠在树上
你开始以为它是柔弱的
那样缠绵环绕
几乎可比拟人间的爱情
但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看见它越缠越紧
绳索般紧勒在它所攀附树木的躯干
它也开花,一串串
宛如一条紫色瀑布从树梢悬挂下来
明亮、干净、美丽
但少有人见它攀附树木身上的勒痕
一道道,像被粗壮铁条所捆缚
紫藤花开年复一年
它对树的缠绕也从树身到枝丫
当我们再也看不到
这棵树木重现它昔日的冠盖婆娑
樟木
一棵被雷霆击中的樟树
被堂兄锯成五截,三截粗的被矮凳架起
两截小一点的被置于地上
失去根、在去年早春雷霆中死去的樟木
在今年早春的时候居然起死回生
置于地上的两截在腰部各长出几簇新叶
那离开地面、被架在矮凳上的三截
也攒聚着体内力量长出了嫩芽
灰椋
天还没有暗下来,河边树上
还停着一只灰椋
它对着残云在水中斑驳的倒影
对着在平静浅水滩中
自由游动的小鱼
以及小鱼身边悄悄出现的月亮
在枝丫间欢快地跳跃鸣叫
像一个贪玩的少年
唯有不复返的时光如夕阳远逝
如灰椋在这个世界
看月色动江流

有声诗歌
一枝桔梗花
那一年春天的黄昏,为风中
止不住咳嗽的母亲
我毁掉一群正在开花的桔梗
用它们白嫩的根
熬了一碗水端到母亲的床前
其时天已暗了下来
寂静夜空隔窗送来一轮月亮
母亲用嘴轻轻吹了吹
月亮就像一个蛋黄在碗中轻轻荡漾
母亲问桔梗花是不是
比去年好看一些
是不是还像天空一样瓦蓝
说祖母刚刚在梦里向她问起桔梗花
祖母的头发乌青
就像她记忆中年轻时的模样
那是她的最后一个春天
皎洁的月光和桔梗嫩白的根
都没有抵消肺热
带给她的胸痛和夜半的辗转反侧
只有祖母用一枝晶莹的、蓝色桔梗花
给她送去安详宁静的睡眠
院子里的衣服
院子里晾上了衣服
一家人衣服,棉麻的或化纤的
可从衣服滴水速度看出
化纤的簌簌往下流
棉麻的则一滴一滴缓缓往下滴
从衣服的成色看
这家有一个懂得生活的女主人
懂得生活的舒适度
也懂得生活中的情趣和品位
晾衣绳上依次是
男人的白衬衣、牛仔裤
小孩的红色圆领衫
然后是一条洁白的连衣裙
只有小孩藏青色西装短裤是化纤的
从衣服的大小看
小孩不瘦
男人比较壮实
女人还保持着苗条的身材
修剪
一棵梨树从栽下开始,就以自己的方式
在修剪着天空,以枝、以叶
也以花朵
从独干到分杈,从叶初长到枝繁叶茂
从简单的美到冗长花枝
带来的美的累赘
它总是不断改变着天空的色泽和构图
我看着它在屋后的山坡上长大
它结果那年我的父亲离开人世
三十年后我的母亲经它身边被抬上山
从它的头顶往回望
它也以自己方式在修剪着人间
山变得越来越矮,天空抬得越来越高
它有花团锦簇,也有
枯枝轰然坠地,它头顶流云去而复返
它的根茎是一只只手
用力把枝干往回拽,像世间所有生命
最终都会尊崇时间对它的修正
回到删繁就简,但
不以那外来的、冒着铁腥味的刀和剪
除夕夜
今夜,我的爱到了尽头,明天是新的爱
它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新的
今夜,我的恨到了尽头,明天是旧的恨
它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旧的
满头白发的母亲在火塘边讲述
一年又一年的除夕,不同的是远远超过
怨恨的爱使甘苦参半的生活
坚持到了今天,相同的是时光马车有着
四个飞转的轮辐,却把人生
赶往宽阔而荒凉的断崖,要经过
多少爱恨的交织,才能到达和白发相配的年纪
我想是我记忆中深藏的、而母亲
省略的那些人情冷暖,以及母亲讲述中
对生活的深深理解和同情
隔窗远眺
透过窗可看见湖水和挂在它腰上的观澜亭
湖面是碧蓝的
不是沧浪之水
不怀沙,不濯污浊之躯
也不洗泥泞之心
昨夜狂风肆虐吹过,浮萍堆在一起
还有夜晚的模样,昨夜雨水漫上她的脚踝
垂柳还在为她泛起的波澜心旌摇荡
但此刻,一切都是平静的,像一个人懂得
如何在喧嚣中和自己安然相处
构树
不是刻意栽下的景观树
它被留存下来
是因为旁边的红花檵木
和白蜡都没有熬过
八年前的那场大雪
它却经受住了当时的寒流
它是小区唯一的构树
既不粗壮挺拔,也不丑陋
属于最平庸的树种
没有人见它开过花
果实刚开始像绿绒的线球
晚秋裂成深红色
看上去让人垂涎
实际上连鸟雀都不怎么啄食
因为来历不明
有人说它的成长是一个错误
但它却一天天用它藏着的鸟鸣和婆娑的枝叶
把我们从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救出
蜉蝣
蜉蝣随水而栖,小而透明的身体
有时停在一截小小草屑上
有时停在水边长满青苔的石头上
当它们在晨光中振翅而飞
就不再进食,也不再收拢起翅膀
直至夕阳沉落,生命消亡
蜉蝣的生命短到不知一天为何物
世人多借蜉蝣生天地间
来表达对人生短暂无常的感慨
但只有少数人知道,蜉蝣
超出人类的价值在于:它们短暂的一生
避开了属于夜色的部分
河床上的石头
河流断流,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流水
还有看不见的水流在其中穿梭
但人们不曾想到河底居然遍布着石头
这些沉在水底的石头并不漆黑
有的圆滑,有的仍保持着锋利的棱角
有的在淤泥中黯然失色
有的在流水的冲洗下,呈现出
绚丽的图案,让人感觉
并非所有事物都是环境的结果
河流两岸是分属不同省的两座村庄
从前它们往来要绕道距此七公里处的
下河大桥,而此时河底的石头
无论美丑、方圆,色泽黯淡,或炫目
它们都在铺陈着这条曾经的沟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