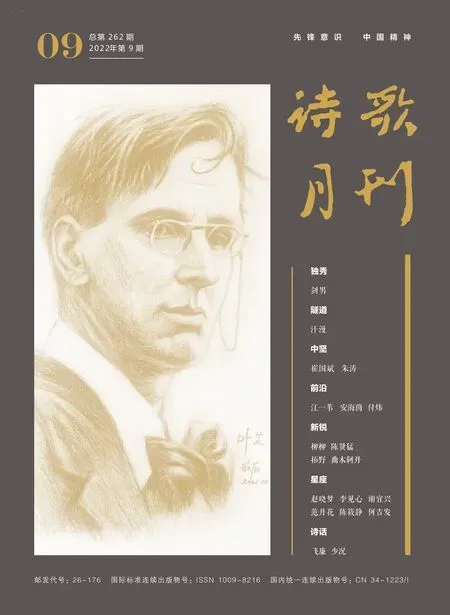我的中原与江南
2022-11-10飞廉
飞廉
读高中的时候很喜欢盛唐的边塞诗,同时也着迷晚唐五代以及两宋的婉约词。一边是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另一边是李煜、韦庄、晏几道、柳永。似乎矛盾,又自然而然。“一片孤城万仞山”和“人人尽说江南好”对我这位出生在中原小城、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有着同样的蛊惑力。
1997 年高考填志愿时,父母在瓜田劳作,教化学的班主任也不能为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留下我独对命运的苍穹。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正是我读过的这些看似无用的古诗词,正是它们为我营造的有关未来的辽远想象,在关键时刻,推波助澜,决定了我的命运。那天,一定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悄然战胜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于是我放弃了兰州,选择了杭州。于是,我因此成为一个诗人,就像菲茨杰拉德的那句话:“诗歌一定是一个北方人关于南方的梦。”
中国自古习惯以秦岭、淮河界分南北,我出生在淮河上游的颍河之滨,地理、心理上都以北方人自居。《世说新语》中有不少南北之辩,最著名的就是陆机陆云入洛所引发的北方士人的围攻。我读大学时,也经常跟同寝室的海宁人Z,代表南北,展开过多次争论,我因此写过一篇短文《南北的优劣》。读大学时,我真诚赞美过一个南方女孩:“她那张脸,正是沈约那一脉古老的血统在悠久岁月里所能造就的最完美的作品,又被江南的斜风细雨浸润和滋养……”
十九世纪法国人丹纳的《艺术哲学》把地理环境当作影响文艺创作的三大要素之一,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和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都从地理学的角度讨论了南北写作的异同。南方人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直呼:“南人之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方人远甚。”南方人鲁迅则非常看不起以南方人为主力的创造社的才子们……这些观点和看法,或许只适合过往某些特定的时期。今天这高科技、大融合的年代,往往南就是北,大西洋也是太平洋,所有的高山大川都近在家门口,所有的经典著作在图书馆都能找到,今天的写作跟之前大有不同,地理学对写作的影响恐怕也更为复杂。
我20 岁南渡,迄今24 年过去了,他乡羁旅的日子超过了故乡,还乡反而水土不服。外表也越发北人南相,如朋友所说“比江南人还要江南”,然而内心深埋的北人血性,只需二三两酒激发,整个人便从“齐瑟和且柔”一飞而入“秦筝何慷慨”了,毫无遮拦的开怀大笑也是藏不住的。诗人沈苇20 岁出头离开江南腹地湖州,在新疆一待三十年,走遍天山南北,烈酒喝了好几吨,乱蓬蓬的大胡子,乍看上去完全边疆化了;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写诗时的敏感、细腻,他待人的温暖、周到,都是典型的江南因子在他身上的持续发酵。
林升“暖风熏得游人醉”和袁宏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只有到了江南,才能理解他们描绘之真切。我在西湖南岸的凤凰山下住了八年,先后又在西湖北岸的宝石山下住了八年(其中三年多,我几乎每天到断桥、白堤散步),江南的软风香雨,我算是从骨子里领略到了。我写了一大批具有杭州地域性的“凤凰山系列诗歌”“宝石山系列诗歌”,以及“钱塘江系列诗歌”,因此被很多人误读为“江南诗人”“新古典诗人”,真让我有点啼笑皆非。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自古就是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今天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有活力的区域之一。当然,今日之江南早已不是六朝之江南,那时写诗多是王孙贵族乌衣公子的消遣,孤寒如鲍照难得一见,“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文风也基本上绝迹了。今日之江南是市井江南的延续,安逸、享乐之风,才子气(文人气),则一以贯之,这才是身在江南的诗人首要警惕的。我常年往来南北,江南诗人和中原诗人都认识不少,大多数江南诗人因地域优势在生活上相当安稳富足,不少中原诗人生活上则相对清苦,因此两方诗人在写作上的关注点也自然差异很大。我很幸运,沾了南北的光,就像中原诗人罗羽所说:“飞廉是被时光赐福的诗人。从河南到浙江,‘龙门不见兮,云雾苍苍’,再到北宋联结南宋的山高水长,在历史、地理空间的转换中,飞廉拥有了两种地域文化所带给他的经验密度。”
我也一再提醒自己,在随笔《细枝低云集》中反复写道:“身在江南,时时要跟这纸醉金迷,软风香雨斗争,跟苏白两堤,凤凰山,二十四桥明月夜,跟塘栖枇杷,黄岩蜜橘,西湖龙井,跟秦少游,唐伯虎,早年庾信……”“江南梅雨天,体内的湿气和阴郁太重,要不停读李白,看鲁本斯,喝雄黄酒,拔火罐。”“江南病。老杜,巴赫,黄宾虹,海明威,莎士比亚,鲁迅……数剂共服,或可愈之。”“要努力做一个世界主义者,纵然像福克纳、乔伊斯那样只书写邮票大的家乡,也可以辽阔如大海。”
还乡,是我免于江南病的天然屏障。有句老话:“隔一条江,像隔着一个朝代。”更何况,从江南到中原,隔了无数江河。每次还乡,回到这自古多灾多难的土地,南北差异之剧烈,每每引发我内心的地震。举一个发生在我父母身上的很小的例子:这几年,我乡老人热于织渔网,我母亲技术娴熟,大概两小时织一张,每张4 块钱,一天腰酸背痛最多可挣20 块钱。跟有的互联网公司动辄几万亿的市值相比,原始而虚幻!然而,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现实。在河南,在中原,在我的故土,我不能放纵我的笔流于逸乐。
习诗的头几年,我写了不少乡情诗,写中原小乡村的风物人事,但因找不到那不得不写的核心所在,很快就写不下去了,这些诗也早已被我销毁了。近年来,我对家乡、对河南、对中原有了深入的认知,我从历史空间、文化层面来重新思考和理解它。以我家门外这条从许由年代流淌到今天的颍河为例,我渐渐意识到它对于我的重要意义。之前的我,正像《打鸣记》这首诗所写:
13 岁之前,我从未出过远门,完全不知
三里之外,一条著名的大河已流了数千年,
脚下这片土地,也早在4500 年前,
就被伏羲定为世界的中心,之后又发生了无数
惊心动魄的大事。——13 岁之前,我俨然
一只小公鸡,在那小小庭院里,鲜亮地打鸣。
而今颍河在我看来:
出生在颍河边,
这构成了我今生最大的寓言。
年过四十,秋风在我的头上紧吹,
只有写出庾信的杰作,
才不辜负它数千年的长流。
——《冬日怀颍河》
这条著名了四千多年的大河,
有一种老子孔子式的伟大庄严。
战战兢兢,我这水边长大的小人物,
多么希望自己微薄的努力能无愧它的教养。
——《春夜崎岖集:颍河骑行》
现在,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之所以成了一个诗人,一定跟颍河数千年的流水有关,一定跟我家乡的建安七子应玚有关,跟庄子有关,跟袁安有关,跟洛阳、开封这两座曾经伟大的城池有关。“现在,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就是世界的中心,这和我童年、青年时代的想法恰恰相反。”(奥尔罕·帕慕克:《父亲的书箱》)“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发现、确认了我母地上的那个小村庄,它确实是中国的中原之中心,而中原又是中国之中心,中国又确实是世界之中心——一句话,那个村庄不仅是中国之中心,也是世界之中心。”(阎连科:《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而今,中原题材重新成为我写作的中心之一,那万古“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颍河,将把我的这些诗引入绵绵不绝的《诗经》《古诗十九首》传统中去。
中国文学史上有几件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大事:苏轼、陈子昂的出川,杜甫、陆游的入川,陆机陆云兄弟的奔洛,庾信的羁旅北朝,贾谊的客死长沙。这几件事,都指向了文人的迁徙与作品的流变这一主题。作为一个在他乡写作的诗人,这几年我逐渐认识到中原对我写作的另外一层深意。
早些年,我经常念叨李商隐的“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认为这是写游子境遇最好的两句诗。而今,我确信,流浪虽然没有尽头,但故园永远不会荒芜,只要颍河的流水还在,我就会继续写诗。最后用我的一首诗《向秦岭淮河致敬的诗篇》来结束这篇短文,作为一个跨地域——中原与江南——的写作者,这首诗表明了我的写作追求:
今晚,我失眠在横断山脉一根断断续续的纬线上。
这些年,一列秦岭淮河走向的雕花木床,
我安稳地沉睡,做梦,苏醒,
露往霜来,风化为秦岭淮河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我,一块界别南北的青石,
渴望把自己的诗篇熔作谢脁和杨衒之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