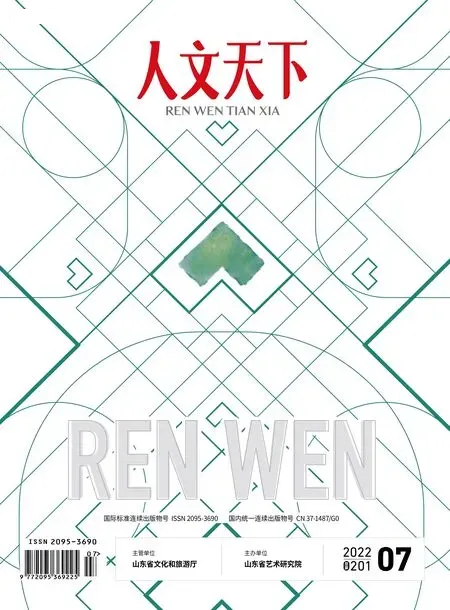沈曾植书法碑派来源考论
2022-09-15■王谦
■ 王 谦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字、别号多至百余,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北京。沈氏为清晚期学术通人、“同光体”代表诗人,亦是书法名宿,其书学理论、书法造诣在书法史上均占重要地位。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中述沈曾植晚年习书情况:“暮年作草,遂尔抑扬尽致,委曲得宜,真如索征西(索靖)所谓‘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披离之美。有清一代草书,允推后劲,不仅于安吴为出蓝也。”这已隐然将沈曾植晚年的草书创作视为清晚期书法之最高成就。
考察沈曾植书法实践之路,早年由科考所需以及家族书法传统影响,取法帖派作品;中年之后,接触碑刻,在写帖的同时亦致力于名碑的临习;晚年综合一生学术修养,同时由彼时新出土之简牍作品而吸收其中的章草元素,以浑厚的碑帖融合基础,创出章草新格。
沈曾植晚岁,常对碑、帖两者作对比、互证,实际已打通两者在概念层面上的壁垒,并不偏执于专习帖或专习碑,这也正是他“不取一法,不坏一法”的诗学主张在书学借鉴上的实践。在学术通人的治学与习书理念中,任何一个个体的、局部的“一”,皆可与学问、书道的整体的“一”相融通,但同时任何一个个体的、局部的“一”都不可能等于或取代整体的“一”,但整体的“一”却因其所融汇的个体的、局部的“一”的增多,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境界。
如图1 所示,为沈曾植晚年书法作品。欣赏寐叟艺术,自然应将其作为整体的“一”来对待和品赏;当将寐叟晚年书风的形成元素,以分析手段将融通的整体打散而一一解绎,则会发现其中来自碑派的营养占据了尤其重要成分。寐叟最迟在三十多岁时,已经研究、用力于碑学。唯寐叟素不喜自我标榜,加上斯时一方面任职于朝廷部司,另一方面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故少为世人所知。在寐叟晚年书风的形成过程中,取于碑派者,主要有汉隶、魏碑、“二爨”三大来源。

图1 沈曾植书法作品 1921 年作
一、取法汉隶
对楷法与隶法书写效果的不同,清末书法家大多有较为真切的体会。郑孝胥曾作较具体的论述,如其在1915 年9 月16 日的日记中写道:“用楷势作书,遇生纸则墨不入,所谓笔不能杀纸也;若用隶书下笔取势,则笔倒墨注,挥霍自如,此间未达一间,久持当可造自然。临造像中活泼变化诸刻,用草隶法似颇得手,以作《瘗鹤铭》亦有合。”隶书与楷书的运笔差异,最主要的在于隶书运笔能够铺毫,即“笔倒墨注”。借鉴隶书笔法,将“笔倒墨注”效果用到隶书之外的书体,是清中期以后碑派书法家在用笔上的一个普遍倾向,观郑孝胥书法,即属于这一方法的实践。以“用隶书下笔取势”“笔倒墨注”的用笔特点来看“寐草”,可发现基本是行草结构而以隶法铺毫写就,即便侧锋,也是在铺毫前提下运用的。
沈曾植《恪守庐日录》记载:“少原来久谈,论《石门颂》妙处不可摹拟,愚以为必软豪(毫)中锋悬腕出之,心通其结字之源,法律森严,而后神趣洋溢也。”这是寐叟自述写《石门颂》心得。“软毫、中锋、悬腕”正与郑孝胥日记所称“古人必以悬肘运指为出奇”为同样的认识。
这一时期,寐叟倾注心力较多的汉隶名碑,见诸题跋者,有《三老碑》《景君碑》《石门颂》《礼器碑》《孟广碑》《娄寿碑》《校官碑》《白石神君碑》《刘熊碑》。比如,沈曾植在《校官碑跋》中写道:
余最喜此碑书法,以为汉季隶篆沟通,《国山》《天发》之前河也。愿(顾)恨拓本漫漶,尝集浓淡干湿数本,合装之,互征其趣。此本虽旧,而拓不工,以其为苏斋物,存之。李乡农。
首行“载”字、“著”字完,“功”“斯”字存半,胜《萃编》本。
《校官碑》全称《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又称《潘校碑》《潘乾碑》,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刻。寐叟对此碑书法的看重,显然在于它与“汉季隶篆沟通”。与此同时,同一种碑刻在不同时代捶拓的拓片,因风化、损泐程度不同,或缘于原刻、覆刻的区别,会出现全字完整程度及字中具体字画的不同,即便同一碑、同一时间甚至由同一拓工所捶拓,拓本的用墨浓淡、笔画粗细也难完全相同。因此,对某拓本的临习研究如欲深入、到位,应取不同版本对照观察,同时参考相关文献。寐叟对《校官碑》“尝集浓淡干湿数本”,“互征其趣”,并与《金石萃编》所摹写碑字全貌作对比,可见其研究之深入。
寐叟平生作隶书较少,但从传世作品看,成就亦极可观。晚年“寐草”之形成,其早年对《石门颂》等汉隶名碑的喜爱与长时间的观摩、玩赏,实与有功焉,其中最显然的影响,即在于取汉代隶书的铺毫运笔与开张字态。
二、取法魏碑
袁昶1892 年8 月14 日日记,先抄陶濬宣《禝山论书绝句》之“注中胜语”:“……子培谓龙门造像,其掠法竟与宋拓《洛神》同势,故于北法为近。”又记寐叟论《郑文公碑》《张猛龙碑》语:“沈乙庵云:‘《郑中岳》似孟子,《张清颂》似荀卿。’”这是以儒学中孟子、荀子的文章风度来比拟《郑文公碑》《张猛龙碑》书法风骨。
其他师友日记,如《艺风老人日记》《翁同龢日记》,也多有记载沈曾植参与的考校碑帖、共赏书画之事,沈氏的碑拓收藏(如《高植墓志》《刁遵墓志》《韩显宗墓志》)也频为大家所欣赏、讨论。
这一时期,寐叟所用功较勤的魏碑,见诸题跋者,有《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贾使君碑》《李璧墓志》《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大昌造像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以《张猛龙碑》为例,寐叟作有五个题跋。其中写道:
此碑风力危峭,奄有钟、梁胜境,而终幅不杂一分笔,与北碑他刻纵意抒写者不同。书人名氏虽湮,度其下笔之时,固自有斟酌古今意度。此直当为由分入楷第一巨制,拟之分家,则中郎《石经》已。
寐叟以《张猛龙碑》为“由分入楷第一巨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张猛龙碑》评为“石本行书第一”,观此碑书法,少数字偏旁偶见连笔,整体用笔仍属魏碑楷书。与康有为相比,显然寐叟对此碑书体所作“由分入楷”的判断更为精当。
寐叟另一跋语写道:“碑字大小略殊,当于大处观其轩豁,小处识其沉至。”倘机械读文字,像是指《张猛在碑》各字之间大小区别变化,要从整体上欣赏其开阔气势和整体格局,从细微处领悟笔意之沉着精到云云,实际此语并非仅就此碑而言,而是就北碑整体所下判断,即整体气象与细节表现均与“碑字大小略殊”息息相关,此两端可分别由大字、小字得到充分体味。如以寐叟大字作品(如对联、大字条屏)、小字作品(如题跋、札记)两方面与此语对照,可得证实。
具体观察《贾使君碑》《张猛龙碑》,多数字有明显的横撑之势,同时多数横笔画同时取“左下右上”趋势,收笔处省去隶书的燕尾式波磔,故很自然地形成斜向合力,既张扬横势,又避免了纯横笔势的平平无奇。这一特点在寐草中有较突出的呈现,只是寐草中的横笔以有波磔与无波磔两种收笔法互见,在取法碑派笔法的基础上使笔画形态更为丰富。但从大处着眼,魏碑对寐草最鲜明的影响,便在于横向取势的体现。
此外,寐叟晚年对《嵩高灵庙碑》也有较多取法,王蘧常在《忆沈寐叟师》一文中提出,寐叟曾取用《嵩高灵庙碑》的古拙隶意及部分用笔。《嵩高灵庙碑》全称《中岳嵩高灵庙碑》,又称《寇君碑》,为北魏碑刻。北魏太安二年(456)立,一说太延年间(435—440)立。碑文为楷书而未全脱隶意,通常认为是由隶书向楷书过渡书体,传为寇谦之书。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寇谦之书法“体兼隶、楷,笔互方圆”,此碑体现出这一特点,同时又有结体自由、用笔无拘无束的特点。
三、取法“二爨”
《爨宝子碑》刻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爨龙颜碑》刻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都属于六朝书法。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如是评价《爨宝子碑》:“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又说:“真楷之始,滥觞汉末。若《谷朗》《郛休》《爨宝子》《枳阳府君》《灵庙》《鞠彦云》《吊比干》……《郑长猷造像》,皆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者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如是评价《爨龙颜碑》:“宋碑则有《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又说:“《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灵庙碑阴》辅之。”
《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在现当代尤受书家和学者所爱重,如当代饶宗颐主张:“‘二王’‘二爨’可相资为用,入手最宜。……学习‘二爨’‘二王’的原因是书法艺术既要讲究深厚,亦要讲究俊逸。在‘二爨’中求古拙,在‘二王’中求流丽,方能不顾此失彼。”这显然也是承袭碑帖同参、融合的立场。
在沈曾植晚年章草书风形成过程中,“二爨”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如张慧仪将1911—1920年视为沈曾植“融碑入帖时期”,认为他尽管广学魏碑,但“二爨对沈氏的影响似乎更大”。但她同时又说:“正如他学习二爨或《嵩高灵庙碑》时,着意于其楷隶互融的趣味,但纯用其法则结体恐会流于生硬,故沈氏参以黄道周、倪元璐的行草,取其转折欹侧的动势,以救板滞。”
“二爨”对沈曾植晚年书风的影响是否“更大”,具体在哪些具体层面发生影响,甚至“二爨”是否曾发生影响,学者们看法不一,大体可分为两派。
其一,认为“二爨”并非沈曾植重要的取法对象,甚至并非其取法对象。如沙孟海认为,沈曾植“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而未有只语言及“二爨”。沃兴华《中国书法史》一书认为:“从后期的变法实践来看,沈曾植书法的结体造型受黄道周影响,点画用笔受倪元璐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沃氏书中虽专列“碑帖融合”一章专论沈曾植书法,在具体论及其碑派取法时列出的主要是汉隶名碑,其中以《校官碑》“对他影响至深”,而未有一字及于“二爨”、魏碑,似指寐叟的“碑帖融合”仅以汉隶碑刻与帖学相参融。
其二,认为“二爨”对沈曾植晚期书法影响很大。这又有具体区别,一部分学者认为沈氏书法取“二爨”的结体,如张慧仪、戴家妙等;一部分学者认为沈氏书法取“二爨”的笔法,如曾克耑在《近代书家评述》中指出,沈曾植“所学的不过是二爨(《爨龙颜》和《爨宝子》)的笔法,章草的结体”。王蘧常认为:“大字方面,以《嵩高灵庙碑》的古拙隶意及部分用笔,参以二爨碑结体及碑刻的厚重之感,其所追求正与其小字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说沈曾植大字是《嵩高灵庙碑》隶意和部分用笔,加以“二爨”结体。
上述各家对“二爨”影响沈曾植书法虽然观点各异,但要研究沈曾植晚年书风是否受到“二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并得出基本接近客观真实的结论,并非不可能。另外,对上述各家意见之由来作一分析,对今后有关书家书风研究亦不为无益。
沃兴华《中国书法史》末章“碑帖融合”专论沈曾植书法:“《校官碑》是沈曾植最喜欢的,他在《寐叟题跋》中说:‘余最喜此碑书法,……’在《菌阁琐谈》中说:‘《校官碑》结字用笔沉郁雄宕,……’所谓‘沉郁雄宕’正是沈曾植后期书法的特征,由此可见此碑对他影响至深。”假设沈曾植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书家,没有传下一件作品,仅根据其文字作品“札丛”“题跋”来探究其晚年定型书风的来源,尚不失为可行方法(其实亦是不得已,因为这种方法在沈曾植这一实例上已可看到确实不准确),那么因为“札丛”“题跋”中未述及“二爨”的文字,故将“二爨”排除在其取法范围之外,似乎于理可通。但是,沈曾植毕竟是有众多作品传世的书家,考察其作品或将研究题跋文献与研究作品结合起来,方可得出更接近事实的结论,而且这样得出的结论,比仅据题跋文献作研究要全面、客观得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可能发生质的扭转。
沈曾植的传世书法,除去众多的文稿、诗稿、翰札之外,通常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亦当在千件以上,其中就有多件直接临习“二爨”(特别是《爨宝子碑》)的作品,而且寐叟晚年即便在臂痛的情况下,临书“二爨”的热情不减。“沈曾植在另一临《二爨》扇面上跋:‘复临数行,弥益性劣,然已臂痛废书矣。’”
沈曾植临习《瘗鹤铭》的情况与此类似。《瘗鹤铭》与“二爨”同样在“札丛”“题跋”中未有涉及,但寐叟存世作品中确实有临习《瘗鹤铭》之作。
“二爨”、《瘗鹤铭》的临作,多数属于意临,而意临则相当于直接借鉴某碑帖而进行的创作。对学者来说,除正视这类临作墨迹的物证意义外,更重要的还需从寐叟晚年书风去具体分析其借鉴的成分,比对其重合的程度。
认为“二爨”对沈曾植书法有影响甚至影响很大的学者中,一部分认为沈氏书法取“二爨”的结体,那么,既然取法“二爨”的结体,必然不会写出章草的结体,则这部分学者便不可同时再认定寐叟所写的是章草;另一部分认为沈曾植取“二爨”的笔法,此一观点相对合理、公允,但如曾克耑所说沈氏“所学的不过是二爨的笔法,章草的结体”,亦未能完全妥切,笔法诚然取法“二爨”较多,但“结体”并未占章草多大比例,如前所述,寐草结体中章草的比例其实低于今草的比例。
较为客观、周到者,则为王蘧常,他认为沈曾植“大字方面,以《嵩高灵庙碑》的古拙隶意及部分用笔,参以‘二爨’碑结体及碑刻的厚重之感”,称“二爨”为其结体的参取对象,是说字的体势参取“二爨”,而非指结字全取“二爨”。王氏之评,以“其所追求正与其小字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语最具意义,其他论者皆不能及此。如果将寐叟晚年临习《爨宝子碑》作品与原碑拓逐字对照,当可在其“意临”之中品味取原碑形体大势、用笔大意,而以己意写出的诸般妙处。
四、沈氏碑派取法对民国章草的影响
在沈曾植之后,章草成为民国初期一些书家有意识的追求,他们用心推究根源,研出新意,并向帖学之外的碑刻取法,赋予作品厚重及欹侧、跌宕之势。这既有书家个体的有明确意识的追求,也有时代审美趋向的因素。在清末民初取法章草(包括以章草为主攻方向)的书家中,多以向碑刻的取法作为书家探求古源、获取古法的渠道。在向章草之外碑帖的取法上,沈曾植亦有引导之功。最鲜明的表现,正是对《爨宝子碑》的倾心与临写,这是沈曾植之后许多章草书家的共同特点,王世镗、郑诵先、王蘧常三家传世作品中都有突出呈现。
王世镗、郑诵先与沈曾植书法成就的差距,容或存在于多个方面,寐叟学养深博与翰墨取法广泛两方面因素应是其他书家未及之处。仅由翰墨取法层面看,王、郑二家,《爨宝子碑》在其成熟章草书风中占了绝对主要的成分,少见其他来源的取法;寐草虽然可见明显“爨味”,但同时来自其他源流的成分亦极鲜明,加之寐叟所擅之用笔法(如铺毫运笔)、结字法(如结字造险、笔势造险),遂使寐草超凡入圣,远远胜过诸家之上。虽然王世镗、郑诵先也曾由帖学入手,但即便比较帖学修养,二家也明显逊于寐叟。在王、郑二名家之后崛起、代表现代章草高峰的王蘧常为沈曾植衣钵之继承人,自称在“三王二爨”之间取法,对《爨宝子碑》亦多有取法,此由其传世作品中的临写墨迹可见用功之深,而其创作中则表现为“以圆化方”,以圆浑笔法化解了爨碑的方笔。
结语
如果按古代书体、书迹问世之先后,沈曾植所取法对象可分为“远源”“近流”,远源包括诞生于汉代的章草、汉隶、二王法书以及北碑,近流包括唐人书法及明末黄道周、倪元璐书法。实际取法的次序,则是远源与近流互有先后交错,如早年接受的传统帖学精华,既有二王法书,又有唐人书法;中年则在帖学基础上引入汉魏碑刻,也接受明末书家影响;晚年则一方面融入简牍章草,一方面大幅度吸收《爨宝子碑》《瘗鹤铭》等碑刻,碑帖合一,造就新的高峰。其最终形成的书风并非某几种来源的简单相加,而是各种来源融汇为一,其中各有不同的表现。
沈曾植的好友郑孝胥在1892 年9 月30 日日记中写有“时贤急南北,扰扰吾无取”之诗句,表达出对将碑、帖截然分流的不认同,这实际是超越南北对立立场,而呈现出的一种超然于碑帖之争又实事求是地取其所当取的客观态度。但在实际取法中,他仍是侧重于碑学,主张“以隶写草,以草为真”,将隶书在书法学习中的地位提得极高。而在沈曾植的书法理念中,这样彻底、肯定地偏于一端的主张极少见到。沈曾植主张,为学“必穷其源流……益探其奥,拓其区宇”,学书主张“学古人者必求其渊源所自,乃有入处”。他向弟子王蘧常传授章草,指出“昔赵松雪、宋仲温、祝希哲所作章草,不脱唐宋人之间架与气味”,即赵孟頫、宋克、祝允明是以唐宋帖学结字、笔法写章草,气息拘限于唐宋之间,去古意殊远。他指点王蘧常书法说:“尔所作不脱北碑间架与气味,总之是一病。”可见,在寐叟的书法理念中,不仅唐宋人习气要摒弃,北碑的习气也是要不得的。
本文着眼于沈曾植书法实践,着重考察他对古代碑刻作品的吸收,倘另选取他对帖派取法的视角,同样可以在帖派领域内解读出一派内容丰实的取法与创新之路。纵观沈曾植取法碑、帖的实践,亦与其治学理念相契合,不偏重一隅,不固执一见,而是将一切古法皆置于“为我所取”的位置,最终形成浑融厚重与灵活机动相融汇的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