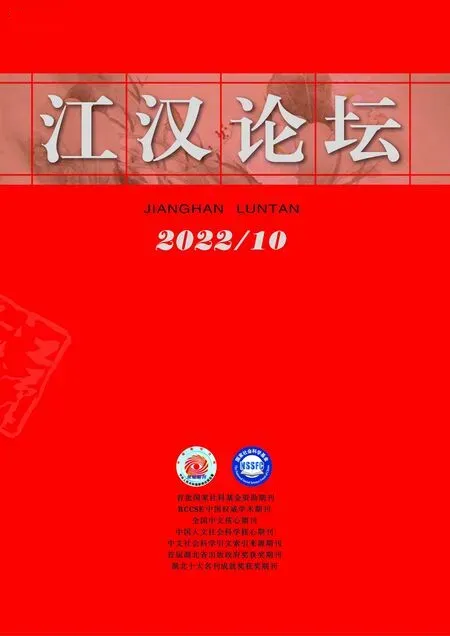德国启蒙悲剧诗学的激情与教化
2022-09-08卢白羽
卢白羽
德国早期启蒙运动领军人物高特舍德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不能将戏剧、尤其是悲剧从秩序良好的城邦里驱赶出去》的演讲。显然,这一题目是在回应柏拉图《理想国》将戏剧以及戏剧诗人从理想国家里驱逐出去的著名提议。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戏剧在舞台上呈现激烈情感的宣泄,迎合并助长了观众身上本该加以克制的非理性的感性部分,撼动理性对情感的绝对统治,从而破坏个人对自身的统治秩序,进而破坏整个国家的统治秩序。据说亚里士多德提出悲剧的净化情感功能,就是在回应他的老师对悲剧的攻讦。自此之后,如何处理悲剧激发观众情感,成为西方悲剧诗学的焦点问题。
戏剧因其公共性与直观性,是启蒙时代向大众传播启蒙思想最有力的媒介,因而成为最受重视的文学体裁。然而戏剧(尤其悲剧)激发观众激烈的情感,似乎威胁到理性的澄明状态,成为启蒙思想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启蒙时期悲剧诗学讨论的焦点在于悲剧在观众身上引发的情感是否具有道德认知与教化功能。悲剧诗学首先关注的不是悲剧作为艺术品本身的审美价值,而是其对接受者的影响。诗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论证受众如何通过文学艺术成为更好的人,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在将艺术自律奉为金科玉律的现代人看来,这种“效果美学”乃文学他律的过时理论。歌德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根本不关心道德教化。道德与文学无关,乃是宗教与哲学要关心的问题。不过在阿伦特看来,诗人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对社会施加影响,恰恰表达了诗人对这个世界的爱。诗人以作品积极介入这个世界,乃是致力于建构艺术家与同时代人的共同生活世界。看来,诗学议题并不仅仅涉及文艺学、道德哲学,甚至也牵连政治哲学。柏拉图的问题应该得到严肃回应。
一、理性主义悲剧诗学教化观及挑战
理性主义哲学家高特舍德自信可以驳倒那些指责悲剧煽动卑劣情感、败坏人心的异议,证明悲剧是启发民智、对人民施行道德和公民教育最有效的途径。他认为首先应当正本清源,明确悲剧典范。悲剧应该是“富有教育意义的道德诗篇……一篇譬喻性质的寓言,意在(阐明)一则重要道理。”文学的本质是寓言,以感性形式向观众传授一则道德真理。诗人应当按照演绎法,从一则道德真理出发,铺陈出悲剧情节。悲剧诉诸感官,激发感情,只是为了更好地达到伦理认知目的。
不过,理性主义哲学虽认定有效道德判断只可能基于理性的判断与认识,却也承认情感仍然在伦理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情感既能够阻碍理性道德真理发挥效用,也能赋予它强大的说服力。悲剧利用精彩情节迎合观众的感性激情,实际上是借此“诱惑”将观众引向道德真理。文学引起的审美愉悦不过是一种引导和劝服观众接受真理的修辞手段。悲剧将美德刻画为美,邪恶刻画为丑,从而引导和培养观众对他们无法在理性上认知的善恶产生情感上的亲近与憎恶,从而实现教化目的。可以看出,高特舍德在传统修辞学意义上理解情感的教化功能,即通过操控受众的情感来影响其判断力。早期启蒙诗学仍然沿用传统修辞学情感学说的认知框架。悲剧情感只是在理性认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接受真理的替代手段。悲剧的审美效果归根到底并非不可替代,也不具有独立价值。
与高特舍德同时期的法国人杜博提出的感觉主义美学将情感从伦理规定中解脱了出来。杜博认为,精神的无所作为会产生无聊,这对精神而言是最大的痛苦。激情是含有巨大能量的感知,它夺走灵魂的无所作为,因此,即便是令人痛苦的激情也能给灵魂带来愉悦。悲剧快感源于此,杜博还强调,这一愉悦感与道德判断无关。所有艺术门类都只对人的感官感知产生影响,并不与道德价值领域发生直接关联,也不涉及理性判断。艺术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传播伦理道德知识,而是为了激荡人的情感而产生愉悦感。悲剧作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以精准的心理刻画呈现激情的真实状态。
杜博的感觉论,尤其是他提出情感具有独立于道德的审美价值,是尼可莱论文《论悲剧》的指导思想。18世纪中期正是感觉论哲学在德国方兴未艾,与理性主义哲学激烈交锋之时。德语区启蒙运动也出现了人类科学转向。如何定位情感,成为构建现代个体的重要议题。敏锐捕捉到新动向的尼可莱希望用感觉主义美学理论来匡正悲剧诗学。尼可莱宣称,悲剧无需考虑道德教化,只需激发观众的激情。如果观众的精神能够在剧烈的悲剧情感震荡之中感受到愉悦,悲剧的目的便已实现。尼可莱指出,高特舍德将悲剧视为道德说教的工具,是造成德国悲剧品质低劣的根源。悲剧作家不要期待通过刻画美德的崇高与恶人遭受报应让观众热爱美德、厌弃邪恶,反而要利用观众原有的道德禀赋来激发他们相应的情感。
为证明悲剧无法完成教化作用,尼可莱区分了悲剧人物感受到的激情和观众感受到的激情。传统修辞学的情感学说完全没有区分这两类情感,修辞学效果学说的根基恰恰在于情感的可传递性。如果没有18世纪上半叶美学与心理学对于情感认知功能的强烈兴趣,尼可莱的这一区分是难以想象的。而只有区分了这两类情感,对悲剧情感的理解才能脱离传统悲剧诗学的窠臼。尼可莱观察到,悲剧人物的情感并不能原封不动地转移到观众灵魂的感性部分。观众被悲剧激荡起来的情感与悲剧人物的情感并不相同。因此,尼可莱得出结论说悲剧不可能用来改善观众具体的激情。比如观众不可能通过观看《美狄亚》学会克制自己的嫉妒与复仇之心。
尼可莱的论文为他的两位好友——此时已在德国哲学界与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门德尔松与莱辛——提供了讨论悲剧情感的契机。三位朋友都意识到,悲剧情感的引发绝非为了以感性方式阐明道德道理,也不是借情感进行劝服的修辞学策略,而是一种植根于感性认识能力的灵魂活动。门德尔松和莱辛跃跃欲试,希望运用“前沿学术成果”重新阐发悲剧情感现象。三位朋友的通信后来成为启蒙悲剧诗学的经典文本《关于悲剧的通信》。
二、情感与认知
作为理性主义哲学家的门德尔松最关注的是悲剧情感的认知功能。
莱布尼茨按照观念呈现的清晰程度,将灵魂获取的认识划分为唯有通过理智才能获得的“清楚认识”和仅有感官和想象力参与的认识活动所能获得的“明白却模糊的认识”。沃尔夫承续这一认知框架,区分了灵魂的上层与下层力量。感性情感属于下层灵魂力量,愉快的情感是对善的不清楚认识,不愉快的情感是对恶的不清楚认识。可见,情感具有认知功能,是对善恶的模糊表象。然而,要保证伦理行为为善,就必须保证对善有清楚明白的认识,这一点却只有灵魂的上层力量也即理智可以达到。灵魂的感性部分(情感与想象力)是有缺陷的认知力,并不能成为道德原则的牢靠根基。
门德尔松认为,观众在观剧过程中沉浸在戏剧营造出来的幻觉里,会接受戏剧诗人建构的虚拟世界的逻辑,包括其道德判断。此时,灵魂的上层力量会自动停止运转,只让灵魂的下层力量来发挥判断功能。悲剧激发观众产生的悲剧情感,是观众的灵魂下层力量对戏剧人物所做的道德情感判断,被门德尔松称之为“戏剧伦理”。问题在于,虚构世界里的逻辑很可能是错误的,只是被诗人巧妙地掩饰了起来。如果未经理性推理验证,灵魂下层力量很有可能会被诗人虚构出来的虚假道德迷惑。因此,观剧时道德感觉作出的道德判断和(现实生活中)理性推理得出的道德判断并不一定一致。一旦戏剧结束、幻觉消失,理性(灵魂上层力量)自动重新掌舵,道德感觉会自动服从理性的判断。按照理性主义哲学认识论,正确的道德观只可能建立在理性推理的抽象符号认识的基础上。但悲剧能感动观众、激发观众激情的前提却是:放弃理性判断,完全沉浸在幻觉营造起来的戏剧世界里。可见,在门德尔松看来,通过悲剧来培养观众形成正确的道德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根本无法现实。
就悲剧应当激发情感而并非阐明道德道理而言,莱辛完全赞同两位朋友的立场。然而莱辛从通信一开始就坚持悲剧激发激情并非悲剧的最终目的。悲剧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道德教化,并且是以悲剧情感为手段。不过,莱辛对悲剧情感作出了严格的界定。
首先,莱辛区分了悲剧激荡观众心灵的不同层面:悲剧人物的激情转移到观众身上的次生情感与悲剧在观众身上激发的悲剧情感。前者是悲剧快感的来源(观赏剧中人物令人不快的悲惨遭遇也会激发愉悦感)。莱辛使用共振琴弦的比喻阐释了这一现象:正如一根琴弦的剧烈震荡会造成另一根琴弦的共振,任何情感的剧烈震荡都能传递到我们身上,令我们感觉愉悦。这种愉悦的根源在于灵魂的任何运动都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现实”,即产生自我意识。接着,莱辛区分了这种“共情”与他视为唯一悲剧情感的“同情”。观众不可能同样强烈地感受到悲剧人物所感受到的激情,因为观众缺乏悲剧人物产生激情的前提条件。莱辛甚至认为“共情”就强度而言根本算不得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愉悦与悲剧教化功能完全无关。莱辛在认同尼可莱对悲剧情感区分的同时,也将悲剧快感排斥在他的关注点之外,客观上杜绝了同情这一悲剧情感陷入重情主义式自我陶醉的危险。
莱辛在通信里多次提到,观众感受到的激烈情感是对悲剧人物不幸遭遇的情感反应。而在悲剧激发的众多激情中,莱辛认为只有同情具有道德教化作用,因此他宣称同情乃是悲剧应该激发的唯一激情。至于为何同情本身就具有道德性,莱辛给出的理由是:“最富同情心的人是最好的人……谁使我们具有同情心,谁就使我们变得更好、更有美德。而激起我们同情心的悲剧也就会使我们变得更好、更有美德……”这其实并非通常意义的论证。不过很明显的是,当莱辛将同情直接等同于美德时,他并不是从理性主义认识论出发来定义美德的。苏格兰道德感学派对人自发的自然本性给予了更多信赖,认为它并不低于理性的判断和推理能力。相反,理性反倒是实现道德感决断的手段。就同情本身蕴含道德因素而言,莱辛的同情观更接近道德感学派。
莱辛信赖同情作为情感的判断即为正确的道德判断,认定只要培养人皆有之的同情心,人自然就会向善,甚至不要理性的匡正,“同情直接教化人,无须我们自己参与;它既教化有头脑的人,也教化傻瓜”。即便诗人诱惑我们对错误对象产生同情,即门德尔松所谓的虚假的戏剧伦理,也无损同情本身的道德性。莱辛甚至提出,悲剧训练产生同情的能力,培养出观众同情的“习性”,就已经改善了我们的道德禀赋。在德国理性主义启蒙哲学语境下,“习性”指的是通过不断反复与刻意训练,将有意识的理性认识转换到无意识层面,从而实现理性对身体以及情感实施更有效的操控。莱辛认为同情本身也可以进行训练而形成习性,从而转化为道德禀赋,成为道德性格的一部分。可见在他看来,同情具有与理性同样的道德可靠性。
门德尔松对此显然无法认同。在“悲剧通信”结尾,他仍然追问,如果没有理性的检验,我们如何保证同情的对象是真正的而非虚假的善?两位朋友对于情感是否具有认知功能,从而是否可以成为美德这一问题,最终也未能达成一致。
然而戏剧作家莱辛似乎并不愿在作为情感的同情是否具有认知功能这个哲学问题上继续纠缠下去。反倒是门德尔松的一句玩笑引发了莱辛的强烈反应:门德尔松要求莱辛向惊叹这一“美德之母”道歉,因为莱辛竟然认为惊叹不能算激情,不过是同情的间歇,目的是使得同情可以持久。两人关于“惊叹还是同情”的争论贯穿整个通信。实际上,取同情舍惊叹,才是莱辛对于悲剧以及悲剧理论的真正兴趣所在。
按照莱辛的定义,观众悲剧激情的对象是悲剧人物的不幸本身,那么同情或惊叹的差异就在于悲剧应该塑造什么样品格的主人公这一问题上。简单来说,如果悲剧主角丝毫不以自己的不幸为苦,则会激发观众的惊叹;如果主角哀叹自己的不幸,则会激发同情。门德尔松与莱辛关于惊叹与同情孰高孰低的争执折射出,在18世纪中期不仅认知结构的等级体系出现了松动,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的等级体系也开始出现震荡。
三、惊叹抑或同情
门德尔松与莱辛对惊叹与同情价值高低的分歧,其源头需要追溯到莱辛同情观的另一个理论来源:门德尔松在《关于感觉的通信》里对“同情”的定义以及在《致莱比锡莱辛硕士的公开信》里对卢梭“同情说”的批判。
在完成于“通信”之前的美学著作《关于感觉的通信》里,门德尔松其实对同情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认为同情是一种混合了愉快与不快的情感,是悲剧情感里唯一产生愉悦的痛苦情感。愉快是源于因对象的完善而产生的爱,不快则是看到被爱对象无辜遭受不幸。不幸更烘托出被爱对象的完善,增加了愉快感的程度。理性认知力越发达、文明程度越高,就越能更好地意识到对象的完善,从而体验到更多的愉悦。
卢梭的同情则与对象的完善程度无关,针对的是“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是一种前理性与前文明的自然情感。一切智识与文化上的进步和文明的成就并不增强、反而削弱了同情这唯一的自然美德。与理智相对的同情成为卢梭批判社会的武器。自然的、真正的人,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是这个自私自利的文明社会的明鉴。
门德尔松认为,卢梭将同情定义为“因别的造物的脆弱而产生的不快”,误解了同情的真正结构。莱辛认同门德尔松从理性主义完善学说出发对同情的定义:同情必定基于对同情对象蕴含的伟大完善,因而同情并非彻底的前理性情感,而是以能够识别完善的认识能力为前提。然而这却并非莱辛同情观的核心。莱辛和卢梭一样,认为同情的关键在于对同情对象展露出来的脆弱所抱有的不忍之心。它并不是理性认知的成就,而是源于前理性的自然情感。事实上,莱辛将同情视为最根本的美德、是一切社会美德之来源的说法,就取自门德尔松在《公开信》里对卢梭同情观的总结。
同情与惊叹都是观众对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的激烈情感反应。如果说引发同情的契机是悲剧人物暴露出来的脆弱,那么引发惊叹的契机就在于悲剧人物对人性脆弱的克服。在门德尔松看来,惊叹的发生,不仅基于对象的完善,并且这一完善还超出了自然天性的界限,通常表现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同情的对象则以深陷困顿为苦,显露出人的软弱。就道德完善程度而言,惊叹的对象要高于同情的对象,因此惊叹是比同情更高的悲剧情感。
门德尔松坚持“惊叹”作为更好的悲剧效果,也有其思想史背景。他多次提到,最能体现悲剧人物非凡品质的是,悲剧英雄在面对厄运时仍然保持内心的从容。这种心绪状态类似于斯多葛主义的道德理想“不动情”。它表明心灵只依靠理性的判断力,不受任何外部偶然因素的干扰。在查尔斯·泰勒看来,这种将意志主宰激情视为德性的新理解,是世俗化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一个明显标志。门德尔松视为超凡美德之标志的“视死如归”等品质,代表着意志“对身体以及产生于身体和灵魂之结合的事物领域(特别是激情),实施至高无上的控制”。然而,门德尔松宣扬的“不动情”有着迥异于传统斯多葛主义的人类学前提。斯多葛主义视激情为错误的意见,18世纪的道德理想则十分重视激情的作用,更强调意志对激情的完全把控。归根到底,门德尔松推崇的真正美德是道德意志的自决与自由。只有在感官欲求与理性道德决断的剧烈冲突中,悲剧主人公方能显出他抵挡外界加诸自身影响、贯彻理性道德主张的强大意志力,彰显出道德主体的自主与自律。英雄悲剧也因此成为体现启蒙道德主体之自主性的理想艺术媒介。
相比之下,同情则是截然相反的美德。如果说意志对激情的绝对把控外显为“不动情”,那么同情的“动情”,恰恰显示出心灵还会因外界因素而产生干扰理性判断的情感,尚不具备对身体的绝对把控。斯多葛主义哲学蔑视同情或怜悯,正是因为它反映了主体能动者意志掌控力的薄弱。在斯多葛式哲学家看来,因不忍心同胞受苦而心生同情,不如内心毫无情感波动的扶贫救弱。莱辛对于意志自由一向并无太高评价,在“通信”中更是将它贬称为“固执”,并宣称,一切引发惊叹、显示出克服普通人性的英雄主义品质都应当排除出悲剧之外。他用半揶揄的口吻说道,门德尔松的确对人性(的软弱)了如指掌,深知如此克服了人性软弱而彰显道德意志绝对自主状态的道德楷模乃是“麻木的英雄”,他们早已超出人性范围,是“美丽的怪物”而不再是“好人”了。
针对门德尔松提倡自塞内卡至高乃依的英雄悲剧传统,莱辛提出以古希腊悲剧作为典范。古希腊悲剧让所有英雄人物都卸下英雄躯壳,哀叹自己的不幸。悲剧主人公的坚毅性格只应使他不至于不体面地毁于不幸。悲剧应该着力刻画的,恰恰是一个仿佛在某一刻有能力对抗命运,却在下一刻再度陷入痛苦、对人性的脆弱有着切肤之痛感受的英雄。
四、莱辛的“同情—恐惧”诗学
在距通信十年后的《拉奥孔》里,莱辛通过分析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详细论述了悲剧应当塑造什么样的英雄人物来触发观众的同情。
《拉奥孔》第四章处理的问题是诗(文学)为什么可以表现肉体痛苦。温克尔曼在《论希腊绘画和雕刻作品的摹仿》中将拉奥孔与菲罗克忒忒斯(以下简称菲氏)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默默忍受着痛苦,显示出灵魂的伟大与沉静。莱辛指出,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菲氏非但不像温克尔曼所说的那样默默忍受剧痛,反而因不堪忍受疼痛而发出长时间嚎叫。
伟大的灵魂能否表达肉体痛苦?这一问题实际上延续了“悲剧通信”时期他与门德尔松的争论。在《拉奥孔》里,莱辛论述道:希腊人认为,因身体的极端痛苦而发出哀号,可以与伟大的心灵相容。古人从不因自己作为凡人而有的人性局限(最为鲜明地体现在身体上)而羞惭。从效果美学来看,只有英雄也虚弱到表达出自己承受的痛苦,才会引发观众对他的关切,激发观众的同情。
菲氏宁可继续忍受痛苦而不改其决断,表现出“坚韧”这一斯多葛哲学美德。然而,莱辛认为坚韧美德并不适用于任何与被动承受相关的方面。“痛苦的表现往往并不出于自由意志,而真正的勇敢只有在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上才可以见出”。如果将自由意志理解为心灵对身体与激情的把控,莱辛显然认为其把控不应该是绝对的。必须承认身体作为物质,在受到外物刺激时会产生相应的反应,灵魂只能被动接受而无法主动掌控这一反应。文明对情感的规训与压抑,尤其对于那些受外界触发的情感的扼制,在莱辛看来反而是一种“野蛮”。身体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应当允许身体顺从自然的要求,在承受外界施加的痛苦时发出哀怨。
他的哀怨是人的哀怨,他的行为却是英雄的行为。二者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一个有人情味的英雄。他既不软弱,也不刚硬,而是在服从自然的要求时软弱,服从原则和职责的要求时刚硬。他是智慧所能造就的最高产物,也是艺术所能摹仿的最高对象。
意志应该使人按照道德律令行动,但在遵守道德原则的同时却没有必要强制压抑人被动而天然的情感流露。“有人情味的英雄”甚至超越了艺术门类的界限,被莱辛视为一切艺术门类所能摹仿的最高审美对象,同时也是最高的伦理理想。
可见,莱辛提倡同情诗学的根源,乃是要提倡一种完全不同于强调理性灵魂对身体与情感实施绝对把控的二元对立人性观。莱辛提倡的人性观既承认理性按照道德原则控制身体与情感,也承认身体同时属于自然,具有无法被精神渗透的属性。每个个体受到自身禀赋、所处时代,乃至人作为有限造物的类属局限,永远无法摆脱“心的自私自利状态”,不可能达到“因美德自身的缘故而去热爱美德的心灵纯净状态”。人的这一局限性,不仅是莱辛诗学思考的出发点,也是他晚年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正是基于对自然天性的重视,莱辛重新发现了“恐惧”这一悲剧情感。以至于有研究认为,《汉堡剧评》时期莱辛的悲剧诗学应该称之为“同情-恐惧”诗学。
亚里士多德提出,唯有担心某种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从而心生恐惧的人,才会在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人遭受类似厄运的时候对他产生同情。因此,恐惧又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自己的同情。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认为恐惧由同情衍生而来,在《汉堡剧评》里,莱辛开始强调“恐惧”的独立作用,恐惧成了同情的内核:强烈的同情必然包含恐惧,恐惧却并不必然包含同情。甚至当悲剧构建的幻觉消失之后,观众心中对悲剧人物的同情也立即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对类似厄运可能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自私的”恐惧。
莱辛以人类科学知识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情感学说。他将“恐惧”理解为一种自我保存的“欲望”,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激情。如果悲剧想要收到良好的教化效果,就必须将人对自我保存的天然欲求考虑进来。这是莱辛对他自己早期同情观的重大修正。一方面,莱辛并不认为人可以崇高到否认或轻视自我保存意志的地步;另一方面,莱辛也不认为人性本恶,就是无节制追求自身利益。同情不仅是对过分强大的自爱的修正,正常的自爱也是同情的必要补充。只有将同情与恐惧视为两种不可分割、相互交融、相互关联的情感,对他人利益的关切与自我保存的欲望、爱他人与爱自己才能同时成为可能。
五、结语
在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眼中,启蒙时期俨然成为以理性之名压抑乃至扭曲感性的新“黑暗中世纪”。然而恰恰是启蒙运动开始探索理性与情感的边界与交融,启蒙时代的悲剧诗学即是这一探索活动的印记。如何看待悲剧激发的激情?为了影响观众固有的情感禀赋,为实现悲剧这一体裁的特有目的,悲剧又应该满足何种前提条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出启蒙时代不同评论家对情感的不同感知与体认。
灵魂的自主性与意志的自由,是理性主义道德哲学的根基。观众在观看悲剧时不由自主产生的剧烈情感对这一根基构成巨大威胁。当高特舍德的理性主义解决方案被推翻之后,门德尔松与莱辛提出了崇高美学与同情诗学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案。
席勒的《论激情》看似追随莱辛,批判法国古典英雄悲剧的冷漠,推崇古希腊悲剧允许表现英雄对痛苦的敏感,从而给予天性更多的空间。然而,呈现悲剧人物承受痛苦的状态,唤起观众的同情,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意志在巨大苦难面前坚持自由与自主,最终以感性形式体现“道德不受自然法则约束的独立性”。悲剧美学沿着门德尔松提出的心灵与身体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在悲剧呈现道德主体的“不动情”、宣示“神一般的灵魂战胜其身体的内心胜利”之中,看到悲剧的崇高道德目的。同情则被斥为“肤浅的看法”,“怜悯……是一种有限的消极的平凡感情……是小乡镇妇女们特别容易感受到的”。莱辛的同情诗学及其对人性界限的洞见逐渐被悲剧舞台上慷慨赴死的英雄所遮蔽。
①⑥⑦⑧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Ausgewaehlte Werke,hg.von J.Birke u.P.M.Mitchell,Berlin,1968ff,Bd.IX/2,pp.492-500,p.494,p.317,p.495.
②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1—407页。
③参见歌德:《亚里士多德〈诗学〉补遗》,《歌德论文学艺术》,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9—553页。
④参见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⑤关于高特舍德的戏剧改革详参王建:《德国近代戏剧的兴起——从巴洛克到启蒙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175页。
⑨⑩ 参见Gert Ueding/Bernd Steinbrink,Grundriss der Rhetorik,5.Aufl.(Stuttgart,2011),p.281,pp.281-283.
⑪参见Elisabeth Décultot,Lessing und Du Bos,Zur Funktion des Empfindungsvermoegens in der Kunst,in Lessing und die Sinne,hg.von Kosenina und Stockhorst,Hannover,2016,pp.81-92.
⑫关于18世纪启蒙文学的“人类科学”转向,参见金雯:《启蒙与情感:18世纪思想与文学中的“人类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⑬⑯⑰⑱⑲⑳㉑㉕㉗㉘㉙㉚莱辛等:《关于悲剧的通信》,朱雁冰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45、77—79、79、19—20、38、97—98、191、34—35、28、35—36、71页。
⑭参见莱布尼茨:《对知识、真理和观念的默思》,《莱布尼茨认识论文集》,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91页。
⑮参见Christian Wolff,Gesammelte Werke,hg.u.bearb.v.Jean Ecole u.a.,Hildesheim,1965ff,Abt.I.,Bd.2,p.23.
㉒参见弗兰西斯·哈奇森:《道德哲学体系》(上),江畅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8页。
㉓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7页。
㉔Mendelssohn,Sendschreiben,in:Gesammelte Schriften,Jubilaeumsausgabe,hg.von Alexander Altmann u.a.,Berlin:Frommann,1929ff,p.86.
㉖参见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36页。
㉛㉜㉝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9、30页。
㉞莱辛:《论人类的教育》,刘小枫选编:《人类的教育:莱辛政治哲学文学》,朱雁冰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㉟参见Jutta Golawski-Braungart,Furcht Oder Schrecken:Lessing,Corneille und Aristotles,in:Euphorion,1999,93,p.417.
㊱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227页。
㊲参见莱辛:《汉堡评剧》,张黎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
㊳席勒:《论激情》,张玉书译,《席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㊴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