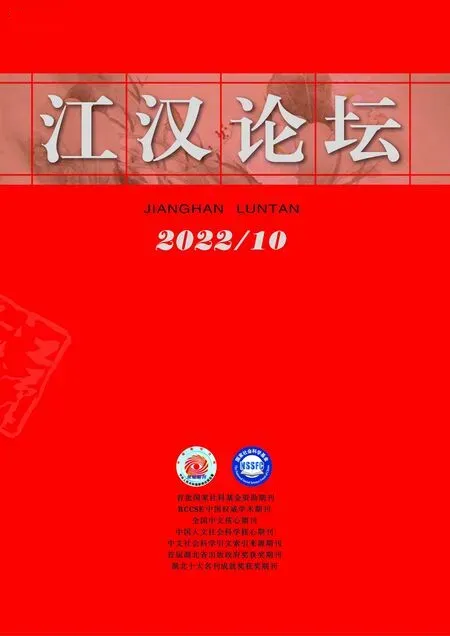旅游场域中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与价值回归
2022-11-08傅才武李俊辰
傅才武 李俊辰
传统村落是保存中华文明的基因库,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中国传统村落旅游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兴起的,先后经历了起步、规范、快速发展、全面发展等阶段。新时代,随着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又进入了新的阶段。2012年,随着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传统村落以其独特的价值成为乡村旅游和学术研究的热点。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三年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旅游和传统村落保护也被作为重要内容写入文件之中。旅游开发的持续升温带动了传统村落的经济发展,扭转了传统村落的衰落局面,实现了“旅游减贫”的目标,但旅游所裹挟的现代性和资本扩张等因素也逐步渗透到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演化当中,造成了空间的功能变迁与结构重组。乡村旅游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以及外来游客等复杂利益主体及其背后牵涉的各类现代性与流动性力量在短时间内强势地涌向乡村空间,使乡村空间在激进的旅游开发与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撕裂与解体趋势,破碎化、脱域化、无序化等乡村空间异化问题日益严重。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乡村旅游的语境,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并以世界文化遗产安徽宏村为研究样本,分析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以及旅游经济飞跃式发展背后所隐藏的空间矛盾与冲突,探讨乡村旅游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重构策略,以期为有效化解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空间异化问题,实现乡村文化空间的价值回归,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
一、乡村文化空间生产的理论架构
“文化空间”概念最早见于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但列斐伏尔并没有对其作进一步阐释。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对空间进行了三重性划分,提出了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这三重空间从现象学上来看分别是感知的(the perceived)、构想的(the conceived)和生活的(the lived),从语言学上来看又分别对应着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三重空间之间辩证统一,分别对应着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其中,“空间实践”强调空间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具有物质形式;“空间的表征”可以理解为对空间的概念化,是科学家、规划师、城市主义者、技术官僚、社会工程师和某些艺术家虚构出的概念空间,它趋向一种文字和符号的系统;“表征的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象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社会主体实际占有和体验的空间,它与物质空间重叠并且对物质空间中的物体作象征(符号)式的使用。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中所蕴含的空间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为解决旅游语境下乡村文化空间的结构异化问题,促进乡村文化空间的价值回归同样具有理论适用性。同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理论,以“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综合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和文化生态学范式来分析乡村文化空间,既可以从系统的角度突出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又可以从动态平衡的角度突出文化研究多线路之间的平衡。传统村落是一个包含人、文化遗产、空间形态和人居环境等因素的文化生态实体,通过传统村落来分析乡村文化空间需要在深入挖掘传统村落历史变迁的基础上突出其现代转型的具体路径,做到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统一。因此,本文将基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背景,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来解构乡村文化空间生产,这有助于深入理解乡村文化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历史性,探寻适合乡村文化空间生产的表征制度和发展路径,建构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生活场景使用者运作机制。
乡村空间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空间。在以传统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中国,与乡村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象征意义和符号系统都是以传统村落的选址布局、礼仪传统和日常生活方式为媒介,存续于乡村文化空间之内。乡村文化空间除了作为具体记录、承载和展示乡村文化记忆的物理场域,同时也是塑造乡村地方身份认同、展示乡村文化价值和再现地方性知识的场景载体,是兼具物质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乡村文化生态实体。乡村是一个拥有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活态社区和原生群落,人和文化同时置于村落环境系统中,构成了完整而平衡的内源自生本体文化空间。从生态自然场域、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场域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整体性意义来分析,可以将乡村文化空间结构层次划分为三位一体的乡村生态文化空间、乡村社会文化空间和乡村精神文化空间。
具体来说,以乡村生态三大场域为内核,社会实践活动在物态文化层面催生出生态文化空间,它承载于实体的地理环境,呈现出山地平原、河湖水系、生物物种、山林草木等乡村自然景观与传统建筑、田园景观、聚落格局等乡村人文景观的表征;在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层面衍生出的社会文化空间则形成于人的生产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两种形式,诸如村规民约、民俗节庆、民间礼仪、祭祀活动、生产技艺、农业生产、产品加工、社区营造等日常生活实践和旅游驱动乡村改造叠置而成的空间聚合体;乡村在心态文化层面演化出精神文化空间,乡村精神文化空间以文化符号、文化记忆、文化象征、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地方认同为内核,在传统聚落空间内不同利益主体的集体协商和建构过程中被生产。上述“生态文化空间—社会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三位一体的乡村文化空间系统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空间与主体意识交融的复合体,与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相呼应,在满足村民生产生活基本需求的同时,更能满足情感、精神与伦理上的价值追求。
二、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东北部,隶属于黟县宏村镇,始建于公元1131年,距今已有891年的历史,是旅游驱动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典型案例。截至2021年,宏村辖区4.1平方公里,耕地768亩,共计13个村民小组、524户、1446人。宏村作为徽州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承载着程朱理学的封建纲常、聚族而居的宗法伦理、村落选址的风水文化,还包括极具匠心的徽派建筑和贾而好儒的徽商治生方式,形成了独居特色的物质空间和人文景观,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集聚着人们对传统乡土时代的所有美好想象。宏村于2000年11月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先后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级风景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画里乡村”“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诸多殊荣。宏村自1986年10月正式开发旅游至1998年1月,先后由黟县旅游局、宏村镇政府、宏村村委会等不同主体参与运营管理,不同等级的管理部门成为旅游开发的主导者,宏村村民不同程度地因旅游而受益,但旅游富民的效能较低。1998年,随着黄山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开始管理和经营宏村旅游,宏村旅游开发进入到了政府主导和资本运作以及村民参与的新阶段。2020年6月,徽黄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股权重组的方式正式控股京黟公司,采用全域旅游理念对黟县全部旅游景区进行整合,宏村旅游开发也进入一体化发展新时代。宏村近40年的旅游开发运营中所呈现的问题是中国大部分乡村地区发展旅游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为旅游场域乡村文化空间的变迁与重构研究提供了理想样本。下面,本文基于资本、权力和地方阶层裹挟之下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
(一)生产主体:政府、企业、游客和原住民
旅游场域作为社会场域中的特殊存在,可以被视为围绕旅游活动形成的客观关系构型。“一个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其文化空间生产必将受到地方政府、开发商、游客以及原住民等多元主体的影响。多元主体根据自身占据的位置,依据自我的权力和惯习进行资本、权利和正义的竞争博弈,以共同推进旅游场域中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多元主体的空间凝视和旅游空间主导者的空间规制促成了“空间中的流动”,使“地方空间”(spaceofplaces)逐渐转变为“流动的网络空间”,并在新的空间中创造了一种关于旅游空间生产与消费、旅游生产与资本推进、旅游生产与权能、旅游管理与信息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网络关系,这种网络关系通过空间流动和规制而运动,成为旅游社会实践的利益主体。宏村的旅游开发是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群众参与的方式进行的,其文化空间生产存在着不同的主体。
地方政府作为凝视主体的构成者之一,它们往往出于经济目的,在目的地空间的“产品化”和“商品化”中实现对目的地的规制。在宏村早期的旅游开发实践中,黟县旅游局、宏村镇政府、宏村村委会作为地方权力的主体行使着规制、约束和管理的功能。
旅游开发商代表资本主体,常常在权力协调中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实际开发者,它们通过资金投入获取利润,或直接代表政府进行开发,充当了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1998年后宏村旅游开发的主体主要是黄山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和徽黄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两个公司分别通过市场运作和全域整合的方式进行开发运营。
游客的游览活动也是一种凝视行为,会对旅游地的文化与景观造成影响。在旅游场域中,“旅游者看到的事物都由符号组成,它们都表示着其他事物;在旅游者目光的凝视之下,一切景观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一切景观都变成了文化景观”,因此游客也形塑着景观文化的空间结构、空间形态和空间关系。游客凝视的欲望在地理空间上获得了延伸,其行为确立了目的地空间的位置及存在,当持续的凝视固化和物化时,乡村文化空间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便随之产生了。
原住民群体是空间中重要的活态文化和历史见证。政府及景区管理主体对村落的空间形态与秩序进行操纵,企图实践其构想中的空间表征。但居民并没有完全接受其控制,而是通过日常生活进行抗争,实现反抗性的表征空间。他们通过使用者的行动策略,重新满足了生活生产的空间需求,夺回了部分空间秩序改写的权力,并在空间实践的过程与结果中体现了生活性。
(二)动力机制:资本增值、权力主导与阶层抵制
在列斐伏尔之后,西方研究者围绕资本、权力和阶层等因素解析了空间生产的机理,资本、权力和阶层被视为影响乡村文化空间生产的主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从根本上丰富和拓展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资本作为空间生产的内在动力,通过对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来完成旅游场域中空间的三级循环;权力则是依靠制度、规划和营销等行动途径,在资本运作中完成制度规则空间的生产;自从资本和权力结合之后,利益分配不公和空间资源失衡问题便产生了,作为原生空间主体的阶层便开始了对社会公共空间生产的抵制。资本增值、权力主导与阶层抵制相辅相成,形成旅游场域空间生产结构,循环式地引发空间的再生产。
资本增值是社会经济空间生产的内在驱动力。哈维提出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认为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投资于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初级循环、投资于建成环境的第二级循环以及投资于科教和社会领域的第三级循环。资本的三级循环理论旨在解决城市的资本化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旅游场域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归纳起来,就是乡村社会经济空间在资本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下,通过资本增值和自我修复的方式创造出与自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空间联结。乡村旅游开发正是在空间生产资本逻辑的影响下运用资金、人力、场地、设备等物质和非物质资源进行“土地—景观—产业”上的空间开发和形成符号性消费场所来实现初级循环的空间生产的;旅游开发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完成后,传统农耕空间向城镇化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化则预示着以改善居住和生活环境为目的的第二级循环的完成;社会经济空间作为一种被结构化的社会关系,则是依靠带有福利性质的社会平衡调节方式,如修建学校、博物馆、文化剧场等方式去实现资本的第三级循环。
权力主导为制度规则空间的生产提供外在动力。在旅游场域中,权力作为一种有约束力的普遍化能力,通过对地方区域的制度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达到控制个人或地方,进而为资本服务的目的。与资本所生产的具象的空间不同,权力所塑造的政治制度空间是非物质形态的,却可以通过制度和规范来约束和促进资本和市场的循环。国家权力作为一种约束力在乡村生产体系中被空间化了,“权力空间化”具体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行政规划和形象塑造来实现“空间的表征”。
阶层抵制是社会公共空间生产的反馈动力。阶层逻辑是从空间使用者的角度出发,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一个生活场景使用者运作机制,反映的是社会阶层赋予空间的意义,即他们对其直接经历和生活的空间的地方感知和文化认同。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将空间生产的宏观逻辑转向微观的生活政治层面,关注空间演化中居民与日常生活的力量,为社会公共空间生产提供了一种行为指导。“抵制”作为日常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在宏观上服从强势群体所设立的主流空间秩序,却暗中突破防范,灵活随机地实施小规模的违规,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一是人们运用日常的语言和文化来破坏占统治地位的权力体系,创造新的空间;二是“行走”,即创造窥探、观察的机会,搅乱和打碎稳定的乡村秩序;三是“权宜之计”,意为“避让但不逃离”。阶层抵制是对资本介入下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主导的反抗,最终通过日常生活的创造力与前述“空间的表征”实践共同建构出旅游地的“表征的空间”。
三、旅游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异化困境
资本增殖和权力主导的空间生产的“合谋”机制,因过分关注文化空间的经济价值而忽视历史文脉及传统文化价值,导致了空间异化现象的产生。在旅游裹挟的流动性与现代性胁迫和资本与权力的双重扰动下,“地方性空间”向“异质化空间”转变加速,传统村落文化空间陷入异化的窘境,出现了生态文化空间破碎化、社会文化空间脱域化和精神文化空间无序化等问题。
(一)生态文化空间的破碎化:资本嵌入改造与景观生产实体化
资本介入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生产异化首先表现为生态文化空间破碎化。生态文化空间破碎化带来的真实生活世界消解、文化变异以及空间权益失衡的负面效应,直接导致了生活世界与空间的脱节、空间资源配置不平衡以及文化与空间的断裂现象。生态文化空间破碎化主要是通过“景观生产实体化”来实现的,这是因为“景观不仅是权力关系的符号化表征,更是实现文化权力的工具”。宏村生态文化空间的景观化是基于物质景观和社会实践改造后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对耕地、灌溉水系、建筑群落、街巷布局、生活居所、生态环境和旅游设施等进行加工、生产和形塑,进而生产出新的空间形态。一是旅游开发所需土地的扩张使得村落建设用地和生产用地急剧缩减,村周边的大量土地被改造,包括政府、开发商等在内的异质主体置换了以原住民为主体的格局,从而造成兼具多元性和异质性的居住空间形态不断出现。以2000年宏村申遗为界,在宏村开发旅游产业到申遗之前即1986—2000年,新增建设用地基本都是用于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主要集中在宏村景区内部。2000年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为保护古村落的整体风貌,宏村内部建设基本停止,仅有极少数村民因生活需要或住房濒危,才被允许建房。宏村新增的建设用地随之更改到一河之隔的际村,如2003年新建的宏村镇政府、2004年新建的宏村中学、2009年建成的“水墨宏村”以及2012年建成的“宏村印象”都位于际村。二是村落中的物理空间重新置换或招商后带来了乡村建筑文化景观的“失忆”现象。进驻宏村的资本对生态文化空间的嵌入主要集中在资源最为富集的核心区域,宏村南北方向的供销社商业街成为资本嵌入后新空间的主要载体,外来商户的入驻和商品化开发造成了沿街建筑文化景观的“失忆”。另外,与宏村一河之隔的际村在西溪河沿岸建造了大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来发展餐饮和民宿,除了在建筑形态、建造技法与材质等方面与村落总体风貌对立与冲突外,直接排放的生活污水也刺激着村落生态文化空间的异变。三是在城市化的牵引下,宏村实现了从乡村传统农耕空间到城镇化乡村生活空间的转向,形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再循环,主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旅游业已接替农业成为驱动村落发展转型的主要产业,宏村也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乡村聚落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现代旅游特色小镇。可见,乡村生态空间被持续压缩和重组,一方面带来了村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同时又引发了村庄农耕经济和传统文化共同体的瓦解,乡村逐渐成为资本运作的载体。
(二)社会文化空间的脱域化:去生活化与权力让渡
在“熟悉的陌生人社会”,权力往往面临着体制转轨、利益转换、阶层转化、结构转变等裂变。在乡村旅游背景下,乡村人口外流及村庄改造会导致村庄熟人社会中稳定的社会关系网被破坏,居民社会互动开始减少,交往空间被分割,邻里关系也日渐淡化。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社会文化空间脱域化问题便产生了。首先,社会文化空间的脱域化表现为民俗节庆去功能化、符号化与舞台化问题。如,作为民俗文化的代表,宏村传统民俗“鱼灯”在旅游节庆活动中成为了表演项目。由于旅游商品化的需求,“鱼灯”失去了其神圣性和功能性,在构建符号表征空间和促进空间消费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去生活化”的后现代消费主义图景,这种表演出来的“舞台剧”让文化逐渐成为“藏品”。其次,由于空间主体权力的不对等与不平衡,不同等级的政府部门成为了旅游开发的主导者,而宏村村民的社区参与能力较弱,空间权益处于被弱化的边缘地位,存在“空间失语”现象。实地调研表明,宏村的保护规划并未征求大多数居民的意见,居民基本上是规划制定后被动接受相关内容。再次,在产权让渡方面,村落风貌的空间改造和空间腾退让原住民搬离了原初位置,虽然他们享受了相应的安置和补助政策,但却失去了房屋产权和空间生产参与权。在搬迁和坚守的两难选择上,一些居民迫于居住窘境选择搬至宏村新的安置区,从而造成了一种“中心—边缘”的空间区隔。与传统生活空间相比,旅游带来的“绅士化”造成了空间消费的两极化,原本属于公共空间的消费场所变成了中高端消费群体的独有空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区隔。
(三)精神文化空间的无序化: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竞争博弈
因为承载了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其在行为、制度、风俗、建筑和公共空间结构上的符号系统,乡村精神文化空间能够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意境和受众的体验之间建立连接,借助隐喻、象征、意指等途径跨越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时间沟壑”,重新唤醒中国人关于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在精神文化空间结构中,“宗族礼法”“天人合一”“中和”“修生克己”“环境生态观”等传统文化记忆成为精神文化空间的主体内容,精神文化空间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唤醒集体记忆来实现对过去累积性的建构。宏村的集体记忆莫过于祠堂中的神圣氛围、匾额楹联、家族历史、书院学堂等建构了集体记忆的表征体系,这种集体记忆也是居民在用最普通的方式强化自身对地方的认同。“图腾崇拜”“祈愿求福”“欢庆丰收”“祖先祭祀”等文化形式依附于物质载体,慢慢沉淀为原住民的共同信念,为其价值观、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涂上了基本相同的“底色”。在原生空间自组织体系下,精神文化空间形成了自洽性的文化空间关系。但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和资本嵌入思路的引入,本土文化的符号化、外来文化的复制拼贴、与本地人生活的割裂让宏村失去了最吸引人的本源,以“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为内容的地方感日渐式微。伴随着乡村文化空间生产带来的村落内阶层分化和人口流动加剧,多元主体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社会交往关系的异质性增强。所以,宏村由村民单一主体依靠血缘关系、宗族权威来维系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政府、企业、村民依靠现代的利益关系、契约精神而形成的社会联结,人际互动的“利益逻辑”取代了“熟人逻辑”,精神文化空间在这一新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下出现了无序化的特征。
四、旅游语境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重构策略
传统村落作为生态文化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有机结合体,不仅要保持风貌完整性和历史真实性,还要保持其精神文化空间的活态性和原真性。结合前文有关空间异化问题的分析,下面从景观空间的价值规训、空间权力治理正义性、村民日常生活实践三个方面提出旅游语境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重构策略。
(一)优化景观空间,实现人地和谐
资本景观化实质上是一种空间资本化逻辑主导下的非均衡城乡空间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实现乡村景观风貌更新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居环境和文化景观的失调,而“空间转移”和“时间转移”是解决空间异化后重构资本良性循环、实现文化空间价值回归的有效手段。第一,注重文化遗产向景区社会转型中“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互动,重塑景观文化权力的普惠性。除了新建消费型基础设施外,还要配套建设相应的社会福利型公共文化设施,如乡村剧院、乡村博物馆、乡村图书馆等,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二,打破乡村旅游纯观光的固化模式,推动景区从单一门票经济走向鲜活的日常互动体验。在村落已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之上,可采取“了解学习—游览观赏—体验探索—购物纪念”的四步法,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开发。比如,通过剪纸绘画、旅游演艺、木雕技艺、酿造工艺的展示与传承等途径实现遗产资源活态性保护和创新性再生产,进而实现由部分地方文化精英向外辐射带动居民生计转型与文化认同的变革。第三,开展村庄保护科学规划,优化旅游生态景观空间结构与布局。要通过合理设计与科学规划,对山林草木、河流湖泊等旅游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对乡村原有的建筑、道路等旅游人文生态景观进行有效的空间组织与重塑,实现生态景观的连续性与和谐性的统一。第四,运用“有机更新”理论,推动乡村分类保护与修复利用。可按照聚集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庄的分类要求,依据不同类别村庄的属性因地制宜地进行个性化保护和提升,配合旅游经济对村庄生产关系不断调整的现实需求,实现有计划的空间改造。
(二)畅通治理路径,保证权力正义性
从社会文化空间多元治理主体入手,搭建和谐共生的对话平台、协同机制和监管渠道是“权力空间化”过程中实现空间正义的重要途径。第一,构建“居民—政府—企业”的良性互动关系。针对乡村旅游开发中空间权力分配存在的问题,需要从顶层设计和制度层面保障空间生产的正义性,树立多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积极建立起村民与政府、企业之间的沟通渠道与平台。应建立村民空间诉求表达机制,针对村民群体的“政治去权”与“信息失权”等空间非正义现象,搭建村民代表、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地方旅游行业组织等多方主体的意见交换平台,增强村民的担当意识和获得感,凝聚乡村旅游语境下多元主体的命运共识,塑造个体生命之间的共同情感与公共精神。第二,构建“文化—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要充分发挥乡村文化产业、旅游业和农业间的产业互促作用,系统解决农村地区“农—文—旅”的发展矛盾,通过农文旅一体化发展形成文化品牌赋智、旅游产业赋能和农业赋值的联动格局。第三,构建“管理—技术—教育”一体的组织监管团队。应通过成立合作社、聘请职业经理人、组建专家咨询团队等方式协调村落内外人力资源,尤其是依靠村落中的管理精英、知识群体等新乡贤及时跟进村庄发展规划、产权处置、产业开发等事项,带领村民自觉投入到文化再生产和村落再发展之中,充分激发村民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实现景区自我造血和全面转型。
(三)回归村民日常生活实践,共筑文化共同体
“以人为本”的主体日常生活实践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对资本与权力主导下的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表征的反抗,也是让现代消费社会异化现象得以消解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主要依托国家权力、产业形态和村庄共同体意愿等力量构成的乡村日常生活实践的底层逻辑来实现,并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塑造成为连接国家权力、产业形态和共同体意愿的载体和桥梁,实现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回归。首先,拓展公共文化下乡的供给服务方式,实现自上而下的文化下乡和自下而上的文化需求相连接。除了拓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制”内容外,还要对村庄内生的文化技艺、文化建筑和文化习俗等进行原真性转换,重建乡村文化公共服务自组织系统,激发村民的集体记忆。其次,运用新科技手段拓展乡土文化和旅游体验的交互价值。除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传播文化内容外,更要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和元宇宙技术等科技手段进行改造式传播,将村落文化的自觉属性和旅游的沉浸价值进行耦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再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风尚引领,构建村庄精神文化共同体。应通过崇尚科学、道德和美德的乡风文明引领,自觉抵制村庄中的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实现村庄精神文化空间和日常生产生活的有机统一。只有将主体的生活意义和全面发展作为文化空间生产的价值旨归,并关注空间对人存在的意义及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才能实现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中主体的自由、机会的平等和文化共同体的回归。
①孙九霞:《传统村落: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旅游学刊》2017年第1期。
②车震宇、保继刚:《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研究》,《规划师》2006年第6期。
③㉛周梦、卢小丽、李星明等:《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驱动民族地区文化空间重构:一个四维分析框架》,《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9期。
④[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⑤J.H.Steward,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pp.33-40.
⑥吴开松、郭倩:《文化生态视域下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研究》,《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⑦张晓琴:《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现代治理转型》,《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⑧㉖傅才武、程玉梅:《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与政策路径:一个宏观框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⑨傅才武、侯雪言:《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艺术百家》2016年第6期。
⑩傅才武:《构建文化生态层次结构理论框架——冯天瑜教授〈中华文化生态论纲〉读后》,《社会科学动态》2022年第3期。
⑪[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⑫⑮郭文:《旅游空间生产:理论探索与古镇实践》,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50页。
⑬John Urry,The Tourist Gaze: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London:Sage,1990,p.129.
⑭孙九霞、周一:《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地理学报》2014年第10期。
⑯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Oxford Blackwell,1982,pp.274-366.
⑰林青:《空间生产的双重逻辑及其批判》,《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
⑱参见孙九霞等:《旅游社区的社会空间再生产》,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⑲胡静、谢鸿瓂:《旅游驱动下乡村文化空间演变研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⑳参见葛荣玲:《西方人类学视野下的景观与旅游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㉑卢松、周小凤、张小军等:《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城镇化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热带地理》2017年第3期。
㉒何绍辉:《论陌生人社会的治理:中国经验的表达》,《求索》2012年第12期。
㉓叶继红:《集中居住区移民社会网络的变迁与重构》,《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㉔[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㉕刘军民、庄袁俊琦:《传统村落文化脱域与保护传承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11期。
㉗郭文、王丽:《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地理科学》2015年第6期。
㉘朱竑、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1期。
㉙龚天平、张军:《资本空间化与中国城乡关系重构——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㉚唐建兵:《应加强风水文化旅游的开发研究》,《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㉜李亮:《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现代性重构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