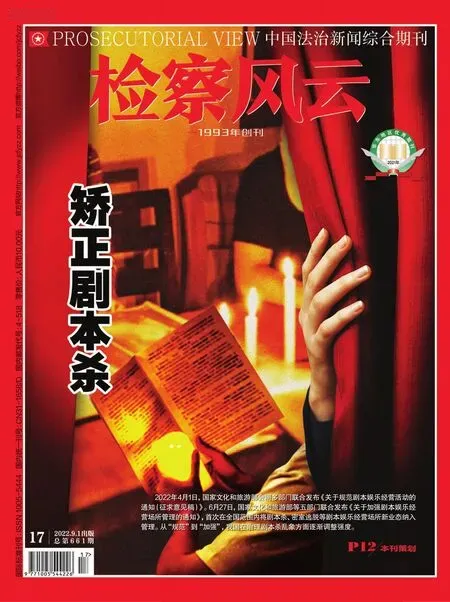平准之法:传统中国物价治理方略
2022-09-07宋伟哲
文/宋伟哲
在日常生活中,物价是老百姓最在乎的事情之一。柴米油盐看似普通,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与社会安宁,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物价问题。物价平稳,就意味着太平盛世。一句“斗米数钱”,几乎就是史家对于盛世的最高赞誉。可是近代以来,传统中华商业文明与法律备受质疑,被贴上了抑制商业、不重法制等标签。其实如果带着温情与敬意去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华先贤在市场管理领域耕耘极深,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充满了东方智慧。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市场领域亦然。重温这段法史,对于今天市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与完善仍不失为良好的历史镜鉴。
敛轻散重
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商业活动就已颇为繁荣。《易经·系辞传》云,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西周时期,提倡礼治天下,周礼中就有一套颇为完备的市场管理制度。据《周礼》记载,国家设立“司市”一职,专门负责市场管理。当时的市场划分有不同的功能区,政府出台了各种法令来规范市场交易,保持物价稳定。市场不是全天候开放,而是有着严格的交易时间,不同的群体需要根据各自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时间赴市交易。具体为“大市,日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开市之时,管理员手中拿着鞭子在大门旁警戒,商人们需持有效证件才能在市场上携货出入。管理市场的各类官员,先要检查货物质量,评估货物价格。准备完备后,把旌旗悬挂到司市办公之所,即宣告开市。司市坐镇市中,处理市场中的重大案件;其余细小纠纷,则由胥师和贾师负责处理。

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物价问题
在市场交易中,政府有一套基本管理原则,即“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大意为使得匮乏的物资充裕,增加利民之策,消灭害民之举,减少奢侈浪费。当时,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欺诈伪劣对商业的危害性,针对百姓、商贾、工人分别制定了十余条法令。比如根据《礼记·王制》篇记载,“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粥”通“鬻”,出售之意)违反这些法令,则依照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宪罚”“徇罚”“扑罚”,翻译为现代汉语分别是“通报批评”“市场游街”“鞭打”。如果行为构成犯罪,触犯刑律,则交由“士”,也就是司法官判刑处理。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些处罚措施的设置梯次有度,颇与当代行业软法处罚、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古人高超的法律智慧。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是中国社会却在大变革中飞速发展。诸侯之中,齐桓公最先实现了富国强兵,成为春秋首霸,这与他重用管仲为相密不可分。管仲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的国力迅速增长。其中,管仲“敛轻散重”的经济思想对齐国的经济繁荣影响深远。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管仲面见齐桓公,痛陈物价失衡之弊,提出了国家对物价进行干预的有效措施。“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也就是说,国家在物价低的时候,对市场上多余的产品进行收购。物价上涨的时候,再把这些物品低价抛售,这样市场物价就可以平稳,百姓得到了实惠,国库也得以充盈。所谓“敛轻散重”,大致可以理解为国家“贱买贵卖”的调控手段。这套市场价格管理法律制度在古代被称为“平准之法”,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专门记载经济史的篇目命名为“平准书”,亦即后世史书的“食货志”,可见“平准”在古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重法惩奸
唐宋时期,传统中国逐渐走向历史顶峰,国家经济愈发繁荣,法律制度也日臻完善,在市场管理、物价治理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已经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敛轻散重”已经不能保持市场和物价的繁荣稳定。市场交易中出现了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国家立重法予以规制,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相关律令法规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唐律疏议》共五百条,其中有七条紧密相连的律文专门规范市场交易,这七条法律全部位于《唐律疏议》第十篇“杂律”之中。
第一条为“校斛斗秤度不平”。它规定“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监校者不觉,减一等;知情,与同罪”。此条法律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市场度量衡。何谓“校斛斗秤度”?立法者在“疏议”中进行了立法解释。“依《关市令》:每年八月,诣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平校,并印署,然后听用。”具体校正的办法,立法者亦在“疏议”作了解释。“《杂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唐代的法律形式由律、令、格、式组成,最常被提及的《唐律疏议》只是“律”,主要是刑法条款,用于打击犯罪。而令、格、式类似于今天的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用于正面规范行为。正如古人所云,“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律和令格式配套而行,从正、反两面来进行法律规制,体现了唐人先进的立法技术。
第二条为“器用绢布行滥短狭而卖”,主要打击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主要内容是,“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赃重者,计利,准盗论。贩卖者,亦如之。市及州、县官司知情,各与同罪;不觉者,减二等”。第三条为“市司评物价不平”,此条法律主要是惩治市场管理官员品评物价不公正之罪。其主要内容是,“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其为罪人评赃不实,致罪有出入者,以出入人罪论”。立法者同样在“疏议”部分对法条进行了详细解释。“谓公私市易,若官司遣评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计所加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谓因评物价,令有贵贱,而得财物入己者,以盗论,并依真盗除、免、倍赃之法。‘其为罪人评赃不实’,亦谓增减其价,致罪有出入者。假有评盗赃,应直上绢五匹,乃加作十匹,应直十匹减作五匹,是出入半年徒罪,市司还得半年徒坐,故云‘以出入人罪论’。若应直五匹,评作九匹,或直九匹,评作五匹,于罪既无加减,止从贵贱不实坐赃之法。”根据唐律规定不难看出,唐朝物价管理官员的工作失误要被判处“坐赃”,即贪腐罪,要承担刑事责任,而非普通的行政处分,可见唐朝对负责品评物价官员的要求之严。
唐朝立法者对市场上的强迫买卖、操纵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也给予重刑打击,即“卖买不和较固”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诸卖买不和,而较固取者;较,谓专略其利。固,谓障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谓人有所卖买,在傍高下其价,以相惑乱。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也就是说,强迫买卖、垄断市场、扰乱价格等行为,将被处于杖八十的基础刑罚。获得非法利润数额较大的,则要以窃盗论罪。在“疏议”部分,立法者还特别指出要把所得赃财偿还给本主。除此之外,《唐律疏议》对于私作非法度量衡、交易不诚信、危害市场公共安全等行为也给予严厉打击。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对于市场、物价的法律规制不局限于《唐律疏议》一部法律。在令格式中,还有更大篇幅专门用于规制市场交易的法律规范,前文所提到的《关市令》就是如此。非常遗憾的是,唐代的令格式并没有完整保存到今天,后人无法窥其全貌。但是从仅存的一些传世残篇,如北宋《天圣令》残卷中,还是保留了不少有关唐、宋令中《关市令》的内容,价值极高。
当然,提起传统中国的法律治理,除了要关注国家法之外,民间社会的软法之治同样不可忽视。在古代市场管理中,商会、行会制定了大量的行业规约。这些规约同国家法相比,数量更为庞大,规则更为细致,不但可操作性强,而且在民间业界具有不亚于国家律令的崇高地位。历史上基层市场物价之高低、商品质量之优劣等问题,都离不开行业软法的规制。依靠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的二元互动,才充分保障了传统中华商业文明的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