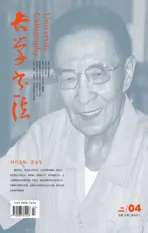黄永年先生的篆刻
2022-09-06刘星
⊙ 刘星
黄永年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教授,在唐史、版本目录学等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被我国版本目录学界称为一代宗师。先生又是当代著名的藏书家,以一己之力所藏宋、元版本图书在当代藏书界也很有影响,由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所编辑的《黄永年古籍序跋集》可知先生所藏以及经先生过眼的宋元孤本、善本之多,在当代学者中很少有人能与之相伯仲。正像先生在《黄永年谈艺录》中所说:“宋人藏青铜器,亦事传拓……此风至清末民国初尚不稍衰,且更进而并蓄碑石。此时期之旧式文人若不知金石则不得齿于通人之列。”受此认识影响,黄永年先生亦深谙金石之学,并由金石之学而及书法篆刻,博学之余,游艺于斯,不管是在书法上还是在篆刻上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深为艺林所重。
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读本科时,曾因为当时成立不久的终南印社跑腿叩响了黄永年先生家的大门,认识了黄先生,并第一次聆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教诲。从此,我就关注黄先生的书法,关注黄先生的印章。后来我在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读研究生时,西安美院科研处曾邀请著名篆刻家傅嘉仪先生来学校讲学,傅先生在论及20世纪西北印坛时,推黄永年、陈尧廷和李滋宣为陕西印坛三大家,尤重黄永年先生之学问人品及印学品质,被列为第一,我当时作为听众,深为赞同!
黄永年先生1925年生于江苏省。少受吕思勉先生启蒙,对史学和藏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时,就喜欢篆刻。据曹旅宁先生编著的《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先生20岁”条引黄先生的话说:“到二十岁遇见郭则豫先生才真开始入门,郭先生……所刻追踪黄牧甫,是一位真正的篆刻家,与时下某些以斯道自诩者不可同日而语。”郭则豫(1890—1952)字组南,别署枫谷,福建侯官人,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建高等学堂。民国初年,尝在北京北洋政府任职,为陈宝琛、宝熙等硕学所激赏,延誉士林,声名藉甚。陈声聪在其所著《兼于阁诗话》中说:“昔居京师时,文字之游,与郭枫谷最为密契。前后为谷社,为七人画社,皆与君同之。君才艺以各体书为第一,篆刻次之,诗亦一往清泠。”陈声聪曾赠郭则豫诗五首,其第四首云:“斯文有衰盛,多艺宁谋身。晚愈耽刻划,弥觉石可亲。左右挚黄趟,上下窥汉秦。使刀若使笔,下笔何其神。於焉小天地,光景能常新。举隅三十五,言印妙无伦。此道今少衰,谁欤老断轮。但恐夺诗力,徒使传印人。”
20世纪40年代初,郭则豫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1944年,黄永年先生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黄永年先生认识了郭则豫先生,并一定是因其“言印妙无伦”的印学功底深深打动了永年先生,由此,永年先生便决定师从郭则豫学习篆刻。郭则豫先生篆刻取法邓石如、赵之谦、黄牧甫诸家而能融会变化。白文多出汉铸,笔方意圆,饶有静穆气象;朱文章法茂密,用刀娴雅,或刚健遒劲,或秀挺婉约,并臻妙境。其治印边款也很精到,跋语尤佳,尝论用刀曰:“气锋无利钝,字要发毛,忌光滑也。欲使字画发毛,刀须直立,以锋向我,就字画逼之。偃刀不特无锋,且能使笔笔流滑无味,与发毛相去甚远。凡庸手作印,往往用刀摩荡往来于一画之中,类磨磐然,治印而染此习,则万劫不复矣。”郭则豫先生的这段经典印学表述,即便是现在看来,也是深刻而智慧的。这不能不影响到黄永年先生后来的印学思想和治印道路。比如,2013年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黄永年谈艺录》,其中《明清以来的篆刻》一文中黄先生说道:“文人印之成熟的,我认为始于吴熙载(让之),大成于赵之谦,其后黄士陵(牧甫)别开生面,吴俊(俊卿、昌硕)、王禔(福庵)、乔曾劬(大壮)、陈巨来均有可取。”这段话,虽然意在叙述晚清文人印发展之大略,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黄永年先生认为“文人印之成熟的……始于吴熙载”,这个观点,是有别于一般印学论著对文人印的基本看法的;二、“黄士陵别开生面”,“朱文参汉金文,多用方笔,是一大创新;白文仿汉,也得浑穆拙朴的神韵,且变化多……”这一观察,虽然说是在谈黄士陵,其实,他对黄士陵的印作的解读很符合现象学的阐释,也就是说,它同时又是黄永年先生自己印学思想的一个反映。我们从他的篆刻集可以看出,他一生治印受黄牧甫影响甚大,追求印面线条的洁、净和气息的雅、静;结字上则受郭则豫影响较大,结构和笔画意在方圆之间,这与黄牧甫的印面结字是有所区别的。在线条形态上,郭则豫主张“字要发毛,忌光滑也”,而黄永年先生的印则取黄牧甫的线多光整而洁净的做法。他曾给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著名教授郭子直先生刻有两方印,白文“郭子直”印仿汉玉印,规整中不乏灵动;而朱文“郭子直八十后所作”以金文入印,线条光洁简净,章法似黄牧甫,既得金文之肃穆,又得黄牧甫之新意,可谓永年先生治印中难得的精品,我初见此印时,甚为惊讶,认为在西北印坛能刻到如此境界的,还没有第二人。“江阴黄永年印”,白文,结字已呈现出永年先生自己书法的特点。线条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方圆对比,协调流美,黄牧甫之后,也不多见能有如此境界者,即便是陈巨来,也不外乎处在伯仲之间。“并蒂”一印,朱文,其章法似有吴、齐的大开大合,该印上密下疏,形成很强烈的形式感,似与黄士陵一派已有所不同。

江阴黄永年印

永年词翰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收藏印

蔡鹤汀六十有四岁以后所作

泽秦所得石刻文字

丽庄秘匧之印
黄永年先生心仪规整一路的工稳印风,这与他出身吴地并一路用心于版本考据之学的严谨治学作风是互为表里的,但其认为写意一路的印风“并不高明”,我则不敢苟同。他在《明清以来篆刻》一文中说:“有两位名气甚大其实并不高明,千万学不得的……一是齐璜(白石),此人并不擅篆刻,中年仿西泠八家,极平庸;后来借画名来卖印,用单刀乱刻,甚至篆法都有错误,初学学之即万劫不复。一是邓散木(粪翁),学赵石(古泥)。赵号称仿汉,已庸俗,邓更变本加厉,所治印不仅千篇一律,且上轻下重像患了什么病似的。”这段话对邓散木篆刻的评价虽然苛刻,确也有中的之处。但是对齐白石印章的批评,则不太符合实际。齐白石学印起步于对秦汉印的研摹,1902年的西安之行,在西安古玩店及藏家手里看到过大量汉代刑徒砖和汉砖的墨拓,由此转而向汉砖、刑徒砖文字及刻法学习,由此印风大变,走出了前人的藩篱,形成自己的印风。其刻法单刀直入,毫无修补,自然率真,简而味长,比之书法史上书风由“二王”到颜鲁公的书风大变,倒十分确切,应该是篆刻发展史上的一大创造。尤其是中年之前所刻微型印,能以小见大,意在秦汉印与黄牧甫之间,令人叹其用功之精。至于对初学之建议,写意印风固起点太高,是不适合初学者的,但不适合初学者并不等于说不好。据我所知,这是走工稳一路印风者的普遍态度,黄永年先生也未能例外。
总的来讲,黄先生的印整体上以格调、功力见称。在风格上,既有仿秦汉印的,也有仿明清流派印的,更多的,则是受到民国时期海派的一些篆刻大家的影响,比如黄牧甫、陈巨来、郭则豫等。黄永年先生的印,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朱文印,尤其是以大篆、金文入印的那些古玺风格的细朱文,刻得非常的精到,成就非常高;仿汉玉印的白文印刻得也是非常好,其作品之佳者,与黄牧甫、陈巨来这些名家大家或当雁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黄先生的印章之所以格调高、书卷气浓郁、韵味隽永,这与他广博的学问是分不开的。黄先生是吕思勉、童书业的弟子,在学术上又和顾颉刚过往密切,深受疑古派学风的影响,做学问注重考据功夫和资料功夫,不轻易盲从前人的结论。其对大名家齐白石篆刻的批评,就体现出了他的这种治学精神。这不是出于偏见,而是黄先生的内心装着非常崇高而神圣的学术目标。以此故,他的眼界就非常高,遇人遇事就非常挑剔。在陕西师范大学一直流传着黄先生的一些逸闻和趣事。当年他的古籍研究所就在校长办公楼的三楼,他每天上下班都要从一楼走到三楼,再由三楼下到一楼,如果他发现某一个厕所或楼道的灯没有关,或者厕所水房里的水龙头没有关好,他就会直走向某职能部门领导甚至校长的办公室,直接训斥校长或处长们,认为给国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令这些领导非常难堪。像这些事,在大多数人看来可能会熟视无睹,但在黄永年先生眼里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认为这种对生活细节的高要求,也是他一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生活中的反映。例如,永年先生篆刻之外长于书法,但据说他的字是不好求的,这不是因为他摆架子,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书法要求太高、太严格了,他认为只有写出一幅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才能允许自己送人。结果,很多人向他求字,一等就是几年,这也造成黄先生的字在社会上流传甚少,独立成幅的书法作品并不多见。幸好,我曾经给原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任天夫先生帮过一个小忙,老先生为了感谢我,就送给我一幅黄先生的书法作品。这幅字每个笔画都一丝不苟,用笔气静而淡雅,没有一点火气,每当展开欣赏时,心里都会有一种如对至尊的感觉。按理来说,这样的大师在我们身边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但是遗憾的是,我在校园里每每见到黄先生都是“敬而远之”,这“敬”是尊敬,是敬仰;“远”是远望,仰望,是高山仰止。所以,反倒失去了很多直接向黄先生讨教的机会。现在想来,这对我的确是一件蛮遗憾的事情。
《黄永年印存》是黄先生篆刻艺术水平的集中展现。这本印谱里的作品总体上能反映先生一生的篆刻成就和造诣,但以个人之见,有个别作品,功力明显不足,境界也差强人意,可能是黄先生顾不上应酬,请他的学生代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编辑者在选编《黄永年印存》的时候,没有认真加以甄别,也一并收录了进去,这不能不说有点美玉微瑕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