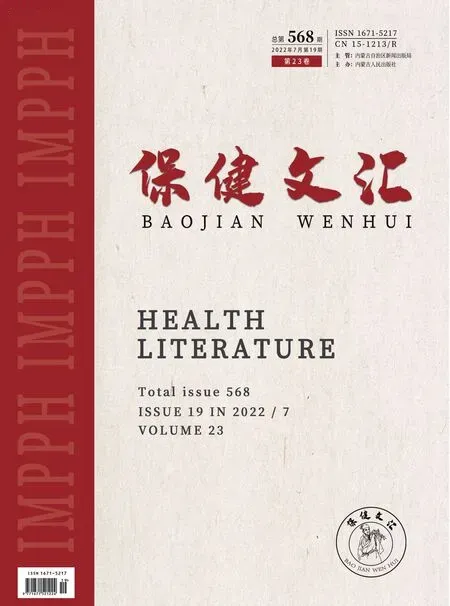论耳聋治肺
2022-08-27徐睿翔
文/徐睿翔
耳聋既可以作为一种患者的自觉症状,又可以作为一种单独的疾病,是指不同程度的听力减退,轻者听音不清,重者甚至完全丧失听力。中医学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耳聋相关的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耳不听五声为聋”,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对耳聋的认识。由于肾开窍于耳,肝胆经络循行于耳,许多医家从肾、肝胆着手论治耳聋。但其实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论述了肺与耳聋的联系。《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肺病者,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指出若肺金受邪,会导致耳聋。后世医家也有相关论述,如: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说:“耳者,盖非一也,以窍言之是水也,以声言之金也,以经言之,手足少阳俱会其中也。有从内不能听者,主也,有从外不能入者,经也……假令耳聋者,肾也,何谓治肺?肺主声。”更是首创了耳聋治肺的理论。本文从生理病理、基本证型、治则治法、临床治疗等几方面对此进行论证。
1 生理病理基础
1.1 经络
肺的经络入耳,《内经》记载:“手太阴之络会于耳中”,《灵枢·口问》进一步论述道:“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素问·缪刺论篇》曰:“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说明耳窃听声的功能与经络密切相关。《温热经纬》也有进一步发挥:“肺经之结穴在耳中,名曰茏葱,专主乎听。”对此,干祖望认为,“听”是指耳的功能,“茏葱”则指的是肺经的经络之气。
1.2 肺开窍于鼻
《灵枢·刺节真邪篇》曰:“刺邪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其声,必应于针也。”清代的张志聪注释道:“朦者,耳无所闻,上窍之不通也。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其声,必应其耳中之针,是耳窍与鼻窍口窍之相通也。”现代解剖证明,耳与鼻通过咽鼓管相连通,以维持耳内压力的正常。若咽鼓管闭塞,耳内形成负压,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增加,液体渗出,则可能导致分泌性中耳炎,继而导致患者听力下降。
1.3 肺主气
《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肺病者……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说明肺气虚损会导致耳聋。《杂病源流犀烛》一针见血地指出:“盖肺主气,一身之气贯于耳,故能为听。”只有肺气充足,才能维持耳正常的生理功能。王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中说:“耳聋,少气嗌干者,为肺虚……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耳者,宗气也,肺气不行,故聋也。”不仅论证了肺气虚所致的耳聋,还进一步提出了肺气不行之耳聋。顾世澄在《疡医大全·耳聋门主论》中说:“耳聋因于气闭者,有因怒伤及肝,痰因于火,或一时卒中,或久病气虚,故耳聋及鸣者,所主宜舒郁调血,用导引宣通之法。”不仅补充了王肯堂关于气郁耳聋的观点,还提出了治则治法。刘河间作为首个明确提出耳聋治肺的医家,在其著作中论述道:“人之眼耳鼻舌身意识神,能为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闭塞者,不能用也。若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无所臭,舌不知味肠不能渗泄者,悉由……不能升降出入之故也。”指出耳的听音功能与气机的升降出入密切相关。尤在泾在《医学读书记》中曰:“古云耳聋治肺,肺主声,鼻塞治心,心主臭,愚谓耳聋治肺者,自是肺经风热、痰涎闭郁之证,肺之络会于耳中,其气不通,故令耳聋。故宜治其肺,使气行则聋愈。”此言记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精妙的总结。
1.4 金水相生
《难经·四十难》言:“肾者,北方水也,水生于申,申者西方金,金者肺,肺主声,故令耳闻声。”最早论述了金水相生与耳的关系。李东垣在《脾胃论》中也提出:“耳者上通天气,肾之窍也,乃肾之体而肺之用。”所谓的“用”指发挥功能的基础,说明耳窍的听觉功能实根于肺。沈金鳌也在《杂病源流犀烛·卷二十三·耳病源流》中提出:“然肾窍于耳,所以聪听,实因水生于金。”指出虽然耳为肾之窍,但要发挥正常功能,仍需要肺的帮助,其论述不可谓不精炼。
2 近现代医家观点
干祖望老中医认为,多数耳聋与肺功能异常有关。“耳聋诸症,但凡有肺卫表证者,均宜宣邪外达”,进而将耳聋分为肺气失宣、肺失肃降和肺气不足三种类型,分别采取宣通肺窍、宣肺化痰、培土生金的治疗方法。邱美和独具创意地提出了“三部三脏”论治耳病的观点,将中耳疾病归属于肺,在治疗急慢性中耳炎时采取宣肺行气、清热利水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陈正平将耳聋的病机分为肺失宣肃、肺气不足两个方面,认为虽然可能因为患者体质、病程长短等的不同产生许多变证,甚至兼杂其他脏腑,但治疗的重点仍是恢复肺气的宣发与肃降。
3 主要证型
3.1 邪阻耳窍
外感风寒或风热邪气,外邪闭阻于耳窍,导致气机不得通畅、清气不能上升、浊气不能下降,轻则耳胀、耳闭,重则导致痰湿水邪滞留,耳中流脓。主要症状有:自觉耳中轰鸣作响,自声增强、听力减退,耳内镜可见鼓膜内陷,若有渗出或积脓则可见液平面;兼有咳嗽,若感受风寒邪气,则痰色白、质地清稀、鼻塞流清涕、舌苔薄白、脉浮紧;若是风热邪气,则流涕色黄、质地黏稠,咯黄色痰,苔黄腻,脉弦滑或濡数。
3.2 内浊阻肺
因外感后失治误治,外邪入里,随邪气性质、患者体质、病程长短、发病季节而演变为痰湿阻滞、痰热郁肺等不同证型,但总体仍是由于各种病理产物郁阻肺部,肺失宣降。主要症状有:听力减退,自听或可增强,鼓膜内陷较为明显,可见液平面,甚至可见鼓膜破损,脓液流出;咳嗽咳痰,若从热化,则痰色黄黏稠,舌苔黄腻,脉弦滑;若是痰湿阻滞,则痰白量多,苔白厚腻,脉滑或濡。
3.3 肺气虚弱
平素体质虚弱,容易感冒,常常自觉少气乏力,或因大病初愈、术后产后等原因导致肺气不足,自觉耳胀、耳鸣,听力下降,耳内镜见鼓膜内陷、浑浊,久病不愈者或可出现钙化斑沉积,鼓室积液多清稀透亮,兼见咳嗽无力,咯痰色白清稀,短气疲乏,舌苔薄白,脉细弱无力。
4 治疗原则
最基本的治疗原则是恢复肺气的宣发与肃降功能。李梴在《医学入门》中指出:“凡治聋,必先调气开郁。”只有肺气宣降有序、气机调畅通达,耳窍才能通畅。明朝的《奇效良方》中强调:“欲以开发玄府而后耳中瘀滞通泄,凡治聋者,适其所宜。”故宜使用宣通开窍的药物,使郁闭的经气重新恢复通畅,耳窃听音辨声的功能才能正常发挥。部分患者除了肺气不通之外,由于耳聋反复发作或耳聋日久,尚兼有肺气虚,故治疗时还应该注意宣肺与补肺相结合。此外,肺气充盛,卫外功能得以发挥,则患者就不易感受外邪,也能减少耳聋的发生。在宣、补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体征,四诊合参,结合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等结果,辩证选用温、清、泻、和等手法治疗,可获得较为理想的疗效。
5 辨证论治
5.1 邪阻耳窍
宜采用宣肺散邪法。若患者外感风寒邪气,应当宣肺散寒,常用三拗汤加减。三拗汤出自宋朝《惠民和剂局方》,方中麻黄专疏肺郁,宣散气机,是开宣肺气的要药,不去根节,既可宣肺散寒,又使发中有收,不至于发散太过;杏仁不去皮、尖,散中有涩,敛降肺气;甘草协调诸药,共奏散寒宣肺、通窍散邪之功。若是外感风热邪气,宜辛凉宣肺,可选用银翘散加减。银翘散为吴鞠通创立,方中金银花、连翘辛凉轻宣,宣透外邪;薄荷、牛蒡子辛凉清热;荆芥穗、淡豆豉辛凉解表;桔梗、竹叶、芦根清热散邪;甘草协调诸药,共奏辛凉解表、宣散风热之功。
5.2 内浊阻肺
宜采用宣肺化痰法。若是肺热壅盛,可清化热痰,代表方为麻杏甘石汤。方中麻黄宣肺利水;石膏清泄肺热,同时制约麻黄;杏仁降气止咳;甘草调和诸药,可宣肺气、清肺热,耳聋自愈。若患者痰湿阻滞,宜化痰开窍,方用二陈汤。二陈汤亦是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中半夏燥湿化痰,和胃止呕;橘红行气,使痰随气行;茯苓、甘草健脾渗湿,以消生痰之源;煎加生姜,既制半夏之毒,又协同半夏、橘红和胃祛痰;少用乌梅,散中有收,使其不致辛散太过。诸药合用,共奏宣肺化痰之功。
5.3 肺气虚弱
宜采用益气补肺法。可选用阳和汤加减。阳和汤出自《外科全生集》,方中重用熟地补血养阴;鹿角胶生血益精;姜炭、肉桂温脾助阳;白芥子消痰散结;麻黄宣肺;甘草和诸药而用,犹如离照当空,阴霾四散,耳聋自愈。
6 病案举隅
病案一:厍某某,女,24岁,初诊时间为2021年2月6日,双耳听力下降,右耳重于左耳。就诊6天前雪天骑摩托车后出现头痛鼻塞,伴流涕咳嗽、恶寒,无发热,咽部疼痛,自服抗病毒颗粒后,咽部疼痛好转。就诊1天前出现双耳听音不清,伴耳闷,听音如隔薄膜,继而出现耳鸣,恍如雷声,昼轻夜重,纳可,眠差,二便正常,舌淡红,苔白略厚,脉稍滑。查体见双侧外耳道无异常分泌物,右侧鼓膜略内陷,光锥缩短;咽部无明显异常;双鼻甲肿大,分泌物增多。电测听右耳27db,声导抗见,B型曲线(鼓室积液)。辨证为风寒束肺,治宜宣肺疏风散寒。拟用三拗汤加减,具体方药如下:麻黄6 g、杏仁10 g、柴胡10g、薄荷6g、白芷6g、辛夷6g、石菖蒲6g、甘草6 g。7剂,水煎服,每日1剂,一日3次。另予院内制剂鼻塞通滴鼻,每次1~2滴,每日3次。二诊时间为2021年2月14日,自述听力明显好转,耳中胀闷感消失,白天耳鸣消失,但夜间偶有轻微耳鸣,纳可,眠仍差,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嘱患者按原方3剂服用,2日1剂,每日2服,继续滴鼻。半年后随访,患者病瘥,再未出现耳鸣耳聋。
此例患者因外感风寒邪气,累及肺卫、祸及咽喉,故出现恶寒头痛等外感表证,且伴有咽喉疼痛,虽自服药物,但仍未能完全祛除邪气,余邪停于体内,阻滞经络气机,肺气升降失司。而“肺主气,一身之气贯于耳,故能为听”,肺气不通,耳的正常功能就不能发挥,故患者出现听力下降、耳胀耳鸣症状。结合病因及其他临床表现,中医辨证为风寒束肺,治法当疏风散寒宣肺。方中麻黄、杏仁调理肺气;柴胡、薄荷发表散邪;路路通、白芷、辛夷石菖蒲通窍;甘草调和诸药。采用中医外治的滴鼻疗法可有效提高治愈率,减轻患者痛苦。本例患者西医诊断为分泌性中耳炎,该病的发生与病毒感染、炎症等因素有关,主要的病理机制是由于炎症等因素导致咽鼓管部分或完全堵塞,通气不良,进而引起鼓室负压,产生渗出液或漏出液。若配合使用滴鼻法,药液可直达鼻咽部,收缩咽鼓管咽口的黏膜,改善鼻腔和咽鼓管的通气状况,减轻患者症状。内外同治,协同增效,共奏宣肺通窍之功。
病案二:刘某,女,29岁,高中教师,初诊时间为2020年5月24日。自诉2020年4月以来,双耳出现鸣响,起初声音较弱,继而加重似蝉鸣,夜间或安静时加重。由于负责高考班教学,工作繁忙,故未予以治疗。自2020年5月以来,双耳听力下降,起立时耳鸣尤其严重,伴有全身乏力倦怠,食欲不振,大便偏稀,不成形,夜间难以入眠,烦躁不安。望诊见其面色少华,舌质淡,苔薄白,舌边有齿痕,脉细弱;查体见双侧外耳道无异常分泌物,双侧鼓膜无明显异常;林纳试验(+)。中医辨证为肺脾气虚证,治宜补肺健脾。拟用玉屏风散加减,具体方药如下:黄芪(蜜炙)20g、白术20g、党参10g、当归10g、茯苓15g、陈皮5g、柴胡6g、香橼6g、石菖蒲6g、炙甘草6g。7剂,水煎服,一日一剂,一日3服。另用王不留行籽贴压内耳、肾两穴位,嘱患者自行行“鸣天鼓”疗法,具体方法如下:两手掌心紧贴于外耳道口使之暂时封闭,两手指置于枕部,食指放于中指上,然后滑下,轻叩枕部,左右手各叩击24次。二诊时间为2020年6月9日,自诉耳鸣减轻,听力逐渐恢复,夜间能安然入睡。再予原方3付服用。
此例患者系高中毕业班教师,时常高声宣讲,生活不规律,导致肺脾气虚。《内经》曰:“肺病者……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肺气虚弱,则无力支持耳听音的生理功能,治当补益肺气。本例患者脾气亦虚,故应肺脾同治。方中黄芪大补肺脾之气;白术、党参、当归、茯苓健脾益气,培土生金,资黄芪益气固表之功;考虑患者压力较大,故加柴胡、陈皮、香橼疏肝解郁;石菖蒲通耳窍;甘草调和诸药。“鸣天鼓”疗法出自《灵剑子导引子午记》,常用于治疗耳鸣、耳聋,独具中医特色。
7 小结
综上所述,肺与耳在病理生理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相关的论述从古至今都有,“耳聋治肺”在临床上确有指导意义。当然,这一治疗方法并不意味着从肾、肝胆论治耳聋是错误的,仍需医者准确辨证、审证求因,不可偏信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