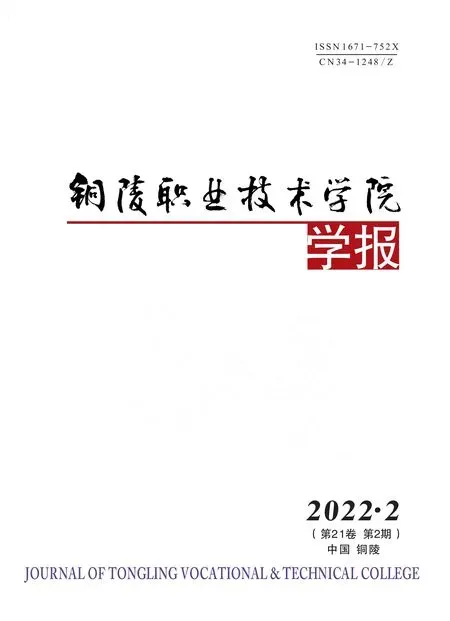ECL视域下3岁儿童母子互动中否定性话语探析
2022-08-23陈诗
陈 诗
(东华理工大学,江西 南昌 330000)
在乔姆斯基认知语言学TG的基础上基于“体”和“认”的核心原则将语言学本土化以形成具有唯物观和人本性的“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语言学ECL。不同于CL或者TG聚焦于零位人本观[1],ECL强调语言表达的人本性——人之所为,为人参之,即在现实与语言之间开启人的先验性,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把握自我内化,以语言这一外在形式呈现主观意蕴,此时不同语境下主体的表达差异性依靠语言这一外在形式显现。话语通过形式的流变服务于主观意愿的表达,所有的意愿性皆可分为两类——正向意愿与负向意愿并形式化为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及基于此两类基础形式的变异,如:疑问形式、祈使形式、强调形式等;满足交际需求目的,如:同意、附和、请求、趋使、避免、否认、责怪、怀疑等。主体的交际都是为了一定的目的性而遵循的交际原则,一旦交际双方的交际需求或者交际原则无法达成一致,否定性话语将会出现以表示说者对听者的情态趋向,如:责备、拒绝、警告、禁止、劝阻等,根据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否定性原则,即凡语言必有否定性的存在[2]。否定性话语指在话语中具有否定功能,包括语义否定与语用否定的话语成分与语言片段[3]。本文结合ECL认知语用学中的主观性因素的作用效力,即将社会现实因素填充进主观认知这一框架,使话语否定性具有语用联结效果。因此,文本不单纯分析语用否定,而是从语用的角度分析否定话语意蕴。同时,3岁儿童处于发展过渡期,与社会联系紧密性弱,以家庭为活动中心,以父母为主要教育者,由此,说话者采用何种言语形式交流、对交际过程中的变通性等言语及非言语的掌握[4],影响着儿童语用行为水平与儿童社会化进程,这一阶段自我意识的产生与多个关键期——分离焦虑期、执拗期、秩序敏感期以及自我意识建构期的非单一性出现促使非意愿意识产生,从而导致不同情境中违背性话语行为出现,并使儿童否定性表达趋向丰富,本文分析了3岁儿童与范围内互动者的言行,以母子的高频性互动文本为主题,以北大CCL语料库、BCC语料库、朱氏语料库、影视相关作品、儿童绘本以及南昌市某一幼儿园实地考察为检索对象进行语料选择分析。因为否定性言语与消极性行为及儿童体内激素水平呈相关性,所以把握情境中言行否定规律,在母子互动中及时调整言语主导者——母亲言行,为儿童的良性循环发展提供指导。
一、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的区别特征
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一个句子的形成过程需要经历由深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转换为表层结构[5]。语境否定可存在于话语否定、行为否定、话语+行为否定等,文本将焦点置于话语否定。话语否定可分为显性话语否定和隐形话语否定,所谓显性话语否定则是话语应答中包含明显消极性态度倾向的否定结构,也称表层结构否定,包括“不”、“别”等的基础性否定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否定延伸,如:“不 xx”、“别 xx”、“不能 xx”、“不可以 xx”等否定标记语或半否定标记语等的独立性或依附性话语成分。而隐性否定性话语则是指有否定意义但没有否定的明显外形,是通过间接或者暗示的手段表达否定含义的一种语用或者修辞手段[6],也称深层结构,需通过语境解构由深层结构解析为表层结构,其外在形式的框架性薄弱,只有在语境中才能发挥其特定的否定含义,且通过形式可表达多种功能,如:请求、安慰、提醒、劝阻、批评、禁止等。3岁儿童的否定语言系统更多倾向于显性语言,以单音节“不”及与“不”相关的延伸词“不要”、“不能”、“不会”、“不知道”等在话语中出现频率较高。隐性否定话语需要儿童接受否定信号,并将其内化,以深层系统框架来表达自我性否定意愿。这一过程对3岁儿童语言表达力要求较高,又与儿童这一阶段此类表达系统的丰富程度呈负相关,因此儿童此类表达一般伴随有不合作性肢体行为或以单纯不合作的肢体行为表达意愿。
二、显性否定话语的细化类别
显性否定话语的出现不同于其他文本形式特征,它以话轮的形式出现,并且一般处于话轮的接收位置而非会话首发者的发出语,即否定意愿的产生是由于与发话者意愿不一致而产生的。由语料分析可知,由于3岁儿童处于语言生长期,对语言的运用力较弱,因此对于显性否定性话语的运用多于隐形否定性话语的运用。儿童更倾向于情感的直接性表达,同样伴随话语特征出现的还有口语型、高频型否定词,如:不会、不要、不要、别、不想等,频率高于非口语型否定话语如:不可以、不合适、不需要等词的出现频率。显性否定话语的表达以音节的长度划分从而区分特定年龄段情感表达力以及语辞的丰富度,进而为教育者的对应性研究提供参照。
(1)单音节显性否定话语
单音节显性否定话语是指由一个有直接否定性意义组成的结构。此类语辞结构单一,一般出现在应答语的话轮之首,尤其是话轮结束直接性的态度趋向,使礼貌程度最低,不合作意愿也最强。出现在话轮之中与话轮之尾的情况较少,出现在话轮之中通常作为否定动词联结主语和宾语,其分离性较弱,因而不分为此类;而在话轮结束通常以主语“我”+否定词的形式出现,且多为连续性相同结构出现,以表达否定意愿的强烈性。除此以外在话轮结束出现的情况较少,此处以“不”为例。
例一:“我们一起和小山羊杠杠玩传球吧。”妈妈大喊。
“不,他会撞到我的。”丽丝回答。(《不再害怕尝试》)
话轮之首以单音节否定词“不”开始,直接表明态度,表达否定性意愿——对发话这请求的拒绝,以直接否定词+预测性结果“撞到”进行解释性结束话轮。
例二:“不!”他喊道。
“分给妹妹一些!”妈妈说。
“不! ”(《不想伤心的男孩》)
连续话轮之首的直接否定词“不”的出现,表明儿童对母亲的指令性话语 “分给妹妹一些”的强烈情感否定与行为拒绝,以此表明强制性意愿合作的不可行。
例三:我周五一定会回来,正好赶得上跟你一起玩捉迷藏。”妈妈说。
“不,别走! ”凯西恳求道,“求你了! ”(《魔法盒子:父母出差孩子怎么办》)
“不”这一直接否定词为表层含义的事理拒绝,接下来否定词“别”有表达否定义,连续否定词素的表达使儿童负向意愿强烈——希望妈妈留下。
例四:“噢,不!”哈利心想。
“只要在手指上刺一下,哈利,所以只疼一小下。”妈妈说道。(《哈利去医院:医院不是个可怕的地方》)
语气词“噢”作为前述语放在否定词“不”之前缓和否定语气,儿童心理活动话语表现为拒斥型行为以表明对对方话语及行为的主观否认。
(2)主语 +否定词
依据上文所述,此类既包括主语+单音节否定词是属于不归于单音节显性否定话语话轮之中的位置性否定词,又包括主语+双音节否定词,以及主语+多音节否定词等多种分类模式,此类模式以否定词汇依托主语的模式完成否定表达,否定指向性与意愿性更加明确。
主语+单音节否定词
例一:一天,妈妈说:“明天妈妈去吃苹果的时候,你可以和弯弯表哥在一起。”
“我不!我不!!”富丝说,“我会想死你的。如果你出事了怎么办?”(《不再害怕和妈妈分开》)
一般而言主语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主体词与否定话语的连用将否定强度直接推进,否定的高强度使母子间的话语冲突强烈,因而否定话语之后的解释性话语则削弱了两者冲突力,使得母子情感受损度降低,话语得以进展。
主语+双音节否定词
例二:“怎么?”妈妈用鼻子爱抚着她的小宝贝。
“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不觉得害怕了。我只是觉得高——兴——!”(《不再害怕和妈妈分开》)
“不在”表示消极情感的表示,即对母亲“不在”这一行为的情感否定、“不觉得”则是情感的转向,即对“害怕”这一词由“不在”这一消极行为引发的同向情感词汇的结果导向,双向否定词的连用消解了否定情感的冲突,根据Zipf的省力原则,双重否定话语不是理想的交际话语[7],对于话语的非直接肯定性陈述表达则是增加情感的支撑力,表达儿童的心理历程,同时也表明儿童否定话语的表达趋向丰富。
例三:“妈妈把这张照片也放进你的手提箱里吧,”妈妈说,“你要是想爸爸妈妈就看看照片。”
“为什么这次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去呢?”泰勒问。(《爸爸妈妈,快回来吧!》)
疑问性话语形式与否定词汇连用是儿童对这一行为——不能和父母同行表示不解与否定,情感意愿——希望和父母同行明确。
例四:他告诉妈妈他不想要静脉点滴,并向医生保证他再也不会吐了。(《哈利去医院:医院不是个可怕的地方》)
“不想”、“不会”以单音节否定词汇+意愿性导向词汇构成情态否定词素这一结构,既完整了句子链接又表达否定意愿,“不会”是对“不想”的否定意愿加强和补充,表明对母亲的情感依赖及对即将发生事件的排斥。
例五:“我不要再洗澡了!”
她变得不爱干净了。
无论她的父母怎么哄她,或是吓唬她,她就是不肯去洗澡。(《拯救浴缸:写给不爱洗澡的孩子》)
“不要”的情感拒斥性强烈,否定宣告型的主语表达表明主体的否定意愿强烈,以限制性否定词表达对“洗澡”事件的排斥。处于执拗期的儿童情绪不稳定性强,且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有短暂的不可扭转性,因此,儿童对母亲的话语礼貌将随着自身意愿的强烈性而不断变弱,不合作期也会加长。
例六:“妈,他打我!”艾西大叫。
“我没有。”弗雷迪叫着,“我把果冻洒你身上了,我只是想把它擦掉。”(《乌云之上有晴空:学会原谅别人》)
以第一人称+直接否定词的表述使话语的顺序性得以展现,即否定意愿(否定艾希所述“打”这一由主体进行的事实行为词)+原因阐述(主体对于“没有”这一意愿的后续解释),虽然表层是家庭中同一层及成员之间的话语否定,但深层表明儿童对家庭话语权威者的间接话语否定。
例七:露娜听了兴奋不已,“你是说我的名字不是一条鱼?”
“当然不是了。”妈妈说道,“那么,我们再来谈谈你的眼镜……”
“没关系,妈妈,我不再介意戴着眼镜了。”(《戴眼镜的露娜》)
话语中否定性语词“不是”、“不再”都是对自身事件的否定作用力,同时以递进的方式传达对母亲所述焦点性话语的反向意愿——一是否定对称谓的不合理理解;二是否定对事件的非意愿。
例八:妈妈一边煎着法式吐司面包一边说:“今天是星期四,你有什么新鲜事儿要告诉老师和同学们呢?”
“我要告诉老师和所有的小朋友我不用后面的小轮子也能骑自行车啦,”凯西说。(《魔法盒子:父母出差孩子怎么办》)
此例的否定词“不用”并非是对话语发出者即母亲的语用否定,而是对自我先前行为的否定——对先前骑车需要用后面轮子的行为进行否定,父母对于儿童否定性话语起引导作用。
主语+多音节否定词
例九:妈妈对她说:“别那么霸道!谁在乎是输还是赢?这只是个游戏!”
莎莉扑向她:“但,我不喜欢输,赢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输不起的莎莉:教孩子如何面对输赢》)
不喜欢=喜欢的否定,是否定词“不”+动词“喜欢”的构式表达构成新的动词义——对所指事件“输”的不满与否定,母子间对于输赢的论断与相反方向的看法以及教养者的正确输出对儿童自我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
例十:“可你又不是飞行员,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呢?”凯西问。
“有时候我必须和他们见面,”妈妈说,“就像你跟约翰、惠特妮用积木搭大城堡的时候一样。”(《魔法盒子:父母出差孩子怎么办》)
“又不是”仍是有与“不是”这一否定词有相似基础否定义的词,但是在“不是”这一完整否定词的基础上加上副词“又”,表示递进式的否定,是儿童对分离事件的疑惑以及伴随分离产生的焦虑。
例十一:萨米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我害羞。”
“嗯,”妈妈说:“记得当你还是个小宝宝时,你经常和米勒先生一起看鸟吗?”(《我要更勇敢:克服害羞的故事》)
与上述案例相似,都是通过对正向动词加以单音节否定词“不”构成对这一动词的直接否定——“不”+“知道”=“不知道”,即发话者对接受话语者行为所表现疑问时自身的疑惑。
(3)双音节否定词
此类双音节否定词排除主语+双音节否定词这类情况,而以双音节否定词或者离合主语与双音节否定词这类位置结构的否定表达进行文本分析。双音节否定词在文本中的位置没有特殊限制,定位灵活,可以位于话轮之首、话轮之中或者话轮之尾,皆可在话语表达中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表达意义。
话轮之首
例一:“要不我们去姥姥家住!”
“好啊!”妈妈一边答应着,一边拿起衣服。(《爸爸妈妈,快回来吧!》)
“我们去姥姥家”这是包含完整主、谓、宾成分的句子,“要不”一词以副词成分附加在句首作为转折类请求话语,指向是对前述主体话语的否定转折,而“要不”这一语体具有选择成分,既可保存前述主体的意愿,又包含自身意愿的方向性,只是指向自身意愿较前述主体者意愿强烈。
例二:“游戏很精彩!我今天可不是输不起了。”
妈妈说:“确实!虽然输掉比赛还是有点儿难过,”
“不过玩得开心就是赢!”萨利说。(《输不起的莎莉:教孩子如何面对输赢》)
与例一中“要不”的语用与结构用法具有相似之处,在语义程度方面存在差异,是对“输”与“赢”之间语境的心态转换,使儿童真正体会到“输”的意义促进自我意识建构。
话轮之中
例三:“雷声不过是响亮的噪声而以。妈妈说。”
“对,它伤害不了我,”贝贝说。(《有时我会害怕》)
“不了”是对“伤害”这一动词的否定修饰,“了”做副词置于动词后,常与“不”连用,表示“某一事件的不可能性”,这一否定结构并不是对话语发出者的语义否定,而是在顺应话语发出者的话语同时对这一描述性事件主体——雷声的否定评价,属于主体双方同向话语意向。
例四:“你今天怎么样,哈利?”
“我的肚子不再疼了。”(《哈利去医院:医院不是个可怕的地方》)
客观事理的陈述以否定词“不”+程度词“再”构成修饰性副词“不再”用以作用于动词“疼”,延续话语发问者对指示事件的反向疑惑。
话轮之尾
例五:“多好的一天啊,我们出去走走吧。萨米,我们下楼去买冰淇淋吧。”
“我带上斯巴克行不行!”萨米问。(《我要更勇敢:克服害羞的故事》)
“x不x”作为话语标记语(所谓话语标记语指在互动式言语交际中从不同层面上帮助建构持续性互动行为的自然语言表达式。)附加在陈述句的结尾用来传递一种肯定或者否定意向[8],在此“不”虽为否定词性,但融入话语标记语这一表达式中却是具有请求认同功能,即我想带上斯巴克,对于母亲否定意愿的正向拒斥。
(4)多音节否定词
儿童的话语系统发达性不高,对于多因此词汇有此事多音节否定词的掌握有一定的限度,但由于母子互动的高频性,儿童对于母亲的多音节否定话语具有一定的选择模仿力,通过对语料的筛选排除将儿童对多音节否定词的习得大致分为离合式、插入式、定型式以及框架式等多重结构进行分析。
离合式否定
例一:妈妈:“宝贝笑起来像只小猴子啊,好可爱!”
茜茜:“别那样说我,我会不开心的妈妈。”
“别那样说”作为否定性质离合型动词,其直接组成成分之间可“离”可“合”,“别那样说”相当于“别说”——合则为语,分则为词[9]。同时,“别那样说”顺应语境中“不开心”这一同向性话语,都属于否定性质,否定第一论元中的话语义表征。
插入式否定
例二:“我希望你的计划里有捉迷藏,”妈妈大声说,“因为我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你绝对找不到我!”
“当然不可能!”凯西大叫起来,“我一定能找到,因为我从来都没输过呢!”(《魔法盒子:父母出差孩子怎么办》)
“当然不可能!”在此作为插入语成分表否定义——否定论元发出语中对论元接收者的的能力否定,插入语位置较为自由,作为母子互动话语中儿童话语成分中的插入语部分,通常不作为话语开端语,而常处在两个小句之间独立使用。同时“从来都没”修饰“输”这一表现性词语也是对论元发出者话语的否定。
定形式否定
例三:“他们叫你什么?”
“他们叫我‘输不起的莎莉’,泰勒先生说,输不起的人什么都得不到,还会失去朋友。”(《输不起的莎莉:教孩子如何面对输赢》20)
“输不起”、“得不到”在此作为连接两个论元——莎莉和他们(朋友)的动词结构,两个论元的配位方式以针对型的位置结构出现——准二价针对定形式否定词。根据施春宏在《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9]中对语块的分类可知,“输不起”、“得不到”属于类似于一般动补结构的惯用语,具有较弱的类推性,通常中间带有“不 /得”等词,易“离”难“合”,惯用语属于定型式中的第三层级结构的一种。
框架式否定
例四:“妈妈今天晚上不能回来了,让爸爸陪你睡好吗”妈妈。
茜茜:“妈妈,当你不在身边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
“当……的时候”这一话语模式指示语块内部的空槽,需要合适的成分补足话语才能形成完整的表达,这一结构属于单槽框架式的否定话语模式,语用表达为对话语发出者的不赞同,对其建议的不接受。
将250个案例抽取量比以10%的比例呈现在文章中,由表1可知,3岁儿童在母子互动中的否定话语以 “主语+否定词”的表达方式为主体,占比50%,说明儿童的主观表达意愿强烈,自我中心性表现突出,否定能力伴随主体的表达生成;进而否定表达以“双音节否定词”、“单音节否定词”、“多音节否定词”呈降序存在于表达序列中。

表1
三、隐性否定话语的细化类别
隐形否定话语的出现频率在3岁儿童话语互动中低于显性否定话语出现频率,并且其否定义的显现需要通过不同事理立场的语境探析由深层话语解析为浅层话语从而表达否定话语的不同功能特征。由此情境中不同话语功能的否定性可由不同话语目的表现出来,即请求、安慰、提醒、劝阻、批评、禁止等类型的话语表现形式,与否定意愿结合,从而使话语的礼貌性增强,避免了直接性的面子威胁行为发生的发生,促进话轮的转换以及话语目的的实现。
(1)请求类话语功能
例一:“小熊糖果不要吃了,会有蛀牙的!知道吗?”妈妈说。
“少吃点,我一天吃一个可以吗?”小朋友。(实际案例)
话语表达并无明显否定词,同时否定义存在于句子中,不同于显性否定表达其否定成分单独成句或者成为特定话语标记语存在,以主观意愿的请求否定会话发出者的要求,视为请求类否定功能话语。“可以吗?”类的话语+明显的问号表达使否定意愿显现——发话者对受话者行为的限制(“不要吃”)。
(2)安慰类话语功能
例二:“我今天做的饭不好吃,太咸了”妈妈说。
“妈妈,你看,吃完了”小朋友。(实际案例)
“饭不好吃”和“吃完了”是一种反向话语表达力的体现,看似与发话者的语力表达相反,但是却和其情感反应一致——饭是好吃的,而受话者的话语深层含义就是——饭是好吃的,从而在否定发话者话语语义的同时执行了安慰性的话语功能。
(3)提醒类话语功能
例三:“宝宝,你看我画的这个太阳好看吗?”妈妈。
“你把这个黄色要涂满!这样才好看呢。”小朋友。(实际案例)
“要”作为意愿性助动词,虽然没有明显的话语否定词,但却将施话者的话语意愿进行否定,以能愿动词“要”+意愿结果来提醒施话者的话语结果。
(4)劝阻类话语功能
例四:“我要去阿姨家拿点,跟我一起去吗?”妈妈。
“回来吧妈妈,琪琪的妈妈今天带琪琪去游乐园了。”小朋友
劝(回来)+阻(不去)的话语表达含义使儿童意向趋于否定即否定行为目的,非直接否定的语辞并不损伤听话者的负面面子,是话语冲突减弱,劝阻效力发生。
(5)批评类话语功能
例五:“小心妈妈,你把我的牛奶弄洒了,怎么喝啊。”
负向义的话语表达使施话者的话语义指向批评即儿童批评妈妈的做法,虽然带有负向词——洒,但并无明显否定词,所以仍属于隐性的否定。
(6)禁止类话语功能
例六:“可以吃一口你的苹果吗?”妈妈。
“你得用太阳和我换。”小朋友。
此类话语出现频率较低,一般是伴随有夸张修辞出现,用以达到绝对拒绝的目的。对于这个阶段的儿童来说禁止类话语表达一般是伴随有明显否定语辞出现,相较于禁止意愿的话语本身带有强否定功能,只是禁止类语辞的表达弹性降低。
如表2所示,隐形否定话语出现的总量在单位时间内搜集到的语例小于显性否定话语的表达量,也就意味着对于这一年龄段的儿童来说话语的表达力有限,尤其是在不违背他人负面面子情况下的否定话语表达,对3岁儿童来说需要一个引导过程。

表2
四、否定话语强度——不同话语形式的程度规则
根据否定话语的程度,否定性话语可分为显性否定(直接否定)、隐性否定(间接否定)以及反诘式否定,根据中国传统礼貌观,否定性话语的表达对话语接收者具有面子驳回以及礼貌消损效力,根据曲卫国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礼貌原则之一:亲近准则——依据面子里的家族血缘关系在具体的语言使用过程中,话语者选择的词语越表示亲近,所给的面子就越大,也就相应的越有礼貌[10]。因此,基于礼貌观的影响,对否定性话语的否定程度的把握则是十分必要,不但对于话语双方共同目的性的趋向程度有影响,而且否定的礼貌性也与话语的达成功能呈正相关。母子间的话语互动对儿童而言更是礼貌观的形成期,否定性话语的运用十分关键。
根据否定的效力而言,反诘式否定>直接否定>间接否定,而礼貌性程度则语词呈反向相关,其中直接否定语反诘式否定的否定受真值义的影响强于语境否定,也即无论在何种语境下都可表达一定程度的否定,语义的否定性不可消解。然而间接否定则受制于语境的限定,其否定阈取决于语境效果以及主题的表达意愿,而其否定语义的真值表现性离开语境则无法直接判断。
结语
将ECL话语功能与3岁儿童母子互动中的否定性情景相结合,以在现实语境中探究儿童的否定话语特征,并观察其对礼貌原则的运用性。母子互动这一设定情境中儿童的否定话语按其对话语的表达力可分为具有明显否定语辞的显性否定表达以及蕴含否定意蕴的隐形否定表达,就其对话语的掌握力度以及表达程度而言,显性否定的话语表达力大于隐形否定话语的表达力,同时在显性否定话语中以主语+否定词这一主观意愿强烈的否定表达量比值最大;隐形否定话语的表达功能按其程度基本呈降序的表达呈现——安慰、提醒、劝阻、批评、禁止。对于这一特定年龄阶段儿童的否定话语表达的研究是家庭教育的重点,不仅对于儿童的情绪情感的引导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儿童个性特征的掌握拓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