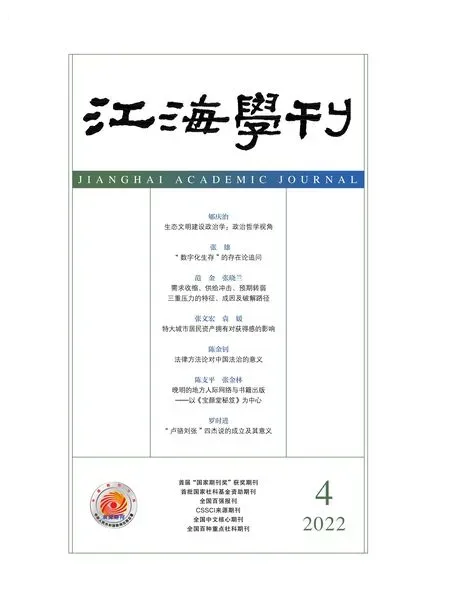晚明的地方人际网络与书籍出版
——以《宝颜堂秘笈》为中心
2022-08-22陈支平张金林
陈支平 张金林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书籍生产的繁荣时代,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庞大。(1)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1年版;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7页。在晚明诸多书籍种类中,丛书是颇值得注意的一类,丛书一般卷帙庞大、收录书籍众多。(2)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第111—116页。我们在翻阅晚明大型丛书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不少丛书和类书如《明文海》《古今逸史》《纪录汇编》等,都详细胪列了所收之书的编辑校对人员及其籍贯信息。(3)如《明文海》的每一种书都列了校对人,不过《明文海》的校对主要是由程荣一人独任其责的,参见程荣纂辑:《明文海》,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据明万历新安程氏刊本影印并补缺本。《古今逸史》的情况类似,校对人即编者本人,只有少数书例外,参见吴琯辑:《古今逸史》,上海涵芬楼1937年影印明刻本。《纪录汇编》则更为仔细,不仅收录的每一种书都列举了校正的人员,而且列举了对读的人,参见沈节甫辑:《纪录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影印明万历刻本,第23页。校对是书籍出版的关键环节,研究出版史,不能不关注校书。那么,这种详细胪列校对者信息的情形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它反映了晚明什么样的书籍出版实态?其对理解中国书籍史乃至更为一般的社会文化史有什么意义?据我们管见,似乎尚未有学者对这一现象予以专门的解读。因此,我们拟以晚明大型丛书《宝颜堂秘笈》为例,对上述问题试作探讨。
大致而言,有关中国古代书籍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文献学的研究,着重考察书籍的材质、尺寸、版本、编目等,也即版本目录之学;一类是所谓“书籍史”范式的研究,侧重考察书籍的生产、流通、传播、阅读等书籍的“生命历程”。(4)[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112页。纵观西方较有代表性的书籍史论著,我们发现西方书籍史研究在史料上的特色是较依赖书籍价格单、订书单、账簿、书商通信等材料,例如书籍史名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就是得益于书商之间的五万余封信件而写作。(5)[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顾杭、叶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可是在中国,这类记载书籍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经济史的材料委实难得一见,我们很难照搬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范式来重构一个书籍生产、流通、消费的历史过程。(6)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然而,中国书籍史也有自身的优势与特点,即记载书籍编校、序跋、题识方面的信息比较丰富,记载文人出版、交流的资料特别可观,(7)关于“文人”与“士人”概念的认识,学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我们也无意重新给出新的定义。大体上,当我们强调的重点是相关人员所具有的“文化”的一面时,用“文人”,当我们突出的重点为人们拥有的官员身份之时,用“士人”。而这些材料直接反映了与书籍出版有关的当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因此,如何就中国书籍史史料的客观情况做出恰当的解读,是需要审视的。是故,我们拟在书籍史视角的基础上带入人际网络的研究视角,对《宝颜堂秘笈》试作解读。
《宝颜堂秘笈》编校者籍贯略考
《宝颜堂秘笈》是晚明著名的大型丛书。自明末以来,各种书目收录《宝颜堂秘笈》时多题为陈继儒辑。(8)丁丙藏,丁仁撰:《八千卷楼书目》卷一三《子部》,《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张之洞:《书目答问》卷四《子部》,《续修四库全书》第921册,第647页;等等。然而,署名为陈继儒(即陈眉公)辑之《宝颜堂秘笈》一开始并无统一的名称,后来六部同类书籍陆续出版之后,版本目录家始把它们统称为《宝颜堂秘笈》,这六辑分别是《陈眉公先生订尚白斋祕笈》(一名《宝颜堂秘笈·正集》)21种47卷、《尚白斋镌陈眉公家藏秘笈续函》(一名《续集》)50种100卷、《亦政堂镌陈眉公家藏广秘笈》(一名《广集》)54种103卷、《亦政堂镌陈眉公普秘笈》(一名《普集》)50种88卷、《亦政堂镌陈眉公家藏汇秘笈》(一名《汇集》)42种86卷、《尚白斋镌陈眉公宝颜堂秘笈》(一名《眉公杂著》)17种49卷。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空青子、无名钓徒等,南直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晚明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山人、隐士,享有极高的声誉。(9)《明史》卷二九八《陈继儒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31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陈继儒》,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1页。然而考察《宝颜堂秘笈》的成书过程,实际的编撰者却非陈继儒。关于《宝颜堂秘笈》的成书经过,沈德先在《续秘笈序》中云:“余既镌《汇秘笈》,犹然不疗饕癖。复从陈眉公簏中索得若干种,辄以艳诧亲好,人亦不靳出所藏来会,而家弟更从荆邸寄我数编。”(10)沈德先:《续秘笈序》,《宝颜堂秘笈·续集·第一帙》,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刊本,第1页a—b。表示《续集》中的书得自陈继儒与诸亲友。(11)姚士粦:《叙》,《宝颜堂秘笈·汇集第一》,第3页。实际上,陈继儒也曾毫不隐讳地与友人说过,“但书坊所刻《祕笈》之类,皆伪以弟名冒之,念此曹病贫,贾不能救正,听其自行,多有极可笑、可厌者”,(12)陈继儒:《陈眉公尺牍》卷一《与戴悟轩》,贝叶山房1936年版,第35页。“《秘笈》非弟书,书贾赝托以行,中无一二真者,此曹贫,不忍督付丙丁”,(13)陈继儒:《陈眉公尺牍》卷一《又答费无学》,第36页。则《宝颜堂秘笈》非陈继儒所编应无疑问。因此,虽然《宝颜堂秘笈》中的若干种书出自陈继儒,陈继儒也参与过诸集的编校,但实际的主事者乃沈德先、沈孚先兄弟。
《宝颜堂秘笈》是商业出版物,所收之书多为消遣读物。大概由于第一集问世之后销路不错,该丛书不断有续集问世,前后共出版了六辑,前文已述之,共收书234种、473卷,其中大部分为明代著作,少部分为明前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宝颜堂秘笈》所收之书几乎全部标明了校阅者及其籍贯,校阅人数合计超过百人,校阅者有时候也是收录之书的作者。如此详细的编校者信息使得我们有可能了解每一种书乃至每一卷书的校对人员与校对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这部丛书的问世和编校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值得仔细分析。
古人云“书非校不可读”。书籍几经辗转流通之后,难免出现讹误缺字,需要校勘。那么这套丛书的具体编校情形如何呢?以下我们拟通过《宝颜堂秘笈》的各书校阅者来考察晚明的书籍编校情况。《宝颜堂秘笈》所编选之书的开头记录了校阅者的姓名与籍贯,经我们初步统计,所有校阅共涉及104人,未注明籍贯者7人,由于范明泰乃秀水范应宫之侄(详后),则《宝颜堂秘笈》校阅者中有98人可以确定籍贯。若以彼时县级行政辖区论,98人涉及14县,其中秀水(秀州)和嘉兴(檇李、嘉禾)82人、海盐2人、苕溪1人、盐官1人、华亭4人、秣陵3人、姑苏2人、无锡1人、新安1人、洪都1人;若以府为限,则涉及嘉兴、杭州、松江、苏州、应天、常州、徽州、南昌八府,分别为嘉兴府85人、杭州府1人、松江府4人、应天府3人、苏州府2人、常州府1人、徽州府1人、南昌府1人。其中,嘉禾、欈里(欈李)乃嘉兴府城一带之古称。可见,嘉兴籍的编校者占绝对多数,编校者是以嘉兴府为中心,囊括江南其他地区,偶有远达安徽新安(吴怀古)、江西南昌者(熊位女)。
不仅校阅者的籍贯比较集中,校阅订正的工作也主要集中在若干校阅者。据统计,陈继儒、高承埏、沈德先、沈孚先、姚士粦、王体元、陈天保、郁嘉庆、张昞、王体国、李日华、张弢校阅的书籍合计达281种,超过校阅总数的一半,亦即近十分之一的人校阅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书稿。可见,《宝颜堂秘笈》的编校虽参与者众多,但诸人在这部丛书中所分担的工作并不平均,主要工作是由一小部分人完成的,上述12人是《宝颜堂秘笈》校阅的主要承担者。既然编校者如此集中于嘉兴一地,那么这些编校者是什么关系呢?绝大多数编校者的籍贯集中于一地反映了什么内涵呢?
《宝颜堂秘笈》编校者的亲属关系网络
我们在阅读有关晚明嘉兴的史料时,发现《宝颜堂秘笈》的不少编校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人际关系。人际网络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最早由人类学与社会学开创,(14)J.A.Barnes, “Class and Committees in a Norwegian Island Parish”, Human Relations, Vol.7, No.1(1954), pp.39-58; E.Bott,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s, London: Tavistock, 1957; Jeremy Boissevain and J.Clyde Mitchell, eds., Network Analysis: Studies in Human Interaction, The Hague: Mouton, 1973.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界运用此种方法推进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15)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边燕杰主编:《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金耀基:《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参见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7、75—99页。该方法的总倾向是主张从“关系”和人际网络的视角来理解社会。在中国历史学界,近年来经若干学者的进一步倡导与实践,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寻求新突破的可贵尝试。如刘永华认为,人际关系网络既可以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又可以是历史研究的方法。从方法论的层面,可以把人际网络当作理解历史的一种路径,体现在对史料的处理上,就是以人名为“指南”,透过检视不同史料中的相关信息,拼接出研究对象的肖像,同时围绕这个个体,重构其人际关系,进而观察此人生活的时代与社会。(16)刘永华:《排日账与19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兼谈明清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史料》,《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刘永华:《“其板不许资与外人刷印”:晚清闽西四保的书板流通与社会关系》,《明清史评论》第2辑,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53—276页。
受此启发,我们采用人际网络研究的方法,结合书籍史的视角,尝试重构《宝颜堂秘笈》编校者的人际关系网络,以求进一步理解晚明书籍史。我们根据关系的性质把编校者的人际关系简单分为两种:一种是亲属关系,一种是非亲属关系,前者主要体现在宗亲关系与姻亲关系,后者主要体现在交友、同年、同僚等非亲属的关系。正是通过这两种人际关系,我们发现,晚明嘉兴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士人为主体的地方性社会关系网络。以下我们梳理编校者之间的人际关系。
沈德先家族。沈德先、沈孚先兄弟是晚明嘉兴的书商,是《宝颜堂秘笈》的实际主事者。沈德先,生卒年不详,嘉兴秀水人,字天生,沈思述子,沈孚先兄,东林党人沈思孝侄。万历三十七年(1609)举人,官上海教谕、国子监学录、桂番审理,升刑部河南司主事。明藏书家、刻书家,与弟孚先以刻书名著于时。沈德先与陈继儒、李日华、姚士粦等过从甚密。沈孚先(1576—1613),字白生,沈思述子,沈德先弟,沈思孝侄。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应天府教授,官历工部主事济南宁督南旺闸口,吏部验封司郎中。幼时聪慧,性喜藏书,著有《尚白斋诗文稿》《人才录》。沈士龙,生卒年不详,字汝纳,沈思孝子,沈德先、沈孚先从兄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晚明嘉兴藏书家、刻书家。沈士皋,生卒年不详,嘉兴秀水人,沈思孝子,沈士龙弟,沈德先从兄弟。沈元昌,字鸿生,沈思孝嗣子,沈德先、沈孚先从兄弟,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官故城教谕。(17)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474页;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纪念版)(精),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28页;丁辉、陈心蓉:《嘉兴历代进士研究》,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111—112页。此外,虽然目前并未发现表明编校者沈元祯、沈元熙、沈元嘉、沈元亮四人为亲属关系的记载,但考虑到他们同为秀水人,各字中间又都带有“元”字,他们同属一个宗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参与编校的沈氏诸人中,沈德先兄弟出力最多,沈德先在《宝颜堂秘笈》中编校的书达35种之多,沈孚先编校的书也有18种,其余诸人校书较少,如沈士龙只校对了赵台鼎著《脉望》第四卷(《续集》),沈士皋只校对了《丹铅续录》第八卷(《广集》),沈元昌只校对了《丹铅绪录》第七卷(《广集》),沈元祯只校对了宋柴望撰《丙丁龟鉴》第五卷(《广集》),沈元熙只校对了宋陈骙撰《文则》上卷(《广集》)和宋陶穀秀撰《清异录》第三卷(《汇集》),沈元嘉只校对了唐张鷟撰《朝野佥载》第四卷(《普集》)和宋陶穀秀撰《清异录》第三卷(《汇集》),沈元亮只校对了宋陈骙撰《文则》下卷(《广集》)。我们之所以详细列出诸人校对的具体卷册,意在指出沈氏诸人的校对反映了《宝颜堂秘笈》编校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编校是随意的,编校者并不专门负责某些书的编校。这种情形在整部丛书中非常普遍,常常是同一部书的不同卷分属不同的人校对,非主要校者通常只是校对某部书的其中一卷。可见,《宝颜堂秘笈》所收书稿的编校并没有专门的分工,编校并不系统,并无一定之规。
那么晚明其他丛书、类书乃至一般书籍是否如此呢?我们注意到大型书籍的编校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例如程荣辑《汉魏丛书》、华淑辑《闲情小品》等,其中的很多书都是由不同的人校对的,(18)程荣辑:《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刊本;华淑辑:《闲情小品》,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晚明建阳书商刘弘毅刊印《史记》和《文献通考》时也曾得到建宁、邵武官员的校订。(19)参见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第122页。因此,校阅的随意性不仅是《宝颜堂秘笈》编校的独有特点,也许也是晚明书籍编校的突出特点之一。这种情况表明晚明书籍出版中的校对尚未全面形成专门的分工,像清代那种高度专门化的校勘在晚明尚非普遍情形,书籍的编校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黄承玄家族。秀水黄承玄家族是晚明嘉兴的望族,见诸《宝颜堂秘笈》编校队伍的族人有黄承玄、黄承乾、黄承昊、黄申锡、黄卯锡等。黄承玄(1564—1614),清康熙年间为避康熙帝玄烨讳改作承元,字履常、宇参,黄洪宪长子,黄申锡、黄卯锡父,黄承乾、黄承昊从兄,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福建巡抚,赠工部左侍郎,著有《盟鸥堂集》《河漕通考》《两台奏草》《安平镇志》等。黄承乾,生卒年不详,字履谦,黄正色子,黄承玄从弟,黄承昊兄。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凤阳府推官,四十六年(1618)充本省同考官,继充湖广同考官,补兵部给事中,未赴,卒于家,著有《理学格言》。黄承昊(1576—约1645),字履素,号闇斋,黄洪宪次子,黄承玄从弟,黄承乾弟,黄寅锡、黄卯锡父,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历官河南盐驿副史、湖南参政、福建海防按察司副使、广东按察使等,著有《闇斋吟稿》《白乐道人集》《律例析微》《折肱漫录》等。(22)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二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44册,第552—553页;崇祯《嘉兴县志》(二)卷一八《艺文志》,《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25页;光绪《嘉兴府志》卷五二,鸳湖书院藏光绪戊寅年(1878)版,第37页b—38页a。黄申锡,生卒年不详,黄承玄长子,黄承乾、黄承昊侄,黄卯锡兄,著有《伤寒具眼》。(23)崇祯《嘉兴县志》卷一八,第725页。黄卯锡,生卒年不详,黄承玄次子,黄承乾、黄承昊侄,黄申锡弟,著有《闺秀诗选》。(24)崇祯《嘉兴县志》卷一八,第725页。可见,黄承玄家族有多人参与到《宝颜堂秘笈》的编校之中,只不过他们编校的书并不很多,两代人所校之书及所校之书的问世时间均不同。这也是《宝颜堂秘笈》编校的又一个特点了。
在姻亲关系方面,《宝颜堂秘笈》可见黄氏编校者的姻亲有屠中孚、郁嘉庆、项梦原等人。黄氏与嘉兴屠氏婚姻关系密切,黄承玄娶屠氏,黄承玄姑母黄观娇适屠中孚,黄承玄从姊妹黄淑德适屠耀孙,而屠耀孙正是屠中孚之侄。(25)沈季友:《檇李诗系》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2页;龚肇智:《嘉兴明清望族疏证》(中册),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376页;赵青撰,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嘉兴市文物局编:《嘉兴历代才女诗文征略》(上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屠中孚,嘉兴平湖人,生卒年不详,字德胤,号敏澜,秀才,著有《重晖堂集》等,(26)沈季友:《檇李诗系》卷一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5册,第406页;光绪《嘉兴府志》卷五一,第42页a—b。其在《宝颜堂秘笈》系列中校书很少,只有《陈眉公订正祈嗣真诠》一种(《普集》)。屠中孚从兄屠谦之女适高道素,(27)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340页。而高道素正是高承埏之父。高承埏,嘉兴秀水人(1603—1648),字泽外,号寓公,高道素子,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历顺天府宝坻县知县、甘肃泾县知县、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等。曾率民抵御清兵,父子皆以清节显,明亡后隐居,拒不仕清。(28)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44册,第499页。高承埏在《宝颜堂秘笈》系列中的校书达四十余种。郁嘉庆乃黄承乾之婿,(29)龚肇智:《嘉兴明清望族疏证》(中册),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页。嘉兴秀水人,生卒年不详,字伯承,别号拙修居士。明末嘉兴藏书家、书画家,喜结客,举家产收书,有贫孟尝之名,(30)光绪《嘉兴县志》卷二五,第14页。在《宝颜堂秘笈》系列中编校的书12种。黄卯锡妻项兰贞乃项德成之女,也即项梦原侄女,是明末嘉兴著名女诗人,著有《裁云草》《月露吟》等。(31)沈季友:《檇李诗系》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5册,第812页;光绪《嘉兴府志》卷七九,第71页a—b。
项氏亦为晚明嘉兴望族,见诸《宝颜堂秘笈》编校者队伍的族人有项梦原、项利侯、项琳之、项燧先等。项氏于鉴赏与收藏尤为一时所重,收藏大家项元汴即秀水项氏族人。项梦原,嘉兴秀水人,生卒年不详,原名德棻,更名梦原,字希宪,明末收藏家项笃寿次子,项鼎铉、项利侯、项利宾叔父,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官历刑部山西司主事、都水员外郎、山东督学、刑部郎中等。项梦原是晚明知名藏书家、刻书家,著有《读宋史偶识》《项氏经笺》《云烟过眼录》《冬官纪事》等。项利侯,生卒年不详,项梦原侄,项琳之从兄弟,著有《无患社诗稿》《薙余带草》。项琳之,生卒年不详,项梦原侄,项利宾、项利侯从兄弟。项燧先,生卒年不详,项利侯、项琳之从兄弟。(32)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五,第411—412页;崇祯《嘉兴县志》(二)卷一八《艺文志》,第726页;光绪《嘉兴府志》卷五二,第38页。项氏族人参加《宝颜堂秘笈》编校的方式与黄承玄家族类似,参与编校的数量不多,且较为随意,大体属于帮忙性质,而非专业的编校。
在姻亲关系方面,《宝颜堂秘笈》编校者中与项氏有姻亲关系的有黄卯锡、沈道明、屠中孚等。黄卯锡已如上述。沈道明,嘉兴秀水人,生卒年不详,名启南,号志堂,道明博综载籍,间为诗歌,书法宗李邕,颇有所得。(33)光绪《嘉兴县志》卷二七,第12页。沈道明与项氏的姻亲关系在于,沈道明之兄沈启原乃是沈德符、沈瑶华的祖父,(34)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二二,第546页;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330页。而沈瑶华正是项梦原的侄媳。(35)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294页。秀水项氏与平湖屠氏婚姻关系密切,至迟从项梦原祖父一代起,两姓即有婚姻往来,项梦原祖父项铨的从兄弟项镛即娶屠勋女,而屠勋正是屠中孚的曾祖父,项梦原曾祖父项纲的从兄弟项经之女又适屠中孚的祖父屠应埈。到了《宝颜堂秘笈》编撰的万历中期以后,两家的通婚更为密切,如项梦原兄项德桢娶屠中孚之妹,项梦原从兄弟项德裕娶屠孟元之女,而屠孟元是屠中孚的叔父,即屠中孚的从姊妹适项梦原的从兄弟项德裕。(36)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七,第428—436页;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293—294、339—340页。
李日华与李肇亨。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号竹懒、九疑,嘉兴秀水人,晚明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子李肇亨,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历汝州佐贰副官、西华知县、南京礼部主事,后辞官归家奉养父母,里居二十余年,与嘉兴地方文人交往甚多,是晚明嘉兴士人圈的核心人物之一。李日华工书画,精鉴赏,著述宏富,较为重要的有《恬致堂集》《紫桃轩杂缀》《味水轩日记》《六研斋笔记》等。(37)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一八,第519—520页;沈季友:《檇李诗系》卷一六,第376—377页。李肇亨(1592—1664),字会嘉,号珂雪,日华子,子新枝、琪枝,明末清初学者,喜藏书,擅书画,工诗文,有《写山楼》《率圃集》《梦余集》《率圃吟稿》《琴言阁新咏》。(38)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一八,第520页;沈季友:《檇李诗系》卷二○,第467页。
范应宫与范明泰。范应宫,字君和,嘉兴秀水人,生卒年不详,范之京子,范应宾弟,侄范明泰。范明泰,生卒年不详,字长康,号鸿超,范应宾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事母至孝,未求仕途。明泰工诗文,好刻书,嗜藏书,著有《米襄阳遗集》《米襄阳外纪》《米芾志林》等。(39)崇祯《嘉兴县志》卷一八《艺文志》,第726页;沈季友:《檇李诗系》卷一八,第421页。
陈邦俊与陈诗教。陈邦俊,生卒年不详,嘉兴秀水人,字良卿,号白石子,诸生,能文章,好搜罗遗文,著有《广谐史》《见闻纪异》《明代异人传》等。陈诗教,字四可,善文词,恃才傲物,好为讥刺文字。(40)盛枫:《嘉禾徵献录》卷四六,第729页;沈季友:《檇李诗系》卷一九,第421页。陈邦俊在《宝颜堂》编校的书有宋丘广庭著《兼明书》第三卷、宋荆溪吴子良著《林下偶谈》第四卷、杨慎著《异鱼图赞》第二卷。
张如兰、张可大与张可仕。张如兰,应天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字德馨,南京羽林卫世袭指挥,官漕运参将,张可大、张可仕之父。(41)黄虞稷:《千倾堂书目》卷二三,第612页。张可大,生年不详,字观甫,号扶舆,谥庄节。万历二十九年(1601)武进士,崇祯元年(1628)升总兵,驻防山东,崇祯四年(1632)升南京右都督,未及赴任,因“吴桥兵变”,败于叛军而自尽,著有《南京锦衣卫志》《驶雪斋文集》《驶雪斋诗集》等。张可仕,生卒年不详,字文寺、紫淀,号紫淀楚人,张可大之弟。(42)《明史》卷二七〇《张可大传》,第6939—6941页;王士祯撰,张宗柟辑:《带经堂诗话》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99册,第104页。
以上是亲属关系可以确定的编校者,至于王体国与王体元、郁之骥与郁之騟、王以纯与王以绳、陈良谟与陈皋谟等,虽然目前并未获见任何能够证实他们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史料证据,但是从籍贯和名字来看,他们或为兄弟或同宗兄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可见,以上编校者很多都是五服之内的亲属,甚至是父子兄弟这样的至亲。由于六部秘笈出版相差三十余年,很多不仅是同辈的兄弟参与,而且是父子、伯侄叔侄甚至祖孙参加,由此可见,这部丛书的出版与嘉兴地方家族的关系匪浅。在姻亲方面,许多编校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姻亲关系,他们或者为甥舅,或者为表兄弟,或者为翁婿,等等。通婚是连接两个或多个异姓家族的最好方式,通过家族之间频繁的通婚,嘉兴在晚明形成了一个密切的婚姻网络。(43)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243—398页。如上文所看到的,《宝颜堂秘笈》的诸多编校者——尤其是主要编校者——正是这个网络中的成员。
编校者的非亲属关系网络
除了由血缘和婚姻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人的具体实践也为关系网络的建构提供了持续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晚明嘉兴的地方性社会关系网络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才得以凸显的。这类人际互动大多属于非亲属关系的人际关系建构。宗亲与姻亲关系的网络是相对比较牢固静止的网络,而非亲属关系的个人交往更具有灵活性与随意性,更能反映人际交往的动态存在。晚明嘉兴士人往来频繁,尤其在文化活动上联系密切,他们常常通过书画鉴藏、诗文唱和、游山玩水、公共活动、祝寿聚会等方式增加了人际交往,加强了人际关系的亲密度,使社会关系得到再生产,在亲属关系之外增添了非亲属的人际关系,从而使这个人际网络变得更加复杂与厚实。作为嘉兴士人网络中的成员,《宝颜堂秘笈》的编校者们自不会例外。他们不仅存在密切的亲属关系,也存在非亲属关系性质的人际往来。以下我们即以《宝颜堂秘笈》主要的编校者为例,依次梳理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以期窥见晚明嘉兴士人人际网络的具体运作。需要说明的是,他们的人际网络不局限于嘉兴一地,而是扩展至整个江南,个别声望卓著者甚至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不过限于主题,本文主要探讨嘉兴的情况。
沈氏兄弟作为嘉兴的刻书家、嘉兴士人圈的成员,参加艺文聚会自是不少的。万历四十年(1612)六月十九日,董其昌在嘉兴项鼎铉家品赏字画,项鼎铉《呼桓日记》曾有详细的记载:“阴。日中大雨。董思白过晤。姚叔祥、沈天生、郁伯承、家昆于番、侄惟百皆次第到。思白亟索《万岁通天》真迹阅之。”(44)项鼎铉:《呼桓日记》万历四十年六月十九日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2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董思白即董其昌,晚明著名书画家,郁伯承即郁嘉庆。这样,他们之间也是互相认识的。同年闰十一月初,沈德先与李日华、徐达夫两次造访岳元声家,六日更是“四鼓别去”,尽兴而归。(45)李日华撰,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沈德先兄弟与李日华关系密切。在李日华辞官乡居甪里期间,沈德先与李日华曾八年为邻。李日华原来住在嘉兴府城东门附近,东门又称春波门,是商贾聚集的繁华地段。然而在写《味水轩日记》期间,李日华并不住在那里,而是住在城外的甪里。(46)万木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甪里正是沈氏兄弟的住处,“余昔居甪里,与沈白生联庐”,(47)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卷二六《周本音先生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63页。因为做了邻居,又有共同的爱好,李日华与沈氏兄弟过从甚密。万历四十年(1612)四月,二十四日晚,李日华和项孟璜会聚于沈孚先宅,相聚甚欢,(48)李日华撰,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四,第2540页。类似的活动非常多。在沈孚先死后,李日华又为其撰写了祭文,李日华感慨道:“余僦居甪里吴氏第,左邻赵驾部青阳,右邻沈铨部白生,二君俱有胜韵。……沈监税荆州,素号脂膏处,皭然不染,止携滇茶一株植家圃,作高斋封之。余深庆托交素心,得数晨夕。而二君前后化去,余亦还春波旧里,暇日追念,为之慨然。”(49)李日华撰,郁震宏、李保阳点校:《六研斋笔记》卷一,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可见李日华对沈孚先很欣赏,对沈氏兄弟的故去颇有不舍。至于声名颇盛、与嘉兴士人往来密切的陈继儒,(50)陈继儒:《陈眉公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0册。沈德先兄弟不可能没有听说过,况且沈氏兄弟出版《宝颜堂秘笈》还是伪托其名,因此沈氏兄弟可能是与陈继儒有所来往的,只不过不一定称得上频繁。然而,他们的叔父沈思孝与陈继儒的关系就很密切了。沈思孝年长陈继儒十七岁,万历三十四年(1606)冬,陈继儒在沈思孝的快雪堂同殷仲春、姚士粦、王淑民等诗文唱和,相聚甚欢。(51)陈继儒:《陈眉公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0册,第108页;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一八《题快雪堂岁寒盟》,《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页。除了亲自见面,陈继儒曾多次与沈思孝通信谈论各种问题。(52)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63、525页。姚士粦,嘉兴海盐人,万历举人,晚明学者,著述宏富。士粦虽是海盐人,但做过沈思孝的幕僚,(53)盛枫:《嘉禾徵献录》卷四六,第726—727页。与嘉兴地方士人往来密切,编校《宝颜堂秘笈》的书为数不少。
陈继儒虽是华亭人,但与嘉兴士人圈的往来很密切,除了上文所述沈思孝,陈继儒与李日华的关系更为密切。陈继儒早在万历九年(1581)即与李日华相识,日华时年18岁,陈继儒授其《毛诗》,自此他们结下了师生之谊。《陈眉公先生年谱》载:“十六年戊子(1588):……李九疑、陈白石自嘉禾来”,(54)陈梦莲撰:《陈眉公先生年谱》,载《陈眉公先生全集》(附《年谱》一卷),《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9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930—968页。李日华此次赴松江是拜访陈继儒。李日华曾如此评价陈继儒:“吾师眉公先生,灵心妙韫,卓蹈遐踪。于学靡所不窥……上足掩商瞿、干臂、毛、鲁、孔、伏之光,而下可刮盲史之膜,胔腐令之骨,卓然表竖天壤间……不轻出也”,(55)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中册)卷一一《陈眉公先生秘笈序》,第533页。可谓推崇备至。由于两人同有丹青之好,常在一起探讨书画、交流心得。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曾多次记载他们品评字画的情形:“今崇祯庚午(1630)之二月,晦甫卧疾,忽令所善鲍老归余。既成购,而晦甫即治后事,若相付者。余庆物之来,而怅友之速化也。越月,陈眉公先生顾余清樾堂,出观,终日赞叹。”(56)李日华撰,郁震宏、李保阳点校:《六研斋笔记》卷三,第131页。陈继儒曾到嘉兴坐馆,许多嘉兴士人与其有师生之谊,(57)陈梦莲撰:《陈眉公先生年谱》,载《陈眉公先生全集》(附《年谱》一卷),《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99册,第954页。再加上陈继儒名动天下,诗文书画造诣精深,因而常被奉为座上宾,与嘉兴士人圈的关系非常密切。据陈继儒《冬余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日,郁嘉庆来访,“伯承以岁杪踏冰霜访予,草堂信宿,非特高义。实以五十,婚嫁皆毕。二子皆秀才,闭门读书史,无烦检课。伯承真冬余处士也。”(58)汪珂玉:《珊瑚网》卷一七“陈眉公冬馀记”条,同前书,第152页。后来他们还一起品鉴花瓶,颇见二人之趣,(59)陈继儒:《陈眉公集》卷一一《书袁石公瓶史后》,第162页。也可见二人关系密切。陈继儒也曾与《广庄》的编校者范明泰鉴赏山水画。(60)陈继儒:《陈眉公集》卷一一《答范长康》,第171页。陈继儒也与顾宪成有所往来,曾和顾宪成探讨读书心得,并把所著呈请顾宪成斧正。(61)陈继儒:《陈眉公集》卷一一《答顾泾阳》,第170页。张可大虽是军旅中人,而且远在南京,但是陈继儒仍与之有往来。陈继儒非常推崇张可大,并以张氏军务繁忙而不能坐而论道为憾。(62)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6册,第510页。
李日华是晚明嘉兴士人圈的中心人物之一,辞官里居二十余年,与嘉兴乃至江南的士人往来密切。李日华笔耕不辍,著述宏富,留下了丰富庞杂的史料,尤其是其暂居甪里撰写《味水轩日记》期间,更是巨细无遗地记载了书画品鉴、诗文切磋、人际交往等家居生活,不仅为了解晚明士人生活留下了宝贵的材料,也为江南士人人际交往留下了难得的素材。除了前述与沈德先兄弟、陈继儒有交往之外,李日华与《宝颜堂秘笈》的编校者有往来者尚有很多。李日华与郁嘉庆的关系很好,“余友郁伯承,勇者也”,(63)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卷二三《先懒庵记》,第874页。常常一起互通书册,切磋读书之得。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李日华拜访郁嘉庆,一起讨论陆游《出蜀记》;(64)李日华撰,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二,第82页。万历三十九年(1611)九月二十三日,李日华曾向郁嘉庆借过三本纪游之作。(65)李日华撰,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三,第208页。他们常常一起参加活动,之间的友谊几乎延续终生。姚士粦是李日华的文友,两人常有诗文唱和,(66)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中册)卷一五《〈段黄甫诗集〉序》,第652页。在姚士粦考中举人后,李日华专门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表示祝贺。(67)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上册)卷一《贺姚叔祥举子》,第30页。李日华与岳氏三兄弟的交情都很不错,他们常常谈论读书心得,互通琴棋书画之得。李日华对岳家三兄弟很是推崇,他曾写信问岳元声有无读《易》的心得相示,其中有云,“谭人间可喜事,或屈指海内胜流,必首推君家昆季”,他与岳元声非常相投,“鄙人尤心折长公孤秀,岂寒岩枯木,气味相投耶?”(68)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下册卷三二《柬岳水部石帆》,1146—1147页。李日华年少时就与岳元声相识,他少时有一次去里社,见人玩一种叫“拘艺”的游戏,其他人都冥思苦想,唯独岳元声嬉笑自若,可见岳元声非常聪明。(69)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中册卷一八《题岳且涟江晓拈时义》,第734—735页。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他们还一起参加过嘉兴楞严寺正堂的募修,当时“议各任募百金”。(70)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下册卷二八《楞严寺募修正殿柱疏》,第1016页。李日华和岳元声曾一起讨论《老》《易》之旨。岳元声六十大寿时,李日华还专门写诗贺寿。(71)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上册卷一《寿岳石帆六袠》,第41页。岳骏声在千里之外的荆楚之地任官时,仍然很关心身在乡梓的李日华,(72)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下册卷三二《答岳石钟太守》,第1156页。当岳骏声过寿时,李日华写了一首贺诗,推许岳骏声“仙级高推第一班”,(73)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上册卷七《岳石钟银台》,第345页。而当岳骏声去世之后,李日华也撰写了祭文。(74)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下册卷三三《祭岳银台石钟文》,第1201—1202页。李日华与岳和声的交往也很密切,万历三十八年(1610)闰三月初一,李日华拜访岳和声,一起品赏《研山堂帖》,(75)李日华撰,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二,第100页。不到十天,李日华又和项孟璜到杉青闸给岳和声饯行。(76)李日华撰,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二,第101页。岳和声是李日华的同年,晋江李廷机是他们的共同座师。当万历四十年(1612)十一月李廷机去职返乡路过嘉兴时,岳和声和李日华一同接待了他。(77)李日华撰,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四“十一月四日”条,第297页。万历四十一年(1613)正月,李日华与岳和声等人造访项鼎铉(字孟璜)的招集园,两人极力怂恿项鼎铉改造园子,(78)李日华撰,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校注》卷五“正月十一日条”,第323页。后来他们还多次到过项鼎铉的园子。当岳和声入京任职之际,李日华特意叮嘱他“惟多噉饭,少饮酒……庶于神用有裨也”。(79)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下册卷三二《又柬岳石梁》,第1150页。当岳和声去世之后,李日华又为其撰写祭文。(80)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下册卷三三《祭同年岳中丞石梁文》,第1200—1201页。李日华不仅与项鼎铉交好,其与鼎铉叔父项梦原的交情也不错。当项梦原还朝时,李日华曾写诗相赠。(81)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中册卷一○《关项希宪比部还朝》,第509页。当项梦原六十大寿之际,李日华写了一篇寿序表示祝贺,对项梦原治《尚书》很是推崇。(82)李日华撰,赵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中册卷二一《项宪副希宪六十寿序》,第830—832页。在李日华的追随者中,还有诸生钱应金。钱应金,字而介,晚明嘉兴人,擅长诗词骈文,崇祯中嘉兴大疫,死者甚众,应金募人掩埋。钱应金与《宝颜堂秘笈·续集》的主要编校者高承埏相友善,凡有著述,“皆承埏为之序”。明清鼎革中嘉兴城陷,钱应金避走乡间,但不幸为盗贼所杀,高承埏将其安葬,并写了悼词。(83)盛枫:《嘉禾徵献录》卷四六,第731—732页。从两人的友谊和钱只校对了一卷的情况看,钱应金的校对可能只是作为朋友略微帮忙而已。
除了编校者之间的人际交往外,也有一些群体性活动,更可以证明晚明嘉兴地方士人网络的存在。三过堂和烟雨楼是晚明嘉兴的著名楼阁,是晚明嘉兴士人进行文化雅事之所,留下了大量墨宝。万历三十八年(1610),致仕在家的沈思孝邀姚士粦、陈懋仁、项利侯、屠兑访三过堂。沈思孝抚今追昔,感念人生,当即吟出一首七律《春日同诸名胜访三过堂》。随后,姚士粦、陈懋仁、项利侯、屠兑相继步沈氏原韵奉和一律。(84)崇祯《嘉兴县志》卷五《建置》“古迹”,第185页。从五人的交往看,姚士粦、项利宾、项利侯应为沈德先、沈孚先兄弟之长辈。万历二十九年(1601)五月,屠中孚、孙光裕、姚士粦、朱廷策、李贞开、彭绍贤六人同游烟雨楼,(85)崇祯《嘉兴县志》卷五《建置》“古迹”,第199页。说明屠中孚、姚士粦、朱廷策三人相互认识。崇祯《嘉兴县志》曾载包衡作《同沈祖量、丘伯畏、陈仲醇、殷方叔集烟雨楼诗》,(86)崇祯《嘉兴县志》卷五《建置》“古迹”,第201页。殷方叔即殷仲春,包衡与沈祖量、丘伯畏、陈继儒诸人同游烟雨楼。如此,包衡、陈继儒、殷仲春三人也是相互认识的。同卷载,王体元、屠隆、黄承昊、项圣谟同游烟雨楼,并有赋诗,屠应诏即屠隆。如此,此五人亦相互认识。万历末期,嘉兴重建烟雨楼,岳元声题写《重建烟雨楼记》,考其立石者,同列《宝颜堂秘笈》编者的有岳元声、沈中英、李日华诸人。此后,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诗文或留有足迹。其中参加《宝颜堂秘笈》校阅的有:岳元声、沈启南、王穉登、何三畏、黄承玄、岳和声、殷仲春、李日华等,可知这个地方文人群体与书商的书籍编校事业或多或少有些联系,同属于一个文人交游网络。
除了以上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之外,书信的往来也值得注意。在交通相对不发达的古代,见面交往仍然是比较费时的。譬如从嘉兴到杭州、苏州,今日交通只需一二小时,而当时李日华至少需要在途中过夜才可到达目的地。(87)万木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第24—27页。在这种情况下,书信的往来就很好地起到了沟通的作用。尺牍的交往一般限于通信双方,私密性较高,是人际交往最直接的证据之一。陈继儒、李日华、冯梦祯等人的文集收录了大量尺牍,证明他们之间的交往是非常频繁的。这类书信非常多,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在地域范围和人群比较确定的情况下,根据书信可以串联起人际关系的网络。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征引他们交往互动的材料,就在于力图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嘉兴地方士人网络不仅通过血缘姻亲建构起来,也通过日常实践建构起来。对人际关系网络的研究,粗略而言大概有两种取径:一种考察人们在具体的情境下如何利用人际关系来达到某种目的,现有历史学领域的大多数人际网络研究就是这种取径;一种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自变量,考察网络如何影响人与社会乃至改变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机制,这种取向认为人际网络可以形塑社会,对社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约略可以窥见,晚明嘉兴以士人为主体的地方性网络正是通过亲属人际关系和非亲属人际关系而建构起来的。这种“非亲属性质的人际关系”包括许多种形式,交游、书画品鉴等,而校书正是其中的一种。可以说,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正是通过校书等实践活动而建构起来的。虽然上文论述了嘉兴存在若干个影响力很大的望族,许多编校者也都是出自这些大族,但编校者的行动却不是以家族,甚至也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行动,而是个体的行动。
结 语
中国古代书籍的出版囊括很多环节,校对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之一。晚明大型丛书《宝颜堂秘笈》所收的每一种书都记载了校阅者的姓名与籍贯,本文通过对校阅者籍贯信息的梳理,发现校阅者多为嘉兴人,且多数是嘉兴府城及其周围之人。进一步探究编校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性质和人际互动,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属关系与非亲属关系性质的人际互动。从血缘关系看,编校者或为父子、或为兄弟、或为叔侄的情况比较普遍,主要校阅者大多出自沈氏、项氏、岳氏、屠氏、黄氏等影响力很大的嘉兴望族。从姻亲关系看,编校者之间或编校者所在的家族之间存在比较多的通婚情形,有的甚至已经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固定联姻关系圈。从非亲属性质的关系看,编校者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密切的人际交往,他们常常一起赏鉴书画、吟诗作赋、交流读书心得、参加地方公共活动等,这种非亲属性质的人际交往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晚明嘉兴文人实际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互动频繁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个网络无固定的组织与场所,也不以家族为行动单位,成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作为这个网络中的成员,嘉兴文人共同参与形形色色的地方文化活动,而许多活动也借助这个网络才得以顺利进行,如本文考察之《宝颜堂秘笈》的校阅在很大程度便是依托于这个网络。《宝颜堂秘笈》的校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校对者的身份也各不相同,不仅校对者校书的数量差异很大,即使一部书的不同卷册也常常由不同的人校阅,校书多者可达数十种,少者不过某书之一卷。这种形式的书籍校阅与出版不同于晚明福建建阳那种分工明确的书籍出版模式,(88)[美]贾晋珠:《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邱葵、邹秀英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也不同于同时期的一人专任校阅的编校模式,(89)如本文第一页注一所举《明文海》与《纪录汇编》例,程百二编《程氏丛刊》也是如此,参见程百二编:《程氏族丛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571页。恐怕更多具有消遣和人情往来的性质,书籍的出版只不过是嘉兴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一小部分活动而已。此时书籍的编校尚不具备专业的分工,书籍出版还不是职业化的工作,尚不具备很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