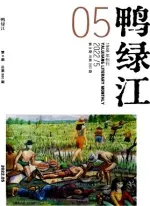托尔斯泰与勿忘我
2022-08-15高海涛
高海涛
那年夏天去莫斯科,是初夏的六月。天空浅蓝,红莓花山楂树的旋律混杂着烟草气息。一个中国作家团,来自东北。其实我们一共走了三个城市: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有人说这条路线就像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三折屏:伊尔库茨克有贝加尔湖和十二月党人博物馆;圣彼得堡有“白夜”、冬宫、夏宫和普希金的皇村;莫斯科居中,正如它作为首都的地位。
莫斯科有什么呢?首先,是钟声和教堂。莫斯科的教堂真是太多了,就连红场和克里姆林宫,整个建筑群也因几座大教堂的簇拥而更显庄严和恢丽。当天有小雨,巴洛克式的,某种嫩绿,某种浅灰,别具格调。一路钟声悠扬,空气中有雨味,钟声也有雨味,我们的中巴车穿过大街小巷,仿佛唐人杜牧的诗句也斜斜飞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但我们不是为这些而来的,一个喜欢读书写作的人,到莫斯科最大的愿望,还是要看看托翁故居,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当导游说要去那个小院,一车东北人,都不虚此行似的振作起来,仿佛走亲戚,又近似朝拜。有人讲起美国的哈佛大学,说某教授给学生讲俄罗斯文学,先拉上所有窗帘,教室霎时昏黑。然后点起一支蜡烛,说此乃普希金也;复又打开灯,说此乃契诃夫也;最后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阳光倾入,光明美好,教授宣布说,这就是托尔斯泰!
很恰当的讲述,大家纷纷点头。不是吗?这就是托尔斯泰。
1
车停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小街,一个小院。导游说这就是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街也叫列夫·托尔斯泰街。于是一行人踊跃下车,刚进院子,却被告知当日闭馆。小院和后边的花园可以看,却不能走进故居的小楼。怎么回事,因为下雨吗?可这是小雨,而且差不多要停了。导游说她也不知道。有人调和,说要不明天再来吧。导游说不行,明天还有明天的行程。总之很无奈,就像远道而来,却被亲戚拒之门外似的。但想到托翁的博大,只好也博大一回,那就去后面看看花园吧,也不枉到此一游。
小院之小,近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赭黄色小楼,绿色屋檐和窗扉,就连门旁陈列的托翁著作也都是袖珍本,手掌大小。想到这就是托尔斯泰写出《复活》的地方,那种失落的感觉,什么似的。刚要转身,对面走出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士,成人版的爱丽丝吧。她衣着显旧,并不时尚,披一条素朴的蓝纱巾,施施而行。Hi,你好!我赶紧上前,试着用英语交流。我学过几年英语,也教过几年英语,那次算是派上了用场。
交流很顺利,她说自己是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因为毕业论文写托尔斯泰,是来查资料的,已经来过多次。听我说了不能进入小楼的情况,她笑了,童话般的,用英语说Follow me——跟我来吧。
就这样,当所有的旅伴都去了花园,我却近水楼台,跟着“蓝纱巾”潜入了托翁住过的小楼。我们走的是暗门,过道很窄。进去,有个俄罗斯老太婆,神情淡漠,坐着不动。“蓝纱巾”向老太婆说了几句俄语,老太婆颔首,指了指旁边桌子上的俄式茶炊,古朴而苍茫。
一些厨具,一架钢琴。托尔斯泰半身塑像,五柳垂胸的样子。许多黑白照片。长长的走廊,十多个房间,一个大餐厅,好像还在怀想当年高朋满座之盛。主卧室,保育室,小教室。大女儿的房间,二女儿的房间,男孩的房间。大客厅,小客厅。托尔斯泰写作的书房。总之楼上楼下,都让人亲切得不行。“蓝纱巾”指指点点,充当解说,给我讲起小楼的旧时月色、托翁的前尘影事。
——托尔斯泰伯爵买下这所房子是1882年,Yes, 全家居住。前后有近二十年。就是在这里,他看书写作,接待客人,还经常到院子里喂马劈柴,有时还要出去打水,远到莫斯科河那边。对,这就是伯爵和夫人。当时来这里拜访的客人太多了,伯爵夫人有时也不胜其烦。
——在俄语中,托尔斯泰有“肥硕”的意思。当然是贵族之家,他姑母能经常见到沙皇尼古拉二世。他父亲的亚麻衣物一定得送到荷兰去洗。他母亲连半个不雅的词都没听说过。嗯,这是他年轻时的照片,谁都年轻过。当年他曾剃掉过自己的眉毛,因为说这样会更浓更密。
——1885年他成为素食主义者,身体一直很好。自行车?是的, 他六十五岁时学会了自行车,非常喜爱。当然也会骑马,八十二岁还能策马扬鞭,看这张,多像个少年,在马上还随手折下桦树枝。应该是在回雅斯那亚·波利亚纳的路上——托尔斯泰的故乡,在莫斯科南面,大约一百二十英里。
——是的,那里有他的庄园和土地。列夫·托尔斯泰喜欢土地,也喜欢亲自干活儿。每年春天或夏天,他都要返回故乡,经常是徒步,每次要走三天,夜里就住在农民家。有时也骑马。托尔斯泰与农民,与故乡,与土地,有好多故事呢。
——你喜欢这幅照片?很多人都喜欢,我也喜欢,喜欢极了。是在他家乡的田野上,他怀里的花儿是勿忘我。对不起,我说了俄语,英语是forget-menot,你们中文叫什么?哦,勿忘我,俄语中没有这个我,就是不要忘了、别忘了的意思……
“蓝纱巾”就这样边走边讲。
我应该记住她的名字,她告诉过我,是叫薇拉还是丽莎?或者就叫薇拉吧,这名字更贴近她的气质。一个多小时吧,薇拉陪我转完了那个小楼。最后我们还到厨房坐了一会儿,薇拉给老太婆几个硬币,请我喝了一杯浓浓的红茶。直到听见外面导游的声音,我才道谢并告辞出来。薇拉坚持送我。走出院子的时候,旅伴们都已坐在中巴车上,导游的眼神复杂,说要先午餐,然后去看契诃夫故居、高尔基文学院和彼得大帝童年庄园。
2
从那个夏天到现在,已经有快十年了。当时一起去旅行的作家,只有几个保持了电话和微信。偶尔联系,还会谈起那次旅行,意犹未尽的样子,说看到谁写的贝加尔湖了,还有谁写的圣彼得堡的白夜了,都感到特别亲切。也有写莫斯科的,但主要是写高尔基文学院,以及阿尔巴特街、莫斯科大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我说,怎么没人写托翁故居呢?他们就说,那得你来写啊,你不是没去花园吗?和那个“蓝纱巾”,车都开了,人家还在下面招手呢。
是啊,我应该写一写那个童话般的小院和小楼。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往事阑珊,提不起情绪,更何况像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巨人,仅凭浮光掠影的印象,也怕说不出什么来。直到前年秋天,收到一本书,看过之后,好像才重新找到走近托翁的感觉与思路。
英文版的《李尔克的俄罗斯》是大学同学从美国寄来的,作者安娜.A.塔维斯,任教于康尼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大学,该书记述了德国诗人李尔克在1899年和1900年两次到俄罗斯旅行,拜访和会见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作家以及和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诗人通信交流的经过和心路历程。本来是随便翻翻,但不知不觉,却被这本书平常的视角和简素的笔调吸引了,特别是和托尔斯泰有关的章节。我读着,就仿佛作者是另一个薇拉,也系着蓝纱巾,正在娓娓道来,接续讲述一百多年前托翁的日常起居、亲情纠葛、待客之道、家事悲欢。
比如书中有一节“在托尔斯泰家吃茶”,写的便是托尔斯泰在家中接待客人的情形。当时的托翁虽上了年纪,仍每天坚持写作,一般只在下午茶或晚餐时会见来访者。宾客很多,多是贵族名流、编辑记者,还有远道而来的外国作家与诗人,如李尔克和莎乐美及其丈夫即是。“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托翁家的待客之道是闻名遐迩的,稍有体面者,据说都会被留下吃茶,与托尔斯泰伯爵共进晚餐。吃茶即吃饭,这几乎是很中国式的表达,宋诗有云“万事卢胡吃茶去,不知谁主更谁宾”,即是此意。至今在南方,请人吃饭时,也往往会说请吃茶。
但是于客人而言,在托翁府上吃茶却并非都是愉快的经历,相反还会时常面临尴尬。首先托翁自己吃素餐,而给客人准备的则是丰盛的正餐,这未免让人感到窘迫。而更觉难堪的是其家中氛围。托尔斯泰和夫人索菲亚往往一言不合,即成风暴。很多人见证,说索菲亚的不近人情已到这样的地步,时常当着客人的面,把家里的书扔得到处都是,并且总是怒气轩昂,甚至对来访者多有抱怨。李尔克就曾亲见过这样的情景,索菲亚正在发火,一个年轻女仆从后屋走出,嘤嘤而泣,后来还要托尔斯泰本人去安抚女仆。还有托尔斯泰的公子,好像也不让人省心,李尔克记得他们那次在托尔斯泰家吃茶,客人们正在举杯,他家的公子进来了,在门厅看到客人们的外套之后,大声嚷道:“嗬,这么多人还在这里呀!”这样说话显然是一个信号,所以客人们都知趣地站起来告辞。他们刚走出房子,恰好复活节的钟声响起,次第应和,回旋浩瀚,送他们出门的托尔斯泰还在讲着什么,但钟声却淹没了他的教诲,久久才茫茫平息。
3
啊,莫斯科的钟声,好一个在托尔斯泰家吃茶。
想起《安娜·卡列尼娜》的题词:“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知托尔斯泰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呢?其实家庭也并不都是非此即彼的,所谓家家都有难唱曲,托尔斯泰家也并不例外,甚至那种难唱的程度更高,更令人瞩目。没办法,这就是生活。
或许还是李尔克说得对,“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这句名言是他那次在托尔斯泰家吃茶之后有感而发的吗?不知道,但对托尔斯泰来说,这无疑是恰如其分的。
还是说吃茶吧,轻松一点。
我有时想,自己也算是在托尔斯泰家吃过茶的人吗?我知道这样想很没劲,但我真的很珍惜那次走进托翁故居的经历。毕竟我在那个小楼里喝过一杯“恰伊”——俄语中“茶”的发音,和汉语接近。这不难理解,因为茶就是从中国传到俄罗斯去的。那大约是明朝万历年间,中国使节向当时俄国的沙皇赠送了几俄磅的茶,从此“恰伊”就在那片土地上流传开来,渐成习俗,下至平民,上至贵族,无不喜好。据说托尔斯泰也对此情有独钟,每天都要喝很多茶,直言茶能唤醒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没有茶,他就无法工作。
实际上托尔斯泰在世时,要去他的莫斯科家中喝杯茶可能不难,“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19 世纪风气好,在莫斯科,想喝茶敲伯爵家的门也没关系。但喝茶和吃茶是不一样的,要真正被留下吃茶并不容易。据说当时全莫斯科都知道,托尔斯泰家有两个门,贵族或社会名流走前门,而普通人或当地的农民则需要走后面的暗门。根据安娜.A.塔维斯在书中的讲述,大作家高尔基也曾享受过后门的待遇(想到我和高尔基待遇相同几乎值得骄傲)。那是1889年,年轻的高尔基已经很有些名气了,第一次到托翁府上拜访,因为穿着比较简单,或者有点破旧,被当成了附近的农民,不仅是走的后门,而且刚一见面,托尔斯泰夫人就开始抱怨,说她丈夫身为伯爵,就是离不开农民,简直不可救药,等等。一边说着,一边打发仆人送高尔基去厨房吃东西。高尔基朴实纯良,也没做任何解释,就很农民地去了厨房,那里有面包和咖啡,当然也有“恰伊”。我读到这个情节,不禁莞尔,忽又感动至深,想起鲁迅的小说《故乡》,说回故乡搬家的时候,他少年时的伙伴闰土来了,见面只是默默地吸烟,吃饭时就自己到厨房去吃。
总之,美是难的,虽然难的未必美。大约十年之后,当李尔克和莎乐美夫妇来到俄罗斯,也是怯生生的,惴惴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运气好,我们会拜访列夫·托尔斯泰”,李尔克给朋友写信这样说。到达莫斯科之后,他们先给画家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拜托他帮忙联系此事。这位画家,我们可以称其为老帕斯,因为他不仅是我们熟悉的《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而且和托尔斯泰有着很深的交往,作为一个素描大师和莫斯科绘画学院的教授,他还是托尔斯泰作品的插图画家之一。当时为了给《复活》做插图,老帕斯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托尔斯泰。在他的帮助下,李尔克与莎乐美及其丈夫才得到了去托翁府上吃茶的邀请。
4
与他们在莫斯科托尔斯泰家中吃茶的经历相映成趣的,是李尔克和莎乐美夫妇对波利亚纳庄园的寻访。那是第二年,也就是1900年5月,当他们再次来到俄罗斯,准备去基辅的路上,恰好于莫斯科火车站邂逅了老帕斯一家。一个小男孩,正睁大眼睛看着李尔克,他就是小帕斯,年仅十岁的未来的诗人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老帕斯是温厚的,这位曾帮过他们的大画家主动提出,可以协调安排他们去波利亚纳一游,因为他恰好从一个铁路官员那里听说,托尔斯泰一家刚刚返回他们的庄园。简直是最好的安排,李尔克和莎乐美当即决定,在没有被正式邀请的情况下去托翁的故乡看看。在火车站给托尔斯泰发了封电报之后,他们就出发了,一种历险精神为他们的行程增添了特殊的意味。
从莫斯科到波利亚纳的路线人很多,他们按照老帕斯的建议,先搭货运列车到一个小车站,再雇一辆马车去波利亚纳村。终于到了,穿过草木丛生的园林,就是那座闻名遐迩的白房子。按门铃,是托尔斯泰亲自开门,让两位不速之客先进屋,并说那个下午可以陪他们多坐一会儿。但是当索菲亚发现他们之后,却以托尔斯泰身体欠安为由,差点把他们从屋里赶出去。他们解释已经和托尔斯泰说好了,等他休息时再见面。索菲亚悻悻地转身离开,去了旁边的藏书室,一边大声说起什么鞋,意思是她的丈夫忙得连脱鞋的空儿都没有。
尽管有点“五马长枪”(请原谅我用这句东北土语)的样子,但这段记述还是有助于人们对托尔斯泰夫人的同情和了解,毕竟索菲亚出身名门,年轻时更是窈窕贤惠,属于“屠格涅夫型的妻子”,说到底,她是真心关爱自己的丈夫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托尔斯泰的所有烦恼和痛苦都归咎于女性和家庭生活,那样不仅有失公允,也是肤浅、片面,缺乏应有的宽容、理解、想象力与幽默感的。
还是李尔克,不愧为杰出的诗人和观察者,他对托尔斯泰的认识不乏深刻和超越。他写道,托尔斯泰身上有数不清的矛盾,这正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标志,而当这位巨匠试图冲破围墙,他的精神也在痛苦中不断生长。恰如在《复活》的开头,那些从坚硬的石缝中奇妙地长出来的春天的小草。
好了,还是让我们轻松一些,回到开头。1900年,暮春或初夏时节,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史上这两个重要的诗人相遇了,但却几乎没有人注意。直到许多年后,年轻的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仍念念不忘。他清晰地记得,当自己还是一个灰眼睛的男孩,跟着父亲老帕斯,在莫斯科火车站见到德国诗人李尔克的那个遥远的五月天。于是,出于崇敬和怀念,他开始给李尔克写信,写了很多信,其中第一封追忆年华似水,是这样措辞的:“您一定还记得莫斯科吧?古老的、迷人的、如今已成传奇的莫斯科……还有托尔斯泰,他的旧家,他的故园……”
不愧是诗人书简,虽然我并没觉得莫斯科有多么迷人,但这两句话却很迷人,几乎连省略号都是迷人的。可以说,这样的句式和语气正是我对托尔斯泰故居的感觉,那个小院,那座小楼,都让人感觉亲切而笨拙,并有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感与乡愁,仿佛你正站在时光的省略号上。
5
还有什么呢?对了,一幅照片。
托尔斯泰晚年,最先进的技术和传媒已被用来传播他的形象。美国的托马斯·爱迪生提供留声机来记录他的声音,柯达公司的第一批照相机刚上市就寄往托尔斯泰家中。还有,据说有很多画家、雕塑家、摄影家,都为争夺他的闲暇时间而相持不下。俄罗斯第一张彩色照片和第一张签名照片,都是托尔斯泰的肖像。所以和同时代的作家们相比,托尔斯泰的照片是非常可观的,以至于在他身后还引起过胶片所有权的纠纷。
而这幅照片似乎更有独特性,在安娜.A.塔维斯的书中,我发现它在不同的章节被多次提到,如同某种线索和象征。其来历是这样的,说托尔斯泰卜居莫斯科的时候,每年总有一两次要回到故乡的庄园去。他往往是一大早出门,在春天的田野上,一边和农民们打招呼,一边从地上拾起一簇簇的勿忘我。有人将这情景拍下来,画家奥尔康斯基非常喜欢这幅照片,坚持把它用作《复活》的封面。
《复活》的封面,还有什么比这个设想更恰当呢?春天的田野,勿忘我开遍的田野,鹧鸪声声,花影重重,花是蓝色的,早晨的雾也是蓝色的,只是深浅不同而已。或许还有几匹马,静立如仪。简直太美了,美得振聋发聩!
而且,那年夏天在托尔斯泰故居,我也见过这幅照片。是的,我见过。我记得薇拉说话的语气和样子,她站在照片前,她的蓝纱巾似乎在强化照片中勿忘我的色调。
“你喜欢这幅照片吗?很多人都喜欢,我也喜欢,喜欢极了……你看多美啊,托尔斯泰好像对那些花说着什么。”
实际上,在莫斯科的托翁故居,许多照片都拍摄于波利亚纳,其中好几幅我印象很深,比如托尔斯泰在刈草,托尔斯泰在上马,右脚独立,左脚正迈上马镫,那一定是在回乡的路上,城南春半,风和马嘶。还有托尔斯泰在给孩子们讲故事,在雅斯那亚·波利亚纳村,他创办过学校,还亲自为孩子们编过识字课本。
但所有的这些,显然都不如这一幅:托尔斯泰与勿忘我。它几乎是托尔斯泰整个生命与精神的审美概括,薇拉说托尔斯泰好像正对那些花儿说着什么,说着什么呢?也许是那句吧,《战争与和平》里写到的,关于那个春天般的女孩娜塔莎——“生命的本质是爱,爱醒了,生命也就醒了”,对吗?
而此刻,我的记忆也正在醒来。我想起了老家,在辽西丘陵深处,山坡上,洼地里,在漫不经心的春天,往往也能看到一簇簇温暖的蓝花,像举着小蓝灯笼。尤其是林地边上,那针阔混交林护卫的田野,有时会一蓝一片。这种花,乡亲们叫它止血草,或补血草,很亲昵的称呼。谁的手划破了口子,把这草捣碎,敷在伤口上,血就止住了。如果碰见成片的,扶犁人就会吆喝着停下,俯身捡起这些蓝花,生怕碰伤了根茎。补血草拿回家,洗净晒干,状如毛参或粉丝,然后纸包纸裹,收藏起来。听说谁家生了孩子,就提上两包去下奶。坐月子的女人,说用这个是最好的,不仅补血,还能催奶。于是吃奶的孩子都扬起小脸,憨憨笑着,那是因为母亲的乳汁也有勿忘我的香气吗?虽然要等若干年后,等上了中学,乃至上了大学,他们才会知道这个清纯文雅的花名——勿忘我,并试着用它来象征自己生命中的美与爱情,母亲乳汁中的香气反而被逐渐淡忘了。
勿忘我在俄罗斯据说还叫热草,热的草,温的草,暖的草,也是民间的昵称,意思和补血草差不多,很贴切。世界上的许多花都是这样,民间总喜欢称之为草。这是因为草比花更贴近泥土,更贴近大地吧。
差点忘了,薇拉送我走出那个小楼的时候,还说过几句歌谣,她说是俄罗斯的《识字歌》。当时恰好是正午,雨停了,附近教堂的钟声错落响起,叮当悠扬,似乎闲着也是闲着,就无意中充当了薇拉的伴奏——
(当)麻雀是一种鸟,(当)白桦是一种树,(当)黑麦是一种粮食,(当)勿忘我是一种热草,(当)俄罗斯是我们的祖国,(当)托尔斯泰是这土地的良心……(当)……
记不太准了,大意如此。
谨以此文感谢莫斯科大学当年的研究生薇拉女士,是她让我走近了托尔斯泰。同时也感谢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的塔维斯女士,是她让我重新走近了托尔斯泰。还有那幅照片,它是否按照那位画家的建议,最终被用作《复活》的封面不得而知,但是现在,当我的记忆开始“复活”,我坚持用它作为那次莫斯科之行以及整个俄罗斯之行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