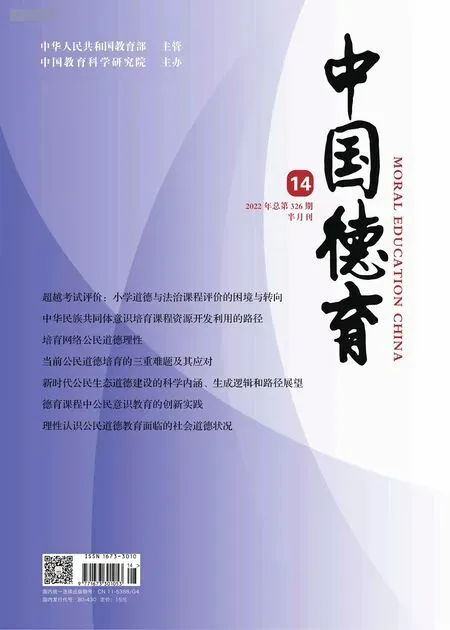当前公民道德培育的三重难题及其应对*
2022-08-13■叶飞
■ 叶 飞
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全面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推动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进步已然成了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培育,一方面伴随着新时代物质文明及道德文明的稳步发展而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前提,从而也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公民道德培育也面临着来自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碰撞、公民道德与公共领域的分离、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割裂等方面的挑战,它们在文化层面、教育层面、技术层面给新时代公民道德培育带来了新的难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公民道德培育的三重难题。寻求对这些难题的有效解决,无疑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任务。
一、当前公民道德培育的三重难题
当前公民道德培育面临的第一重难题,集中体现为公民道德培育的西方语境与本土文化的文化融合难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公民道德培育必须坚决反对“拿来主义”,要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质”。这是培养新时代公民的重要文化前提。但是,我们也无法忽视,“公民”概念及其所蕴含的理念事实上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在古希腊时期,公民概念已在西方文化中扎根。在当时,公民与城邦是一体的关系,公民是城邦的公民,城邦是公民的城邦;城邦作为公民的共同体,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也要求公民积极履行城邦的公共责任。在此背景下,公民的个体性与城邦的公共性是融合为一的。到了近代启蒙运动以后,伴随着自由主义理念的发展,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它更强调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第一性,从而形成了以个体自由和权利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追求社会公共福祉的公民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重人伦关系、道德义务和个体修养的文化难免会产生文化层面的冲突与碰撞,从而带来公民道德培育的文化融合难题。这种文化融合的难题,具体表现为重人伦的文化与重自由的文化、重义务的文化与重权利的文化、重个体修养的文化与重公共福祉的文化的冲突与乃至对立。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则必须更好地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公民文化,推动文明互鉴、文化对话,形成真正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特质的公民道德理念,更好地满足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及教育变革的需要。
当前公民道德培育所面临的第二重难题,即公民道德培育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有机联结难题。道德教育(包括公民道德的教育)与生活是相异的,道德教育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它并非原原本本的生活,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等都含有对生活的再提炼、再创造;道德教育与生活又是紧密相连的,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生活,是为了人们过一种美好的生活。两者构成了有机联结、辩证统一的关系。杜威曾指出,“不仅社会生活本身的经久不衰需要教导和学习,共同生活过程本身也具有教育作用。这种共同生活,扩大并启迪经验;刺激并丰富想象;对言论和思想的正确性和生动性担负责任”。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共同生活则集中体现为公民在公共领域中所过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启迪了公民的经验、理性及想象力,它是公民成长的至关重要的基础。但是,从当前的教育现实来看,公民道德培育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有机联结仍然是不顺畅的。虽然这些年来我们的公共生活领域正在不断走向成熟,志愿者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等也在不断发展,但是距离为青少年提供公民成长的广泛基础还有不小的差距。当前学校及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基础仍需要进一步夯实,才能更好地实现公民道德培育与公共生活的融合,更好地激发公民道德学习的主体精神,从而促进公民道德培育的实效性提升。
当前公民道德培育面临的第三重难题,即是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如何互补互促的难题。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我们已然进入了虚拟空间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这也是新时代所面临的一种全新的技术图景及社会背景。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虚拟生活与实体生活、虚拟教育与实体教育之间的间隔正逐步被抹平。“伴随着以数字化、互动式、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时代而来的不仅是全新的物质生活方式,它更强烈地重塑着人们现有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以及精神生活建构。”如果说实体空间以及实体教育强调的是教师与学生之间面对面的知识传递及情感、价值观的交流,那么虚拟空间及虚拟教育则具有典型的数字化、开放化、个性化乃至于脱域化(Disembeding)等特征,它推动教育活动摆脱实体空间的限制,以电子信息技术、网络虚拟空间为媒介形成了教育活动的网络化、个性化和开放化。这极大地拓展了教育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使得“深度学习”“个性化学习”等公民道德学习方式成为可能。当然,虚拟技术也会带来不容忽视的风险,从而给公民道德培育带来新的问题及挑战。比如,大数据所带来的隐私暴露风险,数字霸权、数字独裁对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贬低,算法歧视所导致的公正价值的缺失,网络暴力、犯罪、色情所带来的道德沦丧等。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空间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公民道德培育必须直面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实体教育与虚拟教育之间互补互促的难题,必须建立起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从而培养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社会公民和数字公民。
二、新时代公民道德培育的路径探索
如前所述,当前公民道德培育面临着西方语境与本土文化的文化融合难题、公民道德培育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有机联结难题,以及虚拟空间技术、人工智能时代的实体教育与虚拟教育的互补互促难题。为了更好地破解这三重难题,培育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公民道德培育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工作。
首先,公民道德培育要坚持文化上的守正创新、融通发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公民文化的互学互鉴,为新时代公民的培养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坚持教育传统中的谦谦君子的教育理念,恪守中国立场,凸显中国风范”,同时也要融通中西,推进文化对话与国际理解。这就要求:一是要形成关系伦理与主体伦理和谐共融的伦理文化。儒家传统强调人伦关系的和谐,强调从和谐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这具有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其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同时,作为新时代的公民,也需要具有独立自主、顶天立地的公民主体人格。公民道德培育需要促进以和谐为中心的关系伦理与以独立人格为核心的西方主体伦理的融会贯通,并以此实现一种和谐的公民主体人格的养成。这也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培育需要建构的一种新型的伦理文化。二是形成一种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相均衡的权责文化。新时代的公民身份是权利与责任相统一的身份,公民道德培育不能偏于以修身为本的责任伦理,而是也要注重以人的自由为本的现代权利伦理,从而建构起权责均衡的文化氛围,使得公民既能够充分捍卫自身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受教育权利等,同时也能够主动承担国家、社会所要求的公民责任,包括遵纪守法的责任,遵守公共道德的责任,参与社会治理、社会公益的责任等。通过这种权责均衡的文化建构,可以更好地促进新时代公民的身份认同及权责理念的健全发展。三是构建一种追求公共福祉的文化。我们的传统伦理也强调了君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以修身齐家为前提,但是“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也确实与西方所强调的公民对于公共福祉的追求有相通之处。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培育,在教育目标及教育内容等方面也应当把传统儒家伦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担当意识,与西方公民对公共福祉的追求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学生不仅关心自我的生活及利益,同时也能以更广阔的胸襟关心他人的利益、关心社会的公共福祉、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从而真正成长为具有强烈的关怀精神、担当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新时代公民。
其次,推动公共生活领域的建构,实现公民道德培育与公共生活的有机联结。《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公民道德培育要“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实践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这表明:公民道德培育不仅是道德知性的培育,更是道德情感、道德意愿、道德实践能力的培育,它需要坚实的公共生活及公共实践的基础。为此,一方面,我们需要构筑民主性与公共性的学校公共生活领域,实现公民道德培育与学校公共生活的有机联结。这就需要进行学校制度生活及课程教学生活的公共性再造。学校制度生活需要打破传统的垂直型模式,形成以民主参与为核心的治理模式,使学校管理活动成为一个民主的空间,鼓励广大的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的治理;同时,在课程教学中,通过公共协商、平等对话等来为学生赋权,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课程对话、教学对话,倡导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交往关系,促进课程教学的公共性建构。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推动校外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建构,实现公民道德培育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有机联结。公民道德培育需要通过整合学校资源、家庭资源、社区资源等,建立起学校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紧密联系,鼓励青少年学生积极参与社区以及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中的公益慈善活动、环境保护活动、法治宣传活动等,从而激发学生的公民主体性及公共道德精神,为其走向社会公共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平台,让他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养成公共品德及公共精神。
最后,推进年轻一代人从“数字原住民”向“数字公民”的转化,涵育当下以及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数字公民道德。新时代公民道德的培育,不仅需要通过实体空间来培养学生的基本公民道德素养,同时也需要紧密围绕数字化社会、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需要,培育学生的数字公民道德,使学生成长为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数字公民”。著名教育家博兰斯基曾提出了“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新技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虽然他们是“数字原住民”,伴随着数字化社会而生,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生就具有数字公民的道德素养。因此,培养数字公民道德,也是当前教育的重要使命。为此,新时代公民道德培育,一是要加强数字认知与数字意识的培育,使年轻一代人对数字化信息技术充分认知和了解,理解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作用、运行方式及使用方法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形成数字健康的意识(过一种健康的数字生活)、数字安全的意识(维护个人的数字安全、保护国家的数字安全)、数字参与的意识(参与信息网络的建设和数字社会的治理),从而为成长为数字公民奠定基础。二是加强数字公民道德的培育,培育学生在数字化、虚拟化的网络社会中的道德责任意识,坚决杜绝网络暴力行为、侵犯隐私行为、侮辱人格行为及其他有违网络公共道德的行为;同时,加强虚拟空间中的权利意识培育,通过这种虚拟空间中的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培育,促进学生健全的数字公民人格的养成。三是要加强数字公民行动能力的培育。数字公民需要具备良好的数字行动能力,虚拟空间是一个需要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共同维护的公共空间。当虚拟网络空间中出现了不公正的行为、不合理的舆论、不道德乃至于违法的网暴事件等的时候,数字公民应当有意愿、有能力积极参与维护网络道德,重塑“数字正义”的公民行动,捍卫网络空间的道德秩序和正义秩序。这是数字化社会、人工智能时代对公民提出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