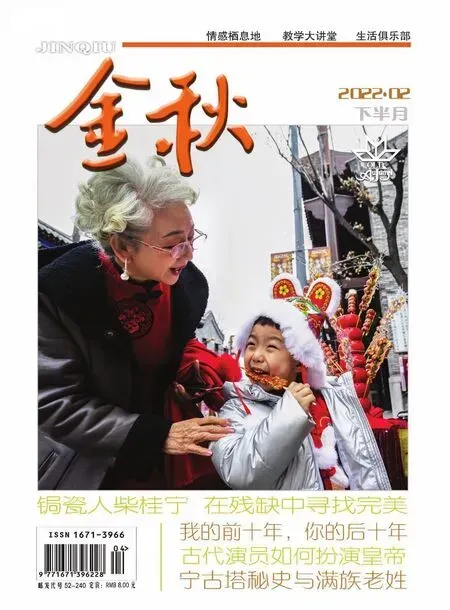豆汁儿,两碗!
2022-08-10深圳韩磊
文/深圳·韩磊
三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不久前,从深圳回到北京,拖着行李箱将近小区大门时,忽然看到马路对面冒出来一家豆汁店,唤作“老磁器口豆汁店”,不由惊喜得叫出声来,半天的鞍马劳顿顿时一扫而光。
第二天早上7点半,急急忙忙出门去喝豆汁儿。
进了店门发现,不大的铺面已经满座,还有十几位在排队。“人够多的啊!”我排进队尾,跟前面的大爷搭话。“今儿礼拜天,没有排到门外头已经不错啦。”大爷扭扭头,笑着对我说。
“两碗豆汁儿,俩油饼!”终于轮到我了,对开票的大姐大声报饭。
好不容易找了个空位坐下来,还是跟别人拼的桌,桌上的碗筷刚刚收拾干净。夹一筷子咸菜丝放进豆汁儿碗里,不等搅拌均匀,就迫不及待地低头溜着碗边喝了一大口。“地道!”我在心里点了一个赞,感觉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周身上下那个美啊!
不到十分钟的工夫,两碗豆汁儿,两个油饼,就着小半碟咸菜丝下了肚,头上微微冒出汗来,感觉浑身舒坦。
美好的一天就从这两碗豆汁儿开始啦!
豆汁儿是北京特产,天南海北跑了多年,没在别的地方见到过。其出身低微,是绿豆做粉丝、粉皮的余料发酵而成的。价钱也贱,像这天早上我喝的这两碗,一共才三块钱。

但熬豆汁儿是功夫,非行家里手不可。据说要顺着一个方向边熬边搅,边熬边搅,火候恰到好处,这样熬出来的豆汁儿才好,不稀不稠。而且熬制过程中不能添水,否则出锅的豆汁儿就澥了。
北京豆汁儿清热、祛暑、健脾、开胃,看起来灰中透青,闻起来一股馊味,喝起来有些酸臭,但喝完之后口中回甘,浑身舒服。京味作家邓友梅曾形容过:“就如同洋人吃臭奶酪,吃不惯者难以下咽,甚至作呕,吃上瘾的一天不吃就觉着欠点儿什么。”
我就属于邓友梅所说的后者。
2005年从河南到北京工作,第一次慕名去喝豆汁儿是在护国寺小吃店。当时要的是标配:豆汁+焦圈+咸菜丝。可说实在话,焦圈不敢恭维,油炸的东西,凉巴巴、硬梆梆的,吃不惯,但豆汁儿特对我的胃口,从此割舍不掉了。只是搭配豆汁的,我就换成了松软的油饼。
此后十多年间,北京老城区大多数豆汁店我都光顾过,比如阜成门的华天小吃,天坛公园北门对面的磁器口豆汁店等等。大约2012年秋天,有一次,我在北新桥一带拍胡同,在一条窄小的胡同里发现了一景:人们拿着大号的可乐瓶子,拎着钢精锅,端着盆,排着十几米的长龙,在一家豆制品作坊买豆汁儿。我大喜过望:一是发现了好镜头,噼里啪啦一阵猛拍;二是发现了豆汁店,拍完这组镜头我也排在队尾,买了一大瓶豆汁儿带回家自个儿熬着喝。就这样,一来二去,北京豆汁儿哪家地道,哪家味正,竟也分得出一二三来了。
外地人,我指的是像我这样的非北京土著,能喝得了豆汁儿的绝对是少数。实际上,许多人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也接受不了它的味儿。
拿我来说,在我们家就是个另类。
迷上豆汁儿之后,抱着好东西一起分享的想法,我很热心地请太太和儿子去喝,太太喝了一口说:“这什么东西啊,喝不了!”儿子则只喝了一口就吐到了地上。最后,他们娘俩儿的两碗也都被我开销了。
后来我还请岳母去喝过,老人家尝了一口,说:“还能接受,可是也不觉得好喝。”我心想,大概老太太也不太喜欢,只不过不想驳我的面子,不忍心拂了我的一片好心吧。
还带几位同学、朋友去喝过,但没一个人能接受。
可我就是好这一口,没办法。
虽然豆汁店离自己家都挺远,可我还是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喝、喝、喝,并且每一次都是两碗。
两碗豆汁儿,两个油饼,配小半碟咸菜丝儿,成了我人生的一大快事。特别是夏天,来碗热豆汁儿,就一口撒了芝麻淋了香油黑中透红的辣咸菜丝儿,喝得汗流浃背,浑身通泰,真是不亦快哉!
邓友梅在一篇文章里记述了一桩趣事,说的是不忘城南旧事的林海音女士1990年从台北回到北京,被问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吗?这位已经73岁的北京“姑奶奶”回答:“别的事没有,就想叫你们领我去喝碗豆汁儿。”文章里写道:吃其他小吃时挺谦逊、挺稳重,豆汁儿一上来她老人家显出真性情来了,一口气喝了六碗还想要,她说:“这才算回到北京了!”
我最多只喝过三碗,距离林海音的纪录相去甚远。看来豆汁儿还是老北京人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