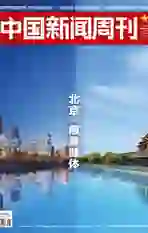何以倾诉
2022-08-09闫晗
闫晗
契诃夫的小说《苦恼》中,一个叫约纳的车夫刚死了儿子,想向别人倾诉心中的痛苦,竟找不到一个能听他说话的人,坐车的乘客们每个都行色匆匆,想着自己的烦心事,催促他快点赶路,不要再说了。故事的最后,车夫只好把一肚子话,说给自己的马听。它认真地听着,仿佛能听懂,让倾诉者得到些许安慰。
话总憋在肚子里,情绪得不到宣泄,人会生病的。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把她的痛苦向鲁镇的人讲了一遍又一遍,她的儿子阿毛没了,坐在门槛上剥豆子时被狼叼走了,她不知道狼会到村子里来……她沉浸在后悔之中,诉说之后情绪应该是暂时缓解了一些的,只是她的苦痛太沉重,还没有释放完,看客们就已经厌弃了这个故事,不想再听下去。
我给一个上小学的女孩讲祥林嫂的故事,她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不可以好好听呢?可在现实中,被全身心地倾听是件奢侈的事。这个小女孩也常常觉得自己说的话没有被父母听到,他们只顾着忙自己的事。
我没法告诉她,他人的遭遇,原本就是故事,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个悲伤的故事,在最初发表时或许尚能震慑人心,叫打趣的人都住了口,为自己不能共情生出些许羞愧。可一旦故事变得陈旧,震撼力也会消失,烦躁的空气滋长起来。对于不必敷衍的人,看客们会明明白白地表示厌弃。哪怕是还算良善的人,也会不留情面。大多数人都是吞噬信息的怪兽,喜欢新鲜刺激的东西。

互联网上听众众多,一有人爆猛料,立即会聚拢大量人群,刨根问底挖出更多线索。可无论是悲伤的故事还是桃色新闻,总会被新一波的故事淹沒,最初讲述的人无法操纵互联网的力量,也渐渐如同祥林嫂似的被厌弃。
春晚曾经有个小品,年老的爷爷一遍遍讲《粮票的故事》,回忆当年捡粮票的事情,像电脑重启似的,儿孙只有假装津津有味地听,才会让老人高兴起来——孝顺,最难的是“色难”。重复是一种酷刑,孙子如坐针毡,得不断做心理建设才能忍受老套的故事。这个小品很真实,我爷爷也喜欢讲年轻时的事情,仿佛穿越到过去的时光一般精神焕发,讲得很好,可大家也不爱听了。对待自家人保持耐心尚且困难,何况是他人。
《水浒传》里有一段因为不被倾听引发的“血案”。江边酒楼上,李逵突然将卖唱“女娘”用两个指头一戳,姑娘立即晕倒在地,起因就是这位歌女突然过来唱歌,打断了他想要卖弄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宋江、戴宗等人不倾听,李逵非常恼怒,不好意思怪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却将气撒在弱势的卖唱姑娘身上。不听别人说话的后果可能很严重,好在歌女没事,宋江赔了20两银子给她的父母。
我看到的关于倾听最温柔的故事,是在史铁生的文章中。那是一个小号手的故事,战争结束了,有个年轻号手回到家乡,却听说未婚妻已嫁与他人,以为他已战死沙场。年轻号手痛苦至极,便离开家乡,四处漂泊。路上,他吹响小号,号声凄婉悲凉。一个国王听见了他的号声,让人把他唤来,问他:你的号声为什么这样哀伤?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听。国王听了非常同情他,但并没有像童话故事里那样,把女儿嫁给他当做大礼包,而是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请国人都来听号手讲他的故事。
从此,日复一日,只要那号声一响,人们便围拢他,默默地来听。就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号手的号声不再低沉、凄凉。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号声开始变得欢快、嘹亮,变得生气勃勃了。时间和温柔会治愈,而音乐又比一成不变的语言耐听些,人们得到了艺术享受,小号手的情绪在倾诉中得到了修复,实在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