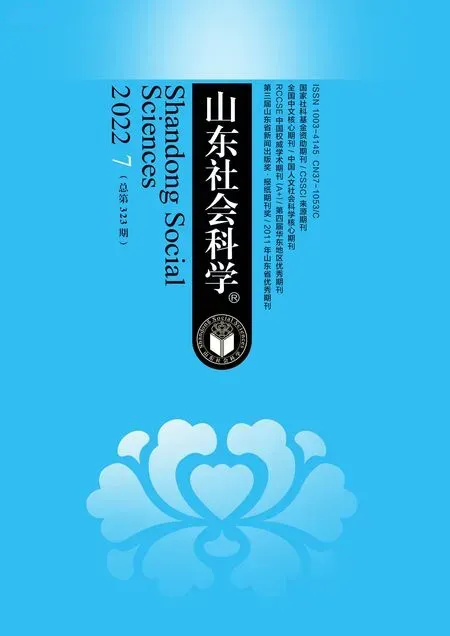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生产保护中的遗产运营与遗产增值
2022-08-09王方晗
王方晗
(山东大学 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237)
农业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最基本要素,当它在农业社会以一种主流生存方式存在时,不会受到关注,也不会被称为“文化遗产”。恰恰是因为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它的价值才被人们所重视。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简称GIAHS)”概念,至今已整整20年。截至2022年5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已涵盖全球22个国家的65个系统,我国已有18个项目被列入GIAHS保护名录,居全球之首。2012年我国正式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2021年底,原农业部和现在的农业农村部共分6批发布了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足见我国政府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我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如何保护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是政府、学界、企业、民众都在关注的问题。虽然已有20年的实践经验,但是如何才能在生产中提高经济效益、助力乡村振兴,在保护的同时实现遗产价值增值仍然是个难题。与单纯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具有重要价值的农业生产系统,包括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投入产出、农民收入,生态系统的水土资源管理、生态服务功能、生物多样性,技术系统的农田管理、物种繁育、产品加工,社会系统的乡村治理、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历史系统的物种资源、技术演变、文化发展等。农业文化遗产是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活态遗产,生态和可持续是其内在属性,生产是手段,在改善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实现遗产价值增值和延续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目标。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农业文化遗产生产保护的视角,把农业文化遗产作为资源,探讨如何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遗产运营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值。
一、农耕社会危机与“农业文化遗产”生成
农业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在当代社会的呈现形式。目前已经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遗址证明我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一万年前。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它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来源,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发现了以种粟为主的农业聚落,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以种稻为主的农业聚落。农业的发展始终受到地理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影响,在距今10000—8000年间中国原始农业就形成了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格局。原始农业的发展使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为食物的生产者,由迁徙者变为定居者,人类进入历史上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孕育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乡风民俗、文化传统,为人类提供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处在农业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然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断被打破。工业化、城镇化不仅带来城乡关系的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农业的功能就是为城市居民提供廉价的粮食和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政府通过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正式建立。户籍制度将居民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农民被限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价格高低也由政府决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将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20世纪80年代农民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生力军。进入90年代,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启动,“城市经济增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劳动力在乡城间的大规模流动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城与乡就此被真正地紧密联系起来”。进入21世纪,中国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农民工大量流入城市,成为支撑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新一轮户口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区分,消除了居民自动迁移的制度限制,大量农业人口流向城市。农业与农村发展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外流,造成农村人口减少、土地流失、空心化和老龄化、农村产业发展缓慢、传统乡村文化消失、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和乡村人才流失。进城的农民接受了现代知识教育,原有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准则、生活习俗均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使传统农业生产因缺少青壮年劳动力而日渐衰萎,也使传统农耕文明面临危机。
与追求快速、高效的工业化相对应,农业领域也在追求高产高效。“十二五”规划中就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及农业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但是20世纪后半期化肥、农药、生物育种及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推广,在实现农业高产、高效的同时,出现了能源、水源、养分的过度消耗和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带来的土地硬化、地力下降、酸碱度失衡、有毒物质超标、环境污染、食品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生产景观、生产制度及生产体系等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也面临被破坏、被抛弃和被遗忘的风险。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生活方式变迁是人类社会前行的必然,然而,当以高投入、高消耗、难持续为特征的现代农业表现出明显的负效应时,当传统村落、传统民居越来越少、乡村风貌日渐衰颓时,人类开始反思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对于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文化安全及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农业遗产保护的重要性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中国第一个GIAHS试点,标志着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发掘保护与传承利用进入新阶段。截至2022年5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共认定了65项GIAHS,其中中国有18项(参见表1),居全球首位。这18项GIAHS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稻作农业系统,包括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二是粟作农业系统,包括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三是农林牧系统,包括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四是经济作物系统,包括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陕西佳县古枣园、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

表1 中国GIAHS情况一览表(5)笔者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全球重要文化遗产网,https://www.fao.org/giahs/giahsaroundtheworld/designated-sites/asia-and-the-pacific/zh/,访问日期:2022年1月5日)和张桂贵的《一文读懂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人民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3956692359596532&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2年5月28日)整理。
中国在通过GIAHS促进农民减贫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2022年5月3项新的GIAHS发布之前,“中国15项GIAHS项目横跨东中西13省(直辖市、自治区)18县(市区)。核心区覆盖农户31.2万户、191.3万人。......围绕GIAHS保护与利用,各地通过加强政策支持、扩大品牌影响、发掘遗产地农业多功能性的潜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式,助力实现了当地农户全面脱贫和农民增收”。中国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2012年,正式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15年,发布并实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法律文件;至2021年底,农业农村部共发布了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均是农耕文明精华的体现,代表了不同的农耕模式且具有典型性、示范性。
浙江青田稻田养鱼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年间的《青田县志》记载:“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于稻田及圩池中养之。”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耕田除草、松土增肥,提供氧气、吞食害虫,实现系统自身循环,维持了生态平衡。”这种特殊的农耕形式与青田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青田县位于浙江省中南部、瓯江流域的中下游,这里土地贫瘠,“九山半水半分田”,先民只能靠山垒石为田。山田面积有限且存不住水,下雨时,雨水顺流直入山沟,当地人称之为“蓑衣田”。为了达到储水的目的,先民长期将水存留在田中,这便为田鱼提供了稳定的水域环境,形成稻鱼共生系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整合有限的水土资源,达一田两用、一水两用、稻鱼双收、互惠共生之利,让我们见证了祖先的智慧。”千余年来,青田人将这一独特的生态农业模式传承下来,2005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首批、中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是另一种农耕模式。敖汉旗位于燕山山脉东段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境内的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碳化粟粒距今已有7700—8000年的历史,同时出土的石杵、石铲、石斧等农耕用具充分证明这里是中国北方发展旱作农业较早的地区。半干旱气候和水资源短缺使敖汉旗先民以种植旱作杂粮为主,包括谷子、糜黍、荞麦、高粱、杂豆等。粟和黍的优点就在于耐旱、早熟、耐盐碱、耐瘠、易收藏,适于在山地或沙地生长。多种农作物套种或换茬种植,形成了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独特的景观。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发源地,它地处东南沿海,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及城区四周海拔在600—1000米的山地十分有利于种植茶树,而河口盆地冲积平原的高肥力、高水分使茉莉成活率高、品质好,独具清香的单瓣茉莉是福州所独有的。因此,“山丘栽茶树,沿河种茉莉”是福州利用自然资源合理种植的形象描述。把茉莉花香与茶香交织在一起,是福州先贤的智慧创造。福州茉莉花茶独特的窨制工艺成熟于明朝。清后期茉莉花茶兴盛,在京津冀一带成为宫廷贵族和外国人的高档消费品。福州茉莉花茶还大量出口国外,“1860年,福州茶叶出口达400万磅,占全国出口总量的35%。1933年,福州茉莉花茶产量增至7500吨”。2014年,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其他如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等均是独具特色的农耕生产方式,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上有政府政策支持,下有企业投资、农民合作自营,扭转了世纪之初的衰危之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些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活态遗产,是农耕文明基因延续的象征。
二、生活中的活态遗产
一般意义上的遗产是指前人留下的具有一定价值的东西,最初是指有形的物质遗产,后来又包括了民间技艺、表演、传说、经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一个重要的遗产项目,反映了古老的人类文明在这里产生发展,可能有一部分这样的文明,或者这样的一个文化,今天已经变了,但是一座古城或一个建筑群,是他们曾经存在的一个历史见证”。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特点是活态流变,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更为宽泛,不仅具有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而且包括了传统农业景观、独特的种质资源、传统农业知识和技术等,具有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多重复合的特点。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负责人帕维兹·库哈夫坎(Parviz Koohafkan)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曾做过准确界定:“GIAHS主要体现的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它不仅是杰出的景观,对于保存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维持可恢复生态系统和传承高价值传统知识和文化活动也具有重要作用。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GIAHS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中国农业问题及农业史专家也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李文华院士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根植于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长期的实践经验,传承了固有的系统、协调、循环、再生的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了许多宝贵的模式和好经验,蕴含着丰富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脉相承。”王思明在总结了中国农史专家万国鼎、王毓瑚、梁家勉和石声汉有关农业遗产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完整的农业文化遗产应该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复合系统,包括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农业生产的对象(土地)、农业生产的方式方法(技术)、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政策与制度)及农业生产依托的生态环境。“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历史时期人类农事活动发明创造、积累传承的,具有历史、科学及人文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闵庆文则认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就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不是指物种、技术、文化、工具等单一要素, 而是由这些要素组成的‘复合性’农业生产系统; 不是指某个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创造的物质或非物质形式的遗存, 而是依然具有生产功能的‘活态性’农业生产系统; 不是完全呈现某个历史时期原真性状态的一般性文物, 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动态性’农业生产系统; 不是为着某种需要进行的现时性建造, 而是历经长期发展而核心价值没有或很少改变的‘历史性’农业生产系统; 不是常遭人诟病、需要改造的一般的传统农业, 而是蕴含人类生态智慧、对当今与未来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典范性’传统农业生产系统。”GIAHS与其他世界遗产类型相比,更加注重人地和谐,是活态的、复合型遗产,目的在于以活态方式重构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生态、文化价值,延续农耕文明。
农业遗址、传统聚落、农业工程、农业景观等既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居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兴化垛田既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乡民们仍然居住在传统村落中,从事香葱、芋头、生姜、洋葱、包菜、莴苣、韭菜等蔬菜的种植和加工;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仍是重要的水稻生产地。而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与农事相关的村规民约、民间信仰、节庆仪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此外,品类繁多的种质资源,如青田青鱼、敖汉小米、绍兴香榧、万年贡米、从江糯米、宣化牛奶葡萄、福州茉莉花茶等,既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又是人们的日常食品。因此,农业文化遗产兼具生产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
农业文化遗产以动态和活态方式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因而在当代也充满活力。活态性是指这类遗产是有人参与、至今仍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且具有较强的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直接的农产品生产、旅游开发等是农民生计的保障,间接的文化服务与生态平衡作用是乡村和谐发展的基础。动态性是指这类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在结构与功能上进行调整,从而不断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玛丽亚·海伦娜·赛梅朵(Maria Helena Semedo)表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通过非凡的生态农业方法证明其可持续农业模式的巨大潜力。通过对农业体系原有特色加以利用,它能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农村发展”。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现代化、城镇化的影响下,许多遗产地的农民特别是年轻农民不愿再从事收益低、付出多的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转而外出打工,使得懂得传统农耕技术与经验的青壮年农民大量流失,农村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传统农耕技艺、农业文化遗产需要有人传承。人是最重要的载体,是活态传承、动态发展的保障。遗产地青壮年的大量流失导致土地抛荒、农村空心化、传统耕作技术无人传承等多种问题,这直接影响了以“活态性”“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稳定性。如何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助力乡村振兴,改善遗产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把年轻农民留在土地上,通过生产使遗产增值,是当前及今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目标。
三、生产中的遗产增值
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目的是通过生产保护,使农业遗产“活”起来,以适应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多方参与、惠益共享”是基本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生产性保护理念非常适合复合型的农业遗产保护。2012年2月,文化部正式制定印发《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定义是:“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意见》重点强调,通过开发非遗产品使之产生经济价值,进而促进文化价值的接续,实现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类似,农业文化遗产是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活态遗产,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独具特色的产品、美丽的景观、众多的遗存、丰富的物种、良好的生态、优秀的农耕技艺和文化均是遗产地特有的资源,而遗产地政府、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及社区农民是遗产的所有者和共享者。早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积极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践证明,只有通过遗产运营,推进产业开发与产业融合,将农业文化遗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建立起一套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值和传承发展。
遗产地的农产品均是具有地域性、富含文化价值的特殊商品,如何提升其价值,使其成为民众认可的有机、安全、绿色、生态产品,提质增效基础上的品牌营造是首要路径。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在乡村振兴中注意发挥农业遗产的引领作用,对遗产地的产品从历史、文化角度阐明其文化价值,从营养成分、生态环境、绿色安全等角度阐明其食用价值。遗产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存了大量的作物品种,如万年贡米、敖汉小米、绍兴香榧、夏津桑葚、云南普洱等。这些产品均是绿色天然的无公害产品,成为遗产地后必须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产量,但切忌一味追求产量而滥用化肥农药,造成环境污染和产品质量下降。为此,需要对遗产地产品品牌进行认证和推广。日本早就开始了农产品品牌标识和认证制度,目的是通过此方式增加经济效益,留住原住民。如世界农业遗产地佐渡岛实施“与朱鹮共生的家乡”稻米认证制度后,稻米售价比常规稻米高出25%—50%。目前我国只有“绿色食品”标志,主要指安全无污染的优质营养类农产品,如绿色水稻、绿色小麦、绿色水果、绿色蔬菜、绿色畜禽肉及绿色水产品。1990年5月,原农业部正式规定了绿色食品的名称、入选标准及标志。2015年重新修订编制了《绿色食品产品适用标准目录》,以“从土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为核心,包括产地环境质量、生产技术标准、最终产品标准、包装与标签标准、贮藏运输标准等六部分。农业农村部应以此标准为基础,结合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产品的特性,增加其中的文化成分,制定《农业文化遗产产品标准》,设计农业文化遗产产品标志,然后对遗产地的农产品进行认证,符合标准要求的可以在产品包装上打上“农业文化遗产产品”字样,认证为绿色、生态、安全食品。农业文化遗产地产品的文化影响力部分是附着在产品上的,归根结底要靠消费者的消费来感知。因此,遗产地政府还应在舆论宣传、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方面下功夫,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精准扶贫,宣传推广本地产品。遗产地的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农民除利用传统的销售、推广渠道外,还要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网络直播等电商渠道进行宣传推广,如“合作社+加工企业+网店”等模式,以增加品牌的影响力,扩大销售量。内蒙古敖汉旗依托小米品种资源优势,建立生产基地,实施品牌战略,生产的优质小米销往全国700余个县,带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在人们日益注重食品安全和生活质量的当下,这是提升遗产地产品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效手段。
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增值的第二个路径是农副产品及旅游商品深加工的产业链延伸。遗产地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农产品上,在品牌影响力的带动下,必须延伸产业链,将传统农产品加工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充分挖掘生物资源,开发功能性食品和保健品,生产出质优价高的农副产品,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如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当地政府和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古桑树群的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进行产品深加工,山东夏津古桑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椹树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桑果汁、桑葚膏、桑葚红酒、桑葚茶、桑叶粉等200余种产品,实现了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双赢。成为遗产地后,许多地方的旅游业也随之兴起,因此需要开发生产富有创意及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旅游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是旅游目的地向游客提供的富有地方特色并具有艺术性、纪念性、实用性的物质产品,包括旅游食品、手工艺品、轻工业品、土特产等。旅游商品具有满足购物者购物需求和传播旅游地文化与形象的双重价值。遗产地需要结合当地的特色产品,在产品品质、制作工艺、实用性能、商品包装等方面下功夫,生产出受游客喜爱的旅游商品。一件精美的纪念品不仅能给游客留下美好的回忆,更能体现遗产地的形象,提高遗产地的知名度。
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增值的第三个路径是沉浸式和复合式遗产旅游。农业文化遗产地悠久的历史、美丽的景观、传统的耕作方式以及农业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社会属性使其具有了旅游所必备的基本要素。因此,农业文化遗产地政府、企业及农户积极从事旅游开发,有些遗产地也因此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如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首个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当地政府趁势加大了对稻鱼共生文化的挖掘,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龙现村挂牌后,专家研讨、学者调研、媒体采访使龙现村声名鹊起,游客纷至沓来。当地村民看到了旅游所蕴含的巨大商机,纷纷开设“渔家乐”“农家乐”,通过“田鱼宴”获得了可观的收益,早在2017年经营户的年均净收入就能达到10万—20万余元。为吸引游客,龙现村还推出舞鱼灯、插秧、包饺子、磨豆腐等项目。旅居海外的华侨也捐建了龙源坑旅游区,龙现村的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获得快速发展,成为浙江省乡村旅游示范点。
然而,这种旅游方式还处在观光旅游的初级阶段,游客以周边地区为主,主要进行“田鱼宴”的消费,并未涉及稻鱼共生系统遗产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也缺乏更深入的文化体验。其他农业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状况也基本如此。孙业红等早在2013年就对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等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资源情况、旅游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并将其分为技术型(浙江青田)、景观型(云南红河)和遗址型(江西万年)三种不同模式,“建议技术型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可持续采用‘市场带动资源’模式,景观型农业文化遗产地采用‘资源带动市场’模式,遗址型农业文化遗产地采用‘节事活动带动’模式”,目的是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但现实的状况是遗产地的旅游仍以低端开发为主,遗产地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民宿、农家乐等。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所在区域,因为收入不高等因素的影响,20.43%的居民不愿意从事香榧产业,72.04%的人视情况而定,当地居民的经济来源中41.94%来自农家乐、20.43%来自民宿,香榧经营只占10.75%。绍兴古香榧群历史悠久,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后,政府也进行了相关宣传,但是居民对古香榧群的遗产价值认识不足,旅游开发过程中又过多注重民宿、农家乐等,没有注重香榧文化的挖掘,导致香榧文化传承受到影响。可见,只有在现有基础上挖掘遗产的文化价值,才能开展更深层次的遗产旅游。
遗产旅游是以遗产资源为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所在地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文化的一种旅游活动。旅游者主要通过旅游获得一种文化上的体验。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旅游活动方式,是旅游活动的高级阶段。在如今“可支配收入增加”和“闲暇时间增加”两大因素的驱动下,旅游者已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而开始选择地域特色鲜明、富有文化内涵的休闲度假旅游。遗产地需要因地制宜,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旅游体验。“经济效益并不是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世界遗产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智慧。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其遗产价值阐释又与国家、民族自豪感紧密相关。因此,这些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都被赋予更高的要求。”农业文化遗产地独特的旅游资源恰好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和复合式遗产旅游体验,主要方式包括:
第一,遗产展馆展示。农业文化遗产地可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产品展示馆,一方面展示遗产地的发展历史、传统的耕作技术,收藏的重要农具、各个年代的物种标本及与农耕文化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如照片、画作、书籍、族谱、账簿等。另一方面,建立产品展示区、生活体验区、数字展示区、动态演示区,游客可以参与其中,提升兴致,加深对遗产地文化的了解。
第二,遗产农场体验。农业文化遗产是活态遗产,至今仍是遗产地居民生活的一部分。遗产地居民可在遗产地农田开辟专门的遗产农场,让游客进行农耕体验。政府还可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让城市居民通过认养制度在农场里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在稻作区,春天设插秧体验,秋天设收割体验;在经济作物区,设置采摘、特殊加工工艺体验。通过提高游客的参与度,加深游客对遗产文化的理解。
第三,美食特产推广。农业文化遗产地独特的产品对游客来说属于稀有产品,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遗产地可通过策划“遗产里的盛宴”,根据季节推出各具特色的美食体验活动,还可通过新媒体和美食博主推广遗产地美食产品。纪录片《古籍里的盛宴》讲述了一个专心研究宋代美食的现代人如何复制出宋代盛宴,为遗产地利用各自的优势产品和地域文化进行美食推广提供了启示。遗产地还可设立特色产品加工体验区,通过特色产品、旅游商品的加工体验,增加游客对产品及当地风俗文化的认知。
第四,学子研学教育。农业文化遗产地地域特色鲜明的住宿餐饮及较大的地理空间,为研学旅游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各遗产地可根据自身优势开展各类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体验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就探索出“农业生产+研学教育”模式,通过鱼桑文化节、桑基鱼塘活动月等开展研学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遗产地还可与农业类大学开展合作,建立实习基地。
第五,“艺术乡建”落地。古老的村落、错落的梯田、五颜六色的动植物为摄影、绘画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遗产地可建立摄影基地、绘画基地,通过举办“主题摄影”“主题绘画”比赛等活动,提升遗产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可通过“一株水稻的生长”“一棵谷子的成熟”“一朵茉莉花的芳香”等短视频比赛活动,增加遗产地曝光度,吸引游客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走进乡村,探索艺术和乡村建设的结合点,通过艺术促进乡村文化复兴。如艺术家渠岩在广东顺德青田村和山西和顺县许村进行“艺术推动村落复兴”实践;靳勒在甘肃秦安县石节子村创办石节子美术馆;林正禄在福建屏南县龙潭村开展“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油画艺术教学,以创意引来“文创移民”和本地村民回归。遗产地可通过“艺术乡建”吸引更多的艺术家、科学家、音乐人、设计师、游客等来到乡村,使遗产地成为既富有传统文化韵味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
以上几种方式有些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有些可以产生间接的影响,增加遗产地的文化影响力。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遗产地的环境承载量,不能一味为了经济效益而破坏遗产地的生态环境。
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增值的第四个路径是实施农业文化遗产全球推广工程。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与中国文明古国及农耕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因此,首先要从国家层面加强宣传推广力度。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应该制作与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纪录片,向世界推广我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BBC制作的纪录片《发现中国·美食之旅》及中国制作的《农业遗产的启示》《探索·发现》《考古中国》等就产生了较大影响;还可以分主题介绍遗产地的农业景观、传统村落、动植物、农事活动、制作技艺、民间信仰等,这些对外国游客均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其次,要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等建立紧密联系,通过在遗产地召开研讨会等形式,扩大国际知名度。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中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到该村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国外学者也大量来此调研,英国BBC、香港有线电视台、香港《明报》等都做了相关报道,龙现村声名远扬,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最后,要提高遗产地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周知的生态、无公害、有文化内涵的产品。这既包括最初级的农产品,也包括经过加工的农副产品及旅游商品等衍生品。要充分体现这类商品的独特性、稀有性,从而保持质优价高的良好品牌形象。
概而言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复杂的动态适应系统,涉及生活中的物种繁育、农田耕作、产品加工、投入产出、农民收入、乡村治理、生态平衡等方方面面。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互利共生,达至价值增值和生态增效的协同发展。作为遗产主体的农民任何时候都应是遗产经营者与利益享有者,他们的“结构性缺失”将导致农业文化遗产失去传承动力。通过政府部门与农业企业的共同参与,把遗产转化为资源,通过遗产运营实现惠益共享,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文化认同感,把农民留在土地上,才能保持农业文化遗产的持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