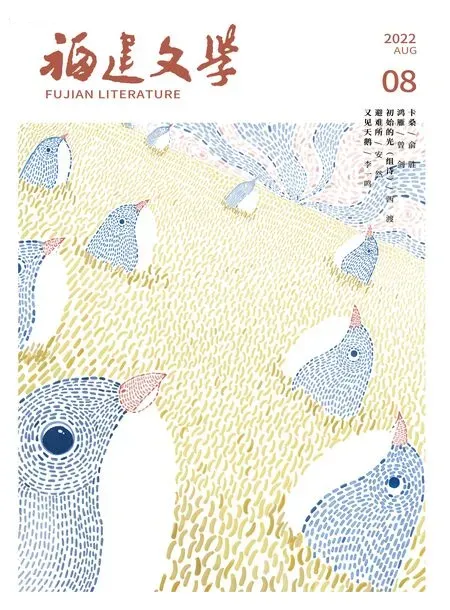兴源府
2022-08-08高寒
高寒
一、兴源府的油车
我是从“兴源府”跨出大门,出嫁为人妇的。对于娘家新旧两处宅子的印象、情感,自然是兴源府深,或者可以说,我青春年少时期的记忆大部分都留在兴源府里。但是,我的同学朋友学生均不太敢光顾兴源府,因为里面有一庞然大物,让他们望而却步、心生畏惧。问之,吞吞吐吐:它像棺材。其实,这是明摆着的答案,我明知故问。
这庞然大物是一辆油车。
从店门口往里面走六七十米,便到一个轩然敞阔的场所,挑空两层高,这就是当年榨油的地方,中间赫然摆设着一个让人悚然的大物件,用石块架起,横放着,那就是用来压榨花生油的油车。油车主体是一大截粗壮、硕大的树干,两米多长,中间镂空,由于三四百年超长的做工时间,油车油腻腻、黑乎乎、脏兮兮的,烟熏火燎般的可怕、丑陋。而经营它的第十代主人,我的祖父,便被永宁人称为“油车欉”。
小时候,我对它极端厌恶、极端憎恨,巴不得一觉醒来,它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们眼前豁然开阔、行动方便,奈何它那么壮硕、笨重,摆在那里岿然不动,占据着那么显眼、显赫的中心地段,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憋闷又烦恼,碍手碍脚是一回事,心里的不舒坦、不畅快更是一回事。
为了表达内心的嫌弃,我们总往它空空的肚子乱扔垃圾,随便把东西挂在它身上,把它搞得乱七八糟、面目全非。更有甚者,有时还爬到它上面为非作歹。这时,父亲便看不下去,勒令我们下来,生气地训斥一顿,他认为这是放肆、大不敬。父亲说,这辆油车年代久远,已经有神,他们尊称为“油车公”,过去经营作坊时,它是榨油的工具、赚钱的功臣,祖辈对它很是爱惜、敬畏,时常供奉。父亲见我们把他的话当耳边风,还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只好神秘地告诉我们,他多次见过“油车公”显灵,是一尊穿黄袍的老爷爷,端坐在油车上。那时我们年少轻狂,还是一副怀疑的态度,过后忘得一干二净。有时要拿东西,再次攀爬上去,当然再讨来一顿呵斥。我们厌恶之情丝毫未减。父亲遇上年节,恭恭敬敬呈上一份供品、点上三炷清香,对着油车虔诚膜拜。他坚持他的信仰,我们有我们的喜恶。如此循环往复。
1993 年年底,娘家盖了新厝,搬离兴源府,迁到镇海石附近,终于有了崭新、舒适的家园。我们欣喜若狂、扬眉吐气,认为搬离兴源府就是一个胜利、一种成功和一次飞跃。
此后,我回兴源府的次数少之又少,避之唯恐不及。
再后来,我偶尔回兴源府,不是以兴源府查某儿的身份,而是以观光者、导游或游客的身份,随作家采风团、带朋友客人游玩,心怀敬畏地踏进曾经生活过的腹地。这种时刻,我总是百感交集。
旅游业悄然兴起后,作为明清古卫城的永宁,是光临石狮者必到之地,而作为永宁曾经的四大商号之一、地处永宁中街的兴源府(荣兴商号的作坊),也是大家必打卡处。
当我只能以外来者的身份远距离地打量熟悉的家园,一种源自血缘的亲切与自豪才油然而生;当我不得不以出嫁女儿的身份参观当年无比嫌弃的油车,一种来自家族的尊严与敬畏才喷薄而出。我知道,我离开了兴源府,但心和魂,还留在那里。
有一次我混在采风团里,听五叔对参观者解说。他说:荣兴商号传到我父亲手上是第十代,传到我们兄弟是第十一代,这油车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躲在一旁的我深深地低下头,担心被他认出来,那时我难堪又悲伤、无奈又惭愧。我知道,这油车是传家宝,是文物,大而言之,是中国民族工业兴起的实物见证,是对外、对台贸易往来的实物载体,它不仅是家族的,也应该是石狮的,然而,它正荒废着,搁浅在岁月深处,被虫子侵袭、啮咬着……
时光倥偬,世事无常。永宁老街改造时,由于人多事杂,兴源府只能由政府收购,换了一笔钱。兴源府离我们更远了,远到我们永远也够不着,永远失去它。但也许,这是它最好的命运与归宿。
后来,六叔出殡那天,送葬的队伍从兴源府前经过,我便快速跑到兴源府门口,通过木板的缝隙往里面探望。一马平川,油车呢?油车呢?也许是距离远,也许是眼花,我看不到它了……
二、二姆的眠床
兴源府里,有一套东西,让我至为想念。那是我们睡了十几年的眠床,其实那不是我们的,是二姆的。
20 世纪60 年代,父母带着我们逃离石狮镇区(那时叫镇,不叫市),回老家,记忆中我已六七岁。
因女孩子多,一间房屋挤不下,便向远在香港的二姆借用她的婚房,二姆慷慨出借.借了她的房间,自然连同房里的其他家具。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结婚家具往往是最值钱的东西,有的贫穷人家,无法一结婚便新打一套家具,便会一代传给一代,结婚时用父母的婚床,乃至用爷爷奶奶的婚床也是有的。有的兄弟多,哥哥结婚了让给弟弟用,也是常事。
那时,我家已过了鼎盛辉煌,但尚未走向末路,祖父祖母便早早为十一个子女准备婚事之物。儿子是一套完整的家具,包括大床、衣橱、书桌、梳妆桌、床头桌、脸盆架,还有两条连椅、四张靠背椅、四把椅头;女儿则是嫁妆,包括金银珠宝、布匹、衣服鞋帽、化妆品、箱笼、一整套的床上用品、一整套的“面前脚”等零零碎碎的东西。
那时我家还有乌槽船走海运,送荣兴商号生产出来的货物去台湾后,便从台湾运木材回来,雇人来府上打造家具。据父亲说,打磨一套家具要两三年,供吃供住,单纯雇佣木工的工钱就要三四百美金。我不懂得那时中国用什么货币,值不值钱,与美金如何换算,但听父亲那口气,应该是天价。他们六个兄弟,就是六套完整的崭新的家具。
我们最喜欢二伯二姆那一套。父亲赞许我们的眼光,他说:二伯这一套用的料最好,是楠木;款式也最新,他当时就执意学习西方的东西,从台湾模仿最新的款式,所以特别新颖、时尚。
其他五人的婚床虽然不是最传统的三十六堵眠床,毕竟还是有繁复的雕刻,雕花、雕人物等各种图案,还有很多镂空的处理,而二伯那套家具,摈弃所有雕琢,很多是一整块、一整板,最多是采用柔美的线条,镶嵌的镜子也多,总之,非常的简洁流畅,非常的新潮前卫。
母亲时常告诫我们,这是亲戚的东西,使用时要小心,不能搞破坏,不然二姆回来,无法交代。我们谨记在心。
我们五姐妹,除了小妹,其他四个都是睡这张床,直到出嫁。
1993 年搬离兴源府时,我们搬走的是父母那一套婚床,这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最有意义的东西。而我们睡了十几年的床,却不敢动它。父母说,那是二姆的,不能动,她借用给我们这么多年,感激还来不及呢,应该完璧归赵。我们都觉得是这道理,虽然心里很是不舍。
后来,高氏祠堂晋主,二姆的儿子,我的堂兄从香港回来参加宗族活动,入住我们新家,但他还是以虔诚的心态回了趟兴源府,特意去看他父母那套结婚家具。他带走一对瓷瓶作为纪念,那是他母亲的嫁妆。那瓷瓶我曾偷偷拿出来当摆设,离开时收回原处。家具太过庞大,带不走。
有一年,我随采风团进入兴源府,抬眼仰视,父母、二伯二姆两间相连的房子还在,我想,那套家具应该也在吧。我没有上去,担心别人认为我觊觎那套家具。
多年以后,我再一次跟着作家团进入兴源府,赫然看到屋顶倒塌、墙壁倾颓,很是触目惊心,忙抬头一看,父母的房间半裸着,而二姆的房间居然不在了,一些木板、梁柱横七竖八倒在地上,地震过的废墟一般。心里大惊:二姆那套家具呢?在一片狼藉的枯木朽柱中,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哪怕一块属于那套家具的木片。我非常遗憾、惋惜,又心存一丝侥幸:也许在二楼塌陷之前,家具已被搬走,放在安全的地方。
回娘家时赶紧问母亲,她摇头,一脸茫然:不知道去哪里呀,没听说被谁搬走。我惊呼:压在那些梁柱底下?不可能,没有丝毫碎片。母亲无语。我表示很遗憾:早知道这样,那次堂兄回来,就让他搬过来寄存我们家。母亲说,我们无权处理。他没说,我们主动提,不妥……我一时无语。
多年后,走过很多路,睡过很多床,但我还是最喜欢、最想念二姆那套家具。我们姐妹都有这情感。有时,想到自己居然睡了十几年楠木床,心里窃喜:毕竟还是奢侈过的。生命,本就不贱。
三、乐园
兴源府的后面是一个大埕,我们称之“后尾埕”,名称不雅,只表明方位,它是我们儿时的乐园。大埕分上下两层,顶埕用水泥铺就,摆放着石板、石条、石桌、石椅,有水井、水槽、厕所等,下埕大多为泥土地,只有一些石条纵横交错,铺成阡陌小道,通向各个角落,其余留以种植花草树木。
记忆中,后尾埕是一个百草园:芦荟、百合花、日日春、茉莉花、玉芙蓉、木槿花、夹竹桃、金银花、番石榴、玫瑰花、月季花、牵牛花、喇叭花、木麻黄、柏树等,反正种得很杂,但不乱,或围成花圃,或绕着围墙栽,或种在房屋前;下埕的西北角,毕业于农校的父亲还开垦出三陇地,围成一个小菜园,种过空心菜、芥菜、白萝卜;夏天,他在下埕的东南角搭起架子,种丝瓜、南瓜、金瓜,架下养鸡养鸭。
有记忆时,祖母已经神志不清了,据说是她受到过惊吓。祖母什么都不记得,却依然爱美,记得用芦荟梳头发。她会穿着小巧的绣花鞋,迈着三寸金莲,悄悄来埕上,挑选一片最为肥美多汁的芦荟,拿回房里梳头,梳得一丝不乱、油光可鉴,然后拿一些纸钱,嚷着要轿子,回娘家去。去干吗?给她父母做忌辰。那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据说,出生于渔家的她,嫁入豪门后,很是庇荫娘家,却不轻易回去,一年也就父母的忌辰回去。这时,她总是打扮得珠光宝气,坐在轿子里,她的儿子呢,小的跟她坐轿子,大的骑着马跟随后面,一路浩浩荡荡的,简直流光溢彩。娘家如何接待,父亲没说,只说他跟着回去过,穿小西装、戴着硕大的金项圈,一路很多人驻足围观。回娘家,成为祖母的重大节日,即使什么都吓跑了,这个记忆片段却吓不跑。一看到祖母掰芦荟,我就知道她局部的记忆复苏了,在另一个时空里。
而我们,到了埕上,那是花样百出。香气馥郁的,剪来插瓷瓶,如百合花、玫瑰花、月季花;摘来晒干,冲泡着喝,防暑降温,如金银花;采来串成项链、打成头箍的,如茉莉花、日日春……在埕上玩耍,常常忘了时间,这也养成我文静、孤僻的性格,没有玩伴的遗憾。
街坊邻居不会向我们要观赏性的鲜花,但有两种花,是经常来讨的,大大方方来讨的。一是玉芙蓉。我家的玉芙蓉很老,长得像一把洋伞,经常开满黄色的小花。烧香拜佛时,放上四朵,好像是不可或缺的大礼;有些老妇人,平常日子也喜欢摘一朵,插在鬓角。另一株经常引来客人的是白色木槿花,可以当药。夏天,有的小孩爱长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懂,大人一般叫“粒子”,我们小孩则叫“桃儿李儿”,这时,用过夜的米粒和木槿花一起捣成泥、敷上,几次就好。我们家的木槿花名气很大,不仅永宁五门城头的人来讨,还引来邻村的。每每这时,大人总很热情,毕竟治病救人,善莫大焉。问明情况,有时还会附加赠送祖父亲自腌制的荔枝,据说那是祖传的秘方,所以每年腌制一大瓮,专门送人。我们小孩是吃不到鲜荔枝的,哪怕一颗。
那时,埕上的番石榴有好几棵,有红籽的,也有白籽的,我们小孩都喜欢吃白籽的,经常爬到树上去摘,熟的放到肚子里,硬的放到米缸里,催熟。后来五叔叫人把番石榴树都砍掉了,说是种果树碍人眼,外面的孩子会爬墙进来摘,容易遭贼,惹麻烦,于是统统砍掉,一棵不剩。其实,在贫瘠的年代,这也是粮食,也可以充饥,但番石榴还是被全部连根拔起,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紧接着,五叔动手的对象转向花草,名贵的、低贱的,一律铲除,只剩下埕中央一棵高大耸立的木麻黄,孤零零地待在那里,突兀而丑陋。后尾埕迅速萧条了。
就这样,春去秋来,岁月更迭,我家的大埕一直了无生趣地呈现在那里,没有花草树木,连声音也少了,听不到鸟叫蝉鸣。再后来,花生间、面线间倒塌,屋顶的杉木被卖掉,聊以维系祖父、祖母的生活,栈库剩下断垣残壁,大埕更显空旷与凄清。
夏天,我们仍然会在大埕上纳凉,但没有暗香浮动,没有虫鸣蛙叫。我们只是吹着清风、望着苍穹,日子就慢慢过去了,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