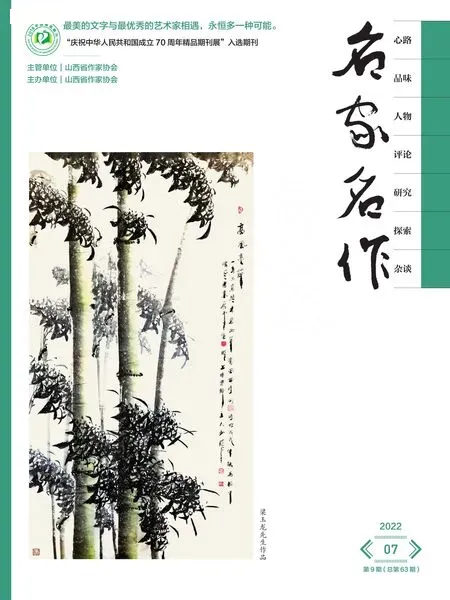非戏剧性电影的叙事策略与特点
——以中国电影为例
2022-08-05杨慧敏
杨慧敏
现大部分电影多以故事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进行叙事,善于营造戏剧冲突,呈现较强戏剧性。影片情节紧凑,环环相扣,情节具有张力且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象,具有电影的力量感。现如今,个人风格与商业影像的融合是电影市场的大势所趋,商业电影大体上呈现出叙事时间小于故事时间的叙事策略,压缩时间使电影叙事节奏更为紧凑。国内商业片发展势头良好,很多导演凭借精彩的叙事方法占据电影市场,涌现出《我不是药神》《疯狂的石头》《误杀》等优秀影片,而也有一部分影片采取淡化情节、非戏剧性的叙事策略,营造出独特的美学性。
电影史上曾涌现出先锋派电影、诗意电影等实验电影,爱浦斯坦与帕索里尼最早研究并提出了“诗意”电影,他们长期、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努力代表了两个可能的方向:一个完全用影像的方式提出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镜头感”概念;另一个探讨了影像中的语言性。早期中国部分电影也呈现出很强的诗意化风格,具有淡情节化的叙事特征,如《小城之春》《城南旧事》《神女》《巴山夜雨》等,不刻意强调情节和戏剧冲突,通过一定的叙事策略淡化情节,将生活中的细节融入情节冲突,使影片更具有真实感且能够引起观众共情,营造出独特的美学氛围和意境,影片风格含蓄,情感细腻绵长,具有东方之美。
除此之外,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导演贾樟柯与侯孝贤,他们的电影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呈现出淡情节化、非戏剧性的叙事化特点,也曾在国际上斩获大奖,备受瞩目。本文通过对此类型影片进行梳理研究,浅析非戏剧性电影的叙事策略。
一、叙事时间的膨胀
(一)以人物内心情感为核,注重细节刻画
淡化情节的影片在叙事中多采用缀合式团块结构:部分影片整体上无连贯统一的线索贯穿情节,而是通过几个相互间并无因果联系的故事片段连缀而成的影片文本结构。影片的各个部分独立存在但又具有统一性,呈现出一种向心性。影片淡化情节,注重情绪的直抒,“形散神不散”的关键在于以人物内心情感为核心,以人物的情感贯穿,巧妙构筑以心理剖析、情感纠葛为核心的非戏剧化叙事。细腻的心理刻画使影片不失一定的戏剧性,具有哲思性。如《城南旧事》,秀英与女儿、小偷朋友、宋妈和父亲的离去,三段故事互无联系,影片也没有完整和延续的故事线索,以英子的眼睛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全片没有割裂感。英子的内心情感活动与观众达到了强烈的共情,伤感离愁的情绪萦绕全片。观众也像英子一样感受到温馨与哀愁交织的思念。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也同样如此,韩三明千里寻妻、沈红千里寻夫以及三峡移民等吸人眼球的故事情节和尖锐的矛盾不是这部影片突出的重点,导演并没有层层设置悬念使故事情节高潮迭起,反而运用平淡的叙事手法,两位主人公寻找过程中,友情、爱情、亲情被细腻地刻画出来,将真实的情感捕捉下来的效果并不亚于对电影情节的塑造。生活中最朴素平淡的情感是大多数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愿望,通过情绪的不断积累形成了影片的内核,更让人感动回味。看似朦胧开放的结局构筑出更加意味深长的意向,激发观众的思考,表现了事件背后导演所寄予的人类情怀和人文观照。
影片注重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情绪细节的展示,常出现一个动作多个角度的重复,看起来单调的动作富有变化,将人物的瞬间感受进行放大和拉长,加深了受众心灵的震撼,从而呈现出叙事时间大于故事时间的效果。如《神女》中,阮玲玉饰演的妓女回到新家中,看到了桌上流氓的帽子,内心是恐惧、崩溃的,瞬间的内心变化被多角度多景别镜头呈现出来,富有层次也更加直击心灵,人物内心的变化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小城之春》中多次出现周玉纹和章志忱的无意肢体接触的镜头和二人的表情镜头,将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和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呈现出来。细节的着重刻画使影片呈现散文化的影像效果,冲淡了密集的情节设置,但却使观众直接感受到人物的情绪变化与心理变化,引起了观众思索和灵魂的触动。
此外,此类电影还常采用定格镜头和升格手法拍摄,拉长了观众的心理时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写意感。
(二)表现蒙太奇的运用
蒙太奇是电影的重要叙事方式,不同的蒙太奇手法呈现不同的效果,蒙太奇可以对电影的叙事时间进行压缩和膨胀。非戏剧性电影中更多地采用表现蒙太奇,表现蒙太奇不同于叙事蒙太奇,更注重表达某种情绪或思想,其目的在于激发现众的思考,启迪观众引发联想。其中隐喻蒙太奇通过对具有相同特征的不同物体进行剪接,呈现出深刻的内涵和寓意,营造出朦胧的诗意。如在《马路天使》中,用花朵被践踏的镜头进行隐喻,展现了小人物的生存图景,《巴山夜雨》中,多次出现的漩涡隐喻具有死亡意向的历史黑洞,蒲公英则隐喻了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我的父亲母亲》中破碎的碗隐喻了母亲对爱情憧憬的破碎,而之后碗又被锔好隐喻了父母爱情的破镜重圆。心理蒙太奇多运用在闪回、梦境、幻想中,如《Hello!树先生》,树在不同情况下会看到父亲和哥哥的样子,心理蒙太奇的运用让我们看到了树的心境,更易引起观众共情。重复蒙太奇、积累蒙太奇都具有表达情绪、渲染气氛的作用,将相似或相同的意向镜头重复组接在一起,不注重镜头与镜头之间时间的联系,侧重传达出的意向,因而削弱了影片时间的完整性,在叙事中拉长了影片的叙事时间,形成了时间的膨胀。如《天云山传奇》冯晴岚病逝后的一组镜头:燃尽的蜡烛,没切完菜的案板,破旧的菜刀,褪色的窗帘,一组镜头加强了悲剧气氛。
二、叙事空间的表意作用
影片的叙事空间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和存在空间,承载故事、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构成了电影的画面造型。戏剧性影片一般呈现出时间与空间的高度集中,叙事空间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或还原真实、揭示细节、展示人物,甚至道具的设计起到引导观众的作用,具有准确性和稳定性。而非戏剧性影片的空间设置更注重抒情性,多有象征和隐喻的作用,不刻意强调空间塑造的精准性,空间构成较为模糊,在影片中注重表意,表达效果更加含蓄。
(一)场景设置——借景抒情
电影场景中常利用空间造型来烘托氛围,表达人物内心情感,以达到借景抒情的效果。叙事空间的主调色彩、场景大小、道具使用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小城之春》,破旧的城墙是周玉纹对爱情绝望的内心外化、破落的庭院是戴礼言对生活无望的内心写照,而屋内空间简单的布置和场景,正是片中人物压抑内心情感,想要爆发的反差式呈现,场景的设置巧妙地化用了经典诗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呈现出战后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感。《巴山夜雨》中“船”是影片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场所,船行驶的两岸景色逼仄又凝重,崇山峻岭之中烟雾迷蒙,人物内心的迷茫犹如雾中行船,正是片中人物和当时社会人们内心的写照,化用了中国古典诗词“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营造出独特的意境和美学意味。《三峡好人》里几次超现实主义元素的运用,如一行人在建筑废墟中行走,留下一个人高空走钢丝的长镜头,还有沈红寻找丈夫时看到天空中的UFO 和像火箭一样拔地而起的建筑。笔者认为此处不必过分深究这些超现实主义元素具体象征了什么内涵,影片意在表达现实本身就蕴含的很多超现实的元素,片中人物对于三峡工程的迷茫和不知所措正如无厘头景物的设计带给观众的迷茫。
(二)空间塑造——营造意境
非戏剧性影片善于营造意境,在表现空间时常采用大景深、大景别、开放式构图,使画面充满韵味。《城南旧事》中,秀贞和英子在一起时一个景深镜头将人物置于四合院的门框之中,洋溢着静谧甜美的氛围,呈现出老北京的样貌,富有诗意和典型的中国格调(如图1)。

图1 《城南旧事》剧照
在《黄土地》中多使用远景、全景,人物在画面中所占比重很小,且多处于画面的边缘位置。大景深镜头将人物夹杂在天与地之间,呈现出人与自然相比之下的渺小,展现出古老土地的沉重庄严,将影片所塑造的空间进行拉伸(如图2、图3)。

图2 《黄土地》剧照

图3 《黄土地》剧照
此外,影片在画面视觉空间呈现上注重留白效果,多采用空镜头,空镜头在影片中具有较强的抒情功能,导演多用来升华感情、渲染意境、烘托气氛。此类影片表现出的画面造型,正如中国传统山水画一样,追求意境,不但能够拓宽观众的想象空间,更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三)注重群像塑造
在非戏剧影片中多注重群像的塑造,群像塑造不同于个人塑造,不是以点带面,而是直接展现社会的一个截面,呈现出的力量远超于单个人物,群像具有表现空间的作用,代表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也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展现社会环境。《巴山夜雨》中,船舱内有工人、教师、艺术家、农民、知识分子……不同的职业涵盖了中国的各个阶层,不同的人物性格多面化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在缀合式团块结构的叙事模式中,影片没有清晰的单一线索串联,故事独立成章,群像的塑造使影片主体与周围环境产生了联系,影片内部形成统一的基调,或体现民俗生态奇观,或加强情感抒发,渲染氛围。《黄土地》中,婚宴、腰鼓、求雨等场面都采用了群像塑造,展现出特殊地域的生存环境或民俗风情,具有渲染氛围的作用;《爱情神话》中,对几个性格各异的上海女人进行细腻塑造,将上海生活刻画得细致入微,讲述上海中年男女的爱情、友情故事,群像的塑造更加贴近真实,且引人入胜;再如《三峡好人》中,通过对奉节县不同人物的描写刻画,展现出三峡大坝建成后当地居民普遍的精神面貌和面临的生存难题。
三、结语
非戏剧性影片在叙事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戏剧性影片,在叙事时间上多采用叙事时间大于故事时间的效果,在叙事空间上意在表意抒情,空间构成较为模糊。此类影片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创设意境,呈现出哲理化和诗意效果,是比较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电影,给予观众审美享受和心理感受。